781 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王飞凌
野兽按:近来在读王飞凌的《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深有启发。他还在自己的博客提供了中文简体版pdf下载。
「中華秩序」,指的是一種由硬性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或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所構成的世界秩序政治意識形態。他的主體是一種以法家權術為核心、儒家語言為包裝的「儒化法家」(Confucian-Legalism)專制帝國政體,王飛凌稱之為「秦漢帝國政體」,因為王認為此種世界秩序乃是由秦漢時代中原的統治者所奠定下來。中華秩序是一種「世界」帝國秩序,是因為統治者繼承了「神聖天命」(Mandate of Heaven)的號召,不只是具有權力及正當性,在規範上他也必須去統治「整個已知世界」,也就是大一統的「天下」世界觀。
這「神聖天命」混合了中原早期的祖先崇拜、自然主義信仰,並採用了儒家的道德語言,成為整個中華宗教的思想核心,但在實踐上,卻是純然的法家思想,也就是對於權力的終極崇拜,以集中的權力建立起「依法治國」(rule by law),徹底控制被統治者,故稱為「外儒內法」或「儒化法家」,酷刑、公開處決、戶口制度、祕密警察、科舉制度等以恐懼為核心的專制手法,普遍見於秦漢政體統治之中。也因此,嘴上說儒家仁義道德、實際上實踐法家權術的虛偽與政治語言扭曲,除了統治者本身的推廣,也早已內化深植人心之中而主動服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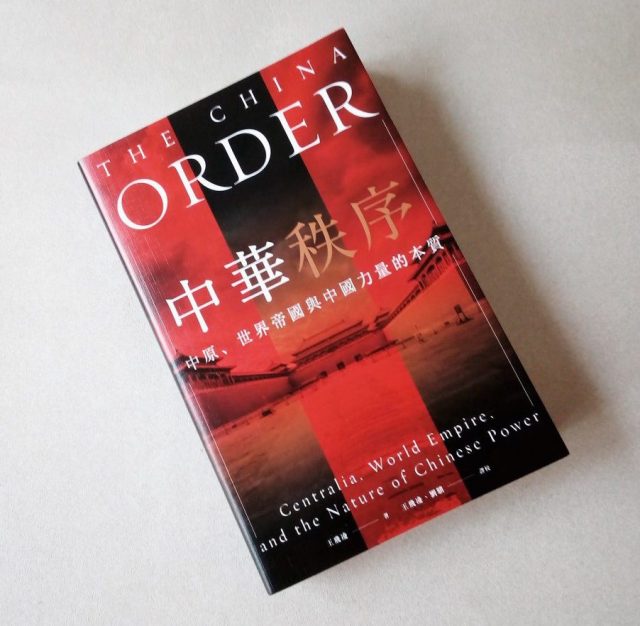
禁书解读 | 余杰:为什么中国应当改名为“秦汉国”?-王飞凌《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
2020.03.04
“超稳定结构”的秦汉秩序造成帝国停滞
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灾难愈演愈烈之际,在台湾年轻一代“天然独”不可逆转之际,在“诸夏意识”呈几何级速度传播之际,从上世纪初即被认为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宏大叙事和身份认同,如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华人等,逐渐受到质疑、批判、解构和颠覆。
香港评论人郑立在《“中国人”不是民族,而是一种宗教》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或中国人三个字,他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怎样将前清帝国的疆域,置于一个新政治实体的统治之下。”所以,统治者以“龙门乱搬”的方式,一时说国籍是中国就是中国人,一时说用汉字就是中国人,一时说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一时说是有“汉族血统”,一时说是自古以来被某些王朝统治过……,虽然里面的东西自相矛盾却尽可能吸纳所有定义,去扩大统治范围。如果拗不下去,就唯有说,你不是中国人,这是“中国”的土地,你滚!可见,如果说中华秩序是一种宗教,就是类似于日本奥姆真理教或伊斯兰国那样的邪教。
“中国”不是一个好国名,这个说法似乎耸人听闻,却是常识。历史学者王飞凌在《中华秩序》一书中指出:“今天‘中国’在中文里的名字,应当改为‘秦国’或‘秦汉国’。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国名比较准确,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对“中国”的真正称呼。这个命名,可以消弭“中国”这个名称中说包含的种族偏见、自大和政治歧义。”用“中华梦”和马克思主义包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上仍是“秦汉式政体”,叫“秦汉国”、“秦汉帝国”、“秦汉专制国”才更恰当。
以秦政而论,谭嗣同在《仁学》中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我在《“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一文中分析说:“秦政作为政治传统,其核心是君权的神圣化;作为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此一互相纠葛、互相支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建构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社会格局,亦主宰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对于中共政权来说,秦政比马列主义重要得多,毛泽东在《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中承认,“百代都行秦政法”,共产党当然不例外。
过去谈秦政的人很多,王飞凌在此将汉政与秦政并列,统称为“秦汉式政体”。秦汉一脉相承,虽然汉初尤其是文景之治时期有过短暂的“黄(黄帝)老(老子)之术”治国,但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汉政就完成了与秦政的完美对接,汉政成为秦政的升级版,秦汉模式形成此后两千年来中华世界一以贯之的“中华秩序”,即学者金观涛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提出的中国文化的“超稳定结构”。
那么,中华秩序的历史表现究竟如何?王飞凌从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科技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各个方面加以评价。他的答案是:对官僚体系和统治精英而言,中华秩序极有吸引力,令他们有如吸食鸦片般上瘾;它也建立了一种似乎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在两千多年里,它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深深内化为某种信条 - 中华秩序不仅可行,而且优越。
然而王飞凌指出,中华秩序的记录十分低劣。人民不仅苦难深重,还周期性地大规模非自然死亡。仅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叛乱,在十年内就消灭了近一亿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泽东时代的人为大饥荒,四年间造成三千万至六千万人的死亡,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秦汉模式或中华秩序低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消除了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比较与竞争,从而失去了对一个垄断性世界帝国的国家权力的内外约束与制衡。它在政治治理和社会经济领域,乃至人们的观念中都形成了一个最糟糕的全面垄断。由此,知识和信息不再增长与共享,人与人之间也缺乏极为重要的信任与协作,长此以往无法避免地出现劣绩和停滞。”
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从马列主义悄然转换为中华秩序,而西方对此知之甚少。所以,《中华秩序》一书填补了中国研究的空白,在中美对峙的今天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重视 - 五角大楼将此书与马汉的《海权论》等其他六本经典名著并列,作为将官培训课程的必读书之一。
中华秩序之下的朝贡体系
在内部政治结构而言,正如王飞凌所说,中华秩序的基础是一个统一的、儒化法家的秦汉专制政体,即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中国版。在中华秩序下,整个中华文明所及的世界天下一统,严格地、通常十分残酷、但有效地推行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两千多年里,无论其种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几乎所有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都是儒化法家的思想。
在对外而言,中国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世界,即一个世界帝国。中国等同于天下,没有外交,只有“理藩”。美国学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在《中国扩张:历史如何形塑中国的强权之路》一书中指出:“在其历史大部分时间里,这块朝代嬗递统治的土地,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国家,更不用说它也不会视其邻邦为国家。不论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关性或适用性而言,它是个帝国,而且大半时间是没有边界的帝国 - 法国人会称之为影响范围(rayonnement)。”
在这个十分有弹性的“大中华和平”的根基下,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相当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们的至尊地位,我们将赐予以政治正统地位并发展贸易伙伴关系 - 以现代国际事务语言来说,就是提供某种范围的公共安全和政治性的国际贸易特权,比如巡守海上公共领域、调停纠纷,准许接受中国近乎普世的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文化和官僚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朝贡制度。
既然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和臣民都一致被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帝国,这种中华秩序之下的朝贡体系就将其他国家都视为“藩属国”,而不是地位平等的“万国”中的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和普通民众,仍然如此定义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及中国如何处理外交问题。虽然理藩院改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改成外务部、外交部,名字换了,其运作的内在逻辑并未变。无论是毛时代的输出革命,还是习时代的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都表明中华秩序高于共产主义、也高于经济利益。秦汉秩序当然与西伐利亚体系不相容:中国以经济收买的方式纠结五十四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支持其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赞扬中国在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有效保证新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这五十四个国家包括白俄罗斯、俄罗斯、巴基斯坦、埃及、北韩、玻利维亚、刚果、委内瑞拉和塞尔维亚等。与中国一样,这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也经常受到外界批评,他们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中华秩序。
帝制时代,朝廷以儒家包装法家;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政权则以马列主义包装中华秩序。一九五六年,中共曾经促使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的自由化运动,既是毛要跟苏联争夺天下武林盟主的位置,也是毛不允许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兄弟”拥有“退群”的权利。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奉命访问莫斯科,当时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张对匈牙利的纳吉政府妥协,和平解决危机。刘则遵毛指示,告诉赫鲁晓夫:中共的意见是必须出兵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在场的翻译师哲记得,邓小平最反对苏联撤军:“不能撤!红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第二天,赫鲁晓夫接受中共主张,决定出兵。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央全会上汇报波匈事件,毛回顾镇反说:“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一九五八年,毛在人大会议上又谈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九六三年,中共在攻击苏联的“九评”中,夸耀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主导角色:“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粹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这就是中共版本的中华朝贡体系,哪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中国不搞霸权、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
不是百年国耻,而是百年维新
秦汉秩序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两千年来,中华世界在地理上隔绝孤立的初始条件,逐渐变成一种持久的心态,甚至是观念和理想,支持着一个统一的帝国秩序。经由帝国官方垄断两千多年的历史叙事发酵,中华秩序深刻地内化到中国人的脑海里,成为高度合法的、理想的,乃至唯一的世界秩序观念。中国历代史家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中华秩序,以之作为衡量、评价王朝的好坏、善恶的唯一标尺:武力强、疆域大的王朝就伟大,武力弱、疆域小甚至不得不接受分裂状态的王朝就卑微。这种评价方式从不考虑民众实际的生活水平和自由程度。
古代史的叙述如此,近代史的叙述也如此。中国本身在其教科书和民族主义的文宣中,把建造现代世界的一百年称为“百年国耻”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为,“反帝”和“报仇雪耻”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在长崎港口为黑船叩门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塑像,即便为中国近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蒲安臣和赫德也被描述成“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者。
而新的观念秩序,必然带来新的历史叙事。王飞凌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并非秦皇汉武或康熙乾隆的浮华盛世,而是“中华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时期,也是中华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实上采取“西伐利亚体系”的时期——包括先秦的中华世界(春秋战国)、宋代的中华世界(宋金辽西夏大理诸国并存)、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华世界(北洋政府时代)。换言之,分裂带来巨大的自由与活力。
重写中国史,尤以重写近代史为重要。王飞凌指出,清末以来,秦汉式政体本身的衰微和王朝轮回的厄运,都因为进口的共和主义,以及旨在实现法治与民主的种种努力而大大改善。与中国官方历史叙事所坚持的百年国耻的定论相反,这段时期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相比都毫不逊色,“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戏剧性事件,复杂曲折的历史情节、各种殷殷期望的启示、伟大的牺牲与成就、深沉的悲伤、沉重的代价、不幸的失败、痛苦的失望及最后的悲剧性结局。所有这些,构成一部宏大而震撼人心的史诗”。比如,租界并非中国的莫大的耻辱,“那些外国人统治的土地,基本上成为免护照、签证的自由港……变成了中华世界里各种新思想、新治理制度、新试验、新闻自由和新式教育的堡垒,重塑了整个中华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就现代化的总体方向而言,它们实际上是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欧洲率先实现现代化并生发出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中华世界却长久深陷在黑格尔的“咒语”之中 –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做皇帝的这种严父的关心以及他的臣民的精神 - 他们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伦理原则,也不能够自行取得独立的公民的自由 - 使全体成为一个帝国”。这种“大分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地中海-欧洲世界一直保持着许多主权单位在政治上互相竞争的分立局面,而中华世界则将大一统作为最高价值和信仰。这就是欧亚大陆东西部之间的“第一次大分野”。十六世纪以来,更大的分野出现了,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不仅各国竞争,而且政教并立,欧洲创造出一个持久而有力的激励机制,促使各国在政治、战争、税收、产权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创新、竞争和试验,从而赋予欧洲主宰世界的地位。只有欧洲人(及其延续的北美人)开始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与扩张、进而实现了社会政治的自由化并且建立英美的全球霸主地位。而关于所谓“中国困惑”的重要答案,就在于经久不衰的中华秩序。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大跃退”
王飞凌的近代史和民国史叙述,清晰的分割了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两个民国”,这也是我在《一九二七:民国之死》和《一九二七:共和崩溃》中反复强调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华人世界仍然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主流的声音,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坚持的妖魔化北洋之外,还有不少所谓的民间反共自由派文人觉青,一头栽进一九二七年之后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将对毛泽东和共產黨的爱戴转移到蒋介石和国民党身上,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王飞凌既否定共產黨,也否定国民党,这两个党都是学习苏俄的列宁式政党,也都是秦汉秩序的继承者,他写道:“北洋时代之后的国共两党主政中国,令中华世界再次沦落为专制秦汉政体。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史诗级的历史大跃退。”
由毛泽东的“大跃进”改写的“大跃退”这个词,是对中共七十年暴政的最佳概括。中共的邪恶,不单单是手段或方法上的错误,更是观念秩序上的歧途。王飞凌指出,中共拒绝引进与模仿英国、美国,甚至是法国,德国或日本 - 这些国家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政治制度,而是从莫斯科拿来共产主义旗号,试图用一种激进的西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 - 即斯大林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制度结构和文化层面全面地改造中国,由此酿成了滔天大祸。
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人对共产主义兴趣缺缺,对帝国复兴则如同打了鸡血般兴奋,热爱秦汉秩序的远比热爱共产主义的多。最近三十年,共产党悄然抛弃马列主义,赤裸裸地打出“秦汉党”的招牌 – “秦汉国”当然不能没有“秦汉党”,中共的核心意识形态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美国之音的一篇题为《台湾大选在即,陆客陆生感触良多》的报道,再度验证了中华秩序在中国人心中是何等根深蒂固、难以化开。尽管大部分陆客与陆生认同台湾民主自由的进步和民风民俗的良善淳朴,但他们仍竭力为中国辩护,并且看不起台湾的“小”和炫耀中国的“大”。比如,一名来自中国北方、正在台湾南部一所大学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说:“我觉得大陆也很民主也很自由,只不过程度不如台湾这么高而已。如果大陆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不自由不民主,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可以出国,怎么大家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他无法解释,既然中国有民主自由,他的父母和国台办为什么告诫他不要讨论政治问题?来自北京的丁先生说:“虽然我对台湾民众印象特好,可那地方也就两个北京那么大,能有什么呀?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江河湖海高山大川,我想上哪儿看就上哪儿看。”他大概不知道,台湾人的护照不用签证就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旅行,台湾人才是“想上哪儿看就上哪儿看”。中国确实很大,能满足统治者和民众的虚荣心,但再大也只是一个“动物庄园”。中华秩序是自愿为奴者的精神鸦片,如王飞凌所说:“中华秩序在中国人心灵里创造出另一种扭曲的双重性,中国人变成一种羡慕暴君心理与奴隶宿命论的复合体,并在文化上内化,在道德上合理化对权力与暴力的实用主义崇拜。”
至今,中国仍然无意回转到人类普世价值的正途上,继续在“大跃退”之路上夺命狂奔。日前,成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入选国家一级图书馆的甘肃省镇原县图书馆发出通告,对馆内所谓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尤其是“含有倾向性”的图书数据进行清查和销毁。通告中的照片显示,图书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在图书馆门口对下架的书籍撕碎后进行焚烧。中国焚书规模暂时无法跟纳粹的焚书运动相比,但“微风起于青萍之末”,全国性的“焚书坑儒”的那一天也不远了。
书名: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
原名: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作者: 王飛凌
作者: Fei-Ling Wang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11/07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60元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
本書的第一部分,描述和分析了中華秩序的來源、性質、前景和意義。凡秦漢政體,必然要以中華秩序作為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來證明和捍衛自己,去統一、規範、統治整個已知世界(也就是「天下」)。它形成於歐亞大陸東部特有的地理生態環境,和形成於歐亞大陸西部的、在法理上強調國際比較和競爭的「西發里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恰恰相反。
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是好的嗎?作者從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文化和社會,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加以評價。他的答案是:對皇帝、官僚體系和黨國體系的統治精英而言,中華秩序極有吸引力,甚至令他們有如吸食鴉片般上癮;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在兩千多年裡,它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國人)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
然而,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記錄卻不甚優秀,甚至十分低劣。中華秩序下的人民不僅苦難深重,還周期性地大規模非自然死亡。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一億人口,占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飢荒,在四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佔到當時總人口的5%-10%。中華秩序下的中華文明長期停滯,形成了「超穩定」結構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華秩序才因「西發里亞體系」的衝擊而崩潰,中華世界不再是天下。
作者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實際上是「中華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時期,也是中華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實上採取了「西發里亞體系」的時期。包括:(1)先秦的中華世界(春秋戰國);(2)宋代的中華世界(宋金遼西夏大理諸國並存);(3)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中華世界(北洋政府時代)。然而,北洋時代之後的國共兩黨主政中國,令中華世界再次淪落為專制秦漢政體。1949年,中共革命的所謂偉大勝利,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個史詩級的歷史大躍退。
作者用單獨一章分析了宋代的「中華秩序之停頓」。他認為,處在澶淵之盟──相當於西發里亞條約的中華版──的宋代(960-1279),不僅創造了中華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代表了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機遇。但它被不幸地遺棄,其深刻教訓也大半被遺忘,直到今天。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作者分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認為北京作為新的「中共秦漢式政體」,建政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文化革命、改革開放,及其伴隨著的各種官方敘事,彰顯出它被中華秩序的內在邏輯和使命所支配的歷史。
和古代的政權不同,中共政權是生活在西發里亞國際體系中的一個成員。身處一個沒有中華秩序的世界,卻深受其必需建立一個中華秩序的艱難命運所驅使,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質上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悲劇性大彎路:耗費了驚人的生命、金錢和時間,除了維護其政權外,卻所獲甚微。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政權本身也有放棄世界革命,不再追求「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種新的大同論,接受美國領導的西發里亞—全球化貿易體系,才得到拯救並壯大。而伴隨著它的富強,陰魂不散的中華秩序意識形態也隨之復甦。因此,北京的新秦漢政體日益強大,代表著對當前世界秩序的一個系統性全面挑戰。中國的經濟模式──「裙帶資本主義」──和它創造的竊國腐敗官僚政治(kleptocracy),令中國對當前世界秩序的挑戰更具有結構性、更有力。
在美國學者王飛凌看來,習近平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過是古老中華的「大同世界」或「天下體系」的現代翻版。只是這個詞更野心勃勃,它不僅僅侷限在東亞大陸,而是要在地球上推行中華秩序。
然而它會成功嗎?它有哪幾種可能的結局?中華世界的歷史已經昭告出答案。
國際書評
「這是一本重要的、紮實而有力的原創性著作,分析研究了從古代到可見未來的中華國家之製度的優劣與長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Edward Friedman。
「這是一本傑作。作者對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作了一個宏大,全面乃至史詩般的評議。其觀點與分析證據充分,令人信服;其引證的中文和英文資料之豐富和多樣令人驚嘆。未來的許多年裡,每一個想要認真了解中國及其世界地位的學生,都會將此書作為必讀書。」——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Daniel C. Lynch。
「這本書是對過去和現在的中華世界秩序和地緣政治戰略的一個充滿創意、令人興奮的宏大探討。它必將成為一本經典著作。」——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Ming Xia。
「作者觀點的陳述和論證是如此的周全徹底,極為高超,任何想要談論中國模式的人都應該閱讀此書。……憑藉其啟迪性和創新性的論點,本書是了解和研究中國模式之意義和影響的理想讀物。」——英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作者簡介
王飛凌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 (CFR) 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 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國的戶口制度》(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5年)。另外發表過中英文文章數十篇,其中一些已經被譯為法、意、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Al Jazeera, AP, BBC, CNN,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聯繫電郵:fw@gatech.edu.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鳴謝
引言
第一章_中原與中華:淵源與基礎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個語義學問題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靈
◎中國人與中華多民族
◎歷史與中華歷史記錄
◎初起:先秦中華世界
◎戰國時代的輝煌與和平
第二章_秦漢政體與中華世界帝國
◎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
◎秦政體:中華極權主義
◎秦天下:一個世界帝國秩序
◎秦漢政體與中華秩序
◎儒家和法家的聚合
◎中華秩序的鞏固和擴展
◎中華秩序的復興與東西方大分野
◎中華秩序的演變和升華
◎從第二次大分立到終極型中華秩序
◎滿清世界帝國
第三章_被遺棄的宋代大轉折
◎宋朝:一個非同尋常的秦漢式帝國
◎宋代的中華世界
◎澶淵體系:歐亞大陸東部的新世界秩序
◎澶淵之盟:中華版西發里亞和約
◎中國人心目中的澶淵體系
◎輝煌的宋代:澶淵體系下的中華世界
◎宋代:中華古典文明的頂峰
第四章_評議中華秩序
◎中華秩序的主要特徵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昂貴的理想:專制統治
◎不相兼容與長期停滯
◎致命的西西弗斯與無盡的煉獄
◎壟斷導致停滯
第五章_百年國恥與進步世紀
◎中華秩序的衰敗與消隱
◎西化成為生存之道
◎滿清帝國不同尋常的崩潰
◎中華民國:機遇、成就與失望
◎重新評估晚清與民國時代
第六章_大躍退與新崛起
◎民國政治:頑固而轉型中的威權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興起
◎毛澤東與民命
◎槍桿子、詭術與諾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秦漢政權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秦漢政體
◎次優化經濟與富國強軍
第七章_天下與西發里亞之間的中華博弈
◎天下使命
◎毛澤東的新中華秩序世界戰爭
◎為敵所救且致富
◎對外開放與韜光養晦
◎中國夢:中華復興與全球治理
結語_可能的未來
引用文獻與著述
引言
人們很容易列舉出一長串關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種種特別之處。然而,困難的是如何解讀和權衡,從而確認和判定正在崛起的中國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和平、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
先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很匪夷所思的幾個悖論和謎團:中國經濟按GDP(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從1990年的世界排名第十躍升至2012年的第二位,預計不久就會取代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最大規模的美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同時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第二大軍費預算(其增速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然而,中國政府在國內外種種無休止地追求更多權力、強化控制的行為,傳達出強烈且不斷加重的不安全感和不滿足情緒。按人均GDP和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中國依然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它卻在世界各地大量撒錢,培育、提升其形象和影響力:僅在2012-2015年就對外承諾了1.41萬億美元,以當今美元計價是60多年前美國馬歇爾計劃的10倍。儘管如此,中國在西方(美國、歐盟、日本)以及從巴西、埃及、印度、以色列、約旦、菲律賓到土耳其、越南,都不受多數民眾歡迎。北京一直誓言永不成為欺凌他國的霸主,承諾「始終維護國際法治、公平與正義」,並呼籲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然而,當第一次面對國際仲裁廷的海事糾紛裁決有利於其弱小鄰國時,其行為與其他任何霸權強國並無二致。
如同預期的,有關中國及其崛起的書籍文章已經汗牛充棟。2014年的六個月裡,全球就出版了一百多種關於中國的英文書籍。其共同主題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有些還特地去「揭秘」中國。但是關於中國的著述與七十年前研究另一個崛起的異己力量——前蘇聯——的學術成果很不一樣。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1947年在《對外關係》(Foreign Affairs)雜誌匿名發表分析蘇聯的文章之後,西方學界迅速匯集起來,產生了一個持續幾十年的對蘇遏制和冷戰大戰略。而迄今為止,關於中國及其崛起的海量文獻大多充滿遲疑,具有濃厚的模糊性和混沌感,缺乏可靠的預測和堅定的政策。多年來「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一直是描述中國及其崛起的關鍵詞。對現在主導世界的領袖們的標準建議,大體上都是一個應付與蒙混戰略,通常混合著一些對中國崛起表示歡迎的接觸、綏靖和讓步(engagement);某些心存恐懼、以防萬一的後備措施 (hedging);以及一種頑固的、試圖同化中國的期待 (incorporation )。
所有這些朦朧不清和猶疑不決,主要原因是對中國的理解既不完整也不充分,對於崛起的中國意味著什麼的認知更是偏頗游移。研究中國,的確很容易迷路,至少是困惑不解,因為傳統的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堆積如山的各種訊息甚至神話(經常是有目的地製造出來的巧妙故事)混亂而自相矛盾,似乎每分鐘都在閃爍變幻。因此,已故學者包瑞嘉 (Richard Baum) 評論說,觀察中國是一個「奇特、令人沮喪、迷人與危險交織在一起的工作」;資深觀察家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則認為,以錯誤的假設進行一廂情願的思考,讓「西方決策者和學術界一再把中國搞錯」。
如今的西方學界,有人在爭論中國的現實與幻像,以及觀察者該如何解釋與構建;有人探討中國人在想什麼、如何想,並得出各種結論和各種假設;有人轉向過去,尋求歷史的相似性,討論中美衝突是否會出現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毫無意義的悲劇宿命。有人開始探索中國特有的中國中心觀念及其影響;有人斷言中國的崛起是一場中國要取代美國、領導世界的百年馬拉松;有人認為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去塑造中國的政策選項和行動偏好,而不是遏制其崛起;有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現了一個強大的「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與「完美的獨裁」,但實際上它不過是個低效而劣質的獨裁國家;還有些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開始走向結束而不是什麼崛起,它的統治正在潰敗。無論如何,很少有人會不同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看法:中國崛起,無論成功或者失敗,對整個世界秩序和人類福祉,都將帶來難以確定但深遠的影響。
中華秩序
本書加入關於中國和中國崛起的探討,試圖全面分析中國力量的本質。通過重新解讀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本書著重描述與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且往往是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的世界政治秩序,奠基於用儒學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即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之上。凡秦漢政體,必然要以中華秩序作為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來證明和捍衛自己,去統一、規範、統治整個已知世界(也就是「天下」)。中華秩序因此意味著一個世界性的秦漢政體。它植根於長期形成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地理生態,這個中華秩序下的世界帝國(world empire),從公元前三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中葉,幾乎統治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民族,並不斷演化以趨於完善。作為一種理念和政治傳統,中華秩序決定了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些關鍵性特質。在這兩千多年裡,整個中華世界(Chinese World)其實也有過多次分裂,形成多國分治時期。其中最主要的斷層期是宋代(10-13世紀)。宋代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豐富而重大,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探討。本書第三章將會對此仔細分析。
在人類歷史上,帝國的擴張和政治上的泛世界主義/全球主義(political universalism)當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各個大陸上都曾出現過可以識別為世界帝國或「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權。中國人的天下概念(即整個已知世界)近似於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的「有人居住的全部」(οἰκουμένη和oecumene),以及後來歐洲人的整個「基督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概念。帝國統治者們,從羅馬人、西班牙人到英國人,都夢想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大帝國,以統治整個已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énē)。但中國人的天下體系即中華秩序,卻是最持久、最獨特的存在,徹底而精緻;在今日中國依然有著無出其右的合法性和實際的影響力。與歷史上許多其他世界帝國(以及想成為世界帝國的政治力量)——如古埃及法老、波斯帝國、穆斯林哈里發、帖木兒汗國、印加帝國,或者世界法西斯主義運動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等等——不同,中華秩序曾連續數百年存在,並統治了其支持者們確信的全部已知世界;在兩千多年內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國人)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作為一個代表特殊社會經濟規範和文化價值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中華秩序是一個仍然活著的思維範疇,猶如歐洲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概念的全球版。
作為一種政體和世界秩序,中華秩序在實踐中可行,經過历史考验,在政治上也是诱人的。但在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方面表現不佳,是個次優化的政治制度。它曾被一些史家有些模糊地稱為「中国人的生活秩序」。中華秩序在中華世界裡形成了中華文明,有别於羅馬帝國之後的地中海—欧洲世界(Mediterranean-European World)文明。後者在事实上遵循、隨後在法理上認可一種國際比較和競爭的世界秩序,即西發里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中華世界在19世紀中期後,也被強力納入了源自歐洲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辟並踐行了秦漢政體。因此,一如以前的帝國君王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命中注定要以自己的面貌去重新規範世界,獲得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權安全。也如同以往的秦漢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它的人民實行低劣欠佳的統治,但卻有能力富國強兵,在国际政治上具有很高的竞争力。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華秩序的意識形態,與西發里亞體系特別是「美國秩序」(American Order)——即二戰和冷戰後的世界秩序,觀念根本對立。一個固執不變的、重新崛起的「新秦漢政體」,必將強勢追求一個新的中華世界秩序,從而給全球人類帶來新的選擇。這對政治治理和世界秩序而言,已經非常明確而且意義重大。
本書之章節安排
本書的第一部分(一至四章),描述和分析了中華秩序的來源、性質、前景和意義。我也嘗試在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文化和社會,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評價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許多世紀以來,中華秩序對各種威權主義統治者們而言,都極有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癮;在中華精英人士中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但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記錄卻不甚優秀,甚至十分低劣。儘管有過多次王朝興亡,中華秩序下的中華文明卻是長期停滯,形成了「超穩定」結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華秩序才因外來力量的衝擊而崩潰,中華世界不再是天下,而被降低為僅僅是現實世界的一小部分。然而,中國的統治者們對此從來沒有滿意,儘管中國和中國人民在這個所謂的「百年國恥」(1840年代-1949)期間其實經歷了偉大的試驗和進步。與中國官方和主流歷史敘事相反,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實際上是中華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時期,即中華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實上採取了西發里亞體系的時期。這些時期包括:先秦的中華世界、宋代、以及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中國。中華秩序的基礎——秦漢政體——在十九世紀末開始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革,但這一變革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強力中止並扭轉。中共革命的所謂偉大勝利,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個史詩級的歷史大躍退。
本書的第二部分,即第五至第七章,試圖揭示秦漢政體所固有的尋求中華秩序的內在邏輯和使命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頑強存活,及其對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影響。剝去掩蓋在中共秦漢政體及其驅使中國去追求中華秩序的必然這個核心問題上的種種有意無意的包裝粉飾,如何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其崛起的性質,以及應該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力量,就變得十分簡單明瞭了。這或許會令許多經常誤報信息、並誤導人們的故弄玄虛的分析家們和過於熱心的辯護士們大失所望。詳細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治理上和社會經濟發展上的總體記錄,將是筆者另一本書的任務。在這裡,本書僅簡略地描述中共為了生存、權力和控制而在國內國外的不斷鬥爭。身處一個沒有中華秩序的世界,深受其必需要建立一個中華秩序的艱難命運所驅使,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質上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悲劇性大彎路:耗費了驚人的生命、金錢和時間,除了維護其政權外卻所獲甚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政權本身也只是通過選擇性地接受西方領導的西發里亞體系,才得到拯救並得以致富壯大。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力量隨著國家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發展,而不成比例地強盛起來;深藏不散的中華秩序意識形態也隨之復甦。因此,中國力量的崛起,代表著對當前世界秩序的一個系統性全面挑戰。這個挑戰包括了國際關係學界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所描述過的兩種基本路徑:一、國際體系中力量的重新大分布;二、世界政治秩序之各國主權平等定序原則(ordering principle)的改變。北京的新秦漢政體日益強大,由此變成一個「非常不滿足的國家」;中國的經濟模式已經變成一個強大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的誘人的竊國腐敗官僚政治(kleptocracy),只會令中國對世界秩序的不滿和挑戰更具有結構性、更有力,也更影響深遠。
本書的各章內容簡介如下,第一章旨在回答三個問題:什麼是中國或者中華?中國歷史是如何編寫的以及應該怎樣解讀中國歷史?什麼塑造了中國的政治思想和傳統?藉由對中華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和一個世界、一個自成一統世界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諸項基本事實的重新解讀,本章探討了中華秩序的豐富而多元的起源。它論述了歷史對中國人的宗教角色以及重新解讀中國歷史的迫切需要。本章也概述了公元前三世紀之前的戰國時代,是一個封建的、西發里亞式的中華世界秩序。
第二章是關於中華政治和中華世界秩序的理念與傳統。中華秩序是中華中心主義的、天下體系的世界帝國秩序,是基於秦漢帝國政體之上的,即表面上是儒家,但本質上是法家(或現實主義)的專制政體。這個政體的性質是威權主義甚至是極權主義,命中注定為了政權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去(或者假裝去)征服和統治整個已知的世界。中華秩序是人們特別努力為之和精心設計的結果,憑藉武力、權術、詭計以及純粹的運氣等偶然因素而得以成功。作為人類政治治理的一項重大成就,中華秩序有著自我強化並不斷複製的機制。它對各民族的統治精英都極具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癮,因此在中國人心裡獲得了一個超穩定的地位,從而能夠主宰中華世界,並使之停滯不前,長達許多世紀。
第三章中,我對中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個特別階段提供一種修正的認識。探討了極有意義、但長期被忽略的宋代(10-13世紀)時中華秩序的中斷。當時整個歐亞大陸東部,存在一個法理上類似於西發里亞國際體系的世界秩序,即澶淵體系。這是個深刻的、一直被曲解乃至拋棄的歷史大轉折,裡面蘊含著對今天的中國和世界領導人都非常有裨益的豐富信息。宋代之澶淵體系的消亡,就像秦國結束戰國時代一樣,是對中華文明的另一個悲劇性摧毀。
第四章考察秦漢政體與中華秩序的特點和歷史記錄。本章總結和評議了中華秩序的主要特徵、異常的持久力、及其強大的復辟能力。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中華秩序對統治精英、對有政治野心的人來說非常有吸引力;但記錄顯示,與西發里亞體系的世界秩序相比,它在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基本是停滯、落後、極為次優化(suboptimal)。中華秩序下的人民不僅苦難深重,還週期性地大規模非自然死亡。本章就如何理解中華秩序的長命與停滯提出了一些看法。
第五章重新解讀並分析了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的中國政治史。在這個時期裡,中華秩序在實踐中分崩離析,但是作為一個深遠的傳統觀念和強大的政治理想,它並未消失。本章考察了中華世界在這個漫長世紀裡經受的巨大衝擊和經歷的宏大變革,認為這是一個充滿實驗和進步的世紀,而不僅僅是中國官方歷史敘事所宣稱的「百年國恥」。這是一個歐亞大陸東部各族人民都取得了各方面偉大進步的時代,但也確實是一個秦漢統治精英們遭受巨大挫敗和屈辱的時代。頑強的秦漢政體通過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了一個看似不可能但最終卻不可阻擋的全面復辟,打碎了許多厚望也令中國人民錯捨了重大機遇。
第六章介紹並解釋了現今中國政治制度的創立及其本質。巧妙地用民命或者民意(Mandate of the People)取代天命或者天意(Mandate of Heaven),毛澤東帶領由外國創立和資助的中國共產黨,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崛起為一個秦國式的極權主義政權。憑藉其精明的權術和強大的武力,中共在1949-1950年贏得了內戰,結束了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中共借助於進口的意識形態術語和重要的外部援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了中華歷史的一個大躍退和大彎路,抵銷了中國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取得的諸多進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一個新的專制集團統治下轉世復活的秦漢政體,一個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黨國。這個新秦漢政體,為了其政權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對內對外都一直殊死奮鬥:對內,與中國社會和文化(上個世紀以來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不懈鬥爭;對外,同時反對幾乎整個世界。這樣的無休止的拼鬥,於是不可避免地帶來悲劇性的政治治理,及失敗的社會經濟政策。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領導人,被迫退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軌道,通過引進和模仿外國,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偉大成果,儘管其總體紀錄迄今仍然是相當次優化的。在民主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比不上七十年前被它取代的中華民國,更不用說與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相比了。
第七章概述1949年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這是一場持久而劇烈的中華大博弈,一方是這個新秦漢政體固國有的天下政治使命,一方是其難以擺脫的西發里亞國際關係體系。被秦漢政體的內在邏輯所驅使,毛澤東本能地竭力推動中華秩序的重建,但是他的世界帝國夢淒慘破滅。當北京被迫暫停它的世界革命事業、隱藏其中華秩序的雄心之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拯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並使其富強起來的正是西發里亞體系。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領袖們有選擇地接受了西方領導的西發里亞體系,並由此獲得了豐厚回報。然而,中華秩序使命深藏未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力的崛起而再度復活,成為主導中國外交的中國夢的一大主要成份。於是決定中國與世界命運的中華大博弈,將會更加強烈地持續下去。
結語總結了中國力量的本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次優化的巨人,但是在國際上仍然頗具競爭力;中國共產黨不懈追求的中華秩序與當今世界秩序,二者之間不匹配和不相容的程度既深且廣。在概述了中國崛起的幾種可能的未來走向之後,本結語也預告了這本書的續篇——探討因應之策。
第一章
中原與中華: 淵源與基礎
若欲了解中國是什麼以及代表著什麼,人們需要面對生活在歐亞大陸東部數千年之久、佔全球人口大約五分之一的各族人民所積累起來的信息海洋。與之相稱的是,關於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知識,還被無數的神話所歪曲、不斷地混淆視聽,甚至會誤導一些最勤奮、最專業的觀察者。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已經闡明了中國的諸多神秘之處,但是還有許多頑固難解的中國特殊性仍然阻礙著中國學的標準化和理論化。學者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已經呼籲許久:中國學急切需要更多的植根歷史的紮實研究。今天,解讀中國歷史依然是正確理解中國的關鍵。然而,那保存完好、豐富而龐大的中國歷史記錄裡充滿了故意的遺漏、無意的錯訛、巧妙的扭曲和公然的偽造。因此,仔細而全面的、帶著修正的態度去解讀中國歷史,是打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黑匣子的前提。本書的第一步是澄清有關中國或中華(China)、中原或中土(Centralia)的一些常被錯過、訛傳或誤解的基本事實。揭示和糾正的這些基本知識,將會有效地展現中華作為世界帝國的多重源頭。為此,本章將探索中華世界的命名來源、生態地理、各族人民及其對歷史的修撰,起點是公元前三世紀之前的封建社會,即先秦時代。那時的歐亞大陸東部,處在一個類似西發里亞國際關係體系的世界秩序之下。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 拉丁文為Sina, 梵文為Cīna, 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 Chin, 公元前770-公元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 Europe)、美利堅(美洲 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 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十到十二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八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 China 或 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 (Cina)而不再稱中國 (Tiongkok)。直到 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 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但是,「中國」一詞在十九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十九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 China (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外,只有在公元四至五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3500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佔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
只是到十九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二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精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精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十九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 China (秦) 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 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 China 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 依然用中國和 China 作為中英文簡稱。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二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需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 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十七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実》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到了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九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十七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精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十九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意。而這些偏見和歧意,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
愛恨千年中國夢─評王飛凌《中華秩序》
◎葉明叡/Emory University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本文同步刊載於《法律白話文》
國際社會應該關注並了解中國夢:中華秩序的復興將把全世界置於一個集權政府之下,一個(但願是仁慈的)獨裁者而非法治制度之下(p.299)。
在台灣的我們,或是世界各國的讀者,為什麼需要瞭解一個獨裁政權所大聲倡言的「中國夢」?或有人說,因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市場,全球資本主義當然都想要謀取利潤,我們台灣人在這之中也是不落人後。1但這本《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2想要告訴讀者的是,人們應該關注瞭解中國的理由原非僅止於此,更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政府,延續秦漢時代以來外儒內法的統治邏輯,意圖輸出其「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至「整個已知世界」,這將對目前主權國家之間以「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為底的國際秩序造成巨大衝擊。
一言蔽之,本書是瞭解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邏輯及其(對中國以外世界的)危險,以及中國/中原地區(Centralia)歷史的最佳讀物。3
本書提要
本書延續八旗文化一貫的解構「大中華/中國神話」出版路線,且由半流亡狀態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著,頗具洞察與說服力。從秦漢政體、宋代、晚清、到中華民國(1912-1949)與中共的「新中國」(1949-),王飛凌在理論上建構了在中原地區長久以來為人所實踐的「中華秩序」的本質,旁徵博引,舉出許多正反事例為證,說明其理論對於史實的解釋力,乃至於在終章提出幾個未來情境預測。
「中華秩序」,指的是一種由硬性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或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所構成的世界秩序政治意識形態。他的主體是一種以法家權術為核心、儒家語言為包裝的「儒化法家」(Confucian-Legalism)專制帝國政體,王飛凌稱之為「秦漢帝國政體」,因為王認為此種世界秩序乃是由秦漢時代中原的統治者所奠定下來。中華秩序是一種「世界」帝國秩序,是因為統治者繼承了「神聖天命」(Mandate of Heaven)的號召,不只是具有權力及正當性,在規範上他也必須去統治「整個已知世界」,也就是大一統的「天下」世界觀。4
這「神聖天命」混合了中原早期的祖先崇拜、自然主義信仰,並採用了儒家的道德語言,成為整個中華宗教的思想核心,但在實踐上,卻是純然的法家思想,也就是對於權力的終極崇拜,以集中的權力建立起「依法治國」(rule by law),5徹底控制被統治者,故稱為「外儒內法」或「儒化法家」,酷刑、公開處決、戶口制度、祕密警察、科舉制度等以恐懼為核心的專制手法,普遍見於秦漢政體統治之中。也因此,嘴上說儒家仁義道德、實際上實踐法家權術的虛偽與政治語言扭曲,除了統治者本身的推廣,也早已內化深植人心之中而主動服膺。6

統治者本身,為了維持自己的專制權力,必須時時刻刻控制、鬥爭政治菁英,政治菁英一方面雖享有奢侈生活與權力,但「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p.167)。統治者自己也為此付出代價,隨時處在驚懼懷疑之中,亦時常死於非命。整個「中華秩序」帝國上下,可以說沒有人有一刻享有如今已開發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尊嚴和安適。
在「中華秩序」當中,由於大一統的天下世界觀,統治者必須「真的」去統治當時整個已知世界,若是實力不足,就必須將自己的臣民與其他地方徹底隔絕起來,不僅是地理上的隔絕、還有認識上的隔絕,假裝外部世界不存在,好讓自己「顯得真的」已經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以完善自己的統治邏輯。
這樣的特性,使得「中華秩序」帝國的統治紀錄非常的「次優化」(suboptimal),無法達到最佳標準和最佳的社會福祉。具體來說,也就是在社會經濟產業發展上相對低落,因為統治者必須壓抑所有獨特創新的思想與科學技術(其中一個相當有效的手法便是科舉制度),同時也得花費大量成本供養擁戴中華秩序的菁英階級。儘管對人民而言在發展和福祉上是次優化,對統治者而言的好處是,一旦「中華秩序」穩固下來,由於其優異的榨取社會(人民)資源的能力7,能夠形成超穩定結構而難以動搖,任何中原的外部入侵者,到最後都被吸納進入「中華秩序」之中而喪失其原有的多樣性。
因此王飛凌認為,「中華秩序」是解釋所謂「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為什麼相對於西歐,中國沒有發生啟蒙運動、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因素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因)。而作者特別在本書第三章,探討他認為「中華秩序」的例外,也就是如今被視為積弱不振的宋代。他發現,宋遼之間維持約三個世紀的「澶淵之盟」,其實已近似於準「西伐利亞」國際秩序(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對外行為),當時候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實際上也是晚清之前中原地區歷史上的最高峰。
總之,中原地區的統治者,不論是誰、如何奪得權力,只要他接納了這樣的思想體系,便可以成為「天命」的繼承人,獲得正當性。因此儘管真正漢人所組成的漢帝國早已消滅千年,中原地區由各個「外族」統治過好幾回,到得最後,不管是鮮卑人的唐帝國、蒙古人的元帝國、滿人的清帝國,甚至「布爾什維克黨」起家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也都可以成為「中華秩序」的擁護者、繼承者。
簡評
本書並無採用目前學術主流的量化實證研究,當然,這也是情有可原,如同王飛凌所言,中國歷史本身就是由掌權者不斷竄改所建構,任何史料,不論屬於公或私部門(事實上,依中華秩序,似乎根本沒有公─私之區分),只要與當權的中華秩序不符,多半早已遭到銷毀。別說是史料,甚至連活生生的自然人,也常遭到「肉體上的消滅」。
對於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說,本書是初探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及其歷史邏輯的優良讀物,並不需要特別的歷史基礎(或說,基於台灣殘缺的義務教育的歷史科訓練)即可輕鬆入手。不同於文飾美化過的中國共產黨版以及中國國民黨版(部分遺留於當前台灣殘缺的義務教育的歷史科訓練)的「中國」歷史,本書提供一個(至少比前兩版本)較為客觀的歷史洞察。
對台灣讀者來說,有幾點可以特別注意。從本書少數段落可推知,王飛凌基本上仍將流亡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視為某種意義上中華秩序的延續,只不過是視為一個成功轉化中華秩序而「脫中華入歐美」的民主化案例;同時,王教授似乎也同意了中華民國在二戰後對台灣的領土主張權利(儘管這可能法理上仍有爭論)(p.212);在論及形塑中華秩序心智的「生態地理」8時採用的地圖,也是當前中國主張的領土範圍(p.36)。總之,作者明確將當前中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視為「兩個中國」(p.40)。這些解讀,從王教授畢竟也是中國人的生長背景而言,是可以理解的。而帶領中國國民黨流亡台灣的蔣介石,確實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中華秩序的實踐者;中華秩序的幽魂,也仍在台灣的四處飄盪。

撇開這些有關台灣比較細緻的爭論,整體而言,讀者在讀完本書後,若能達到對於由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聯手打造的「大中華/中國神話」產生一些最起碼的懷疑,則本書主要功能已經達成。本書論證係以達到學術水準的嚴謹程度,以及附上堪稱最完整中國「天下」論述的參考文獻清單,能滿足讀者更進一步查證之需。可惜王飛凌終非政治學者,雖然博覽群書,本書與政治學現有威權、民主化研究對話之處較少。
小結
如今,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年「大外宣」主調,官方立場也早已丟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中共將會如何繼續實踐其「中華秩序」?從日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言可見一斑。習明確表示:在「對外鬥爭」中,中國要以法律為武器,以法治之名向攪局者說不,並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9這正是王飛凌所描述的「中華秩序」將要與「西伐利亞」國際秩序正面衝突的完全呈現,也是我們做為「整個已知世界」的自由人民,所需要關注瞭解「中華秩序」的原因,因為中華秩序的實踐,依照其內在邏輯之必須,以及歷史上的經驗紀錄,將會造成對於人類文明以及人性尊嚴的巨大毀滅。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p.51)
此為王飛凌在書中引述歐陸史家之語。
在權力者的歷史建構之中,我們仍能讀到一本像《中華秩序》這樣為史實留下些蛛絲馬跡的書,顯示了我們所處時空的自由的可貴,以及捍衛這份自由(即使只是對我們自身而言)所能確保的實際巨大利益。
有關台商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資本及技術引入角色,可參考吳介民老師所著《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9。 ↩
譯自喬治亞理工國際事務學院王飛凌教授在2017年由SUNY Press出版的著作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繁體中譯本(王飛凌、劉驥譯)由八期文化於2019年出版。 ↩
嚴格說來,「中國」是二十世紀初的建構物,China這個用語與中國在過去是毫無關聯的,王飛凌教授認為,應該稱China為「支那」較為精準,若認為「支那」已有負面意涵,可稱為「秦國」或「秦漢國」,或稱中原地區(Centralia),也就是中華的「中央精華」之地,並非指特定地理區域,而是服膺中華秩序政體所在位置(p.31-34)。本文為行文方便,以下不再區分,將中國與中原地區(Centralia)混用。有關China之中譯稱呼中國/支那,另可參考湯海英《文明的遊牧史觀: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八旗文化,2019。 ↩
作者指出,像「中華秩序」這樣將整個「世界」或「天下」納入統治的政治意識形態,並非「中華秩序」獨有,過去基督教世界觀或印加古帝國之世界觀等也是如此。只不過,「中華秩序」是唯一存在至今,仍由一個秦漢政體,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實踐者,世界上其餘部分主要皆已進入「西伐利亞」國際秩序。 ↩
本書中將專制政體下的rule by law翻譯為「依法治國」(此為中國用語),看起來很像是平常我們在說的民主國家「法治原則」(rule of law)。但rule of law與rule by law雖僅一字之差,意義天差地遠,詳細可參考《菜市場政治學》〈「依」法而治還是「以」法而治? –民主與法治的關係〉(吳俊德,2014)。 ↩
有關將中華思想體系視為一種宗教,一個相當簡單易懂的說明請參考《這些都只是常識》〈「中國人」不是民族,而是一種宗教〉(鄭立,2018)。 ↩
如作者所言,統治者可以動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而「基本上毋須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p.165)。 ↩
依作者所言,中華秩序能夠在中原鞏固,獲得長久正當性,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因為實際地理地形氣候因素,頗有地理決定論之意味,但就此部分而言,多僅以事例舉證,較無系統性之分析研究。 ↩
香港特約記者麥燕庭〈習近平:決不走司法獨立的路 要當國際規則引領者〉《世界之聲》,2019年2月17日。 ↩
书名: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
原名:The China Record: An Assess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作者: 王飛凌
作者: Fei-Ling Wang
譯者: 蔡丹婷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3/03/02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60元
★繼《中華秩序》之後
當代中國研究學者 王飛凌 「中國三部曲」最新續作!
首次以大量詳實的紀錄和數據,
全面評估中共黨國的治理方式與社會代價——
何以中共付出世界級的治理成本,治理紀錄卻非常平庸?
「中共最優化」、「中國次優化」是理解中共黨國運作之道的密鑰!
當中國的財富掌控在極少數不受監管、但自信放縱的寡頭手中,
「中共最優化」會輸出到全球,
把「世界次優化」帶給我們嗎?
隨著中國的經濟及軍事力量雙雙往世界第一衝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治體系,將益發影響全人類,遠不只是僅僅塑造中國人民的命運及未來。在如此發展之下,評議這個另類的政治體系和獨特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型,以及理解中國社會內部的實際發展情況,對全世界來說都是迫切之舉。
▋「中共最優化」是什麼?「中國次優化」又是什麼?
延續2017年出版的《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對古代中國秦漢政體和天下秩序的精闢解讀,王飛凌帶領讀者聚焦於現代中國,即「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文化及環境保育等四個領域,展開全面性的評估。
「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實面貌究竟如何?作者指出,中共為了維繫專制,以達成統治的「最優化」,實際上導致了內部治理各方面的「次優化」。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它的治理表現基本上是平庸的,大多為次優化、不可取的,更經常是災難性、甚至是悲劇性的。
換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僅是中共的權力載具,促使中共肆無忌憚地以犧牲民主法治、人民的幸福乃至社會信任為代價,企圖重整世界秩序,更進一步地維持政權的終極安全。如今的中國已成為「國家強、中央富、人民窮」的壓榨掠奪型政體。
▋中共付出世界級的治理成本,為何呈現出非常平庸的治理紀錄?
中共的治理本質上依靠強權和詭計,在牢牢控制政治生活、司法制度、教育、資源分配和社會流動的情況下,黨國付出了近乎世界級的治理成本,呈現出的治理紀錄卻優劣參半。
以經濟發展為例,在外國資金及技術的推動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歷經了數十年驚人的經濟成長,成為按GDP衡量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最大出口國。然而,與一般認知相違的是,1990至2010年代這一由「後發者優勢」推動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對1950至70年代低增長、不增長,甚至負增長的「延遲修正」。此外,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所造成的巨大赤字和經濟泡沫,也拖累了中國經濟,遑論驚人的低效和缺乏創新。
另一方面更關鍵的是,中共沿襲歷史上秦漢政體出於政治目的而審查、控制信息的悠久傳統,始終強制性壟斷中國的所有信息,宣稱「黨要管理(所有網絡)數據」。中共的數字遊戲,本質是以「對內洗腦、對外宣傳」的方式來穩固統治。因此,中國經濟的官方數字,大多由西方諮詢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包裝並背書;許多極具影響力的中國觀察家都因而做出錯誤、甚至是可笑,但卻極具影響力的判斷和預測。確實,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國的大數字,極易導出一些學者宣布「中國第一」的驚人結論。
從資本回報、能源消耗及其他標準來看,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依舊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其統治菁英階層已經獲得了世界級的財富及生活方式。中國的崛起,更確切地說,是中共黨國力量的崛起。
▋從「佛系」、「躺平」到「潤學」,中國為何會流行這些詞彙?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官僚體系,學者估計,領國家工資的「廣義」幹部,總人數到2021年已超過8,000萬人。如此龐大的人數,光是維持其運作就讓中國納稅人付出了天文數字。2019年,一份網路流傳的數據分析得出結論:中國「養」公務員的成本在五年內躍升了77.5%,大幅超過GDP的增長。此外,為維持黨國龐大的財政需求,中國人民背負了沉重的稅收負擔:在中國,收入超過12,307美元即面臨45%的最高稅率;相較美國,年收入超過539,900 美元所面臨的最高稅率僅37%。
從整體生活水平、社會安定、人口流動及選擇自由等一系列社會經濟發展的比較指數來衡量,中國更有著創下世界紀錄的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官方公布的中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僅為美國的7%,不到南韓的10%,為全世界的46%,為印度的108%。即使考慮到購買力平價,中國大多數人的生活仍處於典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國際標準,中國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這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流行佛系和躺平,以及「潤學」彌漫在中國菁英之間的主要原因。這些流行詞彙折射出中國人越來越多的無力感、憤怒、恐懼和絕望,也意味著統治菁英和普通人民之間陷入惡性的治理循環。
此外,承受中共治理災難的,不僅僅是中國人,還有中國環境和中國文化。北京官方吹噓高鐵、移動支付、網購、共享單車汽車為中國的所謂「新四大發明」,由假歷史和偽科學所支撐,這種自我欺騙和自我膨脹,已經大幅取代了謙虛、守禮和理性的美德,深深地腐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和娛樂。黨國帶來的巨大影響,將在社會、文化、心理和生態等方面涉及好幾代人。
▋《中國紀錄》一書給出殘酷的答案!人類文明會因此被改變嗎?
整體而言,本書認為1949年至今的中共黨國,在基因上乃是一種前現代的威權、甚至極權政體(中華帝制秦漢式政體),加上舶來的意識形態,略微修改後的復辟。
然而,這種治理模式作為一種最優化的專制統治形式,卻機敏而具有韌性;它使中共在十分不利的情勢下,仍保有驚人的壽命和權力。中共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和詭計來統治,不惜一切代價只為永遠掌權。
中華世界的歷史顯示,一個蓄意為惡、次優化而不可取,但卻堅定而狡詐的力量,往往會出人意料地成功征服、統治整個已知世界,悲劇性地改變人類文明的方向。中國的崛起,或者更確切地說,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國力量的崛起,正日漸形成一個全球性的大挑戰,人類文明也因此面臨關鍵而影響長遠的選擇。
國際讚譽
「王飛凌成功地將熱情的理念與豐厚、深入且有條理的學術研究相結合。書中對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策及其成效的許多最尖銳的批評,都來自中國的出版物。也因此,在所有深入理解中國的書籍中,《中國紀錄》帶給我們最為有力的思想衝擊,超越所有在毛澤東去世後出版的同類作品。」──羅傑‧蓋斯德(Roger Garside),英國前駐華外交官、《中國政變: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作者
作者簡介
王飛凌(Fei-Ling Wang)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
已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和《中國的戶口制度》。另發表中英文文章數十篇,部分已被譯為法、義、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半島電視台、美聯社、BBC、CNN、《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
譯者簡介
蔡丹婷
師大翻譯研究所畢業。最喜歡翻譯,最愛家人。極喜歡窩在家中推敲字句的日子,更喜歡透過不同語言接觸新知,夢想是能使用八國語言。譯有《形狀》。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銘謝
引言
第一章 政治治理:人民民主專政與黨國體制
大悲劇與大彎路/黨國的基因:毛澤東思想/北京的舊劇重演:習近平思想/中共最優化與中國次優化/人民生命與權力/額外控制的法外手段/徹底而細緻的思想工作/黨政與警察國家/統治階級與菁英貴族/擾民、不安全、少安寧
第二章 經濟紀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模式/毛澤東的大饑荒與大停滯/三十年來的巨大增長/扭曲與失調金融系統/榨取與揮霍/經濟紀錄的量化評估/量化評估之一:GDP、要素與外匯儲備/量化評估之二:財政與貨幣政策/量化評估之三:能源效率和企業盈利率/國際比較札記:那印度呢?
第三章 社會生活:苦難、幸福與抵抗
貨真價實的發展中國家/吃苦與豪奢/不平等與貧窮/災害與救援/飄渺的幸福/用腳投票/嚴密監管、憂慮與憤懣
第四章 精神與生態:文化、道德與自然環境
官本位與社會/中國賢人祠與領袖本色/道德真空與全民健忘/腐敗事例一瞥/學術圈與教育界/「我們人人造假」/出版業、古董文物與飲食潮流/自然環境與生態狀況/超級山寨大國
結語 再看紀錄
注釋
參考書目
引言
在2017年出版的《中華秩序》一書中,我試圖重新解讀並分析中國的歷史及世界觀,透過考察秦漢式政體與中華天下之世界秩序,釐清中國的政治傳統以及價值觀念結構。本書《中國紀錄》是《中華秩序》的續篇,將聚焦於現代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評議其做為一個另類的政治體系模式和一個獨特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型之紀錄。
隨著中國的經濟及軍事力量雙雙往世界第一衝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治體系,將益發影響全人類,遠不只是僅僅塑造中國人民的命運及未來。在2021年和2022年,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國家公開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力量的崛起,已經形成一個系統性的挑戰,甚至對全球秩序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生存威脅。因此,扎實地了解和評估中國的政治治理模式及社會經濟發展模型,對全世界(包括中國人民)來說,都是迫切之舉。在現今的全球主義(globalism)及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時代之中,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體系的強項或優點、弱點或缺陷,在理論上及實務上都十分關鍵。為此目的,我希望本書呈上的簡明分析,能夠使讀者去全面、精準而有用地了解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就與不足、強項及弱點。在探討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CCP-PRC)的活力(viability)及可取性(desirability)等議題時,我希冀能對這個黨國,提出一個客觀事實性的論述,以及一個規範批判性的分析。希望本書的發現會有助於世界對中國力量崛起之現實的政策考量,並由此制定合適的回應戰略。
本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評估,是基於分析其在四個領域的組織特徵及運作表現: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文化及環境保育。考察此四項的目的,在於確認崛起的中國力量做為目前世界領袖候選人的可行性及吸引力,和其取代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能力,以及北京追求以「中華秩序」代替西方主導的「西發里亞式」(Westphalian)世界秩序之可行性及可取性。在過去七十多年裡,中國經歷了許多史詩級的動盪:改革、進步、成功、失敗及倒退,有無數的英雄、惡人、倖存者及犧牲者。我很清楚這非凡的連貫性及偉大的變動,使得拙著之寫作,充滿了許多引人入勝卻又令人謙謹的挑戰。
我首先將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治理,即中共統治下的人民民主專政(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尤其是其在保護中國人民的生命及權利、提供社會秩序與安定,以及公共服務及政府效率等方面的紀錄。接著,我將試圖報告並評議中國經濟,尤其是其在近數十年間的成就及問題,最後再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生活與精神及實體生態。本書將著重於中共治理在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司法正義、財政及貨幣政策、國家主導型經濟成長模式(state-led growth model)、創新、學術及教育、不平等與貧窮、災難救助及流行病預防、文化與道德、社會安定、古蹟及環境保護等領域的運作及影響。透過規範性評估(normative evaluation)與量性及質性資料之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相結合,本書試圖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與特徵,尤其是探討中共做為一個代表不同價值觀及規範的新興強權、乃至一個潛在的世界新領袖,具有或者缺乏哪些效能、效率、力量、永續性及可取性。做為推進中國研究的一個小小努力,本書選擇聚焦於總體紀錄,以提供評價及判斷,而非試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做一個面面俱到的細微敘述。
更明確地說,本書意在展現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正面貌及其究竟代表著什麼。本書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帶給中國的政治次優化(the China suboptimality)、社會經濟表現不佳、文化及環境飽受損害,都是只為達成驚人的中共統治最優化(the CCP optimality),以維繫其政權的壽命與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的前三十年(1949至79年),是一個千真萬確、規模龐大的悲劇。中國共產黨受其內在邏輯驅使,再加上獨裁領導人毛澤東的個人野心及無能,硬是使得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一世紀(1840年代至1949年)裡取得的種種進步及改變生生倒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中共的權力載具,同時中共也企圖重定整個世界的中心並重整世界秩序,以達成其政權的終極安全。為此,中共使得中國走上漫長而慘痛的大彎路,在許多方面都辜負了中國人民,最後面臨一個理所當然要崩潰的局面。
毛之後的中國共產黨的應對之道,則是退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民族國家主義(statist and nationalist)軌道及政策上,以求其政權的生存。因此,在過去四十年之間,猶如巨大的歷史諷刺,中共被其始終想取代的西方主導之西發里亞式國際體系所挽救並且致富,中國人民重新獲得相當程度(但依舊有限)的社會經濟自由及自主權。中國經濟因此經歷了驚人的爆炸式成長,使得數億人口脫離赤貧。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廣泛的科學技術(多來自國外),打造出相當完整且具競爭力的現代工業體系。中國社會和人民日常生活也大幅改善及轉變,且大致是往現代化及西方化的總體方向而去。本書稍後將會詳細報告,大批擁有可觀可支配收入及資產的「中產階級」湧現,且能經常在國內外旅行。成文法的發展和個人權利規範的增生,尤其是在商業領域,提升了可預測性及信任度,促進了市場導向型商業。宗教活動和社會文化普遍也都重新煥發活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積極參與了國際合作:從在全球生產鏈舉足輕重的位置和提供大量外援,到派出大批軍隊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在毛式政治體系的治理之下;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確保中共一黨獨裁的安全與權力,能在中國延續下去。這個黨國的DNA,即所謂「紅色基因」,大多依舊完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一個統計數字上的巨人,從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中汲取海量資源;而中國的經濟成就完全有賴於比較自由了的勤奮的中國人民,更仰賴大量外資及技術的挹注。總體而言,若兼具質性與量性地評估生命安全、民權及人權、自由與安定、生活水平及醫療、經濟效率與創新、道德與文化發展、社會經濟正義與平等、自然災害與流行病管理、古蹟及環境保育等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理及社會經濟發展,最好也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而常常是次優化(suboptimal)的表現。除了系統性地剝奪權利及自由,中共還在中國人民身上強加了極高的機會成本,對中國的社會結構、道德規範、創造精神及生態,造成深遠且多方面的影響。這些重大後果有些也許還來得及彌補挽救,但有些就算不是藥石罔效,也是積重難返,且早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人們造成深遠的影響。隨著中共持續掌權,並企圖按自身形象來影響重列各國,被中共侵占使用的崛起中的中國力量,代表了一個次優化且不可取、但可行且不容忽視的現存國際社會西方領袖之替代選擇,深深地影響人類文明的未來。
(摘自:《中國紀錄》,〈引言〉)
〈第二章 經濟紀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從生活水平、經濟效率、創新和社會文化進步等方面來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是一場災難,充滿了苦難、倒退、禍害和危機。再加上前一章所述,毛主義經濟政策創下了破紀錄的死亡人數,以及對人民公民權利及人權的大規模剝奪,釀成了「中國悲劇」,並在「一場脫軌的革命」過程中造成了廣泛而巨大的破壞。
自1980年代以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情況要好得多,經濟增長令人矚目,技術進步迅速,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隨著毛主義災難逐漸平息,中共為求政權生存,不情願但明智地躲藏起來,即所謂「韜光養晦」。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性地接受了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版西發里亞體系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以換取西方的關鍵救援,為其提供合法性、技術、資本、市場、資源和食品。北京被迫放鬆和調整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極權控制,在相當程度上退出了人民群眾的日常社會與經濟生活;透過進口和模仿,讓中國回到1949年以前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state-capitalistic development)及國家自強(self-strengthening)軌道上,資金來源則是依靠出口和外資。成果就是,毛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爆發性的經濟增長,並取得兩項格外耀眼的成就:GDP的快速增長,以及打破世界紀錄的外匯儲備。據估計,多達4.3億中國人,即總人口的30%,現在擁有可觀的可支配收入,其購買力構成了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規模之大可媲美美國或歐盟。筆者親眼見證了中國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驚人崛起,並親身體會到中國人民對其社會經濟成就理所當然感受到的巨大喜悅和深切自豪。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不斷發表文章書籍,記錄和讚揚中國數十年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同時,中共宣傳部門也藉機自我誇耀,各種各樣追逐私利、有如推銷員的人物自然更是大加捧場和宣揚。
本章旨在超越浮華的外表和一般的常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紀錄進行一個力圖平衡的評估。結果發現,在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裡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官方旗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基本上是在由發展型國家主導的原始資本主義(developmental state-directed raw capitalism)或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軌道上擴展。中共仍維持對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專制統治,過度汲取且管理不良,尤其是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低效率、缺乏創新、資源配置紊亂與金融泡沫、不平等與貧困仍舊是廣泛且持續的現象,甚至嚴重惡化。中國的整體社會經濟表現仍然相當平庸,而且大多次優化,往往表現不佳且成本高昂,從長遠來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綜合觀之,中國經濟仍牢牢地位居發展中國家之列。高GDP增長率和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兩大耀眼成就,在詳加檢視後,尤其顯得暗淡許多。
中國模式
坊間已有無數著作出版,大加讚美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顯著、甚至「奇蹟式」的經濟增長,並常常將其歸功於一個勝過其他經濟體系,獨特而卓越的「中國模式」。然而,正如我將在本章中所詳述的,中國過去四十年來的經濟紀錄雖然迷人,但既沒有展現出什麼奇蹟,也沒有提出什麼新的經濟模式,更不代表中共的治理方式有多優越。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日本、南韓、新加坡、臺灣等發展型國家的經驗高度相似,也深受其影響,都帶上了一層傳統「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的意識形態色彩。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人(在香港和臺灣)和海外華人僑胞的「推助」角色尤其關鍵:他們提供了資本、技術、管理知識,並打通至關緊要的出口管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功勞不過是放鬆了對經濟的部分控制,讓中國人民有空間自主做出自己的經濟決定;同時解除了中國的自我孤立狀態,讓國際資本和外國技術進入。該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廣為人知的作用,或者說某種值得注意的功勞,就在於透過威權資本主義的中央計畫機制,能壟斷資源、與資本家交好、控制和安撫勞工,因此得以專注於支持一些大型發展主義項目,例如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以及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大規模發展。然而,正如我後續將在本章所記錄的,這個角色充其量只是好壞參半,它確實帶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但也伴隨極大的成本和問題,並導致經濟增長的效率持續低落和下降。
趙紫陽等務實的中共領導人在1980年代精明地引用了1920年代莫斯科的權宜之計「新經濟政策」和1950至1970年代東歐「同志們」的經濟改革,在意識形態上掩蓋其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位名聲顯赫的中國老記者曾一針見血地說道,毛後時期的改革「只是試圖回頭與1930年代相銜接」。中共自1980年代以來看似沒完沒了的「改革」,「並不是制度創新」,儘管官方說詞和標籤都如是說。正如一位美國漢學家的分析,發展主義的中國政府允許、甚至「指導」民眾視情況即興發揮,嘗試「用你所擁有的」來致富,才是中國在1980至2010年代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不是中共的「集中威權控制」。一位中國經濟理論史學家在2021年也得出類似的結論:過去四十年來,「當代中國宏觀經濟思想和政策的演變」既沒有理論上的創新,也沒有提出高超的遠見;政府只是嘗試(以不同的想法)去「管理同一個問題」,即要政治控制還是要經濟增長,目的則是讓國家「變得富強」,從而「超越」西方。
任何對經濟增長感興趣的集權且活躍的發展型國家(無論其動機為求合法性和權力或其他),種族比較單一同質,又遇到張開雙臂歡迎的西方國家,當然可以享有可觀的經濟增長。在積累資本和繞過劉易斯轉型(Lewis Transition)以吸收大量「過剩」勞動力的經濟「起飛」之關鍵時刻尤其如此。正如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所總結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正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逐漸退出經濟。」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以及更加克制和記取教訓的江澤民及胡錦濤政權,確實讓出了更多空間,讓中國人民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利潤和舒適生活。隨著束縛稍懈,雖然仍處於黨國政治治理而持續的「中國次優化」狀態下,勤勞又具創業精神的中國人民迅速證明他們完全有能力創造財富和進行經濟競爭,也取得了驚人的成果和巨大的進步,足以媲美(如果不是超越)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多世紀前經濟學家提出的「後發者的優勢」,即利用現成技術和長期積累的豐富的比較優勢,可預期地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增長。
因為其政治基因,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是一個控制和汲取型國家,因其有限、策略性和暫時地退出人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從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中獲得了超額的報償。在沒有真正政治轉型的情況下,毛式秦漢政體的基礎仍然持續著,這種政體始終對中國政治菁英具有高度誘惑力,並且有著深深的結構性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尤其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似乎感到更安全、更強大了,因此一如預料地斷然恢復和延續舊制,拒絕社會政治改革,加強汲取和壟斷,鎮壓異見,抗拒遵從世界的主流規範和價值觀模式。正如一名觀察家在2022年所總結的,中共黨國就像一個巨大的中國公司(China Inc),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中共公司(CCP Inc),滲透並控制著中國經濟,徹底利用其「低人權優勢和其他國家的容忍度(……並表現得好像)國有企業是其業務部門或子公司,民營企業是其合資企業,而外國公司則是該黨的加盟商。」
因此,毛後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社會經濟表現,在本質上,儘管與許多人的直覺相悖,仍然是相當平庸且大多為次優化的,往往表現不佳,並迫使中國人民無止盡地忍受艱辛,即口語所說的「吃苦」。中國的政治經濟,尤其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仍然是政治化且由中共主宰。中國有種特殊的腐敗情事,是所謂的「買路錢」(access money),即企業家賄賂官員以獲得空間和幫助,進而開展和發展某事,如今看來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弊已經大於利,因為它越來越無法與其他對增長不那麼友好但更為普遍的腐敗行為競爭,例如掠奪和欺詐。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造成一大赤字海洋和無數的泡沫,深深拖累著中國經濟,並造成了嚴重的低效率和缺乏創新。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在2021年秋天指出:「自2009年以來,尤其是過去八至九年,中國經濟基本上進入了更深的泡沫化。」從資本回報、能源消耗等方面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典型的發展中經濟體。擁有世界第二大 GDP的中國,看似是經濟超級大國,但這主要是數字上的結果。兩大亮眼成就,高GDP增長率和全球最大外匯儲備,細究之下卻是問題重重。用中國經濟學家因謹慎而含糊的話來說,中國經濟增長是得益於在國內和國外的兩個「逐底競爭」;由於國家對土地、資源和金融體系的壟斷,這種競爭也越來越不可持續。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表現之所以不可改變地走向次優化,肯定有很多原因;一個國家的集體命運也是如此。但具影響力的學者,從謬達爾(Gunnar Myrdal)和諾思(Douglass North),到沈恩(Amartya Sen)及其他人,長期以來都認為政治治理和經濟制度(及其內化或文化),特別是一個適合的國家(proper state)及其有能力的政策,能與運作良好的市場系統合作無間,才是決定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一項採用多種方法的計量經濟學研究在2019年總結道,「民主確實會導致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增長」,尤其從長遠來看,「民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近因之間,存在許多相輔相成之處」。一位受過美國培訓的中國學者依此脈絡主張政治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並認為民主「在促進發展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中國的一位「馬克思主義專家」也同意「決定國家富庶或貧困的祕密在於國家的治理之道」。
儘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一種19世紀式的原始資本主義相當盛行;但該黨國仍然是一個「基本上不自由的經濟體」,其「經濟自由指數」的分數始終「低於地區和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21年,香港和澳門幾十年來享有的極高經濟自由,由於北京對兩個「特區」的政治絞殺,也被視為「丟失」了。面對中共激烈但絲毫不見功效的遊說努力,西方、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各大經濟體,都在2020年代認證中國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體,更不用說是具有可靠法治的市場經濟了。近年來,所謂「中國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更被理解為退化至「黨國資本主義」──中共的政治控制邏輯,進一步取代了中國經濟中的市場機制。「追趕式」(catch-up)增長的快速勃發開始消減,以及在習近平身上狂熱再造一個毛二世(Mao the Second),都強烈昭示著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似乎將面臨更艱困的未來,即便不是全面回歸中國悲劇那樣的毛主義災難。
像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後來者」國家,可能享有可觀的「後發優勢」,得以輕鬆且通常以低廉價格獲得世界一流的技術、大量國際資本,以及發達國家已經開發好的廣大市場。然而,它也可能遭受所謂的「後來者詛咒」(latecomer’s curse)或「後發劣勢」,即一度繁榮的發展中國家隨著時間的過去而停滯衰退之現象,甚至因其社會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不足而面臨更糟的情況。這或許類似於惡名昭彰的「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或「富足悖論」(paradox of plenty),毀了許多自然資源豐富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從發達國家進口和模仿現有技術以發展經濟,即使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增長一段時間,後來者國家的統治者往往沒有多少理由、動機、意願或能力,同時複製發達國家的政治規範和制度。但事實上,這些制度和規範正是永續技術創新和社會經濟發展得來不易且歷經考驗的先決條件和必要夥伴。這種「後來者詛咒」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許多發展中國家會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而無法躋身為發達國家。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所總結的,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只是空談,往往流於表面」。因此,後發劣勢所帶來的詛咒性制度赤字的影響,似乎將持續發生並且仍在加劇,風險越來越大,嚴重性也越來越明顯。
(摘自:《中國紀錄》,〈第二章、經濟紀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