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 降薪失业、以性换租、照料惩罚:疫情下的全球女性贫困|侯奇江
野兽按:这一年读了不少侯奇江的文章,觉得蛮有学养。在微信公号上找到介绍她的一篇采访,是她当年在北大和两位同学在荔枝FM上办吐槽电台的报道。
【博雅人物】“不安于北大”的吐槽三人组
北大青年 2014-10-22 18:15

北大青年微信号:pkuyouth
本报记者:
李佳胜 考古文博学院2013级本科生
王子怡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4级本科生
廖垠雪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2级本科生
侯奇江是个大女人,出去实践,遇到不得不应酬的场合,她豪迈地为一帮软妹子挡酒。但一旦来到录音棚,她就瞬间化身“呆逼侯”,成为“在北大不吐槽会死”电台栏目的主播之一。
而同为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编辑出版专业的扯淡刘和周碧池,是她并肩吐槽的战友。三人进入录音室,在编辑师的“开始”手势后,他们竹筒倒豆子般道出开场白:
“北大有三人,绝情而毒舌。不安于北大,不限于吐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槽’第三季。”
在成为呆逼侯之前,这个来自西藏的姑娘还是一个文艺青年,偶尔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扯淡刘和周碧池——也就是互为室友的刘思毅和周雨晨,是她的同班同学。
大一的时候,侯奇江参加文艺委员竞选,给刘思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就像这样跳上讲台,”刘思毅翘起兰花指模仿了一个拉裙摆的动作,“说了一声‘嗨’,然后戴上她的小草帽,非常热情地开始介绍自己。”
在侯奇江眼里,刘思毅是个非典型的90后,不寂寞,自来熟,见谁都乐呵呵的。大一的时候,他夸张到只要在校园里碰见一个说四川话的老乡就要过去搭讪。“昨天我们去清华参加一个座谈会,看见一个四川人,他就开始说方言。”他见到一个眼熟的人就会惊呼:“啊!我在哪儿见过你!”因为“见人就扯”的性格,他在节目中叫自己“扯淡刘”。
侯奇江转而指向右手边的周雨晨,“和他一开始只有‘业务’关系,他太高冷了。”周雨晨曾获剧星初赛最佳男配角的奖项,修艺术双学位,有1000以上的阅片量,最喜欢伯格曼、费里尼和是枝裕和的作品。当时在校学生会办公室工作的他负责审核文件,身在校学生会文化部的侯奇江经常要去盖章,一来二去,两人也渐渐熟悉了起来。
2013年暑假,一次爬庐山的经历让三人建立起“患难与共”的关系。他们都睡着潮湿的被子,白天就在一起吐槽,发现大家“调性相同”,也能把一些关于时政评论、读书心得、生活感悟的话题聊得很深入、很有趣。
在一次吃火锅的时候,他们突发奇想:不如把聊天的话题录下来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听到。侯奇江随即提出,要不做一个自媒体吧。“鉴于我们面容不够姣好,所以没法做视频节目。”侯奇江笑着自黑道。三个人一拍即合,打造一个校园播客栏目的想法开始有了雏形。

在2013年10月的一个早晨,三人从朋友那里,拿到了老生物楼影音工作室的钥匙,打算偷偷溜进去录制。转动钥匙刚迈进去,一个睡眼惺忪的人突然翻身坐起,吓了三人一大跳。睡在工作室的人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2012级硕士洪川。
了解三人来意后,他在一边默默听完,主动提出帮他们剪辑节目,第一期“在北大不吐槽会死”录制完成,并在几天后登上了podcast的播放列表中。用侯奇江的话说,“我们就这样被川哥收养了。”川哥也从此为“北槽”义务服务至今。
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三人录制节目的感受:“他们工作很热情,始终散发着青春活力。”即使到现在,听了五六十期“北槽”后,每到录制节目时,坐在录音室外,看着玻璃内的三人,听他们对校内校外各种新闻、轶事、八卦插科打诨,洪川仍旧常常控制不住地“笑抽”。
一米九左右的高度,大概能容纳五个人的录音室,呆逼侯、扯淡刘和周碧池同时站在里边侃上一个小时,环境还算自在舒适。这一期节目的录制恰好赶上“北大法学院主席”风波,有听众在微博上@“北槽”,希望主播们就此事发表评论。像往常一样,三人没怎么正经打草稿、写提纲,只是稍微交流一下,呆逼侯拿着手机、刷着新闻就直接开聊,与此同时,扯淡刘把手机放在前方的玻璃窗台上开始计时。
40分钟的时间里,三人从“法学院主席”、“土著和非土著纠纷”侃到宜家又侃到《黄金时代》,常常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无所谓逻辑和节操。他们觉得,跑偏本身就很有趣。于是你经常听到这样无厘头的对话:
呆逼侯(脸红):呃——
扯淡刘(看好戏):感觉她要哭了。
周碧池(正经状):不是,是她要打嗝!
呆逼侯(无奈望天):对不起我们刚刚吃了炸鸡。
凭借着二十年来没来得及宣泄的“积淀”和互动的“碰撞”,三个人经常在节目里抢话说,通过漫谈式录播的形式,他们很快积累起自己的听众群。
自诩慢热、状态不太稳定的周雨晨是团队的基石,当侯奇江和刘思毅经历过栏目最初的“蜜月期”,在第一季的后期出现缺乏话题、不够“嗨”的状况,渐渐萌生退意之时,他就会严肃地说:“既然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品牌为什么要放弃它呢?”
“大概就是因为周雨晨进入状态太慢了,所以一旦进入了就不愿意中断吧。”刘思毅说。
而只要有扯淡刘在,节目就永远不会冷场。相比于呆逼侯的学术和周碧池的高逼格,扯淡刘的趣味性和生活化气息更为浓厚,更加让人放松。
侯奇江是慢热的周雨晨和自来熟的刘思毅之间的性格平衡点。洪川觉得侯奇江非常贴心,一般早上8点左右录节目,侯奇江经常给他带早饭。工作方面也非常有责任心,录完节目总是她在催促洪川进行剪辑工作。
然而靠谱的侯奇江也会有掉链子的时候。
2014年除夕夜,三人准备做一期跨年的节目,正值寒假,三人分居北京、四川、拉萨三地,他们只能通过Skype来录制节目。不能够面对面的交流,临场感的缺失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是节目还是照常录制。

偏偏在打开了Skype开始录制时,侯奇江刚刚喝过一点酒,有些“微醺”,在主播时“谈天说地、挥斥方遒”,“她一个人一说就连着说五分钟”,根本停不下来。远在北京的周雨晨很难插得上话,甚至无聊到了在一边刷微博的地步,节目中经常出现“碧池哪儿去了”的声音。只有刘思毅还惦记着原来的计划,在两人之间勉强维持。
纵使混乱,他们还是硬着头皮播出了节目。本以为这个节目只是用来“自嗨”的三人,却收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
有听众说他们非常不专心,跑题跑得很远,重复一些已经说过许多次的话题,而且分别讲了三人的缺点,比如刘思毅话太多,周雨晨却一点话都没有。
“我觉得我是在批评的声音中第一次意识到听众的存在,第一次在乎他们。”侯奇江回忆。那时“北槽”在荔枝FM上的关注量已经破万,有很多听众都在反映寒假期间的节目做得很糟糕,“我们也觉得是时候做出点改变了。”
经历了这样的一段混乱时期,“在北大不吐槽会死”栏目停播了一段时间用来休整。第二学期伊始,第二季开播。彼时侯奇江已经远赴新西兰交流,三个人的录音状态依旧和寒假时一样,没法再有眼神、肢体上的交流,但个人专栏的节目形式让节目的内容丰富了起来。
刘思毅的专栏以“三人扯淡,以我为主”为指导精神,侧重于生活情趣和趣味性;侯奇江前期的“牧场物语”分享她在新西兰留学旅行的所见所闻,后期的“女权主义”专栏标榜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涉及性本身、性生活、性教育、男权女权的话题,宣扬自己的观点;周雨晨的电影评论和推荐深刻独到,就某一个电影、某一个导演或某一场电影节的点评都非常专业,让整个节目的深度和厚度都提升了一个层次。
现在回想大一的自己,侯奇江不喜欢当时的状态,“我现在不需要向别人展示我有多么正能量多么自信,因为我确信我自己有那些东西。”在新西兰交流归来、阅读了大量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她在专栏里畅谈女权主义的观点和见解,在生活中她为人处事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转变。
“我现在很接受别人和我不同,我也不惧怕别人和我持有不同的观点。”她思维清晰,看问题比较透彻,偶尔很犀利,在三个人中,除了性格平衡点外,她还是那个提供“力度”的人。
节目创办之前,周雨晨的微博粉丝量只有三四十,他自嘲那是因为自己太高冷。现在他的粉丝量已有两千多,“让我特别满足。”侯奇江插话道:“对!他是我们打造的第一个网络红人。”
在专栏微博下几乎从不回复粉丝留言的周雨晨,当遇到了网络上对“北槽”莫名的谩骂时,总是会第一个站出来,口诛笔伐而不带一个脏字。他目前主要专注于北槽的运营,“现在我觉得我不用做些别的什么来证明我在大学里能够做什么了。”
“其实北槽就是我们的组织,让我们非常有归属感,我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也是一辈子的朋友。”刘思毅补充道。他的好友,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生,播客“玩旦去吧”的主播武从文认为,刘思毅本质上是十分理想主义的人。“他修了经济双学位,也常在节目中调侃自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他可以只为了自己做事情的成就感,就在想走的路上走很久。”
“北槽”的关注量现已直奔三万四。早些时候Podcast亚太地区的工作人员提出想把他们的节目放到首页上去宣传,但是希望栏目名能稍作更改,隐去“会死”之类的字眼。他们最终选择了拒绝。“想了想还是算了吧,觉得改了名字就不是味儿了。”
现在已经是大四的三个人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刘思毅选择工作,侯奇江和周雨晨也选择在不同的地方继续深造。但是对于栏目的发展,他们却都很乐观。
“其实我们栏目现在内容上会比较同质化,都学一样的专业,爱好也很相近,比如健身啊,美食啊,包括都是单身这种状态。”侯奇江想,如果以后三人能够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咖,再一起做这个节目,节目质量会更上一层台阶。“到时候我们的观点一定能有更多的碰撞。”“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哈哈!”刘思毅唱起歌来。
说到未来是否还会坚持做下去,“呆逼侯”侯奇江一脸正经:“如果有一天有什么理由能够让我放弃的话,我说不定会放弃的。不过,有什么理由能让我放弃呢?”
(首页图由受访者提供,其他图片来自本报记者)
能找到的几篇近文主要来自澎湃思想市场和端传媒。
东方主义的“眯眯眼”VS父权制的面相学
由于承载着屈辱的历史和焦虑的民族投射,丹凤眼成为进退两难的体征符号。但在一场没有外国人参与的广告营销中,我们内部的分化和割裂,反映了一种基于生理差别和观念分歧而产生的新的“种族化”歧视。

文丨侯奇江
12月26日,某零食品牌广告于2019年发布的一系列广告迎来了意料之外的瞩目。广告中女性模特细长、上挑的丹凤眼造型冒犯了许多人的审美原则,被网友认为是在刻意丑化国人形象,涉嫌“崇洋媚外跪舔洋人审美”。几乎与此同时,国漫电影《雄狮少年》中动画人物的造型也因为“丹凤眼”、“颜值不在线”、“故意丑化”而饱受争议。27日,该广告的模特本人“菜嬢嬢”(网名)在网上回应“辱华”一说的广告,贴出日常照片证明自己的眼睛天然如此,“我小眼睛就不配做中国人了?”然而这样的回应并没有平息激烈的声讨。“眼睛小化妆就要往大了画”和“吊眉眯眼黄祸脸”的指责铺天而来。“菜嬢嬢”在其他短视频中把双手放在眼角处的动作被翻出,进一步成为了她明知故犯的“辱华铁证”。
近年来纠察“辱华”现象的声势浩大,这并不是近期关于“东方之眼”的零星一二讨论。近期某知名时尚摄影师为迪奥拍摄的的艺术宣传、金球奖史上第一位亚裔影后奥卡菲娜(Awkwafina)的长相、奢侈品杜嘉班纳广告《起筷吃饭》等,均或多或少因“眼睛”这一元素而惹出辱华和种族歧视的争议。在关于“什么样的眼睛和眼妆在辱华”的标准大讨论中,愈发精确的面相学与“是否迎合西方审美”的动机论紧密结合:“商业营销就要避开红线讨好消费者”、“知丑犯丑”等不同的批评意见密集涌来。这一复杂的现象正揭示了身体的文化象征性:丹凤眼背后不同的社会意义在讨论中不断地对撞和强化,“东方之眼”已经成为一种复杂的历史经验,其本身已经构成了冲突性的意义。
毫无疑问,在讨论和回答什么是中国的眼睛、什么是西方的眼睛;什么是美的眼睛、什么是丑的眼睛等等问题中,我们难以避免地同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人备受歧视和屈辱的情绪负担,叠加上了空间上始终被西方“他者”凝视的自知自觉。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反对眯眯眼运动涉及到外国品牌或外籍华人,是跨文化交流中反歧视的集体意识,那么到这次中国本土零食品牌事件中,西方的注视只是想象中遥远的、虚构的靶子,它已经演变成了一拨国人对内的、对同胞的审查。而参与这场战争的所有人本质上都是“我方”。因此,这个“西方人如何呈现和凝视中国人”的问题已经内化、演变成了“中国人如何呈现和凝视自己”的议题。
丹凤眼究竟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东方之美”,还是“刻意迎合西方审美的民族歧视”的辩题其实不仅仅是关于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的对峙。“什么样的外貌是辱华的?”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那么基于此的“辱华标准”的讨论,也只能是在相对主义的陷阱中,捕风捉影地研究客观上的生理特征与种族歧视的关系。围绕这次广告反种族歧视所展开的这些微妙又矛盾的讨论,显意识里有着强烈的中西关系的焦虑和国族形象自我表达欲,但潜意识中,仍然蕴涵了国人内化了的文明优劣审美秩序和性别与商业话语的歧视性意见。本文就此尝试拆解这一拨汹涌的民族情绪之下的审美权的争夺战,解释围绕“东方之眼”争论的文化拉锯和权力网络中的不同因素,对这一词舆论进行反思和批评,警惕这些叙事中新型民族主义对国人内部造成自我阉割和排斥分离的倾向。
从傅满洲到花木兰,西方视角下丹凤眼的褒贬流转
诚然,我们无法回避历史来谈论当下。网友激烈的语言也让我们瞥见国人在种族问题上的历史伤痕。比如,指责这次本土零食品牌广告中模特妆容的“黄祸”(Yellow Peril)一词,可以呼应到早期海外华人受到恐惧和仇视的“黄种人威胁说”,即黄祸论,以及20世纪20至30年代颇具规模的涉华题材电影中的丑化现象。在当时好莱坞电影中,为了展现西方殖民秩序和文明的优劣等级,国人普遍被描绘成邪恶麻木的小偷、骗子,以衬托白人英雄的伟大。“黄祸”这种被丑化歪曲的负面国人形象常常是以丹凤眼的银幕形象呈现出来。例如在1929年的电影《不怕死》(Welcome Danger)以及此后的傅满洲系列电影中,中国身份的黄祸角色不但由白人直接扮演,在形象塑造上还用化妆手段,刻意渲染夸张了细长的眯眯眼。
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原因,西方银幕对亚洲人眼睛的强调和刻画成为了一种歧视性的表述力量,眯眯眼(chink eyes或slit eye)成为臭名昭著的歧视亚裔的词汇,眼睛也逐步成为了象征着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民族强弱与中西方文明秩序差异的凝结点。于是,亚洲人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眼睑特征,被塑造成一种事关种族强弱与文明秩序的视觉文本,最终成为中国人文化上屈辱的民族经验和历史印记。此轮大规模集体声讨眯眯眼辱华的现象,可谓一场大型的互联网对这样的种族歧视创伤后应激障碍发作。
然而上世纪20年代距离当下的我们已经百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西方跨文化交流让审美和文化始终接触、碰撞、对话。作为镜面的“他者”,西方在对待丹凤眼以及其凸显这一特点妆容的态度上,发生了许多复杂的变化。从傅满洲到花木兰,从美籍华人演员黄柳霜(Anna May Wong)到同为美籍华人的刘亦菲,东方主义里那种展现遥远东方的殖民想象、渲染异域情调和邪恶低劣的丹凤眼,已经出现了象征意义上的松动和转向。尤其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泛亚裔运动中,化种族特征的劣势为优势的“种族自爱”运动发生。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在其小说中倡导的“黄就是美”、“斜眼睛就是美”,成为这种对抗性话语中的典型案例。其塑造的小说人物甚至通过强化黄皮肤等种族身体形象来挑战“凝视他的白人的视觉不快”,以对抗白人凝视的霸权地位。

当然,这种带有种族本质主义色彩的、刻意强调种族生理特点和文化差异的做法并不完美。一方面,在实践上,丹凤眼虽然被定义成是美的,但这种装饰性的美是将少数族裔的文化看作主流文化正餐的佐料。华裔作家赵健秀对汤亭亭的批评就引起了美国华裔文学现象级的讨论,他认为强调这种差异目的是衬托主流文化的包容和进步,形成了对少数族裔施舍的“种族主义之爱”。2018年的奢侈品杜嘉班纳的广告《起筷吃饭》中,那些根据文化偏见来错误地挪用、演绎中国元素,就是西方时尚业把中国文化当做调味剂进行客体化的例证,这反而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歧视。另一方面,这种主张差别、维护差别、视差别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状态,也正是法国当代思想家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所谓的“新种族主义”的典型特点,即“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幌子下维持现有的种族差异,肯定和赞扬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不可吸收性’来获取种族歧视的正当性。”除了审美倾向,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和实践中,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衍生出的新种族主义已经造成了加拿大、法国等西方国家消极的民族隔离政策,对其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些时候,细长的丹凤眼的意涵更出现了一些随机性和灵活性。例如美国的流行文化里甚至出现细长上挑的眼线妆容的流行趋势,非亚裔的年轻人一度流行上传自拍并且加上#眯眯眼#的标签以追赶潮流。当然,美国新闻网站Buzzword的文章也指出这种愚蠢无知的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一种种族歧视。另外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亚裔在西方国家遭受的歧视和暴力又有所抬头。可见,西方其实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和连续的概念存在,它不但存在历史的惯性,又会受到特定的事件和环境影响,在不同的代际和群体之间也呈现出复杂的政治面貌。如今在网络上谈及“东方主义”和“文化挪用”,普遍充满了负面和批判性的声音。同时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疫情等客观环因素的影响,交流和对话中紧绷的警惕神经并不容易轻易放松。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正面华裔形象在西方作品中出现,转变心态学会接受他者羡艳赞美的目光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过程,我们为何不放下一种客体的心态,看到褒扬性的东方主义中西方态度“有限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学者周宁认为,“肯定式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理想化了东方形象,它也代表着西方观念中的开放和包容,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精神,是西方文化创造性的生机所在。”至于丹凤眼形象的出现究竟是恶意还是善意,仍需要具体语境的判断。
是自我改造还是主动迎合?丹凤眼面相学的悖论
至于我们自己如何看待丹凤眼的讨论,就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在围绕着菜嬢嬢到底是不是在迎合西方审美的讨论中,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了“大眼睛高鼻梁”的审美标准本身实际上是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的确,在外形外貌上,来自西方的“美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人自我确证的想象资源,曾经的政治经济实力对比也构成了白人审美的优越和国人形象的丑化,虽然现在政治经济的客观条件已经改变,但美与丑的二元对立却仍然残留了下来,延续了西方文化霸权里黄种人形象在审美里的“他者”地位。西方世界构建的丹凤眼和国人形象,间接或直接地塑造了“中国的眼睛”,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于是出现了“自我东方化“的过程,即曾经的中国人被迫接受了西方殖民审美,把白人的审美规范内化,主动接受了白人的审美秩序,形成一种隐秘而不自知的文化自轻心态。

如果说,丹凤眼是迎合西方的东方审美,高鼻深目是照搬白人审美,那么亚洲审美的自主性就被彻底掏空了吗?如何重新矫正中国人的容貌和相貌的自我认同,找到属于我们的美的坐标系,也变成了讨论的主题之一。客观地从解剖学来看,亚洲人的眼睑的确与白人的眼睑不同。在《中国美容医学》期刊上一篇关于重睑形成术(割双眼皮手术)的论文写到,“高加索人重睑率达到99%,而亚洲人重睑率仅为50%。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亚洲影响,最初的重睑术被认为是对亚洲眼睑西方化的手术。”我们本可以大大方方地认为单眼皮是美的,但这种取向却受到了上述西方丑化丹凤眼历史的影响。网友们也开始诉诸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形象来自证“丹凤眼”的审美正当性,例如东晋《女史箴图》、唐代《唐宫仕女图》中的女性形象。但反对者依然认为百年前的标准已经不适用于今日,并且认为慈眉善目、低眉顺眼的东方式细长眉眼,与横眉冷眼充满攻击性的欧洲“高级脸”大有区别。在关于“什么是好的丹凤眼”的唇枪舌战中,眼睛成为集“肉身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各种意义的历史再现,其中不乏相互矛盾的驳论。
这样来回往复的辩论揭示了歧视和反歧视、东方和反东方的尴尬处境。刻舟求剑的自我否定和文化相对主义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许多相互矛盾的悖论只有一步之遥。不论是他者还是自我,网络上越是参与“东方主义”的讨论,把关于眼睛的细枝末节的差异放在放大镜下,我们就越容易滑向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强调民族差异,不论是出于恶意还是善意,都在利用种族的逻辑进行褒贬;如果抹去种族差异,则会陷入“自我改造、自我抹杀、自我自憎”的驳谬。而这正是关于丹凤眼面相学通过“种族差别”构造的陷阱。而在辱华焦虑的重压之下,人人都想通过生理特点进行身份的自证和他证,形成了荒诞的局面。实际上,眼睛,作为人种学的整体或许有统计意义上的生物特征,但不同种族都有形形色色的眼睛。在文化上偏执地强调生理差别,强调“差别权”,导致文化相对主义价值取向反而向“文化中心主义”翻转,因此也欺骗性地把“反对种族主义”推向了“种族主义”的边缘。
那么我们如何跳出“差异性面相学”的悖论陷阱,找到突破这一话题的突破口,走出“不管怎么美都是西方美”的死胡同?首先,并不是自我改造才能博得他人尊重,反对歧视要反对的不仅仅是某个具体的形象,而更是这个形象产生和传播的机制。在各种对照比较的差异性讨论中,我们更要注意话语主体的权力差异,到底是弱者在通过强调客观差异来追求平等的合理的诉求,还是强者在利用强调差异在制造歧视的借口?更重要的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我们要摆脱想象中与西方“凝视和被动凝视”的单向关系,转向“平等的互看”。至于在审美上挑战西方中心的霸权视听系统,不必纠结于各种眼睛的类型学研究,更要看到超越身体自然属性的语境和意义,反对“身体/意识”、“强者/弱者”、“阳刚/阴柔”等种种二分态,接受、承认抽象的身份和具体的自我不可能完全分开:“长了一双丹凤眼”远远不如“如何看待丹凤眼”更能说明和反映一个人是否歧视;而国别和民族的身份问题,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拿哪里的护照和身份证、相貌是否符合某个标准的问题,更是关于他的心理认同和行为言论。一个人面对压力时所作出的言行选择远比他的长相能更够说明他究竟是谁。
美人的制造与排除——新型种族歧视与审美霸权
本次广告争议的表面的确是种族自尊引发的焦虑。但丹凤眼的“民族应激创伤”并不足以解释此轮讨论中冰山水面之下暗流涌动着的其他话语力量。一种较为主流批评的声音表示:商业广告不仅仅是个人艺术创作,广告营销需要讨好消费者审美,遵守“大众审美”。这种声音凸显了“大众审美”这一个模糊概念和强势的商业话语在这一议题中的作用。菜嬢嬢本人在微博中也表示“我的职业是模特,我靠这个吃饭……这是我的工作,这些言论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影响”。紧接着,中国名模吕燕和和雎晓雯等人也因为“符合西方刻板印象”受到人身攻击。30日,MTV商业广告导演@洪四蹄H4T在微博上表示,已经有两条广告的女主角因为眼睛小而被品牌方弃用。“两位女生的业务能力都极强,也都是我首推的演员,品牌也非常无辜,谁也不想担这个公关风险。”
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他者”在这次中国本土广告争议的讨论中仅仅是一个被立起来的稻草人。但实际上所有的被批评者和舆论影响的承受者,都是中国人。再一细心观察,被殃及池鱼的并不是所有小眼睛的名人(调侃除外),而大多是小眼睛的女名人。在吕燕微博下“西方辱华工具”、“资本主义豢养的怪胎”等评论,赤裸裸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政治话语。特别是今天这一轮猎巫式的辱华容貌审查,在捕风捉影的标准下对,尤其是对女性名模的“隔离和排除”,更直白地表明其惩罚的对象和标准并不是基于国族的(她们明明也是中国人、是汉族,不是吗),反而是基于性别和商业的身份,甚至是基于对待丹凤眼的立场和态度进行的。而这正是新型种族主义的典型特点:相互斗争的政治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血统或者国家共同体,而是以身体的、身份的、冲突的观念作为边界。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己人攻击自己人”、“自我阉割和排斥”等光怪陆离的现象在这一轮讨论中频繁出现。结合《雄狮少年》的情况,中国超模得到国际认可,中国作品拿到外国奖项,本来是符合“中国美走向国际、中国故事对外输出、中国文化自信”等积极民族主义叙事的正面事件,反而因为这种身体身份的冲突而产生了负面效应。在激烈的舆论对战中,“大眼睛才是美”的大众审美,本质上是一部分人对国族共同审美产生的不符合现实的幻想。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大眼睛才是美。但当一部分人以为这种美学标准是民族普遍的、正统的,并认为是“民族身份的正义观点”,进而导致他们对异见者进行纠正、排除和隔离。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上去这一群人在反对西方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实际上他们反而把国内的女性和观点异议者“种族化”了。打着反种族歧视的旗号进行内部歧视的底层逻辑就在于此,它的结果就是,在一场没有外国人参与的广告营销中,我们中国人出现了内部的分化和割裂,观念的分歧甚至走向了内部群体的排斥和宰制。
至于什么是真正的“大众审美”的讨论,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惨淡的现实,即当西方在彼岸已经开始接受丹凤眼的东方美,尝试接受高矮胖瘦各种类型、尝试反对身体羞辱(body shame)进行审美革命时,我们身处的此岸还在“大眼睛高鼻梁、白瘦幼、黑长直”的理想型幻影中挣扎。如果大眼睛高鼻梁的审美里有“慕强西方、自我抹杀”的成分,那么温柔恭顺的“低眉顺眼”难道不是“东亚儒家文化里男权对女人的性别凝视”?剥离拆分看客们的愤怒,我们不难发现,菜嬢嬢那种富于挑战和攻击性的欧美范儿,冒犯的并不是只是民族的,更是性别的。怒发而冲冠的关公同样是横眉吊眼,却毫无敏感刺激之处,更说明了“温柔温顺才是美”的一元审美观,是针对女性的审美,而“对外的反种族歧视”反而讽刺地成为了男性维护性别审美霸权一种最顺手的、嫁接来的理由。于是,“眯眯眼就是丑”可以说是性别歧视借靠着种族歧视进行审美霸权的狐假虎威。“觉得丑不买单就好”更是借助消费公民的身份进行排斥惩罚的手段。而商业和性别作为隐形的驱动因素,藏匿于虚伪的民族大义叙事后。这种复杂性是“反对歧视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反对长着丹凤眼的人”这一反种族主义的基本常识,为何在网络空间讨论尤其困难的原因。
我们要意识到,在关于美的规范和实践里,侵占蚕食我们身体的自主表达权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凝视,全球化的进程和外部的交流其实只是影响因素之一。来自欲望、政治、消费和技术的驱动因素在不同时刻以不同的权重影响着女性容貌的景观化。在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下,中国女性由解放前的三寸金莲,迎来了解放后改革开放前的淡化性征的劳动身体、随后进入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下的“女人味”的性征崛起,这是历史纵向上强势的政治经济驱动对审美标准的影响;中国男人在形象上摆脱东亚病夫的阴影,进行西化,只需要剪掉辫子即可;而女性则需要经历与缠足同样残忍的放足、割开眼皮眼角,并最终演变成全方位的身体管理和自我规训。如果说从林黛玉式的美人到欧化东渐摩登化的转变,意味着性别之间的男性凝视叠加了一层 “来自西方的国族凝视”,那么从裹脚到割双眼,西方中心审美的入侵、无孔不入散播焦虑的消费主义、医疗美容技术的发展和革新,影响的不仅仅是女人自身,更是男性在婚恋中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取向。就此,歧视性的审美霸权不但在国别之间形成权力差异的压迫,更在性别之间继续传导,女性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最末端,面临着性别、国族、资本等“中西杂糅、内忧外患”的多重凝视,同时受到父权制和东方主义的客体化。
丹凤眼或眯眯眼可以承载如此多的历史负担和文化意义,几乎完全取决于看客的心态和立场,而眼睛只是女人身体的一部分。从古至今,不管在什么权力秩序里,女人都容易成为被施威和发泄的对象。从头到脚,女性的身体成为任由性别、政治、技术和消费多种因素书写的白板。从古代的裹脚缠足到如今的整容手术,女人来负担这种凝视,从中遭罪,将其内化进行自我规训和身体管理,甚至获得受虐般的快乐。这也正是我们眼下发生的现实,眯眯眼的讨论和批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参与批判和猎巫的人中,也不乏女性。眯眯眼的上纲上线,扩大和泛化的不仅仅是性别容貌焦虑,更借助“西方”这一假想敌,强化了内部的敌对心态。当黑人自己用Nigger来化解和反抗种族污名的时候,“黄祸”反而成了部分国人攻击自己人的污名性话语。我们不得不对这样的分裂和内讧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一波反歧视到底在反对什么、为了什么而反对。
参考文献
王宁. 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2):54-62+128.
董金平. 从缠足到美容手术[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06.157.
周宁.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J]. 社会科学论坛,2010,(03):94-116.
杨须爱. 文化相对主义与当代世界的两种民族问题——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再认识[J]. 世界民族,2016,(05):1-9.
唐瑭. 身份、边界与超个体——巴里巴尔激进政治理论中的“政治与主体关系”探析[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120-126.
罗义华. “黄祸论”与晚清民初知识界的国民性焦虑[J]. 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20,(05):56-61.
宁薇,谢易宏. 伦理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冲突:原因探析与化解策略——以杜嘉班纳辱华事件为例[J]. 新闻传播,2019,(17):24-26.
赵轩. 中国表述与表述中国 20世纪20、30年代“辱华电影”评论中的话语角力[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05):94-102.
王晓凤,方青青,陈春野,张敏霞,施帮辉,谈伟强. 亚洲人重睑成形术的研究进展[J]. 中国美容医学,2017,26(02):135-139.
潘敏芳. “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悖谬——论《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中的身体书写[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06):17-24+161.
苏杭. 从傅满洲到花木兰[D].华东师范大学,2020.
汤嘉. 美人制造:民国女性身体之美的塑造[D].华东师范大学,2016.
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和西方身份政治危机——从JK罗琳说起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澎湃思想市场 2021-12-03 15:49
“魔法教母被魔法界除名”已经形成现象级的文化政治事件。它不但成为性别身份政治危机的典型案例,更处于“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与过度政治正确争论风暴的中心。

文|侯奇江
自2020年6月起,《哈利·波特》原著作者英国作家JK·罗琳关于跨性别群体的言论引起了大量的争议。这场争论延续至今,旷日持久,围绕“什么是真正的女性身份”,女性主义对待跨性别群体的态度、公共性别政策的性别合理性等展开,挑起了各方不同立场的论战。同年7月,粉丝网站“破釜酒吧”(The Leaky Cauldron)和“麻瓜网”(Mugglenet)共同发布声明称,将删除罗琳的个人网站链接和照片。电影版《哈利·波特》中若干角色的演员在社交媒体先后与罗琳割席。同年 8月,出于压力,罗琳主动归还了罗伯特·肯尼迪人权组织(RFKHR)给她颁发的“希望涟漪”(Ripple of Hope)奖。时至今日,罗琳引起的争议并没有平息的趋势,矛盾反而更加尖锐。上周,罗琳在推特上称收到许多死亡威胁,且有三位“极端人士”在其家门口拍照,曝光其家庭住址。
“魔法教母被魔法界除名”已经形成现象级的文化政治事件。它不但成为性别身份政治危机的典型案例,更处于“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反觉醒运动”(anti-wokeness)与过度政治正确争论风暴的中心。简单概括,反对罗琳的人认为其恐跨言论与《哈利·波特》书中以及粉丝群体所提倡的包容性价值观产生冲突,进而对她进行抵制,从而实现对歧视和不平等的反抗。而支持罗琳的人,则将其打造成了“取消文化” 的受害人和“觉醒主义”(wokeness)的牺牲品:“一个遭到过度政治正确迫害的女性主义者”。
这样的矛盾有力地展示了近年来美国政治运动中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边界何在的核心冲突。2020年7月,《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刊登了一封150多位文化名人的公开信,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反对意见压制和封杀惩罚。罗琳正是签署人之一。这封信虽然肯定了美国近年来关于种族和社会正义的抗争,但批评因某些言论就被开除、被解雇、被调查的“取消文化”,认为这是过度的政治正确,进而侵害了言论自由。
“罗琳取消事件”并非偶然,它承接了西方身份政治长期蓄积已久的矛盾冲突,成为继种族问题之后,“性别”这一身份政治的矛盾的集中爆发。如果说罗琳带来的争论是性别文化战争中的一个战役,那么“取消文化”、“觉醒主义”和许多话语,仍是文化战场的“武器”。而这些话语在溢出西方政治语境、来到中文世界后,存在大量的语义损失。围绕罗琳的争论,颇具代表性地折射出西方政治思潮中进步主义观念和保守派的冲突。本文退后一步,暂且放下其中关于性别身份的本质与建构之争等话题,而是把讨论重点倾向“取消主义”和“觉醒”等话语的历史和产生机制、介绍它们所经历的“定义斗争”、道德反转以及语义武器化的党派之争和政治背景。或许,这场发生在英语世界的文化战争和相关讨论也可以使我们受益。
话语的武器化——
取消文化、觉醒(woke)与反觉醒运动
在讨论罗琳如何被取消,和“觉醒”到底有什么关系之前,有必要尝试解释一下“取消”和“觉醒”等政治短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些中文自媒体甚至把它们当做同义词——它们虽然共享相同的地缘、历史背景和政治语境,经常同时出现,但具体的含义并不相同。另一些中文文章介绍了基本定义、选择性地筛选出具有倾向性的案例,并且给出了具有立场性的判断,但是并未介绍政治话语形成的历史过程,而这对我们理解围绕这些词汇展开的政治分歧尤为重要。
大致上,“取消文化”是指人的行为或言论违反了一些社会规范,令人反感,于是受到公众的强烈反对。除了社会声望受损,被攻击者往往还会失去工作等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或受到处分等不同形式的惩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取消文化”与中文的“因言获罪”的含义和语境大有不同。中文“因言获罪”往往意味着因向权威谏言、说出真相而受惩罚。而西方的“取消文化”,本来指大众通过社交媒体对名人、明星等不合时宜的话语进行反抗,起初是一种抵抗的态度。根据上下语境,它时而是一句表达不满的玩笑,时而是强烈抵制的态度,也可以是“脱粉”。不管怎样,“取消”在流行文化中种下了“集体抵制行为过分的名人”的种子。
谈论“取消文化”也无法忽略“觉醒”(woke)和“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也有译作“点名文化”)。因为“取消”一个人,首先要在意识层面(awareness)识别特定的价值规范,意识到某些行为或言论有问题,并且指出其错误之处。现实中,除了罗琳,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等名人因为性侵的指控,也成为“取消”的对象。此后,“取消文化”这种独有的抵制模式,也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在概念上演变成一种舆论压制,并且因此引发更多的争议。
“觉醒”的政治意涵则从黑人运动一路上升至全方位的文化战争:它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黑人运动反歧视的俚语,泛指意识到了系统性种族歧视,并且对此保持清醒、警惕,因此也被译作“警醒”。2014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州被警察杀害之后,反种族歧视的黑人活动家们就把“保持觉醒”(Stay Woke)变成了警惕警察系统内普遍存在的歧视和系统性社会不公的口号。此后,“觉醒”一词覆盖的社会议题逐渐扩大,在社交网络上也成为热门标签。它也可以用来反对移民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公,变成了一个以“批判种族理论为核心,以社会正义为进步政治”的词汇。尤其是2020年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掀起了新一轮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美国对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反思在此达到高潮,“觉醒”上升至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几乎成为具有时代性的词汇。
Vox援引作家William Melvin Kelley的话表示,自奴隶制时代,黑人之间谈论敏感问题的许多俚语都存在“编码性的预防措施”。“这样的语言用于保密、排斥和保护。当你的主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就无法惩罚你。”因此,语言上来看,黑人俚语具有强大的创造词汇和短语的能力。流行于特定社区和圈层的“黑话”,表面看上去隐晦而另类,却承载着社区精神和政治意涵。“觉醒”作为黑人地下语言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它是历史政治流变长河中一朵小小的话语浪花,直到社交网络的流行化和特殊事件的推波助澜,它才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美国意识。
尽管已经成为“重塑民主党和美国”的理念,“觉醒”所代表的意义依然是流动的。在社交媒体、音乐电影等流行文化的使用中,“保持觉醒”的政治短语有更加微妙和丰富的意味,语言本身在不断的变化,美国黑人的语言也在不断地被挪用、盗用。尤其是特朗普任期内美国政治分歧的极化、社交媒体的放大、保守意见的反弹,这些词汇的话语意涵展示出极强的模糊性和矛盾性,甚至发展成了道德立场的扭转。“取消文化”不再仅仅是指利用舆论压力公开问责、对某一类言论表达反抗和抵制的做法,而被批评者赋予“失控的社交媒体暴民通过网络暴力恐吓、伤害不同意见的人,从而形成言论审查的氛围”的含义。“觉醒”也明显地遭到众多攻击,这个倡导社会意识进步、号召团结和斗争的口号,被保守派人士当做是一个具有讽刺羞辱性的词汇,往往指虚伪的、表演性的政治正确,于是反觉醒运动(Anti-wokeness)拉开序幕。在西方语境下,“觉醒人士”甚至与中文的“白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语言发展、挪用和语义流转的过程,正表现了话语、文化和权力是如何始终保持紧密的动态关系。觉醒话语正是政治文化战争中话语武器化的绝佳代表,它已经被提炼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总和,更成为文化战争中,话语之役各方擦枪走火抢夺的阵地。《纽约时报》评论文章《觉醒之战》(The War on ‘Wokeness’)就指出了政治语言的强大威力。“语言描述宗教信仰、国家信条和战争口号。语言为我们下定义,决定描述人和事物的方式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语言可以推进自由和平等,也可以导致社会倒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为语言,为谁可以定义它、控制它,为为何讲述、为谁讲述而斗争。”
从觉醒到反觉醒——
文化战争中的价值分歧与党派之争
罗琳是“觉醒”的受害者吗?实际上,因其鲜明活跃的政治态度,对英国脱欧中的种族主义批判、女性主义等其他相对进步的政治立场,很多人认为罗琳本人就是觉醒人士。英国记者和节目主持人Piers Morgan尽管在以前和罗琳有过小摩擦,但在《独立报》的采访中表示了对罗琳的支持,认为她是“你所能遇到的最觉醒的人”。然而,当罗琳陷入恐跨混战之后,许多持有进步观念的人与她割席,而保守人士则利用她受到的攻击,颇有落井下石意味地认为这是“觉醒的失败”。几乎每一篇批评觉醒主义的文章里,罗琳在跨性别上的“觉醒翻车问题”都是无法绕开的典型案例。
罗琳的争议折射出觉醒运动目前阶段的现实处境:虽然与之相关的社会互动没有唯一且正式的权威组织,其语义含义如此流动模糊,但取消文化、觉醒运动的含义和态度有明显的群体和党派差异,代表了西方政治不同群体间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冲突,而这些矛盾就交织在对“觉醒”的观点上。不论使用者意在褒扬或者贬低,在公共讨论中,使用者对觉醒和取消的话语意涵的选择,自然也变成了一个文化和政治区分的过程:即辨别出相对的敌友关系。
脱离党派框架、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的背景,我们就无法真正看到“觉醒”与“反觉醒”之间的矛盾。粗略地说,西方语境下的左派阵营把“觉醒”当做政治进步的标志,而右派则把它当做攻击左派的靶心。近期,尽管自由派人士也作出大量反思和批评,但攻击取消文化和“觉醒”最多的则必然是保守派人士。在美国,根据NBC新闻于5月的统计,共和党的演讲、推文和声明中,“觉醒”一词的频率在2021年上半年显著地增加。在2020年8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上也反复强调“取消文化”是民主党“极左的错误”。这与美国右翼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禁止学校教授关于社会正义和其他“分裂性话题”的举措一脉相承。虽然建制保守派和另类右翼(Alt-right)内也存在大量分歧,但对于保守派而言,进步思潮关于种族、堕胎、枪支管制、同性婚姻、移民和难民等议题的态度,打破了美国社会道德的基础——基督教传统价值观。于是“觉醒”几乎成为保守派人士所反对的一切的代名词。反觉醒运动以不同的形式,被不同的共和党议员提起,成为其传递政治信息最前沿的概念,几乎发展成后特朗普时代保守组织的纲领性理念。
对“觉醒”和取消文化的攻击也来自对进步主义的道德恐慌,这种情绪远早于这些词汇的流行。20世纪六十年代后,伴随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变化,身份政治的诉求与民权运动等政治变化相呼应,进步主义观念逐步成为西方学界和政界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尤其是美国奥巴马任期内,一系列浓厚的带有进步色彩的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否定了保守主义的许多理念。由于进步观念的发展不均,一部分人迅速接受权利主体从“白人男性”向女性、少数族裔等扩散,权利内涵由政治自由向着社会经济权利、福利主义、环境权利等方向深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对这一系列变化感到难受。2016年,特朗普高举“反政治正确”的大旗,就是利用了白人等传统优势群体这种“被围困的心态”。政治学者英格利哈特(Ronald F. Inglehart)分析英国脱欧与西方兴起的民粹潮流时也指出,“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感到自己已经沦为主流价值的陌生人,他们无法共享进步主义的潮流,曾经的主导权力和优越地位日渐衰落。”
建制保守派曾经以最小政府的经济自由政策、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的外交政策和保守的道德文化倾向为特点。然而,移民大潮、高失业率和恐怖主义等问题让保守派极为不满,共和党建制派又在近年来逐步丧失了文化领导权,让自由派在媒体、学界等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动。于是更近的一段时间内,共和党也明显出现了向文化领域争夺话语权的转向。纽约杂志评论员Ed Kilgore在评论文章中称,共和党“下场”打文化战争的原因很简单,“文化战争的吸引力比钱包(经济政策)更大,文化战争的威胁比海外遥远的敌人更直接。”于是,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击战开始了。
从媒体的讨论和大众的批评来看,“觉醒”所代表的进步主义遇到强烈的文化反弹,导致这些话语迎来了下一个生命周期,或是所谓的第二波浪潮。部分自由派开始反思“觉醒”和取消文化中的问题,并借此进一步推动改革;肯定或否定“觉醒”在左翼内部造成一定程度的意见分裂。民意调查显示,中间派民主党占民主党内的大多数,但共和党人将民主党描绘成更“激进”的派别以便于攻击;部分右翼则出于政治实用主义有意无意地对传统产业工人等群体打造了“白人身份政治”,“觉醒”正好成为其道德价值批判的靶子。
唇枪舌战正在激烈地上演。取消文化进一步激发了部分人对进步思潮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恐惧。尤其是在珍视言论自由的美国,保守派担忧取消文化造成的围剿和封杀,导致人们无法在公共作出意见表达,进而侵蚀民主的根基。担忧情绪极化后,“觉醒”成为“政治正确”的邪恶产物。觉醒人士在共和党参议院的口中成为了“觉醒暴徒”、“正义先锋”和狂热分子;主张平等权利的进步观点被当做“煽动性的、分裂性的言论”。在这样的观点中,“觉醒”和“取消”似乎已经成为充满了钓鱼式的构陷、恶意争论和民间私刑的道德闹剧。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士反击称“反觉醒运动”是让保守派上瘾的“猫薄荷”,保守派装作是“觉醒”的无辜受害者,以捍卫自己的特权。
罗琳本人或许是无意,但已经成为这场道德闹剧的主角之一。2020年7月刊载于The Objective网站的《有关正义和公开辩论的更具体的公开信》是针对《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的回复。且不论其他内容,这封信指出,“罗琳是取消文化受害者”并非事实。罗琳在推特上持续不断发表恐跨言论,恶意臆断跨性别人士,并把与变性相关的医疗护理如激素替代疗法,比作性取向转化疗法。她为她的1400万粉丝提供了一个充满语言暴力的反跨性别人群的言论平台,却并未因此而被追究。除了罗琳,该信也悉数回应了哈泼斯杂志公开信影射的其他取消案例。总而言之,对“取消”的恐惧与“取消”造成的实际后果之间是有差距的,那些对别人造成伤害、所谓有污点的人并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取消”的现实能力是有限的。回复的公开信明确地指出了特权阶层对自身优势的傲慢,并认为“取消”是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的方式。
两封公开信的一来一往和围绕系列事件的讨论,可以说是一次激烈的“社会对话”。可见的是,文化战争中的意见分歧和观念分裂在短期内是无法弥合的。
生意经还是麻醉药?
对觉醒营销、觉醒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评
发展至今,对“觉醒”和取消文化的批评,不见得都来自保守人士。持有进步主义观念的人也在对它们做反思。现在较为常见的批评分为三种:一是取消文化造成的伤害是否会有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与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二是针对西方公司制的经济模式里,进步主义在商业营销和品牌方面的虚伪性;三是身份政治过于关注文化清洗和取消,是否背离了经济和政治领域革命的本质。由于其他文章对第一种批评的讨论已经较充分(参考澎湃新闻《林垚:自相矛盾的公开信与取消文化的正当性》等文章)。这里主要介绍后两种批评的声音。
持有进步观点并且以此作为营销概念的公司,首先成为话语炮火对准的焦点。在这种批评中,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由觉醒延伸出的话语再造:例如:生意经式的觉醒(Corporate woke),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泡沫(ESG bubble),觉醒消费主义(consumption woke)和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等。《觉醒公司:美国企业社会正义的骗局》(Woke, Inc.: Inside Corporate America's Social Justice Scam)是这一类批评的代表作。这一类观点认为,公司高举觉醒的大旗是为了转移焦点,让进步人士忽略其商业垄断等经济意义上的剥削和不平等行为。公司在产品包装、广告和市场营销中积极地参加支持同性恋、性别平等等进步话题,以获得年轻消费者的好感,并且扩大其品牌影响力,但这本质上是一个充满正义叙事诱惑的资本主义骗局。
《大西洋月刊》在2020年7月刊登一篇名为《资本主义如何助长取消文化》的文章,进一步明确了对 “觉醒资本主义”批评。此文称,进步主义价值观沦为一个强大的品牌推广工具,公司对进步价值观的支持,实际上是用一种嗓门大、成本低的方式做市场营销。文章认为“觉醒资本主义是一种商业的自我保护”,好让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能够在保证不损害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之上,努力适应消费公民的“正义”事业。这种姿态性的、虚伪的方式,替代了真正的改革。
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是,Helen Lewis的出发点与保守派截然不同,其文章并不是在反对觉醒本身。一些中文自媒体援引该文章攻击“觉醒”时,刻意忽略了这一点。原文章中,她特意在括号中注明:“我在这里使用‘觉醒’一词,不是在嘲讽、贬低,而是要强调‘觉醒’与资本主义不相兼容。” Helen Lewis并不是保守派,她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直接表示其认同进步观念,希望社会能够消除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她反对的是姿态性的虚伪。考虑到在过去的公共政策中,共和党人基本上赞成有利于公司和企业的经济政策, Helen Lewis的经济视角反思对进步运动而言显得更有价值。在文章末尾,她写道:“我唯一想问那些赋权女性领导力的大公司,你们有现场托儿服务吗?只有女性论坛和动力早餐,而不解决职业母亲的真正困难,一切都是装点门面。”此类意见是推动觉醒运动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更向前一步”,但往往也被保守派选择性地利用。
虚伪性的讨论和批评也不仅仅指向公司。从人们参与进步运动的形式到抗争的内容,“觉醒”本身也饱受“表演性”、“发泄性”的争议。一方面,2017年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是美国越战后境内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但温和的游行和静坐被认为是觉醒无效的、姿态性的表演。另一方面,2020年警察暴力执法致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后,美国五分之一的人冒着疫情、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的危险参加了又一持久而广泛的抗议游行。但这一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衍生出了“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美国至少16个州的25个城市实施宵禁。这成为美国保守派活动家口中的“文化革命”,“觉醒”甚至被打造成导致暴力的原因。游行抗议,不论是温和还是骚乱,批评者始终认为都不是斗争的合理方式。而社交媒体发起的新型去中心化社会运动,在某些批评者眼中更成为一种空洞的表演。
抗议真的无效的吗?亚特兰大在2020年6月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虽然短期看上去,游行所呼吁的政策不会立刻落地,但抗议是有效的。“集体行动是一种改变生活的体验。”抗议的力量体现在对抗议参与者和社会的长期影响上。文章指出,社交媒体和街头抗议当然并不是“挥舞即显灵”的魔杖,抗议本身也是高风险的行为。在困难的条件下抗议数周,需要后勤保障和组织能力,更要面对镇压和打击,谈判也并非易事。但从长期来看,抗议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挑战的是民主权力最重要的支撑:合法性。抗议打破了对暴力的垄断。人们可以被迫服从,但镇压和打击无法强迫扭转人们的热情、能力和创造力。抗议吸引了注意力,赢得了对话,将一些临时参与者变成了终身活动家,并就此长远地改变社会。仅就警察暴力执法这一议题而言,抗议难能可贵地打开了公共议事的 “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即拓宽了大多数人在警察系统改革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伴随着游行抗议的发生,媒体开始呼吁取消对警察的资助(defund the police);保守派虽然反对“取消”,但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警察系统的改革——这是短短几年内保守立场发生的重大改变。
此外,多起推倒、移除历史人物雕塑的事件,以及电影《乱世佳人》一度遭遇下架(随后,流媒体平台HBO对电影附加上历史背景说明和警示后重新上架),标志着文化领域里“觉醒的标准”在重新衡量历史人物、文学经典等。相关的争论也就此成为了文化战争的硝烟弥漫处。一方面,颠覆和挑战正在发生,欧洲中产白人男性为主导的经典历史迎来了女性主义、非裔视角等,解构主义或后解构的理念几乎要“修正、重写历史”。固守的保卫者为了延续旧有的道德价值,与主张推陈出新、进行颠覆的变革者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在这一层冲突之上,重视经济基础的批评者甚至认为这个话题根本不值得吵架,他们认为文化决定论耽误了真正的革命:目前的觉醒运动过于强调文化领域的“清洗”和“取消”,转移了资本主义真正的矛盾,麻痹了革命的有效动力,从而阻止了真正进步的斗争。
围绕觉醒和取消文化复杂纠葛的抵牾对抗,向我们展示出了西方政治思潮中的各类冲突。在反觉醒运动的队伍中,更激进一点的 “觉醒人士”甚至和反对觉醒的保守人士肩并肩——毕竟取消文化成为特朗普和奥巴马难得地“达成一致共识”、共同批评过的唯一话题。限于篇幅,围绕觉醒和取消的其他冲突,例如福音派宗教背景和觉醒的宗教化批评等,暂不介绍。但毫无疑问,美国社会应该如何“科学地、整体地、本质地甚至优雅地革命”之争论还将要继续。在实现更平等更自由的社会之前,身份政治仍需要回答并梳理是“谁的平等、谁的自由”的问题。
粉丝背叛还是小群体霸凌?
关于罗琳事件中文的误解
对于围观这一场争论的我们而言,罗琳事件的确给部分中文社交媒体的网民带来莫名其妙的“离谱感”。表面看去,作为“正主”的原著作者被粉丝除名、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被另一群女性主义者攻击,很容易营造成具有狗血娱乐剧情的闹剧。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粉丝背叛正主或小群体霸凌的故事。饭圈的思维框架的套用有些牛头不对马嘴,“女拳锤死女权”的性别污名是一种最为肤浅的理解,但这的确是中文互联网议事的常见框架。
罗琳与“觉醒”有着复杂的矛盾关系,但是在“取消文化”这个问题上,她并没有被完全取消。事实是,作为一个作家,罗琳并没有被禁止写作,她的书仍在出版,并且,她的书卖得更好了。2020年7月《卫报》的报道表示,尽管在跨性别的问题上,罗琳激起了许多争议,但这丝毫没有减损《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受欢迎程度。疫情期间,出版《哈利·波特》的出版社儿童部门的营业额增长了27%,达到1870万英镑。虽然出版社并未透露其中《哈利·波特》贡献的增长究竟是多少,但该出版社的首席执行官对《卫报》表示,罗琳的书是当之无愧的畅销书。美国保守派杂志《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该杂志曾被认为是美国保守派的《圣经》)认真地梳理了罗琳因为跨性别言论而收到的支持和感谢,其中有跨性别人士、女权主义者、研究人员等。虽然她遭受了威胁和反对,但故事的另一部分也应该被讲出来:因为关于跨性别的言论,罗琳不但收获了更多的注意力,也就此收获了大量的支持者。在中国亦是如此。
本文的用意并不是给出“罗琳到底是否是受害者”的定论,她的性别观点是否正确,未来也自有回答。对于罗琳所受到的骚扰和威胁,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于2020年9月接受《The New Statesman》的采访中也表示,“虽然我不同意罗琳对跨性别的看法,但我不认为她该受到骚扰和威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记得,世界各地的跨性别群体在街头和工作场所同样遭受着威胁和骚扰。所以,假如我们准备反对骚扰和威胁(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些事在哪里发生、谁受影响最深、本该表示反对的人有没有容忍这些事,这三个问题我们都应该有全面的了解。对某些人的威胁可以忍,而对另一些人的威胁不能忍,这样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前文已经解释,在西方政治语境下,觉醒和取消是关于不同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争夺。朱迪斯·巴特勒并没有参与公开信的签署,并且坦诚表示,她在公共生活中也犯过大错。“我是教师和作家,我相信缓慢的、深思的争论。我从质疑和挑战中学习。如果因此人们不再阅读和聆听我,我内心是反对的。”但另一方面,她认为取消文化是被压迫群体的强烈政治诉求,不应该被销声匿迹。“民主需要一种恰当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总是文质彬彬的。”
西方民主或许正在经历这种挑战,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危机。文化战争的前提是,挑战权威、进行话语较量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忽略这一前提,轻易地把罗琳的经历打造成一个“因言获罪”的故事,则更是中文对觉醒和取消的刻意误解和挪用。不论怎么看待罗琳事件,对觉醒和取消的批评更不应该生硬地嫁接在中国的语境下。罗琳的取消危机如果是一种发生在远方的危险,那么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我们难以讨论发生在身边更近的事。
隔岸观火的我们如何理解、看待觉醒和取消,更多地反映出我们自身所在的政治心理位置。尽管互联网和全球化让西方思潮的概念唾手可得,年轻一代对身份政治和西方进步主义的话语愈发熟悉,但信息污染和不对称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罗琳事件。我们的经济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外资品牌在中国也处于微妙的政治道德处境,跨国营销在本地面对的截然不同的舆论环境。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现实语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甚至参与“远方的争端”的讨论,或许是我们从他人的经验和反思中受益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王恩铭.美国20世纪末的一场文化战争:保守派与进步派的较量[J].世界历史,2011(05):38-
张业亮.另类右翼的崛起及其对特朗普主义的影响[J].美国研究,2017,31(04):9-31+5.
48+158-159.
何涛.当代西方身份政治思潮的新动向与危害性[J].思想教育研究,2021(07):106-110.
龚思量.专访林垚:自相矛盾的公开信与取消文化的正当性.澎湃新闻.2020.08.09
龚思量.思想周报丨批判性种族理论正成为美国文化战争新战场.澎湃新闻. 2021.06.28
郭志.取消文化,是冲击言论自由,还是无权力者的权力?端传媒.2020.09.01
Inglehart, Ronald,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16-026, August 2016.
Alona Ferber. "Judith Butler on the culture wars, Rowling and living in “anti-intellectual times”. The New Statesman. " 2020.09.22
Kenya Hunt. " How 'woke' became the word of our era". The Guardian. " 2020.11.21
Aja Romano. " A history of “wokeness” Stay woke: How a Black activist watchword got co-opted in the culture war". Vox.2020.10.09
Aja Romano. " The second wave of “cancel culture” ". Vox.2021.05.05
Aja Romano. " Why we can’t stop fighting about cancel culture". Vox 2020.08.05
文中提到的公开信、媒体等:
"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Harper's Magazine. "2020.07.07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
" A More Specific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The Objective. 2020.07.10
https://theobjective.substack.com/p/a-more-specific-lette
Allan Smith, Sahil Kapur. " Republicans are crusading against 'woke'".NBC news. 2021.05.02
Charles M. Blow, " The War on ‘Wokeness’ ". NYT. 2021.11.10
Perry Bacon Jr. " Why Attacking ‘Cancel Culture’ And ‘Woke’ People Is Becoming the GOP’s New Political Strategy" FiveThirtyEight. 2021.05.17
Ed Kilgore. "Is ‘Anti-Wokeness’ the New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 New York Magazine. Intelligencer. 2021.05.19.
Thomas B. Edsall. "Is Wokeness ‘Kryptonite for Democrats’? "New York Times.2021.05.26
Malaika Jabali, Laura Kipnis, " Rebecca Solnit, Bhaskar Sunkara", 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 Zaid Jilani and Derecka Purnell. " We need to discuss the word ‘woke’ ". The Guardian. 2021.11.09
Madeleine Kearns. " J. K. Rowling vs. Woke Supremacy". The National Review. 2020.06.12
Mark Sweney. Harry Potter books prove UK lockdown hit despite Rowling trans rights row. The Guardian.2020.07.21
罗琳被消失事件:觉醒资本主义和取消文化让谁受益?微信公众号“墨带”. 2021.11.20
作为“爱的囚徒”的李靓蕾们: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不容忽视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澎湃思想市场 2021-12-21 12:22
王力宏与前妻李靓蕾近日在微博上的对峙,向我们提供了当代家庭矛盾的一手文本:男性手握性别福利却不履行婚姻义务,女性不愿再是沉默的生育机器和无偿劳动的提供者。
李靓蕾在文章中数次提醒其他女性“防患于未然”,然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且作出反思的不应该仅仅是女人。上层社会中的李靓蕾拥有教育和个人能力的资源,可以作出“漂亮的反击”。社会中下层家庭主妇,即使拥有相同的能力,也不一定能够像明星妻子一样获得公众注意力。对抗婚姻、职场和家庭中的性别不公,不仅仅是女性更聪明地作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性别不公的问题。生产与生活制度上的公私分离,不单是“丈夫与父职的缺席”,更是育儿公共服务和合理社会政策的缺席。

文丨侯奇江
“我决定站出来的原因之一是我不想再有女生和我经历一样的事,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省思。”12月17日,在歌手王力宏于社交媒体宣布已申请离婚的两天后,前妻李靓蕾在微博上控诉前者婚内出轨、家庭冷暴力等。不同于一般娱乐新闻婚内出轨曝光的指责,李靓蕾的文字更多着墨于讲述女性在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后所遭遇的结构性不平等:恋爱中被欺骗的角色期待和婚后连续怀孕哺育的落差;“伪单亲”丧偶式育儿中丈夫的缺位;她遭遇的婚内经济失势、夫家家庭成员的霸凌和来自伴侣的利用和情感剥削。李靓蕾在文章中说:家庭主妇是一份全年无休的无酬工作,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不被承认。“这样不对等的关系,也会让女性处于弱势,即使男生出轨或者家暴也难以有话语权。”
王力宏和李靓蕾在社交媒体上隔空喊话的拉扯难以避免地被社交媒体当做娱乐丑闻狂欢消费,但这起明星夫妻之间的个案纠纷本质上仍反映着婚姻中普遍的性别困境。二人的叙事体现了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和性别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挣钱、女性育儿。19日到20日,两人在微博上就婚内是否出轨、离婚经济纠纷等问题来回进行了数次质询和回应,双方叙事恰好同时暴露了婚姻中典型的性别风险: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的家庭婚姻责任的不对等、出轨等性道德的模糊化、婚内利益分配的失序和两性权力关系的差异。
本文暂且放下此事件中关于王力宏是否出轨等事实性的分歧,希望借助李靓蕾较有自主意识的叙事和对个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口述,讨论其所展现出的女性在不平等的婚恋和家庭生活中所面对的结构性的沮丧和压抑,正视她们在家庭中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痛苦,讨论被长期忽略的照料和生育的社会价值,消除对家庭主妇的污名和对家庭劳动的轻视。李靓蕾所经历的绝非孤案,她所讨论的困境是任何一个女性因婚姻和生育陷入困境、因为性别进行再生产劳动却得不到认可的普遍现象。在这个充斥着性别焦虑和婚育压力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在公共讨论中推进对社会性别不公现象的反思,如她所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一起省思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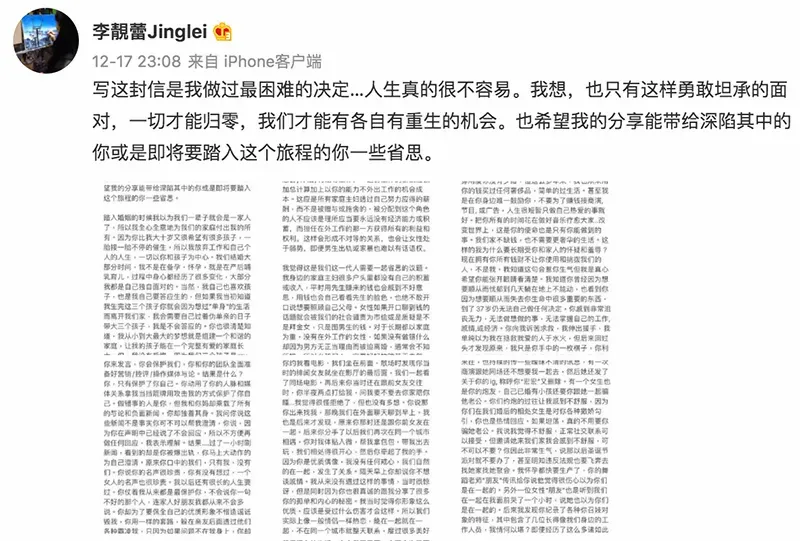
养成式的爱情:父权浪漫观的陷阱
倘若对娱乐新闻尚存记忆,大家应该记得2013年王李二人宣布成婚时,媒体是如何利用两者的年龄差异来打造美好爱情神话:“16岁的李靓蕾遇到了26岁的王力宏,相识十年后步入婚姻殿堂”等等。然而时过境迁,浪漫的甜蜜爱情反而变成了不堪的过往。李靓蕾回顾当时“我还未成年,你26岁与我语言暧昧”和王力宏的“没有联络差不多有十年”的反驳,让这十年有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意涵。
实际上,男性成功人士寻找年轻的女性作为伴侣的“养成”模式并不少见。近期一系列男明星在性别问题上的“人设崩塌”和人们对“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文化现象的反思,都说明了有权势的男性在利用父权的性别优势、通过经济物质甚至精神控制的方式,围猎和剥削女性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李靓蕾指出的“有权势的人操纵媒体、媒体操纵大众,造成社会价值偏差,舆论思维被控制”。因此,男性名流的性别失范不是个别的“不守私德”的个人问题。娱乐工业和造星过程,也正是养成式爱情叙事的教唆源头之一。这些流行于大众文化的符号和话语,把男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性别特权,装点成了一个看似诱人的陷阱。尽管步入这样的关系意味着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等全方位的不平等,但性别规训刻意忽略了男女在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女性所承担的大多数婚育风险。不论是短暂的“性玩物和社交资本”或步入婚姻成为“家养的生育机器”,权力差异都意味着社会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
如果说婚前养成式的爱情是神话,那么婚后家庭主妇个人发展的牺牲和退让,才是千疮百孔的赤裸现实。李靓蕾的婚后生活成为“明星全职太太”难得的口述证言:“我放弃工作和自己个人的人生,一切以你和孩子为中心。我们结婚大部分时间,我不是在备孕、怀孕,就是在产后哺乳育儿,过程中身心都经历了很多变化,大部分我都是自己独自面对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看似帅气优质的王力宏实际上难以完成为人夫和为人父的基本责任。除了长期的丧偶式育儿,李靓蕾后期在爱情政治的角力中继续让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作出了单方面开放式婚姻的妥协:“我还是愿意选择原谅你、陪伴你,只是换一种方式,不奢望你改变了,让你自由地过你想要的生活方式,我退出了你的生活,就带着孩子在家等你。”
从经济物质条件到感情利用操控,女性暴露于婚姻中的风险是多维度和全方位的。李靓蕾的讲述为我们提供了家庭内部性别不公造成对女性伤害和惩罚的一手经验,揭示了婚姻生活中全职家庭主妇的身份困境、被压抑的情感欲望,无偿劳动的照料惩罚(指女性在家庭内部承担照料工作,会导致其低就业率和低薪资水平的情况)和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指因为职场的性别隔离、婚姻和生育等因素,女性丧失职场机遇,获得更低的薪酬待遇等),父职的缺席和婚内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就此延伸出来的道德困境和人际关系危机。幸运的是,她的故事揭开了父权浪漫观下两性关系虚伪的面纱。
李靓蕾有能力通过冷静而富有说服力的文字夺回个人历史的叙事权,但她的控诉和后来的胜诉,更折射出了另一群体的性别困境。在这个始终以男性为中心的多边关系中,李靓蕾并非最弱势的一方。作为合法妻子,她拥有身份的道德优势能够让她写下针对前夫的檄文、为自己说明申诉,并且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而那些前女友、“小三”、被睡的嫩模等,却始终是最边缘的客体。实际上,她们和李靓蕾一样都是父权中心主义下男性性游戏的猎物,是被王力宏利用和剥削的受害者。不论是在和王力宏的关系还是在“小三”的指责中,她们经历的性别暴力和社会压力也源自性别歧视和不平等,但她们更无法反抗这种不公,难以说出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她们的情感经历和个人诉求不被认为具有道德正当性,也因此几乎无法收获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李靓蕾的本意或许并不是要把矛头对准其他女性。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这些情况的知情和忍让,在婚姻关系破裂后又为指责王力宏其他性对象的“实锤”,王李婚姻政治的角逐和利益的争夺,在客观上让其他女性成为他二人之间婚姻悲剧的“陪葬品”。问题制造者和发起剥削暴力的男性只是有了个沾花惹草、无关痒痛的道德污点;合法妻子因为占领了婚内身份和道德优势赢得了舆论胜利;其他女性成为被消音的、被剥夺的阴影中的幽魂。然而,男性始终占主导的、以“合法身份”、“上位”作为女性奖赏的附庸型的婚姻制度,却无法进一步反思。这是我们在讨论李靓蕾事件中仍需警惕的父权观念的陷阱,因为正是“宫斗戏”的看客心态,强化了父权制对不同女性进行分化、规训和奖惩的道德秩序。“正房撕小三”中的道德指责,也正是父权制的幽魂借着部分女性的手,在加害另一群女性。
俘虏式的家庭主妇:是选择还是妥协?
李靓蕾在某种意义上是颇具有自主性的完美幸存者:她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符合“理想妻子”各方面严格的社会要求。她期待幸福完美的家庭生活,“愿意”成为全职妈妈,也想要孩子,于是成为家庭主妇和完成三胎生养哺育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她的个人意愿的。这样的“家庭主妇化”个案,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主动选择成为家庭主妇的故事,已经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主妇叙事。而她的经历和控诉,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许多焦虑和认同,更把“家庭主妇”的讨论拉入了公共空间的焦点。社交媒体不断提出“女人一定要有钱”和“不论何时都要有工作”的危机解决方案。《中国妇女报》也在对该事件的评论中直言“警惕脱离职场的风险”,称“女性参与职场、保留职场竞争力,还是最有安全感的选择。”
舆论隐隐透露出了性别焦虑下,“嫁得好”和“干得好”这两个经典的互斥模式之间大家对后者的选择偏好。然而,这两种所谓的“个人选择套餐”背后的支撑话语都存在简化、理想化女性现实困境的倾向。对个人而言,步入职场还是留在家庭的选择面临着制度结构和文化的多重钳制。是否成为家庭主妇并非完全凭借个人意愿,女性面临的群体性困境,不应该被简化成个人选择和宿命。我们更要警惕对家庭主妇和全职妈妈的二次歧视。作为社会现象,“主妇化”与女性群体所存在的经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在一个排斥女性的、不友善的劳动力市场,女性无法摆脱传统藩篱和陈旧观念的家庭角色规范的要求。个人在缺乏制度性的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女孩该不该回家、能不能回家”的行为动机,受到经济风险、婚姻风险、家庭策略和自我认同等多方位的影响。
在现实中,更多的女性并不像李靓蕾这样具有经济优势,职场和家庭之间的“双肩挑”重担同时压在许多女性的身上。如何兼顾家庭和职业是长期以来女性难解的问题。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女性是首当其冲的下岗和失业人员,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也展现出更复杂多样的面貌。严酷的职场竞争、缺位的制度保障,使得中国女性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成为深受国家、资本和父权三重压迫的弱势群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生命的阶段,回归家庭背后有着不同的行为逻辑。虽然李靓蕾的案例脱离了中国普通女性的情况,属于少数积极主动主妇化的特权阶级,但在中国,类似情况也多见于收入和地位相对较高的上层家庭。同为家庭主妇,她们与来自社会底层的传统主妇有天壤之别。对于她们而言,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家庭实践过程也并非完全的个体自主的选择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下与相关家人的互动、协商、妥协中形成的”。
社交媒体上“不论如何不能放弃工作”的解决方案理想化了职场女性的状态,忽略了职场女性所承担的母职压力。事实上,挣得多不代表女人在家庭内就可以扬眉吐气。根据叶胥等人的研究,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配置不一定因女性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家庭内男性话语权和性别展示的作用依然重要,女性甚至为了缓和家庭性别角色和经济地位之间的冲突,主动提供更多的家务以弥补自己收入更多带来的性别角色失位,以安抚“男性自尊受损”的丈夫。另一方面,全职妈妈则因为没有经济收入而成为丈夫的附庸品,在家庭地位陷入了“俘虏式妻子”的角色困境。学者莎妮·奥加德(Shani Orgad))对这种情况这样总结到:“妇女以自身的牺牲培育下一代,让丈夫们从家务劳役中解放出来,投入职场拼搏。他们的社会权力和地位得到巩固,占据了家庭主导的经济地位,反过来却对没有经济报酬的全职太太们施压。社会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贯穿于两个空间之中。这样导致的现实是,妇女在外被职场男女不平等、以有偿工作为个人价值衡量标准的资本力量所操控;在家庭内部则被父权制的特权所宰制,迎合丈夫的需求,将个人价值寄托在儿女身上。”
是工作还是当母亲,现代女性如何“为自己而活”是一个生存命题。要解决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之间的性别困境,要拓宽女性自身个人发展的空间,不仅仅需要打破职场好家庭观念中的性别歧视,寻求夫妻共同育儿的改变,也需要获得社会福利和公共制度的支持。这其中,最紧迫和最具现实意义的改变之一,就是承认包括家务和生育在内的女性再生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保障婚内女性的个人经济权利,消除母职惩罚和照料惩罚。
“爱的囚徒”:照料惩罚与隐形的家庭再生产
包括生育、照料、家务分工和母职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性别不平等研究的经典议题。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再生产的理论之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开始定义日常生活和代际维系中的照料和生育等行为。简言之,女性在私人领域从事的“隐形的”劳动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用和价值,但是由于此类劳动需要投入感情和关怀,被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认为“去技能化”,难以兑现市场价值,从而对劳动的提供者(通常为女性)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维度。在这一过程中,照料者对被照料者存在感情和爱的责任,家庭或亲密关系里的利他意愿和感情回报,也形成了家务劳动低薪酬、无经济回报的文化原因,学者称之为“爱的囚徒”(Prisoner of love)困境。
李靓蕾有意识地把自身作为母亲和家庭照料者的身份视作是劳动力市场的个体,几乎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学视角的母职研究的典型个案。李靓蕾甚至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家务劳动薪酬计算公式,以弥补自身受到的母职惩罚。她写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女性,选择为家庭付出当家庭主妇,虽然实质上属于‘无酬’工作。但,这只是家庭成员角色的分配,也是家庭重要的支撑……这份工作的薪酬应该加总计算加上以你的能力不外出工作的机会成本。这应是所有家庭主妇透过自己努力应得的薪酬,而不是被赠予或施舍的。被分配到这个角色的人不应该是理所应当要永远没有经济能力或积蓄,而担任在外工作的那一方获得所有的利益和权利。”
在她的辩解和自证中,尤其值得玩味的最后一段关于“跻身上流社会”的澄清,也体现了在“爱的囚徒”困境中女性的意愿、感情与家庭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张力:“我没有‘靠他’获得现在的生活,未来我不需要,也不会为了要跟他拿生活费而受任何的屈辱(虽然是我应得的,但是不用,谢谢。)我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把孩子很好地养育成人。”这一段叙事展现出了家庭成员中照料劳作的现实利益深刻地羁绊勾连着人的情感价值——李靓蕾必须小心翼翼地绕过“处心积虑拜金女”和“怀孕/离婚胁迫要钱”等性别歧视的道德暗礁,才能进一步争取婚姻内合理的经济权利。
事实上,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谈论财产和利益分配是尤其敏感的。王家父子的回复也赤裸裸地展示了父权制的家庭照料安排中,社会不平等被镶嵌在家庭的爱与金钱的二元对立里。关怀和照料如果带有挣钱的目的就不再单纯,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预设形成了一对极富张力的矛盾,这样隐形而又根深蒂固的观念也造成了亲密感情和经济报酬的互斥性,进而,阻碍了照料者获得公正报酬的合理性。事实上,家庭劳动和育儿哺育的性别分工和无偿劳动让女性受到了性别惩罚;妇女回归家庭的再生产没有得到社会的物质及观念支援,更牢固地把她们困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中。感情劳动在家庭内部的交换价值也有限,造成了家庭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低下。而现有的法律中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形同虚设,法律和制度中尚未有明确的规定保障家务劳动者的利益,造成了家庭内部成员生存和发展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不平等。
20日中午,随着李靓蕾对王力宏利用情绪操控(gaslighting)和更多婚姻情况的说明,王力宏道歉,表示将要把房子过户给李靓蕾,参与孩子的抚养教育,并称暂时退出工作。二人之间的“口水战”可以说已经分出胜负,再度引起了社交媒体上盛况空前的热烈讨论。这一热点事件终将冷却,但李靓蕾讲述出作为名人背后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生活体验,利用文字和社交媒体重申话语权、夺回个体尊严、争取自身经济权利的文本,为今年的公共讨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王力宏李靓蕾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为人夫妇、为人父母的男女个人在婚姻层面的伦理挣扎,更精准地踩中了时代性别、阶级焦虑和群体性婚育危机的脉搏。尤其是在三胎政策人口压力、家庭经济紧张和性别文化转向的当下,生产和再生产处于普遍调整变动的复杂关系中,亲密关系和家庭组织模式自然要受到强烈的冲击。
李靓蕾在文章中数次对其他女性的提醒和忠告:“所以女孩们!一定要好好的防患于未然。”然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且作出反思的不应该仅仅是女人。上层社会中的李靓蕾拥有教育和个人能力的资源,可以作出“漂亮的反击”。可以想见,社会中下层家庭主妇,即使拥有相同的能力,也不一定能够像明星妻子一样获得公众注意力。对抗婚姻、职场和家庭中的性别不公,不仅仅是女性更聪明地作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男性参与共同构建平等伴侣关系,解决全社会结构性、系统性的性别不公的问题。生产与生活制度上的公私分离,不仅仅是“丈夫与父职的缺席”,更是育儿公共服务和合理社会政策的缺席。我们要继续追问如何追求性别更平等的家庭结构和育儿模式,改善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内部等不同空间的性别文化。
参考文献:
叶胥,杜云晗.相对收入、家庭成员互动与女性家务劳动供给——基于性别展示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21,27(05):83-97+35.
曹晋,曹浩帆.高学历全职妈妈与英国当代父权制的再建构——评莎妮·奥加德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J].妇女研究论丛,2021(03):124-128.
吴小英.母职的悖论:从女性主义批判到中国式母职策略[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33(02):30-40.
肖索未,简逸伦.照料劳动与社会不平等:女性主义研究及其启示[J].妇女研究论丛,2020(05):12-27.
苏熠慧.重构家务劳动分析的可能路径——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关家务劳动讨论的反思[J].妇女研究论丛,2019(06):68-74.
吴小英.主妇化的兴衰——来自个体化视角的阐释[J].南京社会科学,2014(02):62-68+77.
阿里价值观滑铁卢:职场中的性别霸凌和绩效暴力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澎湃思想市场 2021-08-12 11:50
职场中的女员工不是男性员工的工作福利,更不是为了完成业务目标施以性贿赂的工具。职场性侵不仅仅是法律框架下某个特殊情景下的犯罪,更是公司组织管理必须要切除的普遍毒瘤。

文| 侯奇江
阿里性侵事件在舆论场连续发酵了几日,事件的细节和具体的结果仍在等待警方的调查。当事人在食堂发传单的画面仍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散。在所见到的资料中中,那张宣传单印象令人深刻:白纸黑墨大字加粗地写着侵害者的花名和诉求。在人头攒动的食堂中,一个绝望的女孩被冷漠围绕。她面对的不是陌生人,而是与自己一起并肩工作的同事。食堂里整齐打饭队伍中的冷漠和回避,也是后来人们对6000员工联名倡议不信任的基础。阿里现有的一些高管回复备忘录中,严重的强奸指控被文字构建成体验式的情绪危机,“过度亲密”的非罪化描述表现出一种责任回避的机警——这是职人的精明。根据事件当事人的陈述,嫌疑人王成文的直接领导,P8甘启梁表示早知道要出问题,“已经有意识地只招男生,不再招女生,女生不适合这个工作”,更昭示了女性在维权后二次惩罚的困境:恶性事件的次生灾害似乎注定带来受害者有罪论,但真正犯下错误的人总有各种各样的开脱借口。在关于价值观和组织管理缺失的批评中,我们还在等待真正建设性的、制度性的改善。而我们已经等得太久。
关于强奸、性侵和猥亵,已经有太多谈论,而似乎永远也谈论得不够。强奸不仅仅是性器官对性器官的侵入,或法律框架下的犯罪,更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对人格的羞辱,对人基本权利的侵犯,一种权力暴力。这不是一件只有当事人和警察才可以参与的正义事件,强奸文化里他人的默许即纵容,让女性成为孤岛。尤其是过去多年有所成就的且常常自我标榜价值观的大公司,在追逐发展速度与市占率之外,应该负担起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标准中的性别平等,并不是每年一度的社会企业责任报告才需要考虑的漂绿性的装饰工具。促进职场中性别平等,反思和纠正不平等的性别文化,消除职场霸凌,需要公司组织和管理的改变。这场变革需要决心,更需要行动。
性与酒——职场性别霸凌的权力道具
不同于其他情景下的强奸或性骚扰,职场性骚扰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性霸凌和性侵犯发生在广义的工作场景,行为主体来自雇主、上级、同事甚至是客户。正是因为职场的利益相关和工作关系的叠加,职场性骚扰分为利益交换性骚扰和敌意性的性骚扰。根据当事人的自述,她冒着台风匆忙参加的这个酒局前,她的领导王成文这样向客户介绍:“给你们‘送’来一个美女”。这正是利益交换性的性骚扰典型,她被当做取悦客户的存在——一种有利可图的性资源。女性仍可以是职场中的性猎物,是供观赏的装饰品和男性团队战利品。
职场性别歧视,甚至在工作开始之前就发生了。百度、阿里巴巴及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多次在招聘启事中表示公司里有“漂亮妹子”作为吸引(男性)人才的噱头。与一般职场刻板印象中的男上司和女下属、男老板和女秘书类似,互联网科技巨头中也衍生出一套刻板的性别印象。与男性气质对应的理性的、主导性的技术岗和与女性气质对应的感性的、辅助性的其他岗位,构成了以男程序员为中心的职场象征暴力,边缘化了在科技行业中的女性,而这又是稀松平常的行业氛围。2015年阿里甚至在招聘出现了“程序员鼓励师”的职位,工作内容基本是,相貌姣好的女性取悦不善社交的程序员,甚至为其放松按摩。其他岗位招聘条件中的“不要女性”和“只要形象气质佳”同样是性别歧视这枚硬币的一体两面。招聘条件的性别化描述和岗位性别身份的设置,更是固话了性别刻板,成为助长性别歧视、滋生职场骚扰和性侵的温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嫌疑人个人的责任之外,大公司的工作制度和文化氛围难逃其咎。
大家也已经普遍地意识到,劝酒行为是一种权力确认和意志倾轧的行为。酒桌中排资论辈的仪式和强迫意愿的劝酒,构成一种隐形的暴力。劝说-服从的行为模式,制造出了角色的落差。不论是甲乙方关系、还是上下级关系,都可以通过酒杯的高低,饮酒的次序、酒量的多少来具体表现,几乎是一个可以精确量化的权力构造的过程。顺从的一方在这样的互动模式中表现了自我意志的屈服,强迫的一方通过优势地位的主张再次确认了这种断裂。尤其是在醉酒、出丑、抓住把柄的基础上,共谋的心理基础为建立了类似“结党”的信任基础。这也可以解释一群男性一起羞辱、伤害或者侵犯女性会加深他们之间的连接的心理基础:正常条件运转失灵的时候,越轨而不受罚的共同经验或体会,可以产生权力能量。
酒精和性都是职场暴力的最佳工具。充满了色情和性意味的破冰活动、对私生活强迫性的刺探询问,和酒桌规则一样构成了隐形的暴力侵犯。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规则、要融入合群与取悦的氛围,实际上也构造出场景性的环境压力,为意志或身体侵犯制造了绝佳的机会。权力关系的差异构成了权力控制的基础和确认以及巩固权力的欲望。施暴者违背个人意愿侵入私人空间,通过对感情、身体和理智的故意侵犯,验证权力下的服从性。职场性骚扰或职场性剥削的特殊之处在于,工作带来的利益相关与性别权力不平等相互叠加。这是为什么破冰活动和酒桌饭局往往是职场性别歧视和针对女性的职场霸凌的重灾区。
对酒桌文化和破冰活动的反思是十分珍贵的。暂不论是为了公关还是为了真正改变,6000名阿里人关于此事的联合倡议中所提倡的几点,仍然是目前比较具有可实现性的一个小进步:杜绝破冰团建业务中的涉黄言论和游戏,禁止强行劝酒陪酒的行为。但职场暴力远远超越了劝酒文化和破冰活动。在王成文劝酒强奸的行为之外,那些无动于衷的中层,已读不回的人力资源和“不招女生”的解决方式,让人大跌眼镜。当事人受到侵害后在内网投诉无门,甚至被移出群聊,被逼无奈在食堂发传单时甚至被保安威胁。这一系列操作处理的结果,都让众人感到“没有人性”。那么,大公司是如何丢掉人性的?
绩效暴力——“猎犬型”阿里人的冷漠
在阿里巴巴,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关键词,也是内部成员引以为傲的驱动型管理方法。根据周勇等人对阿里文化的总结,阿里强调激情的工作氛围,借助武侠中的“六脉神剑”、“九阳真经”和其他通俗文化等概念传播价值观,与业绩表现一起构成员工的绩效考核,形成一种顾客至上、市场导向、自我成就的氛围。根据刘春花等人的描述,早期阿里员工通过考核被分成四种:一是有业绩但价值观不匹配,被喻为“野狗”;二是价值观匹配但无业绩,被喻为“小白兔”;三是业绩与团队精神并存,被喻为“猎犬”,即“阿里人”;四是价值观与业绩分值都低的人,是被淘汰的对象。在阿里巴巴,“野狗”和“小白兔”都要自我调整,以成为真正的“猎犬”型阿里人。据一些员工描述,价值观绩效考核在过去几年比重逐渐减弱,较重要的还是业务考核。
结合财经类媒体对阿里淘鲜达业务和线下零售、本地零售的情况总结,性侵事件暴露出的阿里价值观滑铁卢的其他背景信息变得愈发清晰。作为阿里系内部相对边缘的业务条线,淘鲜达在同城零售的行业中排位也不高,远屈居于京东到家、美团等对手之后。竞争激烈的线下零售业务拓展需要争取商家:嫌疑人王成文正是想要利用女下属取悦客户。“带兵打仗的事业群”是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阿里味的阿里人”则是一种高认同的文化倾向,两者结合,形成了一种积极投入工作、保持野心,追求卓越的气质主体,也强化了张扬感情、男性化,江湖化的企业家式的社会性别印象。表面上,江湖儿女,不拘小节,搂搂抱抱,开个玩笑。实质上,台风天也一定要从杭州赶到济南的“鸿门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权力和性别的陷阱。王成文以工作之名压迫,当事人迫于工作的压力出席,这价值观服务的仍然是看似无可厚非的工作绩效,却滑坡于性侵——我们正处在一种普遍的绩效社会中。父权制的文化与绩效暴力的合体,而绩效暴力是一种更加隐形而难以驯服的职场暴力。
这与近年来商业环境的风向不无关系。扩张期丰厚的经济回报让人们普遍接受超长工作时间;自我激励、高度竞争甚至是平台算法的推助下,劳动者普遍被迫让渡出休假休息,甚至是安全工作的权利。阿里看似扁平但与业务高度耦合的等级制度、引以为傲的996福报工作安排、科技互联网行业中普遍崇尚效率和理性的文化,设置了职场中“绩效高于人性”的常态。这解释了事发之后王成文依然积极活跃工作,甚至参加了字节跳动的一轮面试;已读不回的中层、“不招女生”的P8、食堂中站队打饭对呼告声张的女当事人的冷漠,这些群像正构成了职场人的工具理性——从员工到公司,一整套性别化的组织实体、工作语言和职场行为实践。一个有着基本性别意识和常情常感的人一定会对13天都无法得到处理的强奸指控表示质疑,但一个夹缝生存日常甩锅的社畜一定能明白为什么如此激烈的行为鲜有人理睬——职场性侵与相关责任,在公司现有的绩效系统中没有明确的职能分部。当事人都在逃避,那谁来背着个锅呢?
绩效暴力的表现形式也不一定是性别化的,另一些职场不公正并不以强奸这一高度道德越轨的方式出现,也因此更少收到关注和纠正。根据另一个微博账号CarrieWanshunl的自我讲述,这位女性在17年入职阿里,在上班途中腿部摔伤,但是上级依然不允许她坐着开会,也不允许请病假,甚至威胁辞退让她休长假不要再来。此外,绩效暴力的受害者也可能是男性,绩效异化的极端效果在外卖骑手身上变得尤其的明显。同时因为新经济下新的工作方式,鼓励吃苦、勤奋和积极性而被内化成个人能力的隐形暴力。平台系统的终极目标就是绩效,一种根植于算法和制度性的设计的暴力,劳动者自身也更是这一类暴力的终极受害者:“困在系统里的人”。
劳动者的普遍权利正面临着现实社会处境的不断压缩:平等就业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安全工作的权利等,在过去几年甚至存在滑坡。因为疫情、国内外环境等客观原因,职场性别歧视愈发普遍、996福报也带来了“内卷”和“躺平”的讨论,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基本权利面临着不同的风险。而女性劳动者,在劳工和性别身份的双重交织下,本就面临着公/私领域中家庭和职场的双重结构压力。性别歧视、强奸和性侵事件在职场的发生,加重了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边缘化和不利地位。艾丽斯·杨(Iris M. Young)曾经指出了压迫的五个面相:剥削、边缘化、无权、文化霸权和暴力。这种不利地位与女性的身心在职场中所经历的控制权的异化和丧失,恶性循环互为因果:首先,她因为身为女性而难以得到能力的认可,成为职场中边缘的依从客体。而被侵犯的女性甚至要经历完美受害者审视,她是为了勒索还是为了成名?长得好看是太骚活该被侵犯,长得太丑则是丑人多作怪……性别暴政中对女性的物化,更是在文化和道德上进一步的贬低女性,以建立起权力依附,通常是男性依附,和从属的身份秩序。

6000人联名倡议书,一个可能的起点
职场中的男女有别、上下级和甲乙方的交叉格局,创造出了一整套连续而有差别的权力的离心力。处在中心支配地位的权力主体(通常是男性)通过强迫性交、强迫喝酒,矮化、贬低女性或底层员工的偏执举动,来确认这种统治和支配地位。男权社会更是利用职场的业绩规则、酒精等道具,继续发挥一种意识性的威慑,其目的在于宣布男性或上层的特权,威胁并实施暴力,把侵犯作为实现性别霸权意志的行为。从历史的客观来看,部分底层也会产生对权力依附的向心力,服从与归顺,依附与献媚,自我贬低和自我怀疑的挣扎,是职场人常见的两难境地。但是,打破职场性别暴力的历史序幕已经拉开,在过去数年,从高校到职场,从家庭内部到公共生活,反性侵反家暴的声浪一层高过一层,女性在不同的阵地开始了对性别霸权的反抗。反性侵成为过去多年来频繁出现的热题,性别平等的理念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女孩们尚未迎来性别正义的胜利。
反性侵的维权过程,往往严重依赖当事人在互联网的主动曝光或借助媒体求助,也常常是死胡同之后的无奈之选:投诉、报警,或许在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有效的求助渠道。事件发酵的路径也严重依靠网友的传播和推助。近年来,与女性主义觉醒中的身份行为和泛化的性别伦理标签一起,性侵案已经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种经验主义的网络应激反应,会很快上升成“舆情事件”,迎来警方的介入。“舆论”驱动“法律”的模式不断重复。也只有到公权力介入的这一刻,才正式进入合法的程序。
同时,“舆论权力定案”的模式也有许多负面,因为速朽的舆论场里也往往充斥着荡妇羞辱、完美受害者审视、 “想火”等别有用心的构陷和猜测,当事人要接受严格的舆论审查,往往构成二次伤害。从刘强东明尼苏达州事件、鲍毓明事件、到刚刚过去的吴亦凡性侵、还有一些僵持数年仍然悬而未果的案件。这样的事件在网络上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是相对稳定,但现实案件中具体情况的差别,或由于剧情反转、证据的缺乏或损失、舆论的热点的转移,以及利益相关方的潜在钳制,结局却不尽相同。
更残酷的现实是,不论是法律本身还是职场,我们鲜见“制度性的改善”。吴亦凡事件虽然呈现出了东窗事发、明星落马的难得结局,但娱乐行业等团体能做到什么程度的反思和警醒尚不可知。除了大快人心的事后追惩,我们的处境鲜有改变;我们仍被当做热度数据和冲榜的工具,是潜在可收割的消费者,是家庭幸福生三胎的责任所在,在职场中更是人力资本、被归化成市场指标。现代商业给女性描绘了“勤奋工作+幸福家庭”的理想幸福的目标,但本质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种性别化问题的设定中,它更是一个现有经济秩序性别不平等给的陷阱。强奸文化正镶嵌在这样的经济秩序中。男性也并不是这种经济秩序的绝对受益者,底层男性同样被排除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外,成为被剥削和压迫的对象。
一家大公司人力管理和制度章程的改变或许是迈向更平等的社会的一小步。请不要让阿里6000人联名倡议书变成空头支票,我们急需兑现其中提出的各项女性员工职场反省骚扰、反性侵制度,也相信商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除了指望大公司的反思和自我进化,在职场增加性别平等、反骚扰的培训内容、建设畅通的投诉渠道外,我们更急迫地呼唤法律和制度能够紧跟上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我们希望社会第三方倡导组织能够有机地发展,对这样的议题有合理的议事空间,和真正独立而不受利益侵染的媒体一起,对扩张中的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我们更需要学校能纳入开明平等的性教育,公权力有快速反应、专业且没有偏见的警察和司法程序,社会福利组织能够提供及时的救助和支持。我们希望再无性受害者,性侵和强奸的罪例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彻底“清零”。
参考文献:
- [美]苏珊·布朗米勒, 违背我们的意愿,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4
- 周勇,陈柳青.价值观考核在组织绩效管理中的应用——以阿里巴巴为例[J].领导科学,2014(23):44-46.
- 丁启明,章辉.职场性骚扰与女性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J].行政与法,2014(07):101-106.
- 乔·里特尔,吴万伟.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J].开放时代,2014(03):104-122+6-7.
- 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J].开放时代,2012(12):98-112.
- 唐有财.中国城市职场的性别不平等:基于权力的视角[J].妇女研究论丛,2011(04):20-26.
- 孙亮洁,刘明明.论齐泽克对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的批判及对共产主义的辩护[J].天府新论,2020(06):10-19.
- 财新, 原瑞阳, 阿里涉嫌性侵员工被辞退同城零售总裁等辞职
JK制服风波:“又纯又欲”矛盾统一背后的意识形态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澎湃思想市场 2020-08-02 11:44
“又纯又欲”的矛盾背后,是免于被偷拍、被窥视的消极自由和着自主地展示身体的积极自由的权衡。JK制服文化要达到性别脱敏,更需要那些偷窥的人放下手中的镜头。

文丨侯奇江
7月末,上海举行的CP26漫展流出了一条视频。视频中,拍摄的女子指责镜头中身着JK制服的女生动作不雅,并呼叫保安。这一条视频立刻引爆微博等社交媒体,先是激起了JK制服文化群体的对女主不雅姿势的讨伐、随后女权主义者们提出性感无罪、穿衣自由的主张。对于在公众场合什么是合适的拍照姿势、如何展示自己的争论此起彼伏。
JK制服“又纯又欲”的矛盾统一是有其历史渊源为基础的。统一的校服制服与女生叛逆风潮,发芽自日本社会结构变迁的土壤。只有追溯JK制服文化形成的根源,才能理解软色情的越轨行为和反色情的高道德标准是如何激烈地并存于该文化中。
本文通过将JK制服文化视作一种逐步壮大的、跨国传播的少女意识形态,揭示JK制服群体展示的性别和身体焦虑。在武断地对年轻人进行世代指责之前,我们要看到青年流行文化中更多所谓保守和退步的现象,来自于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悲观预期和在此基础上的日益严重的性别剥削。尽管女性同时面对着消费和性别的双重困境,但其产生的妥协和抗争仍可以在不同语境下形成突破,打破亚文化被商业收编的循环。实现性别平等和穿衣自由,需要JK制服圈之外的人的认识和理解,更需要超越圈子、性别和年龄的合作。
JK制服的历史:叛逆的裙底
JK制服的本源,是日本女高中生校服,它是制服大国日本形色各异的制服的一种。二战后军事上的失败和现代化的社会转变,让日本人有普遍的焦虑和不安。工作着装和职业制服对应着社会角色、职业道德和团体精神,进而形成了具有统一感、纪律感与秩序感的日本制服文化。通过服装的统一,日本人找回了集体带来的安全感,找回了民族和身份认同,于是他们疯狂热爱穿制服。换言之,日本人有深重而复杂的制服情结。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各个方面试图模仿欧洲发达国家。日本校服学习欧美,带有正装色彩。另一方面,呼应着战后遗留的尚武思想,日本高中校服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军装风格。现在经典的水手服元素,也是改良自英美海军水手的军装。
转折点发生在1965年,日本开始推行制服自由化,这意味着每个学校可以个性化定制校服。校服好不好看甚至一度成为日本学生择校标准。虽然学校定制校服自由,但对学生如何穿着打扮仍有严格要求,比如不能化妆、限制袜子颜色等。此后,随着日本1970、80年代的经济腾飞,人们的钱包富足起来。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喜爱也激发了青春少女想要展现性感气质、打破统一着装、张扬表现个性的愿望。JK制服的红杏也伸出校园的高墙,来到影视和杂志中。经过一系列女明星的演绎,日本掀起了所谓的不良少女浪潮,催生了丰富的校服文化。校服经过无数改良,分为日式诘襟和西式制服。如今以西装外套、衬衫、百褶裙为主,搭配领巾、领带、制服鞋等配件。
发展至此,JK制服在文化上完成了流行意义的转变。“洋为日用”的西方个性意识和反叛的色彩一度浓厚。高中时期的少女们又正好处在从学生小妹走向成熟女性的交汇点,不论是出于叛逆、还是对身体的表达,少女们不想再服从于千人一面的集体训诫,开始解开扣子、把上衣或裙子变得更短、夸张地堆叠起堆堆袜,以彰显自己的个性。一位00后JK制服爱好者小林(化名)告诉我,在日本,一些裙子加长直到脚踝,是为了藏匿违禁物、方便打架。这一种裙子直接被命名做“不良JK”。
所以,经过“考据”,本着一种玩笑上的原教旨主义,流行JK制服的底色是青春洋溢的,但更是性感而有力量的。否则,它就和星巴克服务员的制服一样只具有职业/社会角色的功能,再好看也没有人辞职了还想穿,穿了之后还想拍照上传社交媒体。
JK制服在中国:营造稀缺感的商品
中国JK制服女孩大多没有动机去追本溯源研究日式格子裙的文化历史。在她们看来,选择JK制服是一种清纯可爱的时尚选择。大家更多在乎商品意义上的“正统”。中国JK少女的快乐是消费主义之神赐予的:繁多的花色和种类满足了收集癖;付钱后收货周期可以长达数月甚至一年,说明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延时满足品;绝版裙更是圈内公认的流通期货,炒作后咸鱼高价卖出可以带来额外收入——它成为女孩们的投资理财佳品。男人炒鞋有“鞋王”。或许有一天,中国女孩炒裙会诞生一代“裙王”。甚至诞生一本畅销书,《裙狗》。
商业对JK制服文化的收编是成功的,女孩们认同的逻辑亦简单粗暴。在JK制服圈内,存在着“日本校供”>“日本设计/制造”>“中国原创设计/制造”>“山寨”的鄙视链。“校供”是指真正的日本高中校服,大多是学校学生在毕业后作为二手商品售出。这种校服是JK制服圈的“黑胶唱片”,因为原汁原味、保真、复古,在圈内最受追捧,需要购买者具有辨别真假的慧眼,一些鉴别技术已经接近玄学。除了夸张的溢价,也需要付出相当的耐心,付款收货周期最长。
其次是日本生产的JK制服,售至中国因成本和关税也相对较贵,收货同样较为漫长。再次是物美价优的中国产JK制服。为了尊重IP,售店需要得到其设计师画手的授权,设计溢价高。店家也常常玩弄饥饿营销术,限量出版。“长达六七个月等待更是对裙子的普遍真爱”——它绝不是快时尚与春花秋叶一起变换的应季商品。随着JK制服的普及,以及JK制服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经济尚未独立的学生,JK制服中穿国产正版的女孩人多量大。且近期风气变换,国潮改良兴起。相比日产,国内生产更迎合国内审美,中国制造或许不再是个缺陷,中国产JK制服也被广泛接受。
身为JK制服女孩,到底意味着什么?另一位身在多个QQ、微信JK制服群的99年出生的朋友告诉我,她已经有了近50条JK制服裙,这在圈内并不算多。尽管有了这么多JK制服,但这仍然是一个充满稀缺感的游戏。身为JK制服女孩的日常,一小部分是穿上JK制服,亲自展示;而更多的是为了拥有和收藏。她需要在手机上守准时间,抢购不同的裙子;她观战过好几次店家超额售出限量裙后被不满的小姐姐破口大骂的混战;也围观了多次声讨抄袭店家、穿假货者的事件。“我自己有日供,也穿国产原创,但我不会穿山寨。我觉得在圈里,穿日供的人的确更有优越感,但穿国产的女孩越来越多,大家也就不在乎。”

JK制服女孩之中的底层是那些穿不起昂贵制服而购入仿版、山寨裙子的群体。在动漫JK制服女主被拍事件里,女主角受到很多“穿山甲”的指责。“穿山甲”是对山寨JK女孩的轻蔑指代,同样适用于汉服和洛丽塔服饰。这位JK制服女主更是经历了铺天盖地的攻击性侮辱,“穿山就是鸡”的圈内话术,赤裸裸地展示了这种商品内在的逻辑。
“又纯又欲” :亚文化的融入与冲突
如果说JK制服在日本完成了演变和发展,因其独特的风格形成一种颇具辨识度和规模的青年文化。那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它依然带有强烈的母国色彩。以互联网作为主要传播途径,以青年群体为主要传播对象,JK制服文化在接触主流文化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其群体内部出现了对色情议题态度截然不同的两极化现象。
一方面,它不可言说的冰山下的“色情制服”想象,俘获了男性观众;校园风水手服作为一种符号,被色情娱乐商业裹挟、强化。在色情或软色情行业里,JK制服成为一种性暗示,把女性置于一种低龄的、学生的身份客体中,不论是高高在上的虚拟制服少女偶像,还是被压在身下的女学生被侵犯的色情剧情,都迎合了以男性为主要群体的受众。尽管非色情娱乐业里也有大量以穿着JK制服的高中生为女主角的动漫、影视作品,但令人惋惜的是,其中对集体的反叛和个性、自我表达的深层次含义,无力抗衡更容易吸引眼球博取注意的色情内容,无力争取更多的流量和曝光。叛逆与个性消解在流动的跨文化传播中,几乎弥散不见了。
在漫展事件中,录像拍摄者在高声呼叫保安后说,“你在外面搞这些动作,不要再给JK抹黑了谢谢。” 这句话背后,也反映出JK制服文化在中国所承受的“福利姬”阴影。福利姬,通常指穿上动漫服装、制服等,拍摄大尺度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售卖借此牟利的女孩。目前虽然缺乏该灰色产业规模等详尽数据,但其严重程度已经引起了全国政协常委的注意。根据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甄贞于2020年6月发表于《人民法院报》的评论,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我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25万人,其中,通过社交工具实施的未成年人网上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主要的犯罪形态之一。文章援引新华社的报道称,“福利姬”成为“未成年人援交”的替代词。文章更是尖锐地指出,此类犯罪形势紧迫,性质恶劣,给未成年人带来了网络欺凌、网络色情、网络诈骗、网络沉迷等方面的风险。
就此,此次事件后关于JK制服圈内部讨论男性凝视与女性的迎合凝视、物化女性和女性的自我物化,是非常有价值的质问和反思。
另一方面,JK制服提供了清纯的形象,收获了一群圈外女性买家。JK制服文化经历了一番改造,在保留其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上衣和裙子变得更长,更宽松,遮盖曲线,避免露出更多皮肤。这样的JK制服被重新定义为清新、温柔、青春、可爱——这是风格的权宜之计,更让许多女孩认为,JK制服是一种时尚的日常着装。改变后的JK制服合理地在电商和社交平台推广售卖,某些单品甚至产生了忠实的粉丝群体,衍生出偶像人格。

2020年7月25日,CP26动漫游戏同人展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现场人气火爆。JK、制服、洛丽塔装店铺在本次展会中也占有很大比重。
身穿改造后JK制服的女孩,为了被圈外常人所接纳,摆脱异样的眼光,就要剔除叛逆的性别表达这一“原罪”。这也是是JK制服亚文化想要被“正常化”,融入社会主流的直观体现。于是,她们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圈内道德标准,除了在购买行为中追捧、强化日供和原版衣服,排斥穿山寨的行为,还猛烈抨击穿衣者的“不检点”,认为色情擦边球的伤风败俗会败坏整个JK圈的名声。这种“不要山寨要正版、不要性感要纯洁”高道德要求的、在网络世界里极具攻击性的人又被称为“JK警察”。这构成了一种网络现象:JK制服女孩除了“买买买”之外,在性别表达方面表现保守,激烈地与“福利姬”划清界限,强烈要求“去性别化”。
不难看出,JK制服文化的发展过程,是其意涵不断重置、界定的反复循环。“清纯”与“欲女”虽说是此消彼长的冲突,其定义、解释和演绎,却被牢牢地掌握在商业力量的手里。当色情行业需要需要水手服满足男性性欲,那么它就是情趣制服;当二次元服装业需要满足清纯少女的消费欲,那它就是清纯的、日常的、安全的。水手服格子裙只需要稍稍改变细节,便翻手为“纯”覆手为“欲”,形成 “又纯又欲”的矛盾统一。
本质上,水手服、格子裙作为风格和符号,也只是被牵线的木偶,而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才是真正能够下定义、给答案的操纵者。不论是色情变得纯洁,还是欲望变回清纯,对于商业资本这个多面手而言,这都是收编亚文化“双管齐下”的法术。稍有区别的是,色情行业是色情商业征用女学生校服这一符号,而收编JK制服的结果;而JK制服的清纯化,则更是它为了融入主流改弦更张、积极“归顺”的结果。
但随着JK群体的扩大,文化上JK制服“又纯又欲”的一体两面无法永远回避其本质的矛盾——在动漫展这个场合下,举着相机镜头的偷拍男性,便遇上了举着手机录像的“JK警察”,矛盾尖锐地爆发了。而那个穿着安全裤趴在地上的女主角,恰好站在了这一冲突之间。是她主动迎合男性凝视、还是被动遭受偷拍?虽然她处在这一文化冲突的焦点、处在社交媒体的聚光灯下,但她的主观意愿已经不重要了。哪怕是提前穿了安全裤,她作出的在时装大片、影视、商业广告情境下屡见不鲜的跪趴撅屁姿势,被放到漫展一众镜头下,打破了JK制服文化“清纯-性感”平日里并不直接对立的平衡。结界被打破了,导火索就这样被点燃了。
“姐姐来了”:撅屁股的合理性
在公众的讨论初始,“公共场合搔首弄姿、故意被偷拍”的批评声是讨论的主调。由于批评中带有大量的人身攻击,一些污言秽语来自女性。不少人感慨,只有女人对女人最狠。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好女孩”与“坏女孩”的割裂。随着事件更多信息的流出和女主角的说明,JK制服之外,很多女权主义者发出声援,强调“我能骚,你不能扰”,“穿衣自由,性感无罪”的主张。其他种种讨论,思路发散,不再一一枚举。随后,许多JK制服或动漫圈内人指出女权主义者的辩护是转移焦点。不妥姿势和不雅举动的指责是基于漫展这一公共场合的规矩,与性别无关,更无关女权。
这种否认带来了一种青年文化更加保守的表面现象。在商业广告、动作影视中都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拍照姿势,何以成为不雅、不妥、伤风败俗?原本应该挑战社会陈规、打破刻板印象、追求多元尊重的亚文化,何以比普通文化更加保守?表面看来,社会文化中主导和支配力量令人困惑地倒错了。而实际上,矛盾是重合的。
JK制服群体本身是以年轻女性为主要对象的,JK制服女孩对“福利姬”的道德恐慌,显然是以男性色情消费带来的性别歧视为基础的。与此类同,在COS世界里,反转性别角色的演绎者承受着一样的眼光。他们让人联想起同性恋、制服癖、BDSM等等。亚文化产生了交集,面对同一种凝视、同一种困境。而一个普通女人,即使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在茫茫人海中最不起眼,也会面临着这种凝视。JK制服文化拒绝打色情擦边球的愿望并非空穴来风。抗拒一种被性别化的身体,进而形成自我审查的做法是较为生疏和稚气的处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女权主义者们“姐姐来了”的声援抢过了JK制服圈内人的话筒,也改变了谈话的走向。如何做对抗?在这对抗后的“穿什么的自由”和“不被看的自由”是一体两面的。不论穿什么,女性共同体都想要珍惜、维护展示身体的积极自由,也要争取免于被偷拍和窥视的消极自由。维护这两种自由绝不是通过让出更多的空间和自我阉割而实现的。
所有亚文化突出的矛盾背后,无一例外地都体现着更大的社会不公。对于JK制服而言,它原本在抗衡的是集体的规训压迫,而现在则面对男性凝视背后的性别不公、贫困与消费剥削的联合收缴。除了在来源地日本有着挥之不去的色情阴影, 在中国,网络售卖JK制服大尺度照片的灰色产业链时隐时现。援交、福利姬和色情擦边球这样的威胁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但一味地指责色情,并不是解决JK制服引发的道德恐慌和文化冲突的终极答案,更无法达到解决青少年援交问题的目的。
以日本为例,日本虽然已经踏入发达国家行列,却面临着隐形贫困大国的困境。虽然近年来中产阶级看似富裕,实则处于相对贫困的边缘。自2000年以来,日本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5个成员国中唯一工资负增长的国家。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日本20岁至64岁的单身女性有三分之一处于贫困状态。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家庭标准户为单位,而不保障单身、离婚女性这样的个体。高昂的教育成本,合法的低门槛的性服务行业,导致很多走投无路、没有家庭和政府支持的女学生为了生存放弃“骄傲”。她们不愿意成为 “现役世代”,不愿意被有劳动意义但低回报的行业榨取价值,转而投入风俗业。
简言之,日本援交女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经济拮据、职场挤压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导致的。清纯或是性感,女孩何以成为这一种女孩而非另一种女孩,在功利论上推测某个个人的动机是无效的;而作为一个群体,看似自主选择的风格,仍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JK制服文化作为一种少女的意识形态,也展示出了这种矛盾。这个群体已经通过强化或者排斥特定的行为,例如购买、穿戴,形成自己的风格,构建自己的身份,连接彼此。而偷拍者不需要JK制服才会举起自己的相机。
在中国,互联网屡禁不止的福利姬和卖肉现象,有待更深入和更严肃的研究和调查。但不难想象,这一完全处于地下边缘地带的产业链背后,其生产手段和服务对象是男性主导的。至于中国新世代青年如何实现性别平等和自由,仍是一个敞口的问题。免受侵犯的消极自由、和自我主宰的积极自由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共同进退。如何实现它,不仅仅是JK制服群体如何融入主流的问题,不仅仅是青年如何让上一代人接纳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
(感谢金晶对此文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黎梦觅. 二次元元素在日常化服装设计的应用研究[D].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8.
[2]申莉轩,杜少勋.浅议日本的制服文化[J].新西部(理论版),2016(02):139-140.
[3]吴斯.消费社会与亚文化风格的互文谱系——基于“软妹”服饰文化的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6(01):90-96.
[4]卢鹏.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J].青年研究,2014(03):84-93+96.
[5] 陈立雄. 特稿|隐形贫困大国日本:中产的塌陷. 财新网. 2020
[6]甄贞. 防范查处网络社交平台涉未成年人犯罪[N]. 人民法院报,2020-06-05(002).
疫论·性别|降薪失业、以性换租、照料惩罚:疫情下的全球女性贫困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澎湃思想市场 2021-02-03 17:11
在外职场歧视,在家“照料惩罚”,性别不公从根本上镶嵌和运作于“家庭-劳动市场”公私两个领域。疫情之下女性多维度的贫困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文| 侯奇江
“我别无选择。”根据路透社2020年4月的报道,一位英国的单身妈妈在疫情期间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当房屋的物业经理一边威胁她,表示要让她失去房子时,却也提起了“以性换租”的无理要求。该女性在英国公平住房联盟(National Fair Housing Alliance)网站上的播客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经历。“如果我不和他发生关系,他就会把我赶出去。”
同是2020年的4月,日本宣布了居家隔离的防疫政策。根据日本《周刊文春》的报道,由于疫情,一名叫做牧野和男的59岁男性公司社员收入锐减。4月5日,夫妻俩在家喝了5个小时的酒,妻子不断抱怨丈夫“挣得太少”。最终,失控的丈夫将妻子殴打致死,结束了两个人近三十年的婚姻。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个小镇Metema,许多做服务员或家政工作的女孩因为疫情被解雇。她们无奈转而从事性工作,否则,她们就只能回到村庄被迫嫁给年长的男性。疫情使许多家庭陷入贫困,女童面临着更大的童工和早婚风险。一个女孩甚至从11岁就开始卖淫。该镇管理劳动和社会事务的小组组长向路透社表示,超过一千名妇女在该地区从事卖淫工作,其中约15%是未成年人。
从英国、日本到埃塞俄比亚,她们只是成千上万个被疫情改变命运的女性的缩影。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与我们并存一年之久。出于隔离的防疫需求,许多城市经历了封城或宵禁,许多家庭被迫隔离。疫情不但造成了难以预计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对公共健康和卫生系统构成威胁,而且引发失业危机和经济滞缓,揭露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系统的脆弱性,强化了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在过去的一年里,疫情影响了每一个人,但对每个人的影响却不尽相同。老人比年轻人更加脆弱,穷人比富人更容易暴露于病毒之中。根据报告,从纽约最富裕的社区到最贫穷的社区,核酸检测的阳性率从35%上升到62%,美国40个州的数据表示,黑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比白人高2.4倍。而涉及到性别,虽然男性更容易感染,感染后死亡率稍高于女性,但女性受到新冠次生灾害的脆弱性更明显。不同人群不成比例地受到疫情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伤害。
疫情更像一枚棱镜折射出性别与贫困的复杂关系。封锁状态下,女性更容易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她们在家庭和护理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偏高,现在又增加了。女性大多从事不稳定的、容易暴露于病毒的行业和领域工作。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0年,疫情使4700多万妇女和女孩的生活状况降至贫困线以下。按照目前通用的世界银行关于绝对贫困的标准,收入低于1.9美元/天即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则是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一半。在2021年,全球可能将有4.35亿妇女和女孩陷入极端贫困。2021年,在25至34岁的极端贫困人口中,男女比例为100:118;预计到2030年,这一差距预计将扩大到100:121。
本文总结过去一年中疫情引起或加剧女性贫困的一些突出情况,重新审视疫情所暴露出的社会不公和性别不平等。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阻止疫情带来的性别平等的倒退和女性经济水平的降低。有必要指出,本文所讨论的贫困也不仅仅指向“收入/消费”的单一维度。贫困同样是就业机会、福利保障、身心健康和安全的缺失。疫情不但带来了健康贫困,它次生的失业、家暴、性和生命安全的威胁,都是贫困的不同内涵和维度。
性剥削:贫困滑坡的性别陷阱
在疫情期间,女性贫困一种特有的性别现象是性剥削的加重。除了文章开头提及的英国的“以性换租”的单身妈妈,在美国,类似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夏威夷州妇女委员会(The Hawaii State Commission onthe Status of Women)的议员Jabola-Carolus对NBC 新闻表示,疫情期间她收到的房东性骚扰房客的举报比她在此工作的前两年都多。这些投诉中,许多房东都是在房客面临失业和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提出了性要求,以减免房客的房租。在以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夏威夷,疫情不仅仅使人们的收入锐减、失去工作,新冠病毒又不得不让人居家隔离——这些情况为房东创造了性侵的绝佳条件。印第安纳州也有类似的案例。2020年4月,美国大约有50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失业总人数接近2200万。虽然一些州颁布了暂缓房租的救济政策,但还不足以让中低收入的租房者有栖身之所。根据美国多户住房委员会(the 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Council)的数据,在2020年4月5日前,只有69%的公寓交了租金,而前一个月为81%。
房东滥用经济优势和疫情,利用女性脆弱的生活状况,威胁将后者赶出家门,要求“以性换租”,直接构成了基于经济和性别不对等的性剥削。另一些女性,则是在绝望的情况下无计可施,不得不转向性服务行业。根据英国《独立报》的报道,新冠疫情导致许多女性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从事性工作的女性首次大幅增加。英国支持卖淫合法化的运动组织The English Collective of Prostitutes表示,上百名女服务员、清洁工和美容师已经咨询他们关于从事性工作的问题。
数年前在中国曾经猖獗一时的裸贷也随着新冠病毒“传染”了邻国日本。根据朝日新闻在2020年5月23日的报道,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非法高利贷对失业和停工的女性群体设下不同形式的裸贷陷阱。一些裸贷直接将“性回报”作为额外的还贷需求。报道中一位北海道的女性在旅行公司兼职。疫情收入锐减之后,她无力负担债务和生活费。走投无路的她用裸贷的方式仅得到了30万日元(约1.84万元人民币)。另一些形式的裸贷要求苛刻,除了借款一周就高达50%的夸张利率,一旦延迟付款就会把裸照发布给贷款人的亲友。此外,非法裸贷还伴有诈骗、敲诈和勒索风险。在公开裸照的威胁下,一些还款需要支付远超当初承诺的利息。
社交媒体、暗网等网络平台更是助长了性剥削。根据德国海因里希·鲍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的报告,在俄罗斯,一些视频直播平台中出现了大量针对女性的“低息贷款”,这些贷款要求女性以直播等形式录下裸体或性行为。俄罗斯联邦统计局(Rosstat)的数据显示,在俄罗斯,女性的收入本来就比男性低30%,而疫情打击的又是女性占多数的旅游贸易、餐饮娱乐等行业。经济情况的恶化也吞噬了女性的性安全,性剥削愈发严重。联合国的人权专家小组警告称,无处不在的网络和摄像头让性犯罪更加隐蔽,犯罪者会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精准地寻找弱势群体进行网络性剥削。该小组敦促各个网路平台利用数据和算法识别这些犯罪,消除对女性的性剥削,缓解疫情中的性别人道主义危机。
“直播裸贷”和“以性换租”是趁人之危,更糟糕的是,在日本部分男性还对女性变差的经济状况有幸灾乐祸的态度。根据南华早报4月30日的报道,日本广播公司的一档午夜节目中,一位观众对节目抱怨说,由于疫情隔离要求红灯区停止营业,他无法像平常一样享受按摩或其他成人行业提供的服务。日本知名喜剧演员冈村隆史(Takashi Okamura)在节目里回应说,“新冠疫情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疫情将迫使更多漂亮女孩进入性服务行业,为男人们带来福音。你应该把钱存着。”
此番性别歧视的言论随后遭受日本舆论的严厉批评。冈村隆史本人和他的公司均为此言论道歉。他本人称,仍有很多人正因为疫情而处于水深火热中,而他的言论对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很不合适。不幸的是,冈村隆史的话从侧面反应了残酷的现实:面对疫情带来的恶化下滑的经济,许多女性面对着贫困的生活压力,不得不进入风俗业成为性工作者。
与此同时,在与贫困为伴的性工作者身上,疫情治理更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难题。疫情下的封锁和身份查验影响了注重隐私的性服务工作。病毒让客户失去的信任感,为了躲避检查和警察,一些性工作者迫于生计从事更危险的交易。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性工作者几乎处于“饥饿或死亡”的绝境。一位35岁的性工作者平时只接“快单”,但疫情宵禁的政策让她不得不留一个客人过夜。几个小时之后,她的胸部和腹部被刺多刀,倒在血泊中死亡。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性工作不被认为是一种工作,性工作者被认为更易传播新冠病毒,受到更多的歧视。英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原本从事性服务业的女性,在疫情期间举步维艰。一项对222名性工作者的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的性工作者难以维持生计,十分之三的人难以获得政府的救助。性工作的罪化更让性工作者无法获得政府关于疫情的健康或经济支持,如何保障疫情下的性工作者的卫生安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挑战。

贫贱夫妻百事哀:激化的家庭矛盾和家暴
家暴虽然不是贫困,但却是一种与贫困相伴的现象。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宣布进入隔离或宵禁的紧急状态。保持社交距离,减少外出和聚会等防疫措施改变了以往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也对人际间和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调整。疫情造成的失业和工作压力,让家庭暴露于社会风险之中。作为一个经济单元,家庭整体收入的下降,不但会激化家庭内部矛盾,也日益凸显女性因家庭角色带来的贫困。女性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居家隔离、远程工作的后疫情时代,家庭恐怕不是提供保护和依靠的爱巢,反而是索取精力和时间的黑洞。伤害和暴力更可能来自亲人。
拉丁美洲的性别暴力在疫情期间尤其严重。2020年的前三个月,墨西哥就有约1000名妇女被谋杀,而截至4月底,墨西哥死于新冠肺炎的女性仅为420人。3月中旬到4月中旬,与前一个月相比,墨西哥家暴庇护所接到的求助电话和信息增加了80%以上。公民运动党(Citizens’Movementparty)议员玛莎·塔格尔(Martha Tagle)对路透社表示:对墨西哥女性而言,比新冠病毒更致命是家暴。暴力才是对女性权利的最大威胁。面对家暴,疫情期间的封锁让女性没有藏身之地。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疫情以来,暴力伤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有所加剧,施暴者很有可能利用疫情期间女性出行和工作的限制,进一步控制、伤害女性。2020年6月17日,南非总统马塔梅拉·西里尔·拉马福萨在疫情暴发百日演讲中说,“今晚,我怀着最沉重的心情面对南非的妇女和女童,我要谈论的是正在我国肆虐的另一种流行病——我国男子针对妇女和儿童的谋杀。在过去的数周内,至少有21名妇女和儿童被谋杀。其中包括在昆士敦(Queenstown)和布拉克潘(Brakpan)的养老院里分别89岁和79岁两位祖母。在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一位老妇人甚至被强奸。”如果不算胎死腹中的婴儿,死于谋杀的最小女童才六岁。他说,“作为一名男子、一名丈夫和一名父亲,我对这种不亚于战争的犯罪行为感到感到震惊。强奸犯和杀人犯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的社区里。”
在英国,2020年,仅从3月23号到4月12号这大约20天之内,有16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法国从2020年3月17日“封城”起,截至2020年4月3日,报告家庭暴力的案件上升30%。塞浦路斯、新加坡分别增加30%和33%。阿根廷的家暴增加了25%。报告预计,巴西、加拿大、德国、西班牙、英国等国的家庭暴力也都有所增加。在一些没有及时家暴统计系统的国家,疫情或许会让家暴翻倍增长。同时,各国的证据表明,残疾妇女遭受伴侣和家庭成员暴力的可能性是非残疾妇女的2倍,遭受性暴力的可能性高达10倍。
我们目前暂时缺乏直观的官方数据来观察中国家庭暴力发生的情况。但根据为平妇女权益机构2020年4月的反家暴检测报告,在中国,根据湖北监利和北京为平妇女支持热线的统计表明,2020年1月到2月期间,家暴求助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1-3倍。为平志愿者检索了到2月底为止的疫情期间的家庭暴力案件报道18篇,涉及2人死亡,其中包括两起殴打出警的警察。报告指出,这期间部分地方公安和司法监察机关依然努力通过远程系统等方式干预家暴,但也有地方以防疫为借口推诿家暴求助。
除了直接的肢体暴力,女性也面临居家隔离带来的抑郁等心理健康的问题。在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因为疫情受到了心理健康的影响。上海大学一项覆盖了36个省的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女性受访者的心理困扰明显高于男性受访者,更容易换上创伤后应激障碍。除了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严格的隔离让很多女性在狭窄的生活空间长时间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湖北等中国中部地区的压力水平最高。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平时女性患有抑郁的概率就几乎是男性到底两倍。而新冠病毒带来的文化和经济影响,例如育儿负担、收入损失等,加剧了两性差距。疫情让女性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根据美国联邦疾控与预防中心的数据,2020年4月以来,44%的美国女性至少出现了抑郁或焦虑等一种症状,男性的这一数值为36%。
在日本,“新冠离婚”一度成为网络热词,成为最突出的疫情影响家庭关系的现象。2020年4月日本政府进入隔离的“紧急状态”,随后出现2008年后雷曼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失业潮。同时,很多仍然有工作的人需要远程办公、居家隔离。面对多方压力,家庭中暗藏的摩擦和矛盾就此激化。一个叫做“丈夫死亡笔记”网站日活量暴增,留言的女性纷纷抱怨丈夫的种种居家劣行,甚至诅咒丈夫感染新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王瓒玮指出,根据日本媒体的网络社会调查,40%的受采访者曾在疫情期间考虑离婚。想要离婚的人中,女性为82%,男性为18%,女性想要摆脱婚姻的理由大多和疫情相关:第一,疫情影响了就业市场,造成了家庭收入的下降,“贫贱夫妻百世哀”,双方无法共同抵御经济压力分道扬镳;第二,家庭成员相互传染的恐惧和分担家务、照料等期待,影响了家庭关系的维系;此外,共同育儿、意见不和等情况也频频发生。
2021年《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篇论文分析了日本疫情中的两波自杀高潮。根据公众号“知识分子”对论文的介绍,第二波疫情中女性的自杀率增加了37%,最大增幅约是男性的5倍。家庭主妇自杀率上升了132%,是六种研究职业中增长最明显的。论文分析家庭主妇自杀的原因时表示,居家隔离和远程办公增加了家庭主妇的工作量和家庭负担,而家暴和其他威胁也增加了女性的压力。
家庭角色的困囿和照料的价值剥夺
另一种发生于家庭领域内的隐形歧视和性别暴力,也是让女性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疫情期间,男性和女性的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都在增加,但平均而言,全球女性每天花在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上的时间是男性的3倍,约为4.2小时。在北非和西亚地区,这一差距更大,女性从事这些活动的时间是男性的7倍。照料和社会再生产的性别化规范(genderednorms)降低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将女人困在了家庭无偿的照料劳动和市场非正式的底薪劳动中,形成了“家庭和工作如何平衡”的难题;其次,当疫情这样的社会风险来临时,女性被认为是有家庭兜底的、低产出低价值的劳动资源,成为社会风险中首先被牺牲裁员的对象。
照料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过程。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南希·福布尔的解释,照料常常发生在有感情纽带的家庭成员之间。洗衣做饭准备后厨的工作虽然重复琐碎,却创造了大部分养老、育儿和抚养后代的社会价值。照料是最私人却也是最具有公共属性的劳作。但照料本身很难变成标准化的、流水线的“产品”,更难以明码标价。血缘、家庭纽带和感情关系,也让照料者难以获得直接的、对等的经济回报。“照料惩罚”正是描述这种付出和回报不对等的、照料者的收入折损。在家庭内,它导致家庭内承担照料工作的成员低就业和低薪资;在职场,性别歧视叠加的照料惩罚导致家政、医护中照料的相关工作收入低于其他工作。为了维持老人、儿童的生活需求,女性往往会牺牲自己来达到目的,这种现象也成为了女性疫情期间的“自我贫困化”。
照料惩罚也不仅仅在“惩罚女性”,它同时会造成卫生系统的羸弱。在菲律宾,女性更难以获取医疗保健的信息和资源,有79%的女性受访者甚至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而男性的这一数值为57%。在东南亚,医疗服务点数量的减少对女性,尤其是孕妇影响最大。疫情以前的非洲,女性就长期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而疫情加剧了粮食品短缺和卫生危机、减少了安全的饮用水与卫生服务。根据国际关怀组织的报告,在非洲最容易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行业,如小贸易和初级生产中,由女性为主的行业占大多数。冲突地区的暴力再度抬头,非洲女性的生存面临严重挑战。《中国妇女报》的报道称,考虑到许多非洲社会持续处于欠发达和边缘化状态,而女性本就处于弱势地位,新冠肺炎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非洲五亿妇女的生活。
在对埃博拉疫情的全球卫生治理研究中,关于性别盲视(Gender blindness),照料(Care)和男性偏见(Male bias)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女性在疫情中两难境地:全球卫生系统一边依靠妇女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照料角色中充当免费的劳动力和工具,一边却在政策与实践中忽视女性的需求,让令女性匿迹隐踪。在与流行病做斗争的过程中,性别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附带问题”,但它其实是社会应急和应对能力的本质问题。如果女性贫困和性别问题继续保持隐形,应对致命病毒仅依靠女性坚忍不拔的品质和自我牺牲,这不但会损害女性的健康,打击她们的经济状况,更会让卫生系统继续软弱无力。和埃博拉疫情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对男女产生的不同影响,同样是照料生产和消费生产中性别差异的结果。要减轻“贫困的女性化”,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们提出,无偿的照料经济必须成为政策制定中具有高度显性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终止经济结构性的性别盲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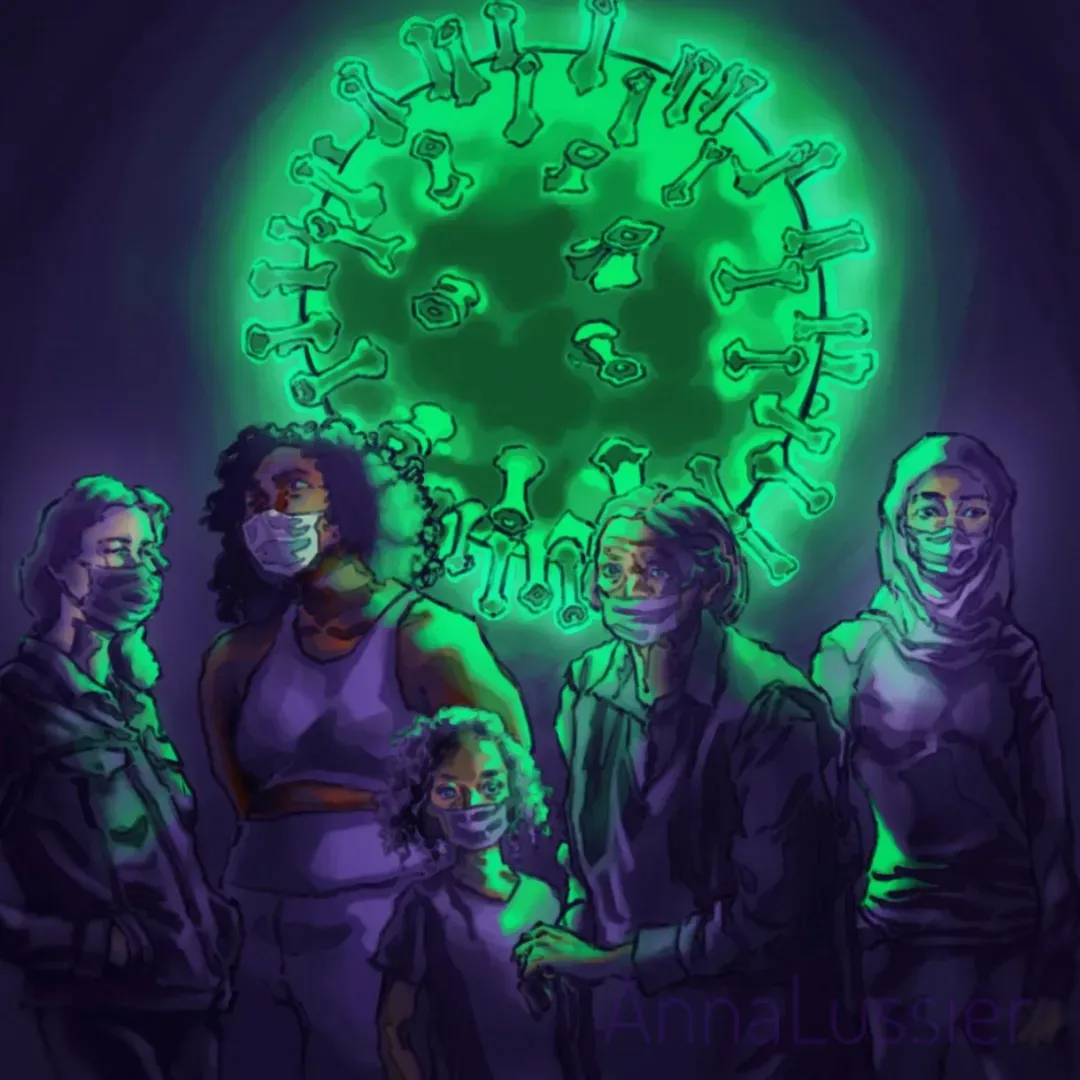
受疫情挤压的女性职场
女性化的无偿照料在疫情的危机时刻是 “缓冲器”,但在有偿高薪的公共领域中成为了牺牲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新冠病毒让2020年全球的全年工作时间减少了8.8%。假设每周工作48个小时,它相当于减少了2.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这比当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损失工时多出4倍。而这些就业损失导致全球劳动收入下降8.2%,这相当于3.7万亿美元,约为全球生产总值的4.4%。
对比来看,金融危机中主要的失业群体为男性,而疫情中的失业群体则主要为女性。在全球范围内,疫情给女性带来的就业损失为5%,男性为3.9%。以美国为例,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与2019年12月相比,美国2020年7月女性工作者减少了10.6%,男性的降幅为7.3%。2020年9月,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是男性的4倍。在尚未实现同工同酬的情况下,疫情更是拉大了相同工作收入的性别差异。
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类来看,女性从业者比较集中的住宿、餐饮服务业也是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部门,就业率平均下降了20%以上,其次是零售业和制造业。妇女占服务业雇员的55.8%。相比之下,男性从业者占多数的是信息、通信、金融和保险业。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在2020年第二、第三季度还有所增加,采矿业、采石业和公共事业的人数也略有增加。妇女在低偿或无偿的再生产性经济中有过高的代表性,但在有偿的生产性经济中却代表性不足。
同时,性别职业隔离(sexsegregation)更加恶化了女性的职场环境。女性被认为是劳动效率低下、缺乏理智和专业性的劳动力,因而不适合做医生、律师、大学教授和技术专业职位,而适合照料的、需要付出关爱和感情劳动的护士、幼儿园老师等职位。这种性别职业隔离造成了两性在经济收入和职业社会声望上的明显差距。此外,即使在相同的工作种类中,妇女在工作场所的职位、级别整体低于男性。在大部分工作领域中,高管、领导层很少有女性的身影,接近60%的妇女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女性主要从事不签订合同,没有社会保险的兼职、低薪、非正式工作,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更容易失业。加上生育和照料负担,母职惩罚和年龄歧视,失业后,女性比男性更难于回到劳动力市场。
抗击疫情最重要的医疗卫生行业就是典型的例子。从全世界来看,女性占卫生部门从业人员的70%,这是女性占多数的行业。但是,医护工作本身同时带有严重的性别隔离。女性被认作是适合专业性较低、薪资较少的护理工作;而男性则是掌握技术的治疗者。“女护士、男医生”的性别划分尤其明显。医院院长、主任和公共卫生系统内的领导层,就更是男性为主的“兄弟会”。这种职业隔离的结果导致了同一行业男女收入的差异。在中国,在线招聘网站BOSS直聘发布的《2020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显示,2019年,医疗业的性别薪酬差异达到38.4%,女性医护收入仅为男性的六成。医疗界的性别薪酬差异始终高居前五位,连续三年都仅次于重体力工业产业。
除了进一步分化收入,疫情增加了许多女性职业的社会风险,更加放大了职业中的性别不公。2020年年初,4.26万名支援湖北医疗人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其中女性护士为2.53万名,占支援湖北的总共2.86万名护士中的90%。来自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最新数据显示,女性卫生工作者中的COVID-19确诊病例比男性同行中观察到的高两到三倍。全球范围来看,工作在一线的女性医疗工作者,比男性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
女性不但作为母亲和妻子照顾家庭成员,也作为医护,照料着疫情下的全社会。但女性面临的职业歧视却并因此减轻。2020年初,中国“剃发明志”的宣传资料夸张地将女性的身体作为动员宣传的符号,但在抗疫成功之后,《最美逆行者》的宣传片却轻易否定了女性所做的实际贡献。剧中,参加抗疫运输队的志愿者全部都是男性。为了凑齐名额,组织者说,“还差一个人,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剧情中男性抢走了“拯救和保护者”的英雄角色,女性又变成了被动自私的客体,固话性别预设的做法引发众多批评。在意大利、新加坡和无数其他国家,都有与疫情有关的女性医护人员遭受人身和言语攻击的报告。
小结
2020年本是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的25周年,全世界的性别平等本应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性别平等的工作反而面临倒退的风险。我们憧憬的性别平等的世界并没有到来——“每个妇女和女孩都可以行使她的自由和实现她的权利的世界,例如生活中不遭受暴力,可以上学、参与决策以及同工同酬。”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履行承诺,完全实现这样的性别平等。
与美好憧憬不同的是,现实是如此的残酷。新冠肺炎疫情是过去一百年内最严重的社会灾难。它放大了各种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瑕疵。从教育、就业到健康安全,女性的发展仍然困囿于性别歧视和两性差异,女性群体的脆弱性尽显无疑。以往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疫情控制或结束后的性别情况也不乐观。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SARS等案例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大型流行病爆发后,男性的经济水平很容易回归常态,但女性的收入则很难恢复到流行病爆发前的水平。在大型流行病结束后,为了及时还债,卖淫的水平也会飙升,性剥削会更加严重。
女性贫困的问题摆在眼前,亟待改变。在公平有效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女性“职业下滑”的滑梯尽头也不是退守家庭。在全球市场化的基础背景下,疫情更是放大了“家庭-劳动市场”两个互动框架中的性别歧视,对于很多女性而言,性别歧视让职业发展困难重重,疫情让女性职场的天花板压得更低;而“照料惩罚”不但压榨女性家务劳动的剩余价值,家暴和其他伤害让家庭不再是可以撤回的、提供保障的 “后方阵地”。性别不公从根本上镶嵌和运作于“家庭-劳动市场”公私两个领域、影响着疫情这样特定条件下社会中关于职业、利润、劳动组织与家庭安排。贫困伴随着暴力和性安全的威胁,女性陷入生产和维系性别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女童和老年女性的处境也不容乐观。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从种族、年龄等其他维度分析多维交叉影响下的疫情贫困问题。但不论女性群体内部是怎样的多元和异质,女性面临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下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女性作为公民和工作者的勇敢付出和坚韧抗争,我们不可能控制疫情。在经济下滑、社会创伤的后疫情时代,社会的修复更需要女性恢复经济活力,否则我们不可能完成全社会的秩序重建和经济修复。我们首先要增加性别不公的可见性,在尝试突破职业天花板、打破性别隔离的同时,让隐形、无偿的家庭照料得到重视,尽量消除照料和母职惩罚对职场的不利影响,在共同抗疫的社会努力中同时消除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我们需要立刻行动起来,得到更多公共政策的支持,纠正系统和制度中的性别歧视。在与病毒斗争的同时,我们也要治疗性别歧视这样的“社会疾病”,促进更平等的社会。
(感谢肖雨对本文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南希·福布尔,宋月萍. 照料经济的特征、价值与挑战:基于性别视角的审视[J]. 妇女研究论丛,2020,(05):5-11.
2、肖索未,简逸伦. 照料劳动与社会不平等:女性主义研究及其启示[J].妇女研究论丛,2020,(05):12-27.
3、王瓒玮. 从新社会风险的生成及演变看日本“新冠离婚”[J]. 日本问题研究,2020,34(04):34-42.
4、李英桃.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的“脆弱性”与“脆弱群体”问题探析[J]. 国际政治研究,2020,41(03):208-229+260.
5、宁满秀,荆彩龙. 贫困女性化内涵、成因及其政策思考[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17(06):5-9.
6、霍萱,林闽钢. 为什么贫困有一张女性的面孔——国际视野下的“贫困女性化”及其政策[J]. 社会保障研究,2015,(04):99-104.
7、Singer, R.,Crooks, N., Johnson, A.K. et al. COVID-19Prevention and Protecting Sex Workers:A Call to Action. Arch Sex Behav,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20-01849-x,49, 2739–2741 (2020).
8、Lam, Elene.“Pandemic Sex Workers’ Resilience: COVID-19Crisis Met with Rapid Responses bySex Worker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Social Work, vol. 63, no. 6, Nov. 2020,pp. 777–781,doi:10.1177/0020872820962202.
9、澎湃,“疫论·劳动|疫情冲击下的零工女性,与她们破碎的流动性,” https://mp.weixin.qq.com/s/lqCsGIQBqkC5mEW1j8fyHQ,2020-04-10
10、World Bank,“GenderDimensions of the COVID-19Pandemic,”h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18731587147227244/pdf/Gender-Dimensions-of-the-COVID-19-Pandemic.pdf,2020-05-09.
11、UnitedNations,“PolicyBrief:TheImpact of COVID-19on Women,”April 9,2020,htps:// 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20/policy-brief-the-impact-of-covid-19-on-women-en.pdf?la=en&vs=1406,2020-05-10.
12、UN Women,“COVID-19and Ending ViolenceAgainst Women and Girls,”htps://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20/isue-brief-covid-19-and-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en.pdf?la=en&vs=5006,2020-05-10.
13、UN Women,“Policybrief: The impact ofCOVID-19 on women,”https://asiapacific.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20/policy-brief-the-impact-of-covid-19-on-women-en.pdf?la=en&vs=1406,2020-04-09
14、UN Women,“Frominsights to action: Genderequality in the wake of COVID-19,”https://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20/gender-equality-in-the-wake-of-covid-19-en.pdf?la=en&vs=5142,2020-09-02
15、CARE:“COVID-19Could Condemn Women ToDecades of Poverty:Implication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Women’s and Girls’Economic Justice andRights,”April 2020,htps://insights.careinterna-tional.org.uk/media/k2/atachments/CARE_-_Implications_of_COVID-19_on_WEE_300420_1.pdf,2020-05-10.
16、Qiu J, ShenB,Zhao M, et alA nationwide survey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hinesepeoplein the COVID-19 epidemic: implications and policyrecommendationsGeneralPsychiatry 2020;33:e100213. doi:10.1136/gpsych-2020-100213
17、HeinrichBöllFoundation , “HowCOVID-19 pandemic affected women in Russia”,https://us.boell.org/en/2020/06/18/how-covid-19-pandemic-affected-women-russia,2020-06-07
18、SophieHarman(2016) Ebola, gender and conspicuously invisible women in globalhealthgover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37:3, 524-541,DOI:10.1080/01436597.2015.1108827
19、联合国,“2019冠状病毒病对东南亚的影响”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impact_of_covid-19_on_southeast_asia_chinese.pdf, 2020-07-17
文章提到的媒体:
1、Reuters, “'Ihad no choice': Sex for rentrises withcoronaviruspoverty,”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britain-housing-harassment-trfn/i-had-no-choice-sex-for-rent-rises-with-coronavirus-poverty-idUSKBN22X2N7,2020-05-22
2、NBC News,“Landlords are targetingvulnerable tenants tosolicit sex in exchange for rent,advocatessay,”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landlords-are-targeting-vulnerable-tenants-solicit-sex-exchange-rent-advocates-n11864162020-04-18
3、Reuters,“Ethiopian girls trapped in sextrade as COVID-19deepensdesperation”,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thiopia-sexcrimes-children-insight-t/ethiopian-girls-trapped-in-sex-trade-as-covid-19-deepens-desperation-idUSKBN27P039,2020-11-09
4、Reuters,“'Hunger or murder': Lockdownpoverty exposesAfrican sex workers to moreviolence”,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health-coronavirus-women-sexworkers/refile-feature-hunger-or-murder-lockdown-poverty-exposes-african-sex-workers-to-more-violence-idUKL4N2D328G?edition-redirect=uk,2020-06-04
5、週刊文春,“外出自粛“家飲みゲンカ”平手打ちで妻が死亡 夫がキレた一言”https://bunshun.jp/articles/amp/37457?page=1, 2020-04-25
6、朝日新聞,“コロナ生活苦、個人間融資に注意 性行為求めるケースも,”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5R5R2CN5QPTIL01T.html2020-05-23
7、知识分子,“新冠疫情期间日本自杀率先降后升,为什么?”https://mp.weixin.qq.com/s/E2Lq-DQItrjRkNsTHN5KjQ,2021-01-26
8、TheIndependent, “Growing numbers of womenturning to sexwork as Covid crisis pushesthem into ‘desperate poverty’,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sex-work-coronavirus-poverty-b1769426.html,2021-01-08
9、SCMP, “Coronavirus pandemic good forforcing ‘pretty girls’into sex work, Japancomediansays,”https://www.scmp.com/week-asia/people/article/3082278/coronavirus-good-forcing-pretty-girls-sex-work-says-japan-comedian,2020-04-30
10、Reuters,“Murders of women in Mexico riseamid fearsoflockdownviolence,”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exico-women-violence-trfn/murders-of-women-in-mexico-rise-amid-fears-of-lockdown-violence-idUSKCN22930V,2020-04-28
11、USA Today,“Job insecurity, child care:Moms reporting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idcoronaviruspandemic,”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20/08/07/coronavirus-pandemic-leads-explosion-depression-anxiety-women-trans/3309916001/2020-08-07
12、The New YorkTimes, “China Long AvoidedDiscussing MentalHealth. The Pandemic Changed That.”https://www.nytimes.com/2020/12/21/world/asia/china-covid-mental-health.html2020-11-21
13、Cyril Ramaphosa,“President Cyril Ramaphosa:SouthAfrica’s responsetotheCOVID-19 Coronavirus Pandemic ,”https://www.gov.za/speeches/president-cyril-ramaphosa-south-africa’s-response-covid-19-coronavirus-pandemic-17-jun-2020#2020-07-17
14、中国妇女报,“疫情之下:非洲妇女面临更大风险,” http://www.nwccw.gov.cn/2020-07/15/content_285671.htm,2020-07-15
从名媛到病媛:女性身体与符号在流量经济中的错配
性别的困境并未因为传播和营销技术的改变而消逝。
2021-10-08

【作者按】:中国大陆互联网上近两个月有两个和女性有关的热词,一个是佛媛,一个是病媛,专指两种网红女性,前者被定义为礼佛的名媛,后者被定义为穿著病人服也还是妆容精致的女性。两者的共通点都是被认为在不合宜的场合有不合宜的装扮。
如9月中下旬,工人日报《狐狸的尾巴哪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央视网评《佛媛:Ω是欲壑难填》,新京报沸腾评论文章《“佛媛”的“僧服”底下,爬满了炫富带货的“虱子”|沸腾》等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开始围剿“佛媛”。此后,《健康时报》一篇《“佛媛”之后再现“病媛”:“生病”不忘化粧》,更是把“病媛”推向了舆论浪尖。宣传机器发动,以上官方媒体的评论内容随后被各大媒体转载,不同的媒体矩阵甚至以视频、解说的方式层层传递。在打击网络平台上虚假营销账号乱象的舆论氛围下,主流文化批评的刀尖直指女性。
随后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数位当事人的澄清。健康时报刊文配图中的当事人,用@张吉晶-cat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维权,她表示,照片仅是个人生活,并未带货,已经请律师介入;另一位当事人称拍照仅仅是记录治疗过程,没有想到图片被盗用,并且因此遭到网暴。微博账号为“零十二画生”账号的女性则被诬陷称“佛媛”。照片里的场景实际为其住的燕方归客栈,她觉得酒店的院落好看,所以拍照在小红书上分享,却被营销号盗图,构陷成在寺庙炫耀。在这几个当事人身上,病媛没有带货,佛媛甚至也不在寺院,而盗用其照片的营销操手却隐身匿形于激烈交锋的舆论中,到底是谁盗取了她们的照片,却无人问津。
在整治网络环境的大势之下,抵制庸俗的“网红”文化成为主流声音。原本是监管对商业社交平台虚假违规网络账号的打击,却延伸成为网络上对女性看似不合时宜地分享精致粧容和打扮的批评。被盗用照片的女性用户原本也是不良营销手段的受害者,但在整治互联网乱象之下,“病媛”“佛媛”等词汇的生产,却转移矛盾焦点,将女性置于新的话语压迫中。这并不是个别记者不遵守基本的新闻伦理核查事实再做报导的偶然失误,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整治政策不慎外溢的误伤效果。长期以来,媒体、舆论与网络消费文化通过制造新的矛盾来重申性别秩序,女性的网络性别身份成为长期讨论的舆论焦点,新经济下的女性劳动者的生存矛盾愈发尖锐。
网络消费主义的兴起和信息社会的转型,迫切地要求人们重新对两性关系重新加以审视。分析病媛佛媛背后积累的厌女社会情绪,拆解大众网络消费文化对“媛”的话语再造,我们会看到粉红经济中女性从事网络市场营销、以带货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困境。在文化身份上,网红成为一种被排挤的性别身份政治,常常困囿于严苛的道德枷锁。病媛佛媛的文化现象,表面是对女性的批评和污名,本质上更是是男权的重构,是父权社会在经济转型中尝试巩固男性特权、愈发极化的性别不公、调整松动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努力。
流量的唤起与崩塌的人设——女性数字零工的职业道德困境
个别现象群体极化的情况,在女性网红的抨击和批评上尤为严重。
在商品随流量而动的新媒体营销时代,新媒体市场营销理论和实践均已经证明,平台销售的工作实际上为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提供了一种参与劳动和经济活动的手段。网红代言、直播带货、都是把网络影响力和商品销售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完成销售某些产品的目的。然而“网红”,并不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正式职业——人们常常忘记,这是一个需要被承认的工作。除了平台零工带来的绩效和种种劳工问题,数字零工的职业道德困境,也往往来源于传统的世俗观念和新兴的销售技术的错配——带货博主必须在发布真实内容和过度分享之间谨慎行事,否则,人设就崩了。
实用主义的网络商品展示需要塑造消费者的临场感、认同感,最大限度地刺激诱导消费。这样的互联网营销手段也确实引来的许多人的顾忌:通过虚拟营销、设立人设模式进行带货的群体,一旦开始就有较强的目的性,便丧失了其原本的道德立场。早在病媛饱受争议之前,直播带货的江哥妈妈、蒙冤27年的张玉环、坠崖孕妇等人,就已经引起了行业和市场的争议:卖货的利益动机与人们同情之间的道德期待,形成了落差,所谓“利用同情博取眼球恰烂钱”的指责来源于此。
同情带来了知名度,知名度可以转换成影响力。如果直播带货中完全遵守市场规则和要求,为什么曾有过痛苦经历的人不可以从中真正收益?然而,“人设崩了”的指责中,依然蕴含着对受害者必须如永远受难的刻板印象、来自正统社会观念的鄙视和既得利益者俯视性的道德绑架。
虚假营销、卖丑作态等极端情况,也并不能为文化上打击女性从事网络销售工作的合理借口。事实是,同样是虚假营销,著名的“带货一哥”辛巴家族曾经售卖实际上为蔗糖水的假燕窝,遭到行业广泛讨论和监管重罚,但批评声中并未产生话语性的性别污名。网络情怀第一人罗永浩也曾经带货“翻车”,承认售假,但三倍赔付就立刻收获人心,获得了老实人的好评,至今高居带货榜。抖音上一度爆红的铁山靠常常讲低俗脏话,口头禅“窝嫩叠”(我是你爹)却被认为是草根的亲和力。
当然,不论男女主播,在过去平台经济草莽生长的发展过程里,都存在涉嫌违规销售等情况。但个别现象群体极化的情况,在女性网红的抨击和批评上尤为严重。网络消费流行文化中只见“病媛”却不见大喊家人、老铁、我是你爹的“糖水燕窝郎”。文化上,人们是不是对男性带货者更加宽容呢?
哪怕是不卖货的素人,也难逃厌女互联网的文化绞杀。许多网友回忆起被严重网曝的B站Up主卡夫卡松饼君,她的真名是赵上上,在25岁时死于肺癌。治疗期间,她在B站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却遭到大量的网络暴力。除了被质疑“为什么得了癌症还那么开心、还能活蹦乱跳”的同时,她也被质疑“卖惨、打同情牌博人眼球”。除了身材羞辱等常见的网络性别暴力,很多人也怀疑她生病是造人设。生前,她疲于向互联网的世界证明她的病历簿、诊断书,护士的存在等“自身的真实”。她去世后,网曝恶意的余波仍然久久未散去。一个生命的消逝能否换来一些反思,也掀起新一轮网络讨论。
赵上上是患病女性在互联网上受到极端的道德审判、性别偏见的典型案例。病媛也只是沉积已久的对女性恶意的爆发。很多短视频平台上的确存在一些抗癌博主,展现日常治疗的生活之外,推销一些非医疗相关的正规商品。只要放下立场,就会发现,疾病的治疗给家庭带来重大的打击,很多“病媛”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采取这种非正式的劳动方式创造收入。她们不得不售卖商品以补贴高昂的治疗费用。只要不涉及虚假营销、没有触碰工商管理和网络秩序的红线,她们的劳动成果为什么无法得到认可?
不论是分享经验,还是带货谋生,女性在网络上记载个人的生活经验史,尝试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经济价值。然而她们的行为和形象却总是被赋予更多的性别意义,带上了更多的道德枷锁。关于网红的道德争鸣和伦理辩论,体现了一个社会新的阶级和数字性别构造中,有关性别的经济和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权力安排。这种张力来自信息经济转型所推动的社会性别建构的隐形进程。

“媛”的污名与反污名——数字身体的商品化与网络性别秩序
作为一个网络新修辞,媛的意义建构展现出了网络商业活动中话语形成、经济实力和商业规则的角逐转换。
从民国名媛的“媛”,到病媛佛媛的“媛”,媛这个名词互联网化后,经过了一系列的语义变迁。原指“美女”有着美好象征的媛,突然与“病”、“佛”等词嫁接在一起,形成矛盾修辞语,就衍生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污名性语义。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同一模式下话语再造产生的“绿茶婊”。学者曹晋等人对“绿茶婊”的研究中就曾指出,矛盾修辞体其所再现出的强劲语义张力,表征了一种转型期中国社会对年轻妇女矛盾的身体政治:女性外在观感本来美好纯净,但身体却可供消费售卖。
媛的身份构筑也存在着爱慕和献媚,同时又遭受正统社会性别秩序的排斥和鄙视。对于病媛、佛媛而言,媒体的抨击更是把“虚荣、矫情、造作和利欲薰心”等负面讽刺意涵烙印在了媛的网络表达里。这种操作树立了一种女性网络失范的典型,进而成为一种新的被贬低的文化身份。
媛字背后意涵的转变,也意味着社会权力和信息秩序的变化。正如福柯认为“话语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规定着,控制着人们谈论的话题以及主题的位置”。实际上,制造病媛、佛媛的人并不一定是女性:千篇一律的低俗内容背后的巨大推手,明明是愈发流水线的网红经济运作模式(MCN)。商业行为失范的始作俑者或许是运作机构,但真正的答案已经在舆论的浪窝中隐了身,个别受害女性反而成为肃清网络环境的靶子。
作为一个网络新修辞,媛的意义建构展现出了网络商业活动中话语形成、经济实力和商业规则的角逐转换。这个过程中,佛媛病媛等话语的再造,则成为了对网络中部分女性行为的规训和审判。新的词汇搅动并重构社会文化的性别秩序,强化旧有的社会性别规范,它巩固的依然是男性的利益。
通过病媛、佛媛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到,网络经济下身体、商品与权力愈发紧密结合,女性的网络形象往往通过视觉符号来强化着某种刻板下的性别操演,女性线上销售工作者承受着来自父权和阶级的多重宰治和剥削。我们确实看到了各种滥用的美颜和失真的照片,甚至“直角肩”、“4A腰”的流行文化,充斥着性别符号的象征暴力。
但需要强调的是,女性的身体只是这种暴力的载体,谁是这种暴力的真正发起?网红的身份是被言说、被赋予的。平台和机构、资金的运作与观众的偏好,也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强加在具体个人选择的动机之上的“真正原因”。正如以女性群体为主要用户构成的社交平台小红书,近期因其在男性网络社群虎扑所投放的广告而引发争议:“超多美女尽在小红书,免费看,不花钱”。这样的广告词配以软色情擦边球的美女配图,构成了屡见不鲜的性别化网络表达。它表达了广告模特本人的意愿吗?它代表了小红书这个社群中记录生活展示照片的女性的想法吗?
在社会转型历史转向的洪流中,我们尚且难以区分鱼龙混杂的千万新媒体用户里,性别化的视觉表达,是机构或个体的主动的积极的自我张扬,还是迎合市场的需求,亦或是兼有之?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主动维权宣布“我不是病媛”的当事人们未想要利用同情换取一些不匹配的利益,更没有像媒体抨击的那样不合时宜地搔首弄姿。而在网上声援她们的那些自嘲是“学媛”、“公务媛”、“医务人媛”的女性,她们加入名媛系列的反污名的行动和言说都表明,女孩们已经意识到重夺舆论场的话语权的重要性:媛本身就是某种积极的女性理想特质,而那些伤害我们的事物可以被改变。
对“受害者带货”或网红的鄙视更是一种阶级分化的行为
我们也必须直面这样的事实:在信息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网红是一个新晋阶级。
对“媛”危机的追溯,我们必须厘清种种难以回避的舆论情绪和历史沉淀。首先,即使在“民国名媛”或西方语境下的“名媛”,这个词汇也暗流涌动着“通过出身、外貌等性资本依附于成功男性”的意涵。而在2020年10月左右,上海拼团名媛这一热点事件和铺天而来的抨击讽刺,更是以一种离奇的方式尖锐地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性别阶级焦虑:女性的炫富、衣着裸露是性道德败坏,连精致的容貌也都有着冒犯的意味——这些费尽心机假冒白富美的网红,触碰了男性社会经济压力焦虑的暗礁:名媛的美是父权猎物的理想型,它首先是性别的暴力符号。其次,名媛的富,在网络视觉文本中展示出被奢侈品和奢华环境,则更是阶级的暴力符号,是底层普通男性难以企及的阶级门槛。
两种叠加的焦虑微妙地威胁到了男性统治和权威。当他们发现,包包是拼的、这些都是假的时,大众情绪中积攒已久的焦虑转换成发泄式的攻击和鄙视,这是男性重构性别特权的胜利时刻。
拼团名媛的“炫富”行为其实并不触犯法律或者伤及具体个人的实际利益(除非是那些觊觎于这些女性财富的男性),其实现实生活里也有带假表的男性,但拼团名媛却成为网络女性文化的耻辱柱。整整一年后,相同的道德焦虑和越轨惩罚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到了舆论对病媛和佛媛的大批判中。
这一次矛盾愈发集中在因为同情而转换成影响力的劳动工作:卖货的经济行为成为最受诟病的争议点。这也正是中国目前愈显发达的数字经济中最具现实意义的社会转型:直播带货让部分女性成为网络公共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更关键的是,网红带货更让普通阶层的女性,甚至可以打破教育、出身的门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个人经济水平的机会。女性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
我们也必须直面这样的事实:在信息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网红是一个新晋阶级。特别让(男)人们所焦虑的是,它不再为男人所垄断。正如艾米•汉瑟(Amy Hanser)对转型中国女性形象的分析中解释的那样:“女性特质的操演总是被标记着阶级的符码”。媛,不单是性别的,也是阶级的。前文“绿茶婊”的分析研究,也已经把女性形象的转变,放到了经济转型推动社会性别建构与阶级重组交织的隐性进程中。
从无产阶级的“铁饭碗”,到市场化社会吃青春饭的“打工妹”,到现在直播带货的“网红”,女性的身份转变可以把近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连接成线。换言之,经济市场的转型不断地催生出中国城市新的阶级,性别话语在这种社会变化中尤其具有代表性。
然而它也不尽然是女人的胜利。某种意义上,直播带货或各种类型的网络零工,给女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局部改善了女性生产资料的情况。但原有陈旧的消极社会性别观和市场经济转型的话语相互共谋,一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观念得以正当化。否则,网红不会是一个有微妙负面意涵的名词,佛媛病媛这样的话语也根本不会存在。不论女性的性别身份如何七十二变,消费和围猎名媛的是高富帅,凝视和谩骂名媛的是屌丝,男性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是隐身的主体。部分男性对佛媛、病媛的攻击,不但是为了巩固其性别身份的正当性和正义感,也是阶级的某种“对峙”:通过对白富美的攻击中获得道德和语言的精神胜利。
更复杂的是,除了外部男女间的不公平,内部来看,名媛和与之相关的身体、商品和社交场景,在视觉传播的过程中进一步符号化,加剧了网络空间中女性身体的性别化和商品化。对名媛和佛媛的激烈批评并不仅仅指来自男人。原本处在优势阶层的女性,甚至其他希望遵守原有规则的女性,也自觉不自觉地希望与之划清界限,通过巩固和强化父权制对女性的身体政治来区分群体内部的不同类型。部分女性在松动的阶级调整中保持原有优胜者的地位,充当道德监督人的角色,以获得男性的尊重。此外,无孔不入的网络消费主义、网红经济中的诱导、不规范等问题,在另一种程度上也间接的强化了数字经济鸿沟下愈发被动的女性劣势,让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呈现出纠缠的复杂性。

父权重构——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
或许,在历史上某个细微的时刻,酿造淡味啤酒的妻子或许也认为,只要保持虔诚,宗教压迫就不会伤及她自己。
请允许我再将目光拉远一点点,来说明病媛和名媛此刻处于舆论靶心的历史经验。根据历史学者徐善伟的研究与分析,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新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女性一度在纺织、酿酒和零售业中占据了优势,不但成为重要的家庭经济支撑,甚至在社会纳税贡献中构成相当比例。在宗教、生养医疗方面,10世纪的欧洲女性已经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和经济地位也显著提升。由于十字军东征战争离家等原因,贵族女性开始继承家庭财产,随母姓的比例大幅提高,11世纪法国南部随母姓的人所占的比例一度上升到12%。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关系面临新的调整,两性关系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平等。宗教迫害为男权社会制造了完美的借口,女性成为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巫术指控成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女性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
让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在啤酒酿造和销售业中,当时的人把售卖淡啤酒的女性称为淡啤酒妻子(alewife),并形容为“古怪、女巫般的年老女性”、“品行不端的女商人”。医疗行业对女巫的指控,也伴随着医学院只招收男学生的禁令。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娜·拉纳(Christina Larner)直言:“猎巫运动的目的就是整肃女治疗者的领地,以便为男性同行开路。”徐善伟对通常遭到巫术指控的女性类型的总结道:正是不符合男性所规定的女性行为标准的行为,使她们成为巫术指控和诉讼的对象。她们被认为太有个性,不符合宗教和道德要求,喜欢吵架,尖酸刻薄。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结局。自15世纪后期开始,纺织、酿酒、零售、治疗等这些原本主要由女性从事的行业中,女性遭到排斥,且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1461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城的市政当局通过法令,禁止妻子、女儿和织工的女仆去纺织作坊工作。三百年内,猎巫运动让大约五万至十万人被处死。它最终演变成了对女性的迫害——审判处死的人中75%到80%为女性。限于篇幅,宗教迫害的性别因素,本文不再讨论。
坦言,把病媛、佛媛的网络攻击直接对应于历史上人道灾难的猎巫运动,或有危言耸听的嫌疑。或许,在历史上某个细微的时刻,酿造淡味啤酒的妻子或许也认为,只要保持虔诚,宗教压迫就不会伤及她自己。论者各有所言,读者自有判断。
我们所唯一确定的是,经济转型会带来权力关系的改变,要经历失序后重建秩序,重新安排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变化过程中有所冲突,会有所代价。回到现实,我们身处的这一个时刻,新经济领域内全新的传播技术和消费模式早已侵入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改写着原有的传统的伦理和文化。随着快手、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兴起,除了当做日常记录和交流的普通用户,网络红人、直播带货也愈显发达,女性作为“消费公民”的数字身份不但对平台和品牌至关重要,薇娅、李子柒等红人也通过不同的模式,成为新经济领域贡献较大的劳动群体,直接撬动了市场营销和销售等环节,成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构成。网红的崛起,让性别与阶级秩序表现出最明显的动态张力。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女性虽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活动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逐渐逾越了男权社会所规定的界限,但也引起了男性权威的焦虑。男权的重构,就是需要巩固岌岌可危的阳刚之气,夺回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侵占抢夺可以由女性开拓的生产资源,重新把女性至于被支配地位的过程。男权的经济思维也往往利用传统性别观念中的不平等,把女性消极观念延续到不断扩张的数字化商业进程中。
病媛、佛媛,是媒体与互联网内容的再生产,这些词汇的出现,意味着女性的符号、身体与性别,仍然面临着价值观的错配。消极的女性观念,让新经济领域中关于女性的歧视与暴力的阴魂不散,性别的困境并未因为传播和营销技术的改变而消逝。这是女性的数字化生存备受威胁的时刻。然而如何让另一部分人打破性别竞争的对立思维,共同拓展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的网络生存和发展空间,是我们当下历史的复杂命题。
参考文献:
张小强,李双. 网红直播带货:身体、消费与媒介关系在技术平台的多维度重构[J]. 新闻与写作,2020(06):54-60.
曹晋,徐婧,黄傲寒. 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以“绿茶婊”为例[J]. 新闻大学,2015(02):50-59.
徐善伟. 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J]. 史学理论研究,2007(04):34-41+158.
塔玛拉·尼斯(Tamara Kneese). 杜云飞译. 劳动论丨女性带货博主:数码时代居家劳动的线上零工. 澎湃思想市场
关聪 原瑞阳 谁来监管辛巴 财新周刊
反代孕狂潮的偏见:隐身权贵、失足孕妈,和成为众矢之的男同性恋?
狂热的舆论扭曲了关于代孕的集体认知。反对代孕的大讨论中,“谁在代孕”和“谁在消费代孕”的基本问题仍然充满偏见和错误认识。
2021-01-25

1月18日,大陆明星郑爽和前男友张恒在美国代孕弃子的消息如巨石落水,激起舆论千层浪花。录音中郑爽反悔代孕、意图弃子的轻率态度,引发了舆论的愤慨。随着事件的发酵,不同媒体从女性与身体,法律与伦理,地下黑色产业链,各国立法实例和纠纷实践等等角度对代孕议题竞相报导和评论。对公众而言,一度神秘的代孕话题揭开面纱。有钱就能代孕的普遍现象、触目惊心的代孕纠纷和伦理困境一一浮出水面,拨弄着敏感的大众神经。
剥削女性、外包生育、婴儿工厂、贩卖生命……不同立场的道德谴责汇合成了情绪汹涌的大合唱,反对代孕成了压倒性的主旋律。但是“到底是谁在代孕”的集体认知却仅限于“有钱人”和“同性恋”,而贪腐高官这样的特权阶级接受代孕送子的贿赂时却能保持隐身。反对代孕的民意也逐步从“仇富”变成了“恐同”——“有钱人突破伦理,为所欲为”的矛盾逐渐演变成了“男同性恋传宗接代,剥削女性”。铺天盖地的媒体曝光和疯狂的舆论非但没有增加沟通和理解,反而加剧了分歧和割裂。
虽然反对代孕的声音整齐划一,但为何要反对代孕的原因,却不尽相同。社交媒体上焦虑的中产阶级用居高临下的、想像的知识替代代孕的种种现实。在缺乏对孕妈、代孕者和历史案例的了解下,部分女性主义的零碎观点沦为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不少网友仅凭借极端案例的只言片语和娱乐圈的捕风捉影,隔靴搔痒地纸上谈兵,大做道德批判。代孕议题深陷朴素的生物本质主义泥潭。反对代孕的狂潮,逐步升级为反对一切合法代孕可能性讨论的偏执。“非蠢即坏”,“代孕Biss(必死)”的极端、简化态度,更是掐灭了不同意见之间沟通的希望。
汹涌的舆论情绪、偏颇的集体认知、复杂的道德困境、性别与阶级的交叉勾连,围绕代孕的话题撕裂了不同的圈层和群体,挑起了更深的矛盾。我并不支持代孕,本文也并不是要反对“反对代孕”,而是在主张反对代孕的同时,纠正部分错误认识和误解,反对针对少数群体的代孕污名,促进开明的良性讨论。

舆论盲区中的“有权人”
多个贪官代孕受贿案、黑社会胁迫代孕案,虽然同郑爽的惊天言论一样让人大跌眼镜,却未引起舆论的注意。
就在郑爽张恒代孕弃子消息爆出的前两天,即1月16号,《财新》发布了一篇名为《沪上“小红楼”往事》的特别报导。该文章披露了上海杨浦区黑社会组织头目赵富强逼迫女性卖淫,以性行贿,囚禁女性的犯罪事实。其中与代孕相关的犯罪细节残忍至极。一名受害者称,被拘禁期间,她连续十余日遭强制注射催卵针,再被戴上眼罩送至某诊所,在未注射止疼药的情况下被强行取卵。这样的伤害造成该女子腹腔严重积水,如同怀孕六七个月,使其住院治疗约一个月。另一人称自己也有类似的遭遇,两名女性至今不具备生育能力。近20年间,涉事的9位女性中,有1人受其哄骗剪断了输卵管,3位分别与其结婚并再离婚,至少6人与赵富强育有子女。案发后赵富强被判入刑,而这些未成年子女,连同多名代孕生育的儿童,或面临户口、上学及缺乏经济来源等问题。因生育孩子非部分女性的主观意愿,只能暂时由生物学上的曾祖父母抚养。
这一极端案件或许具有某种程度的特殊性,但与贪污腐败相关、涉及代孕的案例并非唯一。根据《财新》于2019年8月的报导,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因受贿1.53亿元被判无期徒刑。案件披露,山东一老板关成善为感谢王保安在项目申报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投其所好,找了两家代孕中介。代孕妇女为其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出生一周后,王保安落马。
从舆论观察的角度来看,上述贪官代孕受贿案、黑社会胁迫代孕案,虽然同郑爽的惊天言论一样让人大跌眼镜,却未引起舆论的注意。在一浪更比一浪高的代孕批评和反思中,贪腐官员一直是隐形的。这舆论差异背后的原因着实令人深思。诚然,《财新》是定位于专业人群的付费媒体,覆盖读者受众有限,但类似消息并非为此一家垄断。《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也报导了“送子行贿”的王保安贪腐案;新京报2018年的《以“代孕”为名进行钱色交易的官员》则报导了当年10月被双开的包头市林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福荣。他假借“代孕”之名行钱色交易,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生育三名非婚生子女。这些都是对读者完全开放、可以免费阅读的内容。
在批评市场和资本的同时,另一个关于代孕的隐秘真相不应该被轻易忘记:代孕也是权力的异化。真正的特权阶层或许可以免于舆论的批评和民众的道德审视,但传宗接代似的生育诉求不仅限于普通人。“是谁在消费代孕市场”的舆论诘问中,我们不应该放松对“有权人”的警惕。
国家干部、体制内高层官员及相关联利益群体,应该是中国社会真正的权贵阶级。勾结官员收买法院、警察的黑社会组织头目,更是富有影响力的特权。这一类人群不但把握大量的社会资源,在地方或行业拥有实质影响力,且最不易受到监督和约束。当然,生育技术的更新进步和代孕市场的出现是外部环境的前提条件,而“膝下无子、传宗接代”的陈旧思想、钱财和权力之外膨胀的生育欲望,更是官员个人代孕、接受代孕行贿的内部心理动机。作为行贿腐败的方式,代孕是权力异化的新手段;代孕生子、代孕受贿是官僚隐形特权的延伸,是寻租行为的新变种。

抵制代孕就要恐同仇男吗?
到底谁是代孕群体?同性恋群体是代孕的主要力量吗?
与上述舆论真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许多网友找出了涉嫌“代孕”或“弃子”的明星名人,掀起了狂热的舆论审查,捕风捉影地清算其私生活。人们重提2017年徐静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代孕很正常”的言论;陈凯歌去年拍摄的涉及代孕话题的短片《宝贝儿》再次遭受三观不正的指责。于正、陈坤等娱乐圈红人和明星也遭到代孕质疑。
时尚博主gogoboi未婚但有一个混血女儿,一时成为众矢之的。#gogoboi清空女儿微博#的话题登上热搜,其微博评论中充满了“死基佬”、“代孕biss(必死),你等着封号”的羞辱和威胁。在许多主流财经媒体的报导中,同性交友软件Blued的代孕中介业务“蓝色宝贝”,成为最典型的中介代表。又因为其上市招股书对利润和行业情况的详细披露,批判代孕的矛头对准了性少数群体。同时,一些关于少数群体出柜、代孕的纪录片因为“坐实”了拍摄者的代孕行为,而成为讨论的风口浪尖。
部分女性主义者和酷儿群体的关系因此变得剑拔弩张。一些人认为,男明星、男同性恋代孕或弃子,都不曾引起如此规模的舆论风暴,本质上还是“民意只围猎女性”的区别对待和双重标准,“错就错在她是女的”。“都同性恋了还繁殖癌,醒一醒”、“贱Gay没有子宫”、“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彻底恐同”类似言论的子弹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中随意扫射。男同性恋群体因为生理性别和无法走入异性恋婚姻的性向,成为了代孕攻击的靶心。
到底谁是代孕群体?同性恋群体是代孕的主要力量吗?研究性别社会学的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李在洲,曾经在中国中部城市进行地下代孕产业的田野调查。在《澎湃》的采访中她说,调研的中介表示,绝大多数代孕客户是不孕不育的异性恋夫妇,少部分是同性恋,另有少部分单身生育。由于代孕是地下产业,孕妈和代孕者都倾向于保护个人隐私。国家没有统计,中介也不会详尽地调查。单身生育的群体,中介也不能确定其性向。另外,还有客户是失独父母或二胎开放之后过了育龄的夫妇。此外,《财新》在2017年关于代孕的调查报导中,业内人士也表示,“难治型不孕不育者是代孕的主要需求者”。根据这样的事实,同性恋群体不应该被过度代表成为主要的代孕群体。
本质上,代孕合法化与同婚合法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议题,其覆盖的适用人口和规范的公民权利各不一样。当然,婚姻和生育息息相关。对于异性恋而言,领结婚证往往也意味着得到了合法生育的许可;但同性恋受限于生理的天然限制,即使合法结婚,也不能自然地实现生育权,必须采用代孕等技术手段才能育子。在这一环节才需要代孕技术的法律许可。因此,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并不意味着代孕的合法化。呼吁平权运动不等于支持代孕。包括单身人士、同性恋群体在内的许多群体都在尝试传统异性恋婚姻之外的家庭组合方式,但这不意味着代孕是他们的绝对主张和诉求。
在中国,代孕违法吗?
从严谨的法律角度来看,中国尚无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公民代孕。
“在中国代孕违法。”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近期,包括党媒、官媒在内的许多媒体都发出过“中国代孕违法”的说法。社交媒体上,“代孕违法”的说法更是铺天盖地,中国人从未如此富有“法的精神”。然而,从严谨的法律角度来看,中国尚无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公民代孕。
中国卫生部于2001年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这仅仅是一项行政规章,规制的对象是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并不限制人民的公民权利。换言之,开办代孕的医院和机构违法,但该管理办法对选择代孕的普通“代孕顾客”没有约束力。“中国法律明令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才是严谨的说法,而且,它也是机构和从业人员在行政层面的违法。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曾提出过“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不过这一条款在草案审议期间被删掉。实际上,代孕在中国地位尴尬,《财新》在报导中曾将此现象总结为:“法律不禁,政府不许”。
不禁止,不等于合法,也不等于违法。对自然人而言,代孕没有对应的罪名,也没有相应的惩罚。虽然法律不一定承认代孕合同的有效性,但它不影响代孕事实发生之后,父母、亲属或孕母与孩子亲子关系的确认。从法律执行层面来看,全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纠纷案就是一项有力的例证。2013年,一对已婚夫妇在做了试管婴儿之后不幸车祸身亡。这对小夫妻的双方父母都想要胚胎以延续血脉。根据国家辅助生殖技术及胚胎处置的规定,医院不能擅自将冷冻胚胎给他们。于是两家老人各为原告被告,对簿公堂,要求法院判给他们对冷冻胚胎的处置权。法院在二审决定将胚胎处置权判给四个人。拿到胚胎之后,老人们还是希望能代孕抱孙子。经过重重波折,最终胚胎被顺利送出境,孩子在老挝代孕成功。
《新京报》2018年的报导详细记述了上述案件的经过。4枚胚胎从南京的医院运送出国,在老挝孕育出一个生命,再跨境回国。这个过程需要许多合法手续。如果跨国代孕是明确的违法行为,这样的案例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判决书,近期涉及“代孕”纠纷的案例证实了这样的社会现实:2015年至今,涉及代孕的的各类案件激增,其中民事案件多与物权纠纷、合同纠纷、家庭关系等其他纠纷相关;刑事案件与贪腐、人身伤害或谋杀等有关;行政案件多涉及医院、卫健委等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等纠纷。但是,没有个人仅仅因为参与了代孕而受到法律的惩罚。
同样选择了跨国代孕,这四位老人的具体条件、生育诉求和行为动机与郑爽张恒截然不同。简简单单的一句“代孕违法”并不能排除另一些代孕行为实际上受到情、理、法各方的合理支持。悬停的法律条规,模糊的法律现状,现实中颇具弹性的行政操作……法律非但没有引导、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构成了代孕争议性的一部分。
在中国,与法律概念同样重要也常常被混为一谈的是行政命令。与曾经的独生子女政策、现行的二胎政策类似,代孕也是一项涉及人口管理和社会家庭结构的公共政策。作为生育技术的代孕,它也反应出着国家在关乎民生、人口决策上的行政意志。合法化了如何管理?罪化了如何惩罚、惩罚谁?不论是堵是疏,在细化落地代孕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同时,它都需要考虑到多方利益,与现有的产假产险、生育托养、户籍与教育等婚姻人口制度相互配合适应。

代孕就是在压迫女性吗?
反对代孕的理由中普遍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朴质感情和“强迫洗脑、被迫自愿”的代入恐惧。这些反应是合理的,但也是有局限的。
近年来性别议题的广泛讨论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信息资源较为丰富的城市中产女性首先开始直视生育对身心的负面影响,诉说产后抑郁和育儿的辛劳苦痛。逐步改善的性别观念打破对母亲角色的浪漫化想像,反对母子关系的道德绑架。“母职惩罚”说法的提出,是为了改善育后女性面临的职场挤压和下降的社会地位。这其中的进步难能可贵。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婚驴”、“繁殖癌”的羞辱性词汇普遍流行。暂且不论对错,它们也反映出许多单身未生育的女性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焦虑和质疑。但这都是一种带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性别认识,并未得到普遍认可。
在这样的舆论底色下,反对代孕的理由中普遍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朴质感情和“强迫洗脑、被迫自愿”的代入恐惧。这些反应是合理的,但也是有局限的。其他媒体对世界各地代孕情况的报导,大都是从曝光、揭露黑产的角度入手。“代孕妈妈都是被洗脑、受压迫才出租子宫”,“代孕只能是贫困下的无奈选择”,这样的叙事,更成为媒体和舆论中“唯一正确的现实”。
然而现实不只有这一种。李在洲的田野调查说明,代孕妈妈其实有主观能动性,不一定全部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生育奴隶。首先,她们不是绝对贫困的社会最底层。很多代孕妈妈来自农村或者城乡接合部,拥有初中到高中学历,并且做过打工妹、农民工或者开过小店。其次,短期内的经济诉求是她们做代孕母亲的主要动机:欠债或者家人重病时,代孕对她们而言是挣钱最快的选择。面对这份工作的道德压力,有一些人会在代孕时假装打工,再把代孕赚的钱悄悄存起来,留给以后自己的孩子花,增加自己和孩子的经济安全。
最重要的是,做代孕其实是她们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选择。在访谈中,她们表示,工厂的工作强度极高,精神极其匮乏,收入非常低。流水线上的工作不能带来技能经验的累计,还会接触到危险器材、化工毒害。年纪大了,体力精力不好,也得走人。虽然生育存在风险,对身体也有伤害,但很多代孕妈妈有过生育经验,了解生育的潜在风险。大部分人会在身体条件尚能承受的时候代孕一两次。赚够了钱就会回家。
中产阶级的年轻人看待代孕妇女,缺乏对底层生活的理解、想像和知识,很多发言实际上是在投射自己的焦虑。
回头再来反思舆论中对自由和伦理的讨论,有很多“以中产阶级之准绳,衡量底层女性之困难”的情况。一种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代孕是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是新自由主义对人的异化。但这种简单否定的观点,也没有站在代孕妇女所在的阶级立场思考如何满足她们的经济和实际生活需求,或者如何实现生育的劳动力解放,反而立刻拔高到宏大的理论层面,指点江山,把代孕话题变成了“左右的路线之争”。
即使在看似保护女性、标榜性别进步意识的言论中,也有许多实际上传统保守、自相矛盾的观点。生物本质主义出于保护女性的名义,抵制“贩卖身体”的商业行为。但它强调怀孕是一种关乎女性身份的生育劳动,子宫和生育能力才是女性性别身份的本质。女性的价值在于生育——这一直是女性主义所反对的。家庭道德伦理之说强调母子关系的不可分割,浪漫化天然生育与母职的伟大。一味强化女性的母职,也是女性主义所批评的。
法学家罗翔“自由不被限制,一定会变成对弱者的剥削”道出了追求公平正义的法理理论中,对自由合理限制的理想,它的真意在于“有限制的自由”而不是“抹杀自由”。但网络中时髦的“洗脑说”和“建构说”对罗翔的金句简单粗暴再利用,轻易地全盘否定现实生活中女性自主选择代孕的可能性。
被问及如何看待代孕,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上说“我就是代孕的产物。我妈妈代表我爸爸孕育我。所有人的出生都是以妻子一己之力将两个人的事独自承担受尽苦难代表丈夫怀孕。”此番言论难能可贵地突出了传统家庭框架内女性承担绝大多数生育劳动和风险的事实。但是,代孕概念的泛化背后是对女性生育主体性的彻底消解。不妨来思考,生物学上血脉的延续并没有排斥母系,在谁都不能单性繁殖的条件下,为什么是男性借腹生育,而不是女性借精怀胎?身孕即代孕的观点本质上仍是一个男性主体立场的观点。
代孕正是这样一个由性别和阶级相互交叉影响的复杂辩题。在《澎湃》的采访中,李在洲表示,中产阶级的年轻人看待代孕妇女,缺乏对底层生活的理解、想像和知识,很多发言实际上是在投射自己的焦虑。有些媒体中俯视的同情将代孕妈妈看成了失足的、卖孩子的妇女,但代孕母亲实际上会灵活地利用生物学和文化上的证据来判断亲属关系,找回道德支点,厘清劳动价值。舍身卖子的妖魔化是对代孕妈妈错位的批评,“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其实对代妈未必是一种尊重”。
无处安放的生育权
中国各项政策的生育主体一直是异性恋的已婚夫妻,而非公民个人。生育权一直是适龄异性恋夫妇的特权。
公众的偏见似乎已经将代孕视作道德和伦理的洪水猛兽。但是,即使完全禁止代孕,不同群体关于生育权的诉求和矛盾,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实践层面,不孕不育的异性恋夫妻、失独夫妇实际上已经合法地采取包括试管婴儿在内的各种生育辅助技术。在代孕议题的舆论中,他们也拥有最多的理解同情,享受着最宽松的舆论环境。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个“公民”的范围显然包括所有人,可见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限于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也包括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公民。但是,这是理想化的“应然”。实际上,中国各项政策的生育主体一直是异性恋的已婚夫妻,而非公民个人。现实生活的通常情况下,只有结婚才能获得孩子的出生许可,只有结婚,生母才能享受产假产险等生育保障。生育权一直是适龄异性恋夫妇的特权。
单身女性也已经开始争取婚姻之外的育儿权利。2019年12月23日,中国第一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开庭,原告说出众多单身女性的心声,主张自己作为未婚女性冻卵的权利,且指出了生育技术在政策上的性别歧视和不公。根据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国女性只能因夫妻不孕或患有癌症,才能获准冷冻卵子。一般的单身女性不能冻卵。然而,《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却允许男性仅出于“生殖保险”目的,以备将来生育而保存精子。
法庭上,代表医院的被告律师道出了反对冻卵的理由,其中许多与反对代孕的理由一样:取卵对女性身体有伤害,单身生育可能会造成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冻卵技术的应用可能会推迟女性生育年纪。而原告女性的反驳认为:已婚夫妻可能因离异造成单亲家庭,单身冻卵女性也可以选择组建家庭,“整体的社会问题不能由单身生育来背锅”。
这是女性凭借自由意志主张积极采用生育辅助技术的案例。一位女权主义者很可能出于“支持女性身体自主”的想法支持女性单身冻卵。但是,同样作为法定意义的单身女性,她会支持小三、二奶这样的人吗?基于不同的身份、动机和具体生育诉求,代孕愿望在不同维度的道德象限中定位不同,折射出了社会变迁中的矛盾而复杂的伦理困境。
代孕或许不是最理想的实现生育权的方式,但探索传统婚姻之外的新型家庭组织方式是多元发展的趋势。
让我们先搁置下道德相对主义的讨论,或是基于性别、性向、阶级等身份光谱的差异。冻卵或代孕,作为某一种生育手段,或许是错误的、可否的,但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对于任何人而言,延续生命是一种普遍的愿望;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生育不应该只成为符合某种道德规范的人类的特权,就算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占大多数。
在生殖技术的发展下,社会不会、也无法原地踏步不前。代孕或许不是最理想的实现生育权的方式,但探索传统婚姻之外的新型家庭组织方式是多元发展的趋势。包括代孕在内的各项生育辅助技术当然是带有、或者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技术。它的技术本质注定要重构以前建立在传统生育基础上的社会人际关系。它会牵动与之相关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更需要法律和政策的回应。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它既有可能造成对女性群体的不公、强化基于血脉的父权继承,也有可能因为改变人口再生产的传统模式,而松动现有父权的异性恋家庭模式。
它究竟是可以撬动社会结构的杠杆,还是固化社会结构的螺丝?目前与它相关的社会价值将走向怎样的历史方向仍不明晰,还需要经过更多的价值辩论和实践考验。但这样的辩论应该是开明开放的,这样的实践应该是寻求共善(common good)和最大化福祉的。代孕问题或许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这样的争论或许没有正确的完整答案,但不同群体关于代孕的沟通应该在道德分歧中寻找共识,弥合割裂的身份,谋求新的合作秩序。新技术和相关讨论应该是不同圈层、群体和心灵意识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隔开我们的囚笼。
参考文献:
1. 王淇. 关于生育权的理论思考[D]. 吉林大学, 2012.
2. 郑玉双. 破解技术中立难题——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再思[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 21(01): 85-97.
3. 杨彪. 代孕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 市场、道德与法律[J]. 政法论坛, 2015 ,33(04) : 34-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