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 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程映虹
野兽按:最早读到程映虹的文章还是在“世纪中国”时代,后来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也读了不少他的文章。后来在端传媒读到他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述,也是非常认可。今天想起他出版于2008年的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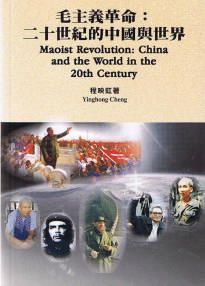
共產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國際性的運動。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國際共運的產物,中國的 變化又反過來對國際共運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尤其是在毛時代。遺憾的是,對於後一方面的問題,國人的研究還有不夠。程映虹這本書應是迄今為止在這一領域的最 有份量的著作。本書結合歷史敘述與理論分析,作者尤其善於選取特殊人物與事件,通過引人入勝的描寫,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雖然講的是毛主義的認識,並進而加深我們對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認識。全書史料豐富翔實,敘述條理分明,文筆生動 流暢,讀來不但增長知識,而且發人深省。—— 胡平(紐約)
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與衰變無疑是二十世紀世界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但對這一事件的有價值的研究與分析至今仍然極為有限。如何解讀中國共產主義不僅是理解和把握當今中國的關鍵,也與中國的未來命運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息息相關。程映虹的《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跳出民族主義,為主宰中國大半個世紀的毛主義的運作機理提供了新解,也為我們瞭解世界共產極權主義的共同本質提供了鑰匙。—— 陳彥(巴黎)
本書描述和分析了毛主義和文化大革命對世界上若干地區和國家的影響及其後果,對於回顧、總結20世紀共產運動這個歷史性任務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具有開創和 填補空白的作用。雖然毛主義是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的產物,但它仍然具有東方專制主義的特徵,由於毛的個人野心,毛主義也是蘇聯模式與意識形態的競爭者, 它的影響與作用有其獨特性,當然它的後果、結局、災難、慘劇與失敗與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完全一樣。本書雄辯地闡述了這一論題,是很有啟發性的歷史教科 書。——徐友漁(北京)
程映虹,任教於美國特拉華非州立大學,畢業於蘇州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東北大學。研究興趣在世界史和國際共運史。英文專題論文發表於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Modern Asian Studies, The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ld World Studies, History Compas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學術專著 : Creating The New Man :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塑造新人 : 從啟蒙運動的理想到社會主義的現實》)將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世界史」系列出版。中文學術論文曾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世界歷史》、《史學理論》、北美《當代中國研究》等雜誌。另有學術類文章在90年代的《讀書》和《方法》等雜誌發表。
后记
本书是现当代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相结合的尝试。更具体说,是对革命史和激进的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互动关系的研究,是对毛主义的中国在国际共运史上的作用和世界历史上的定位的初步尝试。本书各篇的写作和修改经历了多年时间, 大部分篇目发表于中英文学术和思想杂志,经修改后汇集成书。
直到修改定稿之后,我才觉得刚刚对一个困扰了自己多年的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但已没有时间去展开论述,这就是作为一个历经一个多世纪、涉及数十亿人的生死和命运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整个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共产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凡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共产主义批判、破坏或者最起码是限制的,都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制度、规范和成就,例如阶级,财产,城市,家庭,商业,货币,教育,道德、宗教和艺术等等。在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革命最激进时期,这些都受到了彻底改造或者破坏。从根本上说,文明建立在社会区分和劳动分工之上,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这种区分和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共产党革命就是要从财产制度和职业定位上彻底消灭这种区分和分工,创造“全面发展”的人,同时消灭和这种区分和分工相联系的观念,甚至包括学生对师长的尊敬和外行对内行的服从。这就是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所说的彻底决裂和毛泽东所提倡的破四旧。
文明的推动力离不开个人利益和个人追求,而共产党革命要消灭的就是人的“私”。文明的进化也是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发展,追求自由和权利的过程,而共产党革命就是要用“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取代自我意识,用“阶级”和“集体”的自由和权利(实质是党的利益)取代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文明要求一种起码的普遍性的道德作为人际交往的规范,共产党革命否认道德的普遍性,说只有阶级的道德,凡是符合这个阶级的政治需要的就是这个阶级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又被转换成利益,所以共产党统治下人际关系最终变成毫无遮掩的的利益关系。文明产生了礼仪、修养、优雅和品味,共产党革命把这些一概斥之为虚伪、奢侈和矫揉造作,代之以赤裸裸的野蛮和粗鄙。知识分子之所以无一例外在共产党革命中遭殃,就是因为相对来说他们代表着文明所创造的知识和制度。列宁、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等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的背后实际是对人类文明的敌视。不错,马克思主义者也谈学习谈知识,例如列宁说过“用人类产生的一切现有知识来武装自己”,有人也许会说这难道不是提倡文明吗?但这句话体现的恰恰是在文明面前的妄自尊大(“一切”)和实用主义(“武装”),它正好表明象列宁这样的人不但不懂人类文明的博雅精致,而且还把自己高高置于文明之上。也许它唯一值得称道之处是毕竟好过毛泽东时代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反文明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革命本身是一个不断粗俗化和野蛮化的过程。《共产党宣言》中至少还有一点知识,还有一点文明,虽然它们被用来装点一个反文明的核心观念,即用阶级斗争史来取代人类文明史,看到的只有压迫和斗争,没有和谐和进步,高扬的是一种憎恨和愤世嫉俗。到了毛泽东那里这种粗俗和野蛮不再有任何掩饰,简化到只剩下四个字:“造反有理”。但正是这四个字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共产党革命尤其是毛主义的革命就是要造文明的反的实质。毛泽东反文明的态度始于他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到60年代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宣布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扬言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干脆用痞子语言取代意识形态概念而登峰造极。所谓痞子就是不承认文明规范和社会礼俗之徒。毛泽东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受“规矩”束缚,到了晚年尤其好称“不信邪”。这种“规矩”和“邪”往大说是人类文明的政治、道德和职业规范,往小说是他自己这个党内部的一些最起码的运作程序。不过,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领袖毕竟还为改造和限制文明的基本制度和规范而绞尽脑汁,发动了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而红色高棉(极端的毛主义者)则干脆不再改造,而是把它们全部废除。
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和参加者常常感叹他们事业的“艰难”,夺取政权后的社会改造要比武装斗争更为不易,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夺取政权说穿了不过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而建立政权后的社会改造要破坏的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要扼杀的是基本的人性,那当然决不会容易了。苏联和中国的农民对各自的政权要彻底毁灭传统乡村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和生活、建立“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的抗拒和抵制就是无数“反革命”的事例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也可以有新的解释。所谓“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它实际是共产党政权把文明破坏到了危及本身生存后,走投无路之际逐步向传统和常规回归,开始承认一些文明的基本规范,很多政策和“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其实并没有关系。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重要政策是取消知识分子、干部和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不再强行把父母和子女拆散,这实际上是承认必须尊重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作为人类文明最基本单位的完整性。应该指出的是,人类自有家庭以来,只有奴隶制才挑战过这个制度(奴隶主可以随意拆散奴隶的家庭,把夫妻分开,把亲子拆散) 。改革开放之初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恢复正规高等教育和高校招生,这无疑是宣布“工农兵上、管、改大学”的反文明的“教育革命”的失败。
然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把它说清楚,又需要另外一本书了。至于为什么共产党革命要革文明的命,它和其它反文明的社会运动之间有什么异同,反文明又有什么魅力,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参与者,招惹那么多的朝圣者,至今还有那些“红色记忆”在召唤恐怖幽灵,则是一个更复杂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了。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文明当然充满了矛盾和问题。文明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化)在社会的层面(政治经济)和个人的层面(精神和心灵)上始终有两面性,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高级有机体和具有创造性的人类来说,文明终究胜过野蛮,对文明的批判不能逾越文明本身的底线,不能质疑或挑战文明的基本规范和制度。共产党革命对文明的破坏是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破坏了这个底线,摧毁了很多制度和规范,而当代西方学界很多时髦的学说则企图从观念上解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解构本质上是智力、语言和概念游戏,是文明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我异化的产物,其导向是反文明的。难怪很多西方“后学”大师和信奉者对共产党革命不但当时情有独钟,今天也还在千方百计杜撰出很多听上去很有学问的废话来为大跃进和文革辩护,因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共产党革命在精神深处吸引他们的其实是那个反文明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过是当年“政治朝圣者”的嫡系后代。
--原载:《民主中国》,2008-02-07(htt
何清涟:为共产主义祛魅的历史还原者
——读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在中文世界里,程映虹已经相当有名。在“百度”搜索栏输入他的名字,有关他的辞条高达11万2,000多条。尽管有不少条目因网路监管的原因已经打不开,但这足以说明曾有那么多的网友转载过他的作品。这对于一个由于政治原因其作品几乎绝少可能在今日中国出版的学者来说,足可安慰,因为他的读者之多,远远超过了许多在中国能够自由传播的作者。
我读程映虹的作品,始于约十年前。吸引了我的是他那篇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切·格瓦拉为什么出走?”在我看来,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把格瓦拉这位“尘世的耶稣”从超级神坛上请下来,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前路迷茫。共产主义信仰本身包含着对人性的极度贬损与改造人性的狂热,这一精神特质必然使这个运动在人类社会陷入死胡同。而在格瓦拉身上,这种共产主义的基本特质更为明显,这使他对现存秩序永不满意,需要不断寻找新的革命战场。程映虹想阐明的“格瓦拉出走”,其实不仅仅只是行动上的出走,而是这种精神特质必然带来的困境。因此,他在这篇文章中最后的发问是:“他(切·格瓦拉)却为什么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他有什么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终革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又是什么‘解放’?更进一步说,是什么使得他自认为有权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会,而且再造个人呢?”
那时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此后,凡看到署有“程映虹”之名的文章我必然要读。再后来,他成了《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主力作者,多年来积累之功力进入喷涌状态,佳作绵绵不绝。
程映虹对苏俄十月革命时期的历史挖掘,是网络上的抢手读物。对于苏俄十月革命的介绍,中文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尽管如此,程映虹的许多短文还是以其独特性引人入胜。我就读过他写的许多文章,如“高尔基从‘海燕’变为‘乌鸦’的故事”,“列宁的齐人之福”等。还有一篇文章我已经记不清标题了,但还很清楚地记得内容,那是谈“十月革命”后苏俄妇女的悲惨境况,她们不仅没有在这场宣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分享到任何“胜利果实”,她们的肉体反而成为“胜利果实”被苏维埃的革命者按等级任意分享。
如果以为程映虹的长处只是写些小文章披露一下共产主义运动中那被刻意掩盖的阴暗面,那可就大错特错。那些小文章只是程映虹在完成大作品的同时,将大历史的边角余料顺手拿来雕琢的小品而已。作为一位有眼光的历史学者,他的真正功力还在于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史、尤其是对毛时代“输出革命”时期那段国际共运史的宏观把握与深刻分析。在分析“反右”与“文革”时,中国人一直有一个见仁见智、说过千遍但其实还是没有得出合理解释的问题,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文革”这种今天看来无异于自毁的运动?程映虹的研究正好从这个角度诠释了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的国际背景,廓清了这团历史疑云。他的研究不仅展示了毛泽东为了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与苏共“斗法”的历史过程,还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帝王气慨,从“红色高棉”大屠杀直到中共在东南亚国家的“输出革命”。这些东南亚人民不堪回首的痛史后面,处处闪动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身影。这些中国人本应知道的历史,在那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今仍是“国家机密”。作为这些文章的编辑者与阅读者,我能够惦量出这些文字在祛共产主义之魅时将会起到的重要作用。
优秀学者对历史研究的贡献,可分为几方面。一是史料方面的贡献,即挖掘整理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做基础工作。如宋永毅在爬梳“文革”史料多年之后,终于将他整理的文献资料汇集为一个数百万字的资料库,为“文革”研究作了一项利在当代、功在久远的奠基工作。其间爬梳整理之苦、筹划组织之难,作为学术界人大都能够理解。但因此受到中国当局之拘捕,经历牢狱之灾,却是生活于民主制度下的人士绝难想象之事。
二是对已有史料搜集整理,同时挖掘新的历史资料,再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重新做出解释。这方面,一个原非历史学家的华人作家张戎女士作了杰出贡献,无论当下一些毛泽东研究者感觉如何不舒服,她这本书今后都是研究毛泽东的人士绕不过去的一个读本。
三是还原因种种政治因素而被严重扭曲的历史。程映虹对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挖掘研究堪称这一类型的代表。做到这点,看似不难,其实却非常不容易。这是以下几个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从学术的政治需要来说,在当代国际社会,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权利、殖民历史等才是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时髦课题,共产主义运动史早已成为被研究者遗忘的角落。以美国为例,一度贵为显学的苏联研究在1989年之后一落千丈,许多苏联研究专家不得不改做其他研究。此情此境之下,探讨与现实国际政治无关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自然很不容易申请到研究经费,更不是一些学术杂志青睐的题材。
第二,从学术的理论创新来说,自由主义学说早就对共产主义理论做过入骨批判,这方面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其代表作。而对共产主义极权政治批判得最彻底的当属汉娜·阿伦特,她在这个领域的学术成就至今仍难被超越。更兼“冷战”结束之后,自由主义学者们失去了共产主义极权这个大敌而刀枪入库,左派及其同血缘的新左派则因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而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所有这些,使得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不再受到关注。
第三,在中国,由于当局此刻还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口头上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扒粪”工作自然不可能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
就是在这条冷清的小路上,在这块被刻意遗忘的冻土中,程映虹凭借学者的责任感,凭借共产主义受害者要为共产主义祛魅的信念的支撑,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垦垦,从历史尘封中掏挖出一块块历史碎片,努力还原成完整的历史拼图,将本来属于专业圈子共享的成果推向了公共阅读的平台。每当听到映虹在电话中告诉我与晓农,他又发现了新的历史资料,可以做哪方面的研究时,我们也跟着他一道高兴。
但如果将还原历史拼图理解为纯粹的史料整理工作,那是不理解历史研究的性质。一个好的历史研究者,史识、史才、史德三者缺一不可。“史识”者,顾名思义,就是对历史的见解要高人一筹,要能够于细微处见大势;“史才”就是历史研究的能力,要能够将散落在各种资料中的历史片段串珠成线,对历史事件或者人物条陈缕析,最后自成一家之言。更重要的是,凡研究者,从俗入雅易,由雅入俗难。
将一些简单道理装点成高深莫测的学术玄谈比较容易,大多数研究者都有这等本事;但要将深刻的道理深入浅出,把宏大叙事化为普通读者都愿意阅读的文章,还少有学者做到。从这点来说,程映虹还真做到了由雅入俗。而“史德”即历史学家的学术良心。程映虹在美国大学任教,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虽然无政治压力,但有另外一种现实利益的压力。如果他将精力花到一些时髦话题上来,申请研究经费等会容易得多。但出于对母国的拳拳之心,出于对人类经历过共产主义浩劫之痛,他选择了一条崎岖的学术道路。
人类历史上,尽管不少统治者都有篡改历史的癖好,但能够自成一体的建构谎言(包括销毁史料并建构虚假的历史),却只在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发生。而且这类国家的统治历史越长,在重重谎言之下辨识真相就越困难。我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告别共产主义学说并清理这段历史遗产。我也相信,人们也会记住程映虹这本学术论文集《毛主义革命: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记住这些文章在祛共产主义之魅的过程中所起过的重要作用。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出版。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8 Issue 1
劳尔说: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推荐程映虹新著《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胡平)
2008-01-17
最近,香港的田园书屋推出旅美学者程映虹博士的新著《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程映虹来自中国大陆,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后赴美留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德拉瓦州立大学任教。程映虹博士长期专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九十年代在国内出版了一本《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卡斯特罗传》,殊不料引起古巴外交部的强烈抗议,于是被中宣部下令查禁。后来这本书又由香港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发行。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国际性的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既是国际共运的产 物,并一直受到国际共运风云变幻的强大影响;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共产主义又反过来对国际共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毛时代。遗憾的是,对于后一 方面的问题,国人的研究还很不够。程映虹博士这本《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应是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的最有份量的著作。
《毛主义革命》全书共有十二篇,涉及的题目很广泛。作者讲到毛主义、特别是毛的文革理论 对世界的影响,其中,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最令人发指。这对那些至今仍然崇拜毛,特别是赞颂毛的世界影响的人是当头棒喝。作者还讲到中共和苏共、和古巴共产党 如何在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堂皇旗号下对人心的控制和对自由的侵犯,讲到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为何一度对毛式革命那么迷恋,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巨大诱惑 和危害作出了精辟的剖析与批判。
本书结合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作者尤其善于选取特殊的人物与事件,通过引人入胜的描写,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毛主义革命》一书虽然讲的是毛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但它又反过来加深了我们对毛主义的认识,并进而加深我们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认 识。全书史料丰富翔实,叙述条理分明,文笔生动流畅,读来不但增长知识,而且发人深省。
早先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八九之后,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 中国成了硕果仅存的共产大国,于是有人把这句话改成"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其实这话说得不准确,因为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比中国更不社会主义的 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在经历了堪称翻天覆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改革后,却仍然能保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不变,而且还造成持续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 倒是一个世纪之谜。
本书有一篇专讲古巴的卡斯特罗为什么拒绝中国模式的改革。其中写到卡斯特罗明知社会主义弊病丛生,但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顽固地拒绝 改革,"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书中还引用了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讲的话。劳尔说,他之所以拒绝中国模式的改革,是因为他"不想为把坦克开 上街头负责"。这就提醒人们:所谓中国模式,并非只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诸如此类;中国模式还意味着六四屠杀。
这道理一想就明白。共产党是靠消灭私有制起家的,如今它又回过头来搞私有化,那无异于釜 底抽薪,自己取消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出要求结束共产党专政的民主化洪流。面对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产党都不敢镇压,而不敢镇 压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镇压,是没脸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心虚,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有强烈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重兵在握, 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与人民达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车开上街头,残酷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
我要强调的是,六四屠杀不但是十 分残暴的,而且是极其无耻的。从卡斯特罗兄弟拒绝中国模式这件事,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古巴共产主义的进退维谷,也可以进一步醒悟到中国模式本身的无耻与野 蛮。在所谓中国模式居然受到很多称赞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所谓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良知的肆意践踏与公然蹂躏,不要忽略所谓中 国模式对人权、民主、正义与和平的巨大威胁。
毛泽东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祖师爷——读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余杰)
二零零九年二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南美。在与墨西哥华侨见面的时候,他说,中国能够基本解决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他还指出,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2010-09-02
新华网上的许多愤青对习近平的讲话感到莫名振奋。有人说:“习近平同志就是好样的。道出国人的心声,长中国人的威风。”还有人说:“只有这样的直白才更显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的底气;只有直白才更能表明一个走向强大的中国的鲜明态度;也只有直白才更能让国人感到痛快!”但我看来,这段讲话逻辑混乱、粗鄙不堪:中国人民确实了不起,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党和政府。被人民养起来的党和政府,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反之,将十三亿饥饿和贫困的人民驱赶到全世界去,难道是中国恐吓其他国家的杀手锏吗?这才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思维方式呢。
更何况,所谓“不输出革命”,只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共对外交政策调整的结果。在毛时代,中国可没少“输出革命”,中国“输出革命”的政策,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某些地方此种灾难仍未结束。中共当局从来没有为自己当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向受害的国家和人民公开道歉,如今反倒理直气壮地说,虽然过去我们干过坏事,但现在没有干了,所以你们要对我们感恩戴德,这简直就是恶魔的逻辑。从这段讲话中看出,习近平先生的历史知识相当有限,我想向他推荐历史学者程映虹所著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这本书描述和分析了毛主义和文革对世界上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及其后果,堪称一部中共“输出革命”之历史,正如政治学者吴国光评论的那样:“当代中国任何一位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准的人,如果尚未读这本书,恐怕还不足以说是受过了教育。”
毛泽东为个人野心牺牲民族利益
在人类历史上,毛泽东是比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更邪恶的独裁者,毛泽东主义也是比法西斯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更邪恶的极权主义模式。毛泽东以革命之名,行恐怖主义之实,不仅屠杀本国人民,而且将暴力革命的毒素向其他国家传播。近年来,毛泽东在中国境内的暴政逐渐为人所知,如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面对杨继绳之《墓碑》、杨显惠之《定西孤儿院记事》等著作,任何一个毛派愤青都难以否定铁的事实。但是,毛泽东一意孤行地“输出革命”的政策在中国境外造成的罄竹难书的罪恶,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受贫困折磨的亚非拉国家,被毛主义毒化之后,更是雪上加霜、社会分裂、暴力不止。毛泽东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祖师爷,本拉登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正是一本梳理毛主义如何为祸世界的奠基性的杰作。
作为研究国际共运史方面的专家,程映虹对毛主义的研究,重点不在于中国国内的党内斗争,而在于毛“输出革命”的思想与行动。随着在中国国内说一不二的“红太阳”地位的确立,毛逐渐产生了与苏联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竞争的雄心壮志。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运动,这一运动终止了在苏东共产党国家内部的造神运动,使得赫鲁晓夫本人亦不再具有斯大林那样“半人半神”的身份。毛泽东发现在国际共运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卡里斯玛”式的领袖的真空,便决心让自己不仅成为中国人的“红太阳”,而且成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存在革命可能性的国家的“红太阳”。对此,程映虹分析说:“文革期间,包括文革前数年间,由于毛有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欲望,中共推出了世界革命的总体战略,试图以东南亚和中国的近邻为中心,将中国推动的‘世界革命’辐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为了实现其个人野心,毛一方面不惜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内政。如果说今天中国对第三世界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占有更多的能源和资源,因而被视为一种新殖民主义;那么,当年毛泽东的目标便是让毛主义席卷世界,为达到这个目标,甚至无视国际法准则和外交惯例,中共的驻外使馆甚至成为颠覆所在国政府的巢穴。在《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中,程映虹引用毛泽东与老挝、缅甸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毛说:“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毛还提出具体的建议,你们“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以历史上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说这些少数民族都很能打仗。毛的战略考虑是:利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将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作为东南亚共产党扩大武装时的兵员。至于这些被当作炮灰的中国少数民族民众的生命的价值,这个暴君却从来不予考量。
尼泊尔和印度毛派的血腥杀戮
在西方,毛主义的信奉者多为反体制的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多是坐而论道,至多就是到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去朝圣和取经;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则真有一群毛派知识分子将毛主义付诸实践,如红色高棉以波尔布特为首的领导层大都有留法的经历,秘鲁“光辉道路”领导人古兹曼曾经是大学的哲学教授。浪漫的乌托邦狂想,一旦进入社会实践层面,就直接导致人间地狱的可怕结果。毛主义不仅没有给其他国家带来安定、繁荣和幸福,相反,正如程映虹指出的那样,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各不相同的亚非拉国家,毛主义影响所及,都产生了相似的结果,那就是:“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被颠覆,伦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毁,和平生活被破坏,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极致。”
毛主义不仅契合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而且如艾滋病病毒般污染整个世界。在亚非拉国家,有作为其徒子徒孙的柬埔寨“红色高棉”、秘鲁“光辉道路”、斯里兰卡“人民阵线”等恐怖政权、组织和运动;在西方国家,则有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日本“全共斗”等不一而足。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以及毛泽东本人外交策略的翻转,这些毛派政权和组织被抛弃之后大都灰飞烟灭,步入历史。如今仍然活跃印度和尼泊尔的毛派武装,其残忍与恐怖,倘若马克思复生,亲眼目睹的话,定会魂飞魄散,甚至马克思本人都会被就地枪决。
在印度,毛派分子声名最为狼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由马祖达领导的印度毛派共产党,仿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做法,开展“那夏里特”运动。其主要战略是残杀乡村精英,用马祖达的话来说就是:“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马祖达还宣称:“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时至今日,虽然印度毛派的全盛时期已过去了,但他们还拥有数万名游击武装队员,活跃在全国一百五十多个地区。印度总理辛格指出,毛派叛乱分子“是印度国内安全面临的一个最大考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毛派武装形成了一条从北部与尼泊尔接壤地区绵延到南部卡纳塔卡的“红色走廊”。近年来,毛派分子实施过几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如袭击火车、组织劫狱,还曾经对警察局、议会办公大楼和难民营发动一次协同突击,造成超过三十人丧生,而且大多是被斧头砍死。
尼泊尔的毛派反政府武装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他们残忍地拷打并杀害许多被俘的警察和尼泊尔皇家军队的士兵,驱使孩子参与前线的战斗,“童子军”成为其杀人机器。自从一九九六年毛派武装与政府军发生剧烈冲突以来,已经有四千七百多名尼泊尔人死难。尼泊尔毛派奉行毛泽东“打了就跑”的策略,不时袭击警察哨所和地方政府机构,夺取武器和钱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其领袖普拉昌达时,这个“小毛泽东”侃侃而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一种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集成的科学,是从震撼世界的群众斗争中发展而来的。作为一种科学,它要不断地、持续地发展。‘普拉昌达路线’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根据尼泊尔的条件的运用,也是对它的一种丰富。”就像毛泽东在国庆典礼的程序中自行添加让群众呼喊“毛泽东万岁”的口号一样,普拉昌达毫不掩饰地提出“普拉昌达主义”——所有的独裁者都那么相似,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某种“主义”。
当今中国政府与国外毛派之间的微妙关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陷入四面楚歌的毛泽东转而联美抗苏,一夜之间便与曾经不共戴天的美帝亲密拥抱。这一举措给许多国家本来已经日暮穷途的毛派组织以致命一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毛本人,居然成了毛主义的叛徒,证明毛主义本身就是一朵外表美丽、内含剧毒的罂粟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左翼青年终于梦醒。对此,新加坡毛派首领、“社阵”主席李绍祖哀叹说:“一些同志因为不同意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很快感到心灰意冷。”而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余柱业在晚年则反思说:“马共没有胜利,还算是马来西亚的幸运。万一马共成功,我们会看到柬埔寨的那种局面。”
当年,中共是各国毛派的铁杆支持者。比如,程映虹在分析中共与印度毛派的关系时指出:“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时期却被中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新发展。《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就是习近平力图告别和遮掩的中共“输出革命”的历史的一部分。如今,中共当局冷若冰霜地宣布与各国幸存的毛派恐怖组织划清界限。既然要承担“大国职责”,就要像习近平所炫耀的那样,不能再“输出革命”了。二零零五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公开表示,北京随时准备帮助印度镇压其国内的反政府游击队,他说:“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孙玉玺解释这些毛派游击队持有中国武器,是因为在八零年代的苏阿战争中,中国曾与美国、巴基斯坦一道,给予阿富汗抵抗力量不少支援,“后来,很多武器流入黑市,然后流散四处……”如此这般,便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如果说今天中国国内的毛派多是纸上谈兵的新老愤青,那么经过选举获得政权的尼泊尔毛派则让尼泊尔成为全球惟一公开奉行毛主义的国家。中国的毛派们有福了,在世界屋脊上终于有了一块风水宝地继续实验毛的伟大思想。他们应当立即申请移民尼泊尔,与毛主席的追随者们一同战斗,或者将子女送到尼泊尔去接受无产阶级血与火的锻炼。然而,规定重庆中小学生必须高唱红色歌曲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却将宝贝儿子薄瓜瓜送到资本主义的心脏英国去留学;自称无产阶级剧作家的张广天,不去尼泊尔为热爱毛主席的当地人民免费演出,偏偏拿了欧洲基金会的资助,跑到欧洲去跟资本市场共舞;《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大都拿着来之不易的美国的绿卡,占尽大洋两边所有的好处;声称萨达姆在关键时刻进口了数万本《毛选》的军事评论员张召忠,自己却不愿作为志愿军到伊拉克去跟伊拉克人民并肩战斗,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萨达姆同志被活捉并被处以绞刑。中国真的没有了继续将毛主义撒播到五湖四海去的忠心耿耿的传教士,所以习近平才顺水推舟地作出从此不再“输出革命”的庄严承诺。那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毛主义,是否从此就寿终正寝了呢?程映虹的笔墨好比瓶塞上的那个印戳,只有当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选入程映虹著作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对此一事实感到放心:从此以后,恶魔再也不会从瓶子里跑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