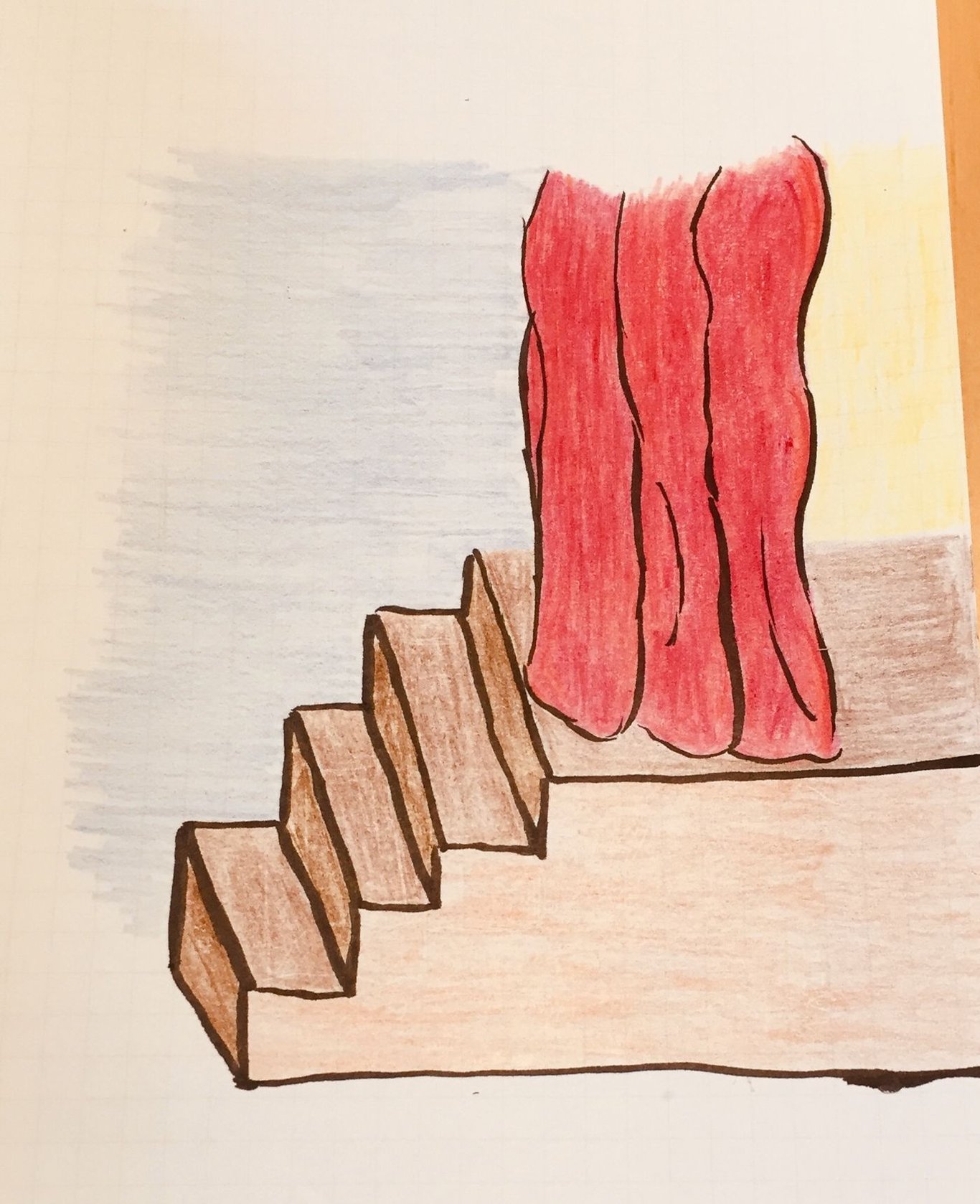首都警報:偏逢
十一個月前,走下飛機的那一刻,巴黎·法蘭西就感覺到事情不對勁。
只是她當時不知道,過了近一年後所有人還是在同一個問題裡掙扎。
這天早上她量出了好幾個月來第一次正常的體溫。她原本決定要久違地出門,去看一場電影,或滿足小小的購物慾(就算沒人看得見她,她仍會當個守法的法國公民把錢留在店裡。)不然前幾天她只能躺在床上聽台北報告這是台灣第七天零確診,再聽她帶點歉意地說「早日康復」。
早上的一通電話更加深了她的好心情——
「三十六點六,」柏林快樂地說,「終於要結束了吧?」
「很有可能喔,畢竟現在不是十五世紀。」
柏林嘆了一口氣。「跟城市綁在一起的壞處就是連自己的身體狀況都要押在當地的醫療團隊和政府上。」
「你說出了我們全部的心聲,」巴黎說,「不過至少我們可以出國吧?」
「對,」柏林一如往常地講出所有事實,「這種型態的病毒不會由我們傳播,這是——妳是不是有電話進,法蘭西?」
巴黎看了一下手機螢幕。「是加萊,我等一下再跟你說。」
一接起電話,加萊的聲音便射了出來:
「福克斯通說發現變種病毒。」
巴黎的全身瞬間僵掉。「在哪裡?」她以空洞的聲音問。
「倫敦。」加萊緊張地說,「目前還不知道詳情,有新消息我會通知妳。」
「好,謝謝。」
加萊掛上電話,柏林的聲音又重新傳出來:
「法蘭西?」
巴黎說不出一句話,從加萊那裡得到消息是一回事,但是要親口說出來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法蘭西,發生了什麼事?」
「變⋯⋯變種病毒,柏林。」
「誰?」
她深呼吸,撥開臉上的頭髮,卻只吐出一個L的音。
柏林立刻會意,「是英格蘭?」他輕聲說。
巴黎沒有說話,她幾乎無法呼吸。
「我必須承認我當時很慶幸黑死病是在義大利爆發,」柏林謹慎地選著用語,「而不是英格蘭。我很確定義大利有重建的能力,但如果是英格蘭⋯⋯」
巴黎當然清楚他說的是什麼,當時她時時刻刻守在失去意識、全身發黑的佛羅倫斯身邊,不時檢查她微弱的呼吸和脈搏。那時所有能夠來的城市也都在義大利半島不敢離開,深怕一不注意佛羅倫斯他們就會立刻斷氣。後來他們才知道,當一個城市失去所有城市功能時便會陷入昏迷,等到城市被重建時才會甦醒。
「⋯⋯我就會更擔心。」柏林把話說完。
巴黎仍然保持沉默。她知道,柏林這句話包含了千言萬語。
接下來的時間巴黎不斷接到各個首都傳來的壞消息,訊息來得太多太快,使她失去了部分的時間感,整天渾渾噩噩地在家裡閒晃。不過她的渾渾噩噩是很拘謹的,她還是讓頭髮、衣服保持整齊,也沒忘記照料陽台上的花——花都可不能讓花枯死。
「妳在想英格蘭?」一天柏林來電時說。
「我瞞不過你。」她嘆氣。
「法蘭西,他不會有事的——妳想想看,以前那麼多瘟疫,鼠疫、西班牙大流感之類的,他不是都撐過來了嗎?」
不就是因為這樣,他才讓我們擔心嗎——巴黎想。但她覺得還是不說的好,尤其是當對象是柏林的時候。
雖然巴黎早已習慣柏林用事實安慰人的方法,但她還是不得不承認這沒有什麼效果。
後來的電話也好不了多少——當巴黎聽到台北說台灣也發現變種病毒時,她甚至斷片了一陣子,回過神時她正在滔滔不絕地糾正台北的法文文法錯誤。
「噢,我的天,」她連忙用中文說,「我很抱歉,台北。」
「沒關係。」台北說,「我知道你們最近都很辛苦。」
巴黎點頭。她還想再說些什麼,但說出口的只有「Bonsoir」。
「午安。」華盛頓說,「謝謝妳過來,多一個人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沒什麼,」巴黎回答,「不過你還好吧?病例不是增加得很快嗎?」
「我還不是最嚴重的,中西部那裡才慘呢,昨天才增加——算了,根本數不清。」
巴黎在電話前坐下。「那我就從東半球開始囉?」
「好。」華盛頓拿起話筒。
以國際換日線為界,他們一個往東,一個往西地打電話給每個國家的首都。自從電話發明以來,「首都電話」一直是個首都間最快速的聯絡方式,而在這次疫情中,它的目的是在新聞發布前傳遞最新消息。
巴黎的手指在清單上游移。馬久羅、蘇瓦、維拉港、威靈頓⋯⋯
一旁的華盛頓快速講著西班牙語。「是的,我很好,」他說道,「謝謝你,哈瓦那。」
過了一會兒,華盛頓小聲地對她說:「抱歉,能幫我說一下嗎?我在這種狀況下不太能講荷語。」
「沒問題,拿來吧。」
「還好嗎?」
「看來又增加了不少病例。」華盛頓苦笑道,順手量了一下耳溫。「三十九點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
「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巴黎問。
華盛頓搖頭,吞下一顆退燒藥。「只能先壓一下,這幾天應該都會像這樣吧⋯⋯」
於是他們又繼續打電話,巴黎清單上的城市也開始往西移動。仰光、新德里、德黑蘭、布加勒斯特⋯⋯
最後,交會在了本初經線。
「Hello, this is Liverpool. Who is speaking, please?」
「哈囉,利物浦,我是巴黎。請問倫敦在嗎?」
電話另一頭換成了法文。「倫敦現在沒辦法接電話⋯⋯」利物浦欲言又止。
「我明白了。其實只是要報告一下美國疫情⋯⋯」說完,她將話筒遞給華盛頓,讓他去解釋新一波大流行的情況。
「我不能說我很意外。」巴黎說,望著躺在病床上的倫敦。
「因為他沒有接首都電話?」
巴黎搖頭。「應該說,在加萊告訴我的時候就知道了吧。」
「也是,畢竟英格蘭的免疫力本來就很差啊。」柏林說。
「還好沒有用到後線。」
「不會用到後線吧,英格蘭又沒有失去所有城市功能。」
「倫敦的免疫系統可能撐不住啊。」巴黎嘆道,「愛丁堡說要看下週能不能拿掉呼吸器。」
「有點困難吧。」
「柏林。」
「嗯?」
「你覺得倫敦知道⋯⋯那些橋的事情嗎?」
「應該知道,他那時候沒有昏迷。」
「唉,偏偏是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