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出国不是一次浪漫的旅途,而是一场资源有限的歼灭战
一
我依然记得2023年3月17日我和伴侣阿米举行线上婚礼的那天,因为中国和美国犹他州时差的缘故,婚礼定在北京时间晚上11:30举行,好朋友们陆陆续续等候在了Zoom会议室里,见证这一场不同于世俗的婚礼。
婚礼就定在我们的出租屋举行,提前三天我们才通知朋友们,大概有20多个朋友能参加在线婚礼,只有一对情侣朋友有空到达现场。我们没有提前做任何形式的婚礼布场,没有设宴款待,自然也没有收取大家的祝福红包。
已经到了睡觉的点,前来参加婚礼的其中一个朋友打了一声响亮而悠长的哈欠,抱着他们的宠物狗坐着打瞌睡,另一个朋友正兴致勃勃地调试相机,她架了一个固定机位,又手持一把微单,十多平米的小屋因此显得隆重起来。我和阿米戴着他们准备的白色头纱,从衣柜中各选了一身白衬衫黑裤子的行头,就等在了电脑旁边。
白天我和阿米都忙了一整天工作,誓词是一小时前抽空写的。看着Zoom里越来越多的熟悉的头像蹦进来,我的手心沁出了汗珠。我在心里默念一遍誓词,又确认了一遍那对花了600块钱买的稀有金属戒指。我咬着嘴唇歪头看了阿米一眼,她似乎读懂了我的忐忑,伸出手轻轻摩挲了一下我的手背。
仪式时间到了,牧师带着一顶可爱的绿色圆顶礼帽出现在会议室,操着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幽默地跟我们打招呼。他非常较真地花了20分钟时间,反复确认婚礼的两位见证人,而后用5分钟快速结束了仪式,我和阿米只有3分钟的时间宣读誓词,交换戒指。一场30分钟的线上婚礼就这样结束了,因为太过紧张,我们出了一身汗,又因为太过幸福,我们都掉了眼泪。

我和阿米是一对女同性恋伴侣,五年前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像是做一道让人头疼的小学数学题,我们分别从G大的北门和南门相向而行,7分钟后正好在校园中心的湖畔相遇。那天我们都化了精致的妆,我清晰地记得阿米的口红唇线勾勒得近乎完美。那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一年后我们会从同学变成恋人,更没想到四年后我们会以这样简单得甚至有点敷衍的方式举行一场婚礼。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唏嘘感叹于我们的爱情,但事实是,我们是心血来潮才决定领证的。我们想要作为配偶前往澳洲留学,虽然知道澳洲是common law,并不像中国一样只认可官方颁布的证书,但为了提升成功率,我们还是打算用法定的方式去确认我们的关系。
经过Apostille(海牙认证)的结婚证飘洋过海而来,证书上印着我们名字的英文花体字,笔画勾连,散发着油墨的清香,沉甸甸的,是信任和爱意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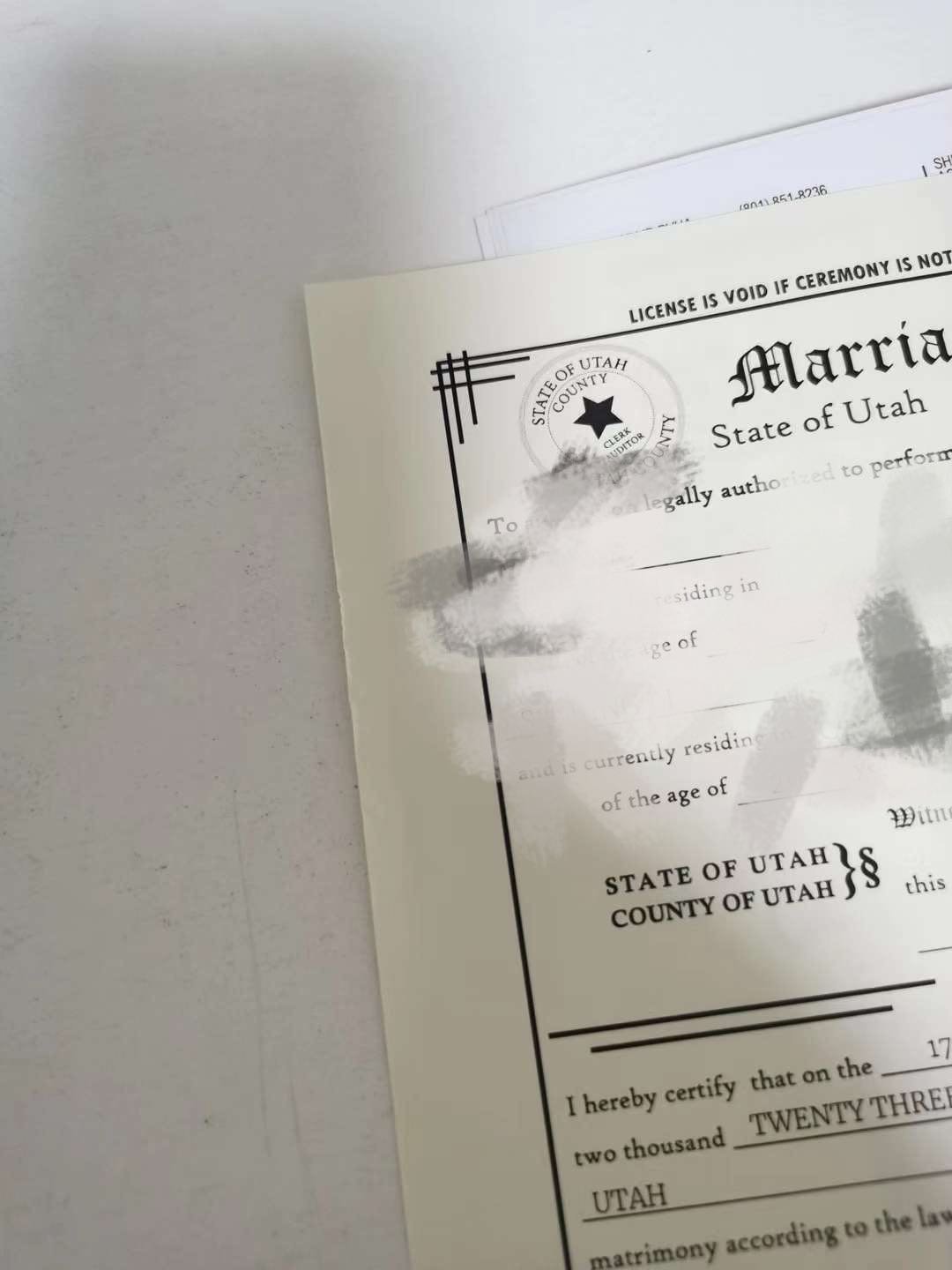
二
2022年下半年,经历三年漫长的疫情封控,和一年做300多次核酸的噩梦之后,我和阿米萌生了出国的想法。
时代的一粒微小尘埃落在普通人头上都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阿米辞职后找工作一直不顺利,投出去的近百份简历犹如石沉大海,眼看着越来越少的存款,她便想着去打工度假,挣一笔钱再做打算,如果幸运还能学一门手艺。
我当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既不会被裁员也不会被降薪,但我并不开心。体制内的领导们热衷于给未婚同事介绍对象,每当他们问我有没有对象时,我就会陷入两难,说自己还没有男朋友吧,我会被介绍给其他男性,说自己有男朋友吧,又是对自己性取向的不忠。但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我通常谎称自己有男朋友。
我的一部分工作跟疫情防控相关,每天陷在红头文件的套话里让我不胜其烦,因工作中的疏漏招致批评。我想到了母亲,一个可怜的乡镇幼儿园园长,因为园里司机师傅的某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而被行政领导骂了半个小时,通报批评挂在了各个工作群里。
10月底,我被单位派去外地做疫情防控的志愿者,每天早出晚归,挨家挨户上门录入信息以及核酸采样。我穿着白色防护服在疫区巡逻,居民看到我就像耗子见猫一样躲起来。一个月后我从隔离酒店回家,进门就看见那只臭猫对着我炸毛哈气,它不认识我了。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起初我们希望通过whv(working holiday visa)的方式出去。恰好10月中旬,新西兰的whv网上申请开放,我打算碰碰运气,特地订了一间电竞酒店,因为时差的缘故四点多起床抢whv名额。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电脑,两个小时过去了,移民局的系统一度瘫痪,最好的战果也仅仅是填完了表单信息,但从来没能提交成功。我尝试点击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的入口,一片冷清,唯有中国的战场厮杀正酣。
2016年朋友抢澳洲whv名额的时候,仅靠自己在网吧操作就轻松拿到了名额,没想到几年过去,新西兰的whv这么火爆。后来我了解到,几家靠服务器和代码运作的代抢中介已经瓜分了这1000个名额,散户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再去网店一搜,一个新西兰代抢名额已经涨到了近万元一个。
我进了几个代抢群,里面正讨论得热火朝天,抢whv名额已然被拆解为一件高精度的工作。哪家中介的代抢成功率最高?有人做了excel表对市场上的几家中介进行对比分析。还有别的办法出国吗?有人详细整理了各个国家的优劣势。甚至有专门的whv网站持续更新相关信息,从澳新两国的whv实时资讯,到whver的国外打工记录。中国人的内卷真的无处不在。
巨大的焦虑在微信群里蔓延,我也被鼓动着花费两万多元购买了两个代抢名额。每次看到购物车里的那两个名额,我就像《药》里的华老栓一样,“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
澳洲whv已经从抢名额改为了随机抽取,是否能中全凭运气,而且抽签时间不确定。新西兰whv下次开放是在2023年8月,预计会比22年更为火爆。果不其然,再看群消息时,几家中介的代抢名额已经一扫而空,最高的溢价已经达到一万五一个。
太离谱了。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说明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23年3月,我和阿米决定不再靠whv出国,咨询过多家中介之后,我们打算通过留学的方式出国,因此转让了之前购买的两个代抢名额。
如果能够成功,我作为主申请人去澳洲读书,阿米作为我的伴侣,可以以副申请人的身份跟我一同出国。我要申请的是硕士,所以学签不会限制伴侣的打工时长,这是一种非常具备性价比的出国方式。
三
在网上扒完澳洲几乎所有的公立大学后,我们将主要目标确定为澳洲一所非八大学校的社工硕士专业。一是因为这所学校7月份还有入学名额,我们能够尽早出国,二是因为这所学校地处偏远地区且学费便宜,日后也可以为移民加分。计划敲定之后,我一边着手准备申请学校所需的各项材料,一边准备英语考试。
除了学历证明、身份证明、资产证明和个人简历外,最重要的材料莫过于persoanl statement,陈述自己为何要出国留学,为何要申请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理由和动机要足够个性化且令人信服,学校才会发放offer。
为了判断申请人是否有移民倾向,移民局也会重点关注个人出国留学的动机和与国内的牵绊,后者通常是国内的不动资产和需要照护的双亲,GTE(Genuine Temporary Entrant)及佐证材料往往会成为下签的关键。
不到400词的GTE前后改了六版才最终定稿,为了证明我没有移民倾向,我把家里的不动产权证、汽车注册登记证、独生子女证、一家三口在国内买的保险都找了出来,阿米也把老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村民建房用地批准书贴进了材料里。说来也好笑,我们出国留学本身就存着移民的打算,却在这里拼命证明自己读完书之后就会回国,就像是一个不得不去圆满的悖论。
为了英语考试出分更快,我选择了PTE (Pearson Test Of English),不同于雅思考试需要长期的英语积累,这个考试更重视应试技巧,只要足够努力,尽可能多地刷题,就能快速达到专业要求的听说读写四个七的分数。

4月份的第一次考试,我的口语成绩以一分之差没能达到要求。距离学校开学还有两个月,但我们还有许多递签的材料要准备,移民局审核材料也需要时间。考虑之后我辞去了工作,专心准备出国留学的事情。
没有了工作收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开支,我们没有续租之前的房子,而是短租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隔间,房租是之前的三分之一,在那里我备考PTE,准备递签材料。
床垫是劣质的席梦思,睡一夜起来腰酸背疼,像是夜里被人揍了一顿。楼上的废水顺着白色PVC管道冲下来,像是无数小沙粒瞬间被抛洒在地板上,每次被这种声音吵醒,我都安慰自己这是好运即将到来的征兆。
虽说要准备的材料非常多,但按部就班地来就没问题。令人头疼的是我的护照状态,因为上一份工作性质的缘故,我被原单位备案为国家工作人员,4月底辞职之后他们没有向公安发函取消我的备案状态,这意味着我即使拿回了自己的护照,也被限制出入境,这无异于对我宣判了死刑。
我赶紧跟单位负责人事的同事联系,沟通的过程就像在博弈,我既不能让她知道我要出国的打算,又要确保她帮我这个忙。我说想趁自己最近有空,带父母去香港澳门旅游,目前的证件状态限制我出入境,既然我已经离职,那这个备案就应该取消了。
万幸她乐意帮这个忙,很快提交了申请,但半个月过去了,护照状态还是没有改变,这让我变得异常焦躁,每天都要登录国家移民局小程序查询结果,三五不时还要催促前同事帮我跟进一下。每次的沟通让人倍感压力,等待的过程更是让人煎熬。一个月后的某天,当我再次点进小程序,发现不再弹出“国家备案工作人员”的窗口了,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经过近一个月的全职备考,我在五月上旬拿到了合格的英语成绩,但由于学校的拖延,我接到澳洲教育部发放的COE(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已经是6月初了,但好在其他材料已经准备得七七八八了。
解决了英语考试和护照的问题,出国体检前又出了一个意外。我们跟一帮朋友聚餐,好巧不巧其中一个朋友后来被确诊为肺结核,我们因此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要去结核病防治中心做X光片检查以及结核菌素皮试。
不幸的是,我的左手手腕处做皮试的位置,在一周内起了一个直径超过20mm的圆形红肿,且伴有瘙痒的症状。我去网上查资料,有人说这是结核菌阳性的表现,又有人反驳说这种情况没问题,无需担心。一时间众说纷纭,让人无从判断,反倒是让我更焦虑了。
结核病是出国体检重点筛查的项目,而且中国在国际上是结核病高发区,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那真的是让人欲哭无泪。
一周后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去看检查结果,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只求各路神仙保佑我的身体不要出问题。医生看了我的X光片,摸了摸我手腕处的那片红肿,又拿直尺量了量,笑着告诉我检查结果没有问题,让我放宽心。
如释重负!又险过了一关。
在准备出国这件事情上,我和阿米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士,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打怪一样通过各种各样的难关。阿米擅长搜集信息并做出决策,而我的执行力强,工作效率高,所有的材料及翻译工作基本都由我负责。遇到挫折,我们相互为对方打气,听到好消息,就一定要为自己庆祝一下。
四
准备递签材料的过程一波三折,让我们见识到了老百姓在中国办事能有多难。
阿米是在农村自己家里出生的,因此没有医院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后来也没有为她补办。公证处规定,1996年后出生的居民要提交出生医学证明才能办理出生公证,这让我们真正犯了难。
“那你跟你父母做个亲子鉴定,证明你是他们的孩子。”
阿米被气得眼睛都歪了。她从小是留守儿童,自己还有个弟弟,近些年她跟家里的关系闹僵了,因此她打算出国的事情是瞒着家人的。况且不仅她父母不跟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他们两人也不在同一个城市打工,做亲子鉴定这件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后来公证处给出了另一种方案,由老家村委和当地派出所各出具一份材料,证明阿米是她父母的亲生女儿,然后带上父母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和阿米的身份证明去做公证。
中间还出了个小插曲,阿米父母当年的结婚证竟然是伪造的,是阿米的爷爷为了拴住阿米的母亲,托关系拿了一张空白证件,自己填了双方的信息,连个红章都没有。所谓法律保障都是做给体面人看的,而满眼望去,农村尽是这种野蛮的故事。
这样不合法的结婚证公证处自然不认,阿米硬着头皮找各种理由,让父母重新补办了一张结婚证,这才将她的出生公证办下来。
最终我们整理了近60份材料,包括40页的两人关系证明,按照学业论文的格式,我制作了目录,按照日常生活、旅行、社交等方面将我们两人的关系梳理了一遍,从租房合同和日常经济往来,到两人合照和每一次出行的票据,每一个可以证明我们伴侣关系真实性的证据都被我贴进了文档里。我进入了跟自己死磕的状态,也许我把材料做得扎实一点,把格式理得清楚一点,下签的几率就会高出一点点呢。
其实最大的难题还是出在钱上,两人出国至少要准备50万元的财产证明,而当时我们手里只有10万元储蓄。我愁得胃炎都犯了,剩下的40万要怎么变出来呢?阿米的家庭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只能尝试寻求我父母的帮助了。
我之前有意跟父母提过自己要出国读书的事情,好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不出所料地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但一段时间过去,他们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表示愿意支持我的选择。
跟父母商量后,我们决定让父亲短期贷款20万,他的工龄长,收入稳定,贷款利息可以拉到最低,无论是否下签,两个月后我们立刻把这笔贷款还上,选择等额本息还款法也不会损失太多钱。父母再向亲朋好友借款10万,我向朋友借款10万,承诺两个月后就还给他们。
赌上全部身家,成与不成就看这两个月了。如果能成,我们手头的积蓄能扛一段时间,到了澳洲就尽快找工作,剩下的路就靠我们自力更生了。
我和阿米决定一起递交签证材料,共同承担下签或者拒签的结果。我们都没有向各自的父母出柜,爸妈一直以为我是自己申请签证出国留学,我骗他们说正好阿米被抽中了澳洲whv,我们两人可以一起出国,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虽然欺骗父母不好,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递签之后是漫长的等待,我们每天都要焦灼地查看好几遍群消息,时不时询问中介目前的进展,一遍遍地刷新网络平台的相关资讯。澳洲移民局对于配偶签证材料的审核会更严格,伴侣两人同时递签被拒的概率要高于单独一人递签。那段时间,我和阿米的额头爆了很多痘痘,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
对于身边的一些朋友而言,出国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他们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穿梭旅居。而对于我们来说,准备出国的过程像是一场歼灭战,我们只能选定一个目标,用尽所有的资源精准打击,其中有处处碰壁的狼狈和焦虑,也有捉襟见肘时不得已的锱铢必较。我们不是有钱人,父母不能负担我们出国的费用,我们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去够那个高高在上的门槛,就像在拼图,努力去凑齐缺失的那一块。
这次机会对我们来说不是尽力就行,而是非如此不可。我已经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债台高筑。失去了应届生身份,阿米找到合适的工作亦是希望渺茫。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如果结果未能如愿,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还能做什么,这就像是一场赌局。
经历了三周焦灼的等待,已经是6月下旬了,距学校开学还有两周。在一个没有预兆的早晨,阿米急切地摇醒熟睡中的我,拿着手机惊喜地喊道:
“下签啦,下签啦!”
睡意朦胧中,我还以为她是在诓骗我,直到看到微信群里中介发给我们的下签确认信,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两人的澳洲签证终于下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澳洲啦!
那天大概是我人生中最为欢呼雀跃的一天,经历大半年的煎熬和准备,我们终于为自己搏回了一次出国的机会,为自己的人生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我们将在一片自由的国土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过一种表里如一的生活。
五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抵达澳洲之后的生活开支,我们打算将国内的床单、被褥、枕头、衣服、小电锅和烧水壶等生活用品人肉背到澳洲。我们整理了三个28寸的大箱子和三个20寸的小箱子,小心翼翼地调整每个箱子的重量,正好用完了两张机票包含的托运行李额度。
虽然拖这么多行李我们俩会比较辛苦,但好在我已经提前联系好了前来接机的校车,我们俩还年轻,可以折腾一下。
我们从成都出发,跟当地的朋友们道别。品尝了四川的美食,去澳洲后就很难再吃到熟悉的味道了。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对新生活的期待。
飞机降落在墨尔本机场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前来接机的是学校的一位东南亚女生,她热情地跟我握手,我大方地向她介绍阿米:“She is my partner。”我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假装自己有男朋友了。
我们提前在Airbnb订好了民宿,房东是一个当地白人女性,拥有一个非常大的house,还有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刚到的前两天,我们办好了手机卡、银行卡和公交卡,在这里生存下去没有问题了。

第一次跟外国人交流时我非常忐忑,阿米竟然害怕得躲在我身后一言不发。我们走进一家餐厅,想要点单时甚至都无法组织一句完整的话,看到全英文的菜单时更是傻了眼。我问服务员有没有意面,服务员面露尴尬但又不失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们是一家西班牙餐厅,因此没有意面哦,但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招牌菜。”
我随机点了两份菜品,吃到中途感觉有些头晕,起初还以为是食物中毒了,后来翻看菜谱才发现,那两份菜都含有酒精,一个是sherry,一个是mojo。来到澳洲的第一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澳洲正值严冬,晚上八点的气温接近零度,我们缩在羽绒服里,步行走回民宿,路边的商店已经打烊,漂亮的小房子在黑夜里影影重重。
澳洲,我们来了。
注:原文发于微信公众号“三明治”,此文为作者重新修改后的版本。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