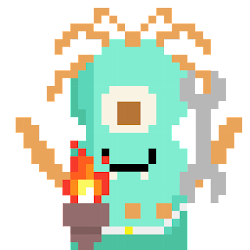促進文化參與的媒介
文化參與性 的概念
關於“文化參與性”的概念(cultural participation)可以追溯到二戰後聯合國成立初期的人權宣言(UN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其中包括了第27項: “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此舉將文化生活定位在基本人權之中,隨之歐洲各國也開始設置政府機關支持文化藝術活動, 例如英國半官方撥款機構的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或者是法國文化部(Ministère de la Culture)的成立等。
法國文化部的第一任首長是作家背景的馬爾羅(Andre Marlaux),他與當時總統戴高樂關係密切而備受重用,是戰後法國國家文化發展的重要推手。他將文化與公民社會概念的關係陳述為 “將文化民主化”(democratisation of culture),意思是文化生活不只是某階層的特權,而應該是 所有人 都能接觸到的基本權利。依循這個想法,文化部在50年代草擬了一個“文化去中心化”的大綱(plan of decentralisation),推行公眾文化普及。與此同時,這個計畫也帶有一種國家自豪感,要將 優秀的 法國藝術文化傳播開去,消除公眾接觸文化活動的障礙。除了從地理上將城市中心的文化資源分散到各個省份/城鎮;在經濟方面政府以降低或取消入場費用的方式使藝文活動更可負擔;以致在建築方面也強調空間的通透性和可達性,成果可見於5/60年代在法國各地設立的十多個文化中心。
從“文化民主化” 到 “民主文化” 的演變
然而這些表面上意圖良好的文化政策在1960年後期受到社會相當強烈的批評,伴隨著當時其他社會問題,官方文化機構被看成是保守精英階層的代表。例如英國藝術委員會的資助方向被質疑為偏向如古典音樂與歌劇等傳統中產藝術類型;而法國文化部對於什麼是“優秀”藝術文化的官方定義也不受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所認同。在法國各地新建的文化中心更在1968年社會運動期間成為被佔據的主要場地,也是民眾對建制(包括文化機構)不滿和對立的表現。
在早期“文化民主化”論述當中的“所有人”其實是一個意義含糊的抽象整體,並沒有意識到社會中的不同社群的差異於矛盾 和 當時正興起藝術文化表達的多樣性。Marlaux在這輪社會運動的衝擊下最終於1969年下台,隨後政府的文化政策方向也演變為更著重多元包容的“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1],指向不再是單一的整體,而是由不同個體組成的群體。這種轉向也拓寬了藝術文化表達的定義,考慮藝文資助對象的方式不再是 單向從上而下的評價定義,同時也容納非主流的藝術形式與流行文化產品。

雖然在20世紀中後期官方文化機構致力於打破公眾接觸藝術文化的障礙,可是一般大眾(尤其是工薪階層)對於文化活動的參與程度還是很低。英國藝術委員會於1980年代初期的一個大型調研指出,公眾不參與文化活動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接觸不到藝術,而只是“不感興趣”[2]。當文化普及在接觸層面上有所改善後,文化參與的問題則變成如何吸引公眾對藝文活動的興趣,尤其是在80/90年代還要與大眾流行商業文化競爭。
以參與為目標的空間設計
因而文化機構更需要爭取公眾參與,而前述的場所概念也就包含了空間設計和功能策劃兩個重點策略,並可參考Nora Sternfeld提出什麼是“真正民主參與”[3](tru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一個基於社區發展公民參與性的論述。套用在文化規劃的討論當中,“公眾參與”可以理解為兩種類型:1 邀請參與(invited participation)- 主要由文化機構/藝術家策劃,邀請特定群眾參與簡單的任務共同”完成“作品;2 自發性參與(self-created participation)- 項目的設計主要是一個框架或場所但並沒有特定的成果目標,其中參與者有更大的決定權去實現他們的文化體驗[4]。在這種自發性的參與中,文化機構與公眾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單向的“製作人 對 受眾”(producer to receiver)而是更具互動性,並通過文化活動達至令參與者充權(empowerment)的願景。
那麼,公眾如何通過文化活動得以充權和讓自身文化被關注,並對什麼文化被生產/製造(produced)有話語權?上篇提及的場所營造案例可以進一步闡述這個從官方主導至公民自發的轉變。倫敦南岸文化中心(Southbank Centre)在1960年代的原意是政府建造公共文化設施讓公眾有更多文化參與的機會,及後於1990年後期至今的更新規劃開始設想如何引導公眾參與公共空間的設計和使用。其中包括在上篇介紹的女皇演藝廳下層的滑板活動場所,由公民團體自發參與而推進的公共空間改造。這個更新後的滑板公園在2019開幕的同時也讓我們思考,最終得到官方認可和資助後這種參與的性質有否被改變?

這裡自1970年代起,在沒有任何政策或機構的支持下自發形成了滑板活動聚集地,在過去幾十年中亦成為了這個亞文化的重要孕育地。直到在最近的公共空間更新設計中,滑板活動已經成為了“被認可”的文化活動,更將原來的場地改造得光潔亮麗。這個會是當初聚集在這裡的滑板使用者的期望嗎?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一個很好思考的切入點:現在來這裡玩滑板的人是否已經變成“被邀請”的參與者(invited participants),還是他們還有空間可以在這裡進一步策劃“自發參與”的文化行為?新的公共空間有著更好的配套設施,滑板場地連同周邊的海濱空間也成為了熱門的公共活動場所,隨之而來也就是關於監控和管制的問題。這點可以在以後的篇章再作討論。
關於文化參與性的文藝經常在公共空間設計和規劃中備受爭論,而在“邀請參與”和“自發參與”的場所之間又該怎樣平衡?在支持尤其是較小眾的文化發展的同時如何能夠避免將文化簡化為一個單一靜態的目標成果?設計師在參與性設計當中的角色可以成為一種媒介,以一個促進者(facilitator)的身分,不是直接提供結果,而是協助各持份者之間形成一種共同願景。按照這樣的路線考慮,場所營造和文化參與更英國被視為一種長期任務,隨著不斷變化的外部設備環境演進。
[1] Evrard, Y. (1997). “Democratizing Culture or Cultural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 27(3), 167-175.
[2] Evans, G. (2016). “Participation and provision in arts & culture - bridging the divide”. Cultural Trends, 25(1), 2-20.
[3] Sternfeld, N. 2013. “The Rules of the Game: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Representative Museum.” In CuMMA PAPERS.
[4] Eriksson, B., et al. (2019). Cultures of Participation : Arts, Digital Media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英文原版:https://threshold.blog/2021/10/05/cultural-participation-and-its-ag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