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卖女性内衣的中国商人
2011年,何伟(Peter Hessler)准备搬去埃及之前,纽约那边的编辑跟他说,你去过中国之后,埃及看起来可能就太平淡了。
他跟何伟说,“开罗简直就是一滩死水。”
那时距离他和他的太太张彤禾(Leslie T. Chang)一起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已经过去4年。作为和平队「96一代」的一员,他和张彤禾——出生于纽约的华裔物理学家之女,在其超过10年的中国生涯留下了5本非虚构作品。

准确的说,那时候他们尚未是合法夫妻。直到去埃及的前一天,他们才领了结婚证,即便那时他们早产的双胞胎女儿已经17个月大了。领证的唯一理由是,他们听说在埃及,如果外国配偶的姓氏不同,当局有时候会刁难不给同居签证。
而促使他们决心尽快出发的原因,则是2011年初埃及爆发的持续运动,执政了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下台。7000年的文明古国突然换了天,可以写的东西恐怕又多又迫不及待。
从2011年10月开始,何伟一家四口在埃及住了5年,那也是 Arab Spring in Egypt 过后的5年,他的观察最终汇总在了2019年5月出版的这本 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中(八旗文化今年1月也已出了繁体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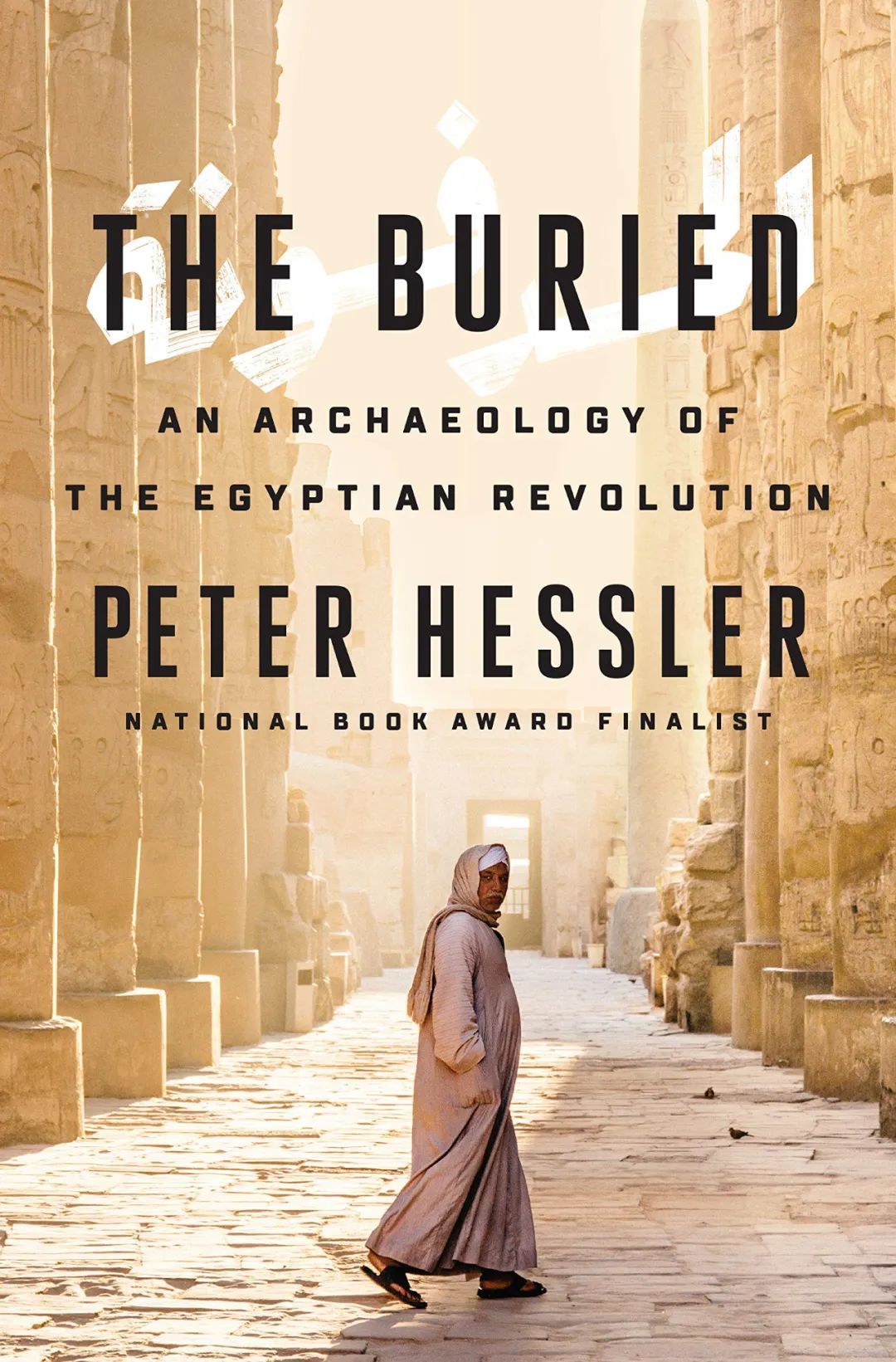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何伟用了两条时间线,向前的是以北边的开罗为主的政局演变,回溯的则是以中南部(上埃及)的卢克索为主的考古进展。好看的还是穿插其中他所擅长的小人物故事。而对于回溯线,不熟悉古埃及历史的人会看得比较吃力,好比像我,在金字塔之外对古埃及迄今还有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于20年前的那部《游戏王》。
也是在这种回溯的过程中何伟觉得,埃及的时间观异于他国。古埃及人用两个词来指称两种不同的时间:「djet」与「neheh」(这两个词无法翻译成英语)。但公元前3000多年时古埃及人已经会书写,之后3000年他们却并未写出“任何在现代意义下堪为历史著作的作品”。
在你我的世界,时间是一条直线,一个事件延续另一个事件;而这些事件的积累,以及有影响力的人所采取的行动,便造就了历史。但对古埃及人来说,时间并非线性,而“事件”则是个启人疑窦的概念。事件是异常,事件是脱轨,事件中断了世界的自然秩序。古埃及人对历史存在方式的定义与我们不同。
芝加哥大学学者雷蒙·约翰逊曾写过,古埃及人“视正常的时间为循环,表述着无止境重复的现在”。他试图解释,这是对埃及南方地貌的本能反应——「neheh」的灵感得自于尼罗河河谷的循环,而「djet」则反映沙漠的无时间性。

另一方面,在法老时代结束之后,这片土地自公元前186年到20世纪中叶,再没有任何一个埃及裔统治者出现——一连串的外来领主,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奥斯曼人,在近2000年掌握了尼罗河。
埃及发明了「国家」的概念,为西方文明订立许多基本的王权表述方式,但它却失去了统治自己的能力。
事实就是,如此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像尼罗河一般形塑了当今埃及,以至于何伟认为连埃及人自己都逐渐看清,这个国家的两次能够称之为现代革命的事件——1952年引领埃及真正独立的自由军官革命,以及2011年最新的这场给埃及带来首位民选总统的运动,在规模上都太过局限,远远还不足以改善埃及的个体生活。
何伟写到后面有这么一句评价:
人在埃及时,无论关注的是选举、非法棚户区、制造业,或是垃圾清运,我的感想常常都是一样的:这么有天分,却这么没组织。
他认为埃及这个Spring最严重的失败之一是,“即便经历了这一切动荡,大多数埃及人却从未被迫重新思考女性与年轻人在自己社会中的角色。”在宗教和民族主义之外,埃及仍然是一个“老年人控制年轻人,男人控制女人”为主流的国度。
不过有意思的是,全书所表现出来与何伟抱有相似观察的人,反而是一群在埃及卖女性内衣的中国商人,尽管他们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视角。
女性内衣是在埃及的中国人从事最多的生意之一。尤其在2009年中埃签订贸易协议后,从中国进口衣服变得容易,内衣市场更是兴盛。纺织和服装业一直是中国在埃及的投资主要领域。
如何解释在一个阿拉伯世界,几乎所有穆斯林女性都戴着头巾,甚至用尼卡布把全身罩得只剩下眼睛,而女性内衣却成为精明的中国商人集中涌入的生意?这正说明了这是个文化相当微妙的市场。

在何伟探访的日子里,中国商人跟他说了很多种可能的消费理由,诸如埃及男人更高涨的性嗜好,他们可能要求女人晚上在家里为其跳舞,诸如“外衣保守,使得埃及女性更讲究外人看不见的另一套衣服。”埃及女性恐怕需要三个衣橱,一个装公共场合穿的衣服,一个装私人场合穿的衣服,还有一个装性感的衣服。但也有一些更实际的理由,除了内衣,中国商人也卖类似睡衣的轻柔服装。在埃及的南方,夏天温度常常超过40摄氏度,但传统标准却要求女子在公开场合裹上层层衣物。
在位于埃及中部的阿斯由特,商贩告诉何伟,有些当地女性一个月会到店里好几次,有几个人买了超过一百套的睡衣与小裤。阿斯由特是其最穷困的省份,也算得上是埃及最保守的地区之一。何伟在那里见识了很多举家来买女性内衣的情形。
但很多时候都只是这些商贩们的猜测,他们只做生意,也不期待能和本地人像何伟一样去做文化交流,他们分不清埃及人的宗教流派,甚至并不能说多少埃及阿拉伯语都靠边生活边学——因为阿语存在词性变化,许多商贩日常都是跟女顾客打交道,以至于出现“一群中国男人用着女性才用的语法说话”。
一开始何伟很好奇,这种文化淡漠是怎么能做好内衣生意的。但慢慢他发现:
中国男子以女性口吻说话也有某种让人卸下心防的效果,而他们也不用假装缺乏性趣。他们对于埃及文化和传统懂得少,关心得更少,这似乎让顾客更自在。在这个遥远的地区,“缺乏文化意识”实际上却成了一种有效的商业策略。
来自浙江的林翔飞(音译)是其中较为成功且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最初到埃及,卖三样中国制品:领带、珍珠和内衣。重点是,之所以选择这些,不是因为他知道上埃及喜欢什么,而是因为它们的尺寸很容易装进公文包里。随后他和他的妻子从女性内衣中赚到了第一桶金,当他发现阿斯由特遍地的塑料垃圾一直无人处理后,2007年他在当地成立了一间垃圾回收工厂,买进了江苏制造的一条生产线,雇了30人,每天能清洗和磨碎四吨的塑胶。
林翔飞把处理过的物料卖给开罗的其他中国人,让他们拿去生产丝线。这些丝线之后会再卖给女用内衣制造商董卫平在内的埃及成衣业者。每当有人把塑胶瓶丢在艾斯尤特路边,这个瓶子就有机会经过中国人三个阶段的加工与制造,之后化为女性内衣回到城里──卖的人还是中国人。
但随着在埃及开工厂的中国商人增多,他们通通发现了一个和中国迥异的难题。在红海与苏伊士运河交汇处的一个小城,有一个中埃合作的工业园区。在一切硬件就位之后,这些工厂主发觉劳工,尤其是埃及女性劳工,比在中国难找得多。一个叫做吴志成(音译)的工厂主告诉何伟,在中国他发现农村来的女孩到厂里工作都是为了逃离家人和家乡,随着她们融入工厂和宿舍的新集体,会进一步想独立和成功。但在埃及,“她们并不想逃离什么,她们只是为了赚钱。”
而她们赚钱是为了购置婚约里明订该买的东西——包括厨具、卧房家具、衣物与其他家庭用品,新郎则主要负责一套房子和主要家电。一旦结婚她们绝大多数就会马上辞职,对工厂而言流动率相应就高启。而在2011政局动荡之后,许多家庭比以往更不愿意让女性出门工作,一定程度上导致埃及每位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增加了15%以上。
我在埃及观察到规模各异的中国商业活动,小至中小企业主,大至拿政府资金的大型计划,而这些活动的结果一概取决于同样的社会议题:女性地位。女性内衣商人用自己的草根直觉,嗅出一种从埃及的性别差异和婚姻传统生财的聪明方法。与此同时,国有的工业区──以生硬的方式试图引入中国的发展样板──却因为女性的不足在失血。

有很大一部分的内衣商人和何伟一样,在2016年离开了埃及,因为当地的经济在崩溃,埃及磅不断贬值。但不管时局如何,他们最终和何伟产生了某种程度上接近的看法:埃及的根本问题与穆斯林兄弟会、军队或总统完全无关──问题在于家庭。
因为在中国呆了太久,以至于何伟自觉不自觉地会把这两个古国产生联系和对比,这多少为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减轻了理解难度,可能因为这5年的体会,又让他在2019年8月回到了中国的成都。
在那早前的6月,67岁的穆尔西在一次出庭中出现晕眩,随后死于心脏病发作。而半年之后的今年2月,91岁的穆巴拉克也走了。埃及没有成为2011年那群人想要的模样。
by 大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