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孤寂更好,可惜只餘下寂寞──讀劉以鬯《鏡子裡的鏡子》後感
這篇寫於1969年的中篇小說,是時年五十的劉以鬯先生中年危機的投影嗎?我心想未必,但讀畢後,在腦海盤旋的只有偌大的「寂寞」兩個字。

承上文《你是「孤」、「寂」,還是「孤寂」?》所論,劉以鬯此篇小說的主角林澄並不孤獨,他擁有一個世人眼中美滿的家庭,林太太為他誕下一兒兩女,又是中環一間商行的老闆,薄有家底,不愁生計日用。但在這樣的背景下的這位中年男主角卻陷入人生中最大的失落,劉以鬯透過他和妻兒間的互動,呈現出他那無人明瞭、滿是空虛的內心。
先論述故事中帶出的一點:「物質」,或者用一個較易理解的字眼「生活豐足」,無助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甚至是導致關係疏離的一項因素。林澄的太太是一個沉迷打牌的女人,有多沉迷?看文中的描述:「如果星期六只可以打二十圈的話,星期日就該打三十二圈。」兒女皆當父親是提款機,二女夢娜看中了一件衣服,打去商行央父親給她錢買,嫌衣服一百八十元太貴的林澄,被女兒說了數句後,回應一句「你到寫字樓來拿錢吧。」而兒子夢麟呢?作者描述得最直白:「對於夢麟,父親只是一棵搖錢樹。儘管林澄怎樣設法在物質上滿足他的要求,但在夢麟的心目中,一把吉他也比父親重要得多。」物質上的供給並沒有為林澄贏得妻兒們的尊重,連遠去加拿大讀書的大女兒夢蘭每回寫信論述近況,寫下心事,也只會寄給妹妹夢娜,絲毫沒有提到林澄。作為父親,他只能依靠女兒夢娜的轉述才能得知大女兒的近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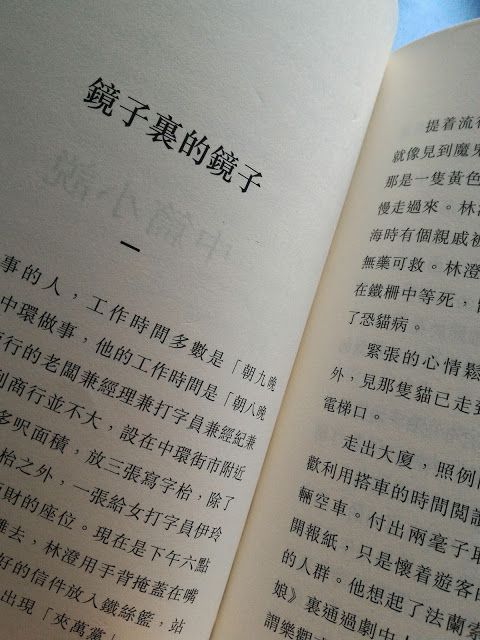
是否因為這男主角本身的粗鄙不堪,才讓這最親的身邊人無視他?雖然他如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對金錢有一份追求的熱心,錙銖必較,在年宵市場選中一盆四季桔,為著三十五元抑或二十七元而議價不斷;因著機票太貴,不願大女兒在假期回港等。但他卻絕不能稱作粗魯乏味、不學無術的人,他熱愛電影,會看杜魯福和費里尼的作品,愛保羅紐曼的戲,懂品評查理.卓別林的偉大和江郎才盡;他習慣閱讀,睡前「總愛抓本書來看」,不是八卦周刊(姑勿論1969年時有沒有),而是能歷經時間沖刷的好作品,故事中他便引用過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葛拉罕姆.格林的《問題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魯迅的《祝福》、達夫納.莫里哀的《群鳥》(The Birds)(希治閣曾改編成同名電影)和詹姆斯.法雷爾所寫的主角龍尼根(Stubs Lonigan)(來自其著作《龍尼根》三部曲);他喜愛音樂,有自己的品味,雖不喜歡新潮的披頭四,認為只是「囂叫與喧嘩」,但喜歡老派的爵士樂和傳統流行音樂(Traditional Pop)類型的冰哥羅士比(Bing Crosby);他沉於思考,具有深度,讀報看到巴黎和談陷於僵局會思想和平的「虛幻」,聽到別人自殺的消息會聯想起世界的冷酷和人的劣根性,他會讀加繆(A. Camus)和沙特(Jean-Paul Sarte)來思索關於人的本質和生存的意義。這樣的一個人,你可以不認同他、不喜歡他,但總不會看不起他,他有其生活品味和情趣。但遺憾的是,他的家人真的看不起他,或許是認為沒有這樣的必要,或許是認為他不值得放心機去認識,他一向就是(認知中)這樣的人,結果是他們完全沒有嘗試去認識、去理解這位最親近(卻不親密)的身邊人。
林澄的寂寞其中來源於,一家人共十多二十年的相處,卻只換來最表層的認知,甚至可能是錯誤的了解,連枕邊人也如是,聽來真是無比的可悲。以林太太為例,她對他已沒有愛。老夫老妻,沒有往日的激情,也應該有轉化後的親情吧?抱歉,真的難以感受到情份。二人在年宵市場準備回家的對話透著一股疏離:
(二人對話梅花間竹,林澄先說話)「不如走去搭電車吧?」「你捧著這麼一大盆花,怎麼能夠擠上電車?」「這裡截不到的士。」「如果不買這盆四季桔的話,搭車是一點因難也沒有的。」「現在只好站在這裡截的士。」「風這麼大,我受不了。」「既是這樣,只好步行回家。」「你一個人走吧,我去搭電車。」
在家中日常的生活也缺乏相處,而林澄是以忍耐的方式去應對:
星期二,林澄放工回家,妻子在打牌。
星期三,林澄放工回家,妻子在打牌。
星期四,林澄放工回家,妻子在打牌。
星期五,放工時,林澄打電話回家,知道妻子在打牌,獨自走去鄰近餐廳吃東西。
星期六,放工回家,又被牌聲包圍,林澄感到難忍的痛苦。
最令林澄難受的,或許是太太對他的不了解。他在二十年前患有「恐貓病」,一見到貓會心驚膽戰。他曾發惡夢,夢到一隻大得超乎尋常的貓在戲弄他,他在夢中最後竟驚駭得再也不願活下去,不想再受心理的痛苦,寧願那貓快些殺死他,其心理病可見一斑;再舉一例,他商行寫字樓附近有一隻貓,林澄間或會碰到牠。有一回,貓去到他辦公室內和他對望,作者用了一節將林澄內心的反應寫得無比細緻:
貓眼有如兩支槍,指著他。
他產生了殺死牠的念頭,他的手,依舊放在打字機上。
打字機旁有一把長剪刀,如果將這把長剪刀擲中那隻貓的話,威脅就會隨之解除。殺死一個人,要償命,殺死一隻貓,尤其是殺死這隻瘦貓,不會被視作罪行。
當他這樣想時,手指已由打字機移到那把剪刀上。情緒緊張,脖頸上的血管像蚯蚓般凸起。「咪嗚」,瘦貓叫了兩聲後,掉轉身,慢吞吞地朝大門走去。
牠從門縫中走出。林澄釋然舒口氣。
身為他的枕邊人,林太太竟忘記了丈夫這嚴重的心理病,有一回在家發現老鼠後,給了林澄一句:「既然發現老鼠,就該養一隻貓。」這樣的家庭生活,這樣的夫婦關係,實在很難給予林澄一種心靈上的滿足,二人就像只是剛巧生活在同一空間,僅此而已。林澄其寂寞之來,確有其因。
林澄的寂寞是日常的累積,但引發他陷入思想這個命題的,是他遠在加拿大的女兒夢蘭,她寄了一封郵簡給妹妹夢娜,信中的一句打動了她並不在意的父親:「忽然感到無比的寂寞,彷彿四壁皆是鏡子,見到的只是自己。」夢蘭身處異地,同房鄰居皆是外國人,語言、文化皆不通,生活無所依傍,自然念掛親人,精神上的寂寞也來得合理。但林澄情況不盡相同,生活上他是家人的依傍,家人也在旁,同住一屋,寂寞是來自這些人的冷漠和疏離,比起大女兒那短時間因著客觀條件無力改變的狀況,但期盼總在前方,只要她語言上過關,開始適應當地生活後,她的情況只會越來越見改善;林澄卻相反,子女越長大,他們的隔膜和代溝只會越厚,太太也沒有想改變現行生活模式(日夜打牌)的可能,我們可預見,林澄不孤獨,但寂寞會隨著年日越來越深。
女兒信中的那句話,原只是內心情緒的反映,這一意象本是虛幻的,作者以這一意象貫通整篇小說,讓林澄不只是內心經歷這意象的衝擊,立時生出反應:「寂寞有如醫生用的針,將痛苦注射在他的血管裡,使他一連打了兩個寒噤。」還讓他在真實的世界中數次去經歷這個意象:
(三)
在中環下車,走進永安公司。二樓男裝部有許多鏡子,站在兩鏡之間,可以見到許許多多重疊的影子。這些影子排列得非常整齊,一個繼一個,伸展到很遠的地方,像兩隊兵。
他見到了許多「自己」。
(二八)
林澄走進那家西服店試衣室時,才知道自己處在一個三面有鏡的斗室中。
從一面鏡子裡,他見到太多的自己。
從另一面鏡子裡,他見到太多的自己。
**********************
(二九)(終章)
他見到鏡子裡的他。
鏡子裡的他見到他。
夜總會的氣氛更加熱鬧,人很多。他忽然感到無比的寂寞,彷彿四壁皆是鏡子。
鏡子外的他離開鏡子。
鏡子裡的他離開鏡子。
這是怎樣的自己?一個在冷酷的世界中找不到快樂,不知道生存意義的自己,沒人理解、沒人想理解、沒人嘗試理解。
到最後,終歸只有他自己一人。或許,這種寂寞,才最傷人,才最累人。

後話:劉以鬯先生著作甚豐,但除了出名的《酒徒》、《對倒》、《打錯了》數篇小說外,其餘便較不為人所認識了。其實劉氏筆耕數十年,精篇甚多,值得細閱。
朋友若有興趣認識一下其著作,好讀網有精心重製、校對和直行排版的《酒徒》供文友閱讀,實功德之舉。內地的大佳網也有劉氏《劉以鬯小說自選集》的試讀,有序言及〈對倒〉的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