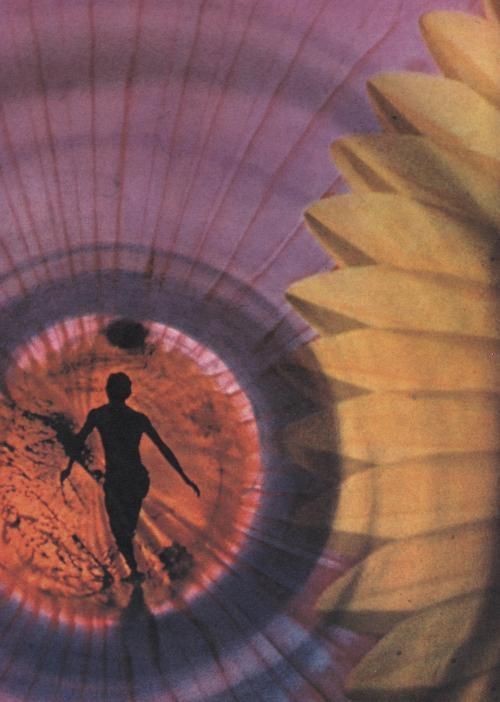奶奶最後的歲月
我沒有了寫日記的氣力,我受到了莫大的刺激。我的精神是異常的,反復的。我奶奶的精神狀況也是如此。
昨天,她竟對媽媽說了謝謝,一整個白天,她沒有和往常一樣睡得醉生夢死,而是睜著圓鼓鼓的眼睛,看向無有之處,舅舅造訪我們家,走之後,她對媽媽說,讓舅舅明天再來玩。我感到驚奇,昨日的她性格大變,一個人老了,會有多重人格嗎?如果我是奶奶的觀察師,也許經受不住這些使人唏噓,哀嘆,驚奇,憐憫的日常。
自半年前從姑姑家接奶奶來休養,她的床周總是有來不及清理的嘔吐物,她以前是一個貪嘴的老太婆,飯前飯後都要吃幾個奶油面包,現在她什麽食物也咽不進去,她麻木的癱在床上,身上長出了好些褐色的痂塊,她無法移動自己,只有等痛苦將自己拽起。整個臥室像一個難聞的小池塘,喉頭從陣陣痙攣中迸射出酸臭的黃色液體,像要把人世間的苦水,一口氣都吐出來。光線閱讀著潮濕的地板,上帝給將死之人留下了一份發黃的情書。
曾經,她最強大的本領是讓我們受苦。她是霸道的,充滿懷疑的。當我回憶過去,想到她我會率先想到一個巴掌,因為一巴掌,是我與她發生的第一種關系,也是後來橫亙在我們中間,占據要領的唯一一種關系。以她教育我父親的方式,自我降生之後也響應在我身上,父母常抱著嬰兒時期的我躲避她的追打,上學前,我站在她家紗窗門前望向行人來往的戶外,她不由分說就打了我一巴掌,原因是那個路人正在吃東西,我不能看別人咀嚼。除此之外,她還會每年去樹林裏拾撿長長的樹枝,有一回她打發我和她一起撿,她說要尋找修長的、結實的,適合做成棍棒的樹枝。陽臺上有一個專門囤積棍棒的角落,我問那麽多棍子是用來做什麽?她說留著打我用的。我信了,我心裏認為她一直等著我考試失利,或者其他該被管教的理由,來讓這些寶貝棍棒發揮用途。
奶奶無疑是一位統治者。從小,我父母不太管我,我們家的規矩基本都是奶奶訂的,比如從上小學的第一天起,我不能看電視,同學來我家找我會被她呵斥走,打電話會直接被掛斷。飯桌上不能講話,吃飯時手必須端著碗底,盡管碗底是滾燙的,於是,尤其在節假日期間,與她長時間呆在一起,我有一種坐牢的感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舉一動都在她的監視之下。某個寧靜的下午,她發現我作業本上的字體張牙舞爪,抄起棒子教訓了我一頓。一些年頭過去了,我才知道不是只有我經受著這些,爸爸告訴我,她和爺爺一向都是雙劍合璧,而打他的時候是讓他跪下來,捆綁在中學門口,用鞭子抽,讓姑姑的男朋友站在旁邊觀賞。
她的身體被釘在了床上,非常瘦,肢體如長矛,彎曲著膝蓋,骨頭方正,板硬,像一把斜放的交椅,這與她往日高大、健壯的形象對比強烈。還記得她是如何對我們說青春期的她每天走十裏山路,一日三餐只吃紅薯的日子。她的頭發曾經白而強韌,應該在高空中飄舞的白風箏,如今枯黃、稀疏,殘存在擡不起來的腦門上。她幾乎是裸體的,只靠被子遮蓋,皮膚上斑斑駁駁,有時我的眼光會從肋骨的陡坡上消失,放慢速度,媽媽擦拭她下體時,她的生殖器暴露在我面前,儼然是一個松弛的黑色塑料袋,一朵碩大的烏青發黴的爛石榴。我得承認這樣活著,無異於在一個了無生氣的地獄。死神坐在人們即將變成灰燼的遺物上,她們融化、慢慢反射出無色的虛無。那個冬天,竟敢被稱作療養!
我想到她的殘酷和蠻橫,一次又一次送走我偷偷養起的狗兒。趁我上學,她趕到我家來宰掉了我的兔子,待我到家後發現桌上的兔肉,他們正若無其事的吃飯,我只覺得心口霎時停頓,我不再思考,不敢也不願意表達出悲傷和憤怒。她常有一種執拗的表情,表面上看那是不近人情的嚴厲,我從姑姑臉上也能體認那種表情,實際上那是一種從來沒有享受過樂趣的神情,她不懂得情趣為何物,她視一切的友誼為利用。她從不微笑。
在姑姑家住的那半年,開始,我們看望她,她腿腳不便,正漠然的在桌前吃蝦,幾個月後,聽聞她的健康每況愈下,姑姑每天把她鎖在屋子裏,自己泡在健身房或麻將館,飯點再回去弄飯,照顧一個老人自然沒有照顧小孩可愛。電話裏她已神誌不清,以為媽媽要接她來我們家住,爸爸自然是不同意的。她每天好像都有一個新念頭,內容都是重復的,就是她以為我們很快就會去接她,莫須有的記憶和思緒侵蝕了她的頭腦,最後一次去姑姑家看望她時,她的模樣不行了,她的身體癟進昏暗的床褥裏,眼睛空洞無神。我們都心知肚明她已時日無多,而姑姑抱怨著照顧奶奶有多麽令人惡心,她幾乎是咬牙切齒地說,她跪在地上求我奶奶死,不要拖累她,奶奶卻不死。
我和爸媽其實早就於心不忍,奶奶最初的願望就是來我家,由我媽媽照顧,無論她多麽敬畏她自己的女兒,她知道,她希望最後的時光能有一點兒柔情,她的女兒和她一樣,比老虎更殘忍。
奶奶生於上海,她的普通話帶著一股抹不掉的潑辣腔。她說六,是「落」,她說涼快,是「風涼」。至於奶奶是怎麽到江西成家的?據說她和爺爺在監獄裏相識,結婚後生下我爸爸,又離婚了,姑姑和我爸爸同母異父,姑姑的父親又是誰?我不知道。這段背景令我憶起很久之前的過去,在奶奶家我每天望著窗外發呆,那是一片灰色沙漠般的景象,土堆的農房,灰暗的天空,灰暗的街道,垂頭喪氣的路人,奶奶指著其中一棟灰色塔樓說那是一座女子監獄,以後也可能是我的去處。她向我描繪過好幾種未來,譬如成績不好,我會去做街頭清潔工。然而大概是我的成長不如她的期待,我考上重點高中後她並沒有顯露出絲毫的高興,反倒添了一絲沈重。在中考前,她多次遊說我父親,我初中畢業後早點打工掙錢是一件好事。
奶奶的手,一天是癟骨,一天腫的像肉包。她混亂的記憶在反復,她的手也在反復。有時她的手忽然到處亂抓,亂摸,用舌頭含混的包卷著嗓音,面孔猙獰,媽媽一大早就抱怨不休,我不敢進房間。奶奶睡在我的房間,而我轉移到爸媽房間,我悄悄的贊同了衰老作惡的秩序,我想盡可能遠離她的折磨,我不敢去共情,被綁在一個恐慌的夢中。我們都能感到這個春節,死朽的力量對每個人的威脅,爸爸在飯桌上說,她早點走,對大家都好。一會兒後爸爸又像吃了一記怒氣,跑到房間裏刻意在她耳邊咒罵,他盼望著奶奶立刻死,可現在不是一個好時機,人們在新年裏厭惡苦難的人,家裏有老人的害怕老人這時候死去,千萬別現在死,要辦後事,就沒法過年了。如果老人想死,便會受到責罵。爸爸似乎想趁著她最後的聽覺,急不可待的用最堅決的、狠毒的措辭告訴她,她是一個可恨的人,可恨的母親,所作所為都可恨至極,給他帶來一生的陰影。我不知道奶奶究竟有沒有聽到,能不能聽懂,那些語句卻蹂躪了我的心神,我接近精神崩潰了,臉色煞白的坐在書桌旁邊,按下手機的錄音鍵,我無法重復爸爸的惡意,他憋了一輩子,就是為了這番真話,他渾身洋溢著舞臺上才能爆發的能量。
她慢慢腐朽在惡臭中間,在我們的眼皮下失去所有尊嚴,而她已經無法在意了。我希望她早已深陷我們無從探知的,與死神交往的夢中,像一個毫無知覺的植物人錯過我們的談話。否則可能是最糟糕的臨終體驗,在肉體死掉之前,我們先把她的心殺死了。她的心也許早就碎了,也許她就沒有心,她鞭笞過的家人一起掰碎了她的心,如今再不會有什麽動靜。遠處夜色中的居民樓像燃燒的煙蒂,爸爸已經受夠了,抽著煙嘆息:「得有屬於我們的一天」。
奶奶的存在像一團黑色的霧慢慢散盡,我將永遠記得,那天傍晚,她第一次說謝謝,她甚至也想微笑,流露出五官無能為力的慈悲,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人生頭一次感受到了她的善意,抑或說是謙卑,她將死之日難得有一日升起表達欲,在她失去了所有表達工具後,可是如果你看看她的臉龐,你會看見她的眼眶裏全天都含著一滴流不下來,也不收回去的熱淚,除了我竟無人察覺, 因為沒有人會在意一個老的快死了的,不能自理的人的淚。
於我而言,死仍然是一個傳奇。這是為什麽它總在我心中激起戲劇性的悲壯。時至今日,我仍然無法講述死亡,奶奶的葬禮是我爸媽倉促操辦的,姑姑甩下奶奶後再也沒有出現。她死了,話題應該到此為止。我從未經驗過死亡,我只看見過慘狀。巨大的耳鳴聲像那些日子留給我的彌久不散的回音,也像我尚未停泊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