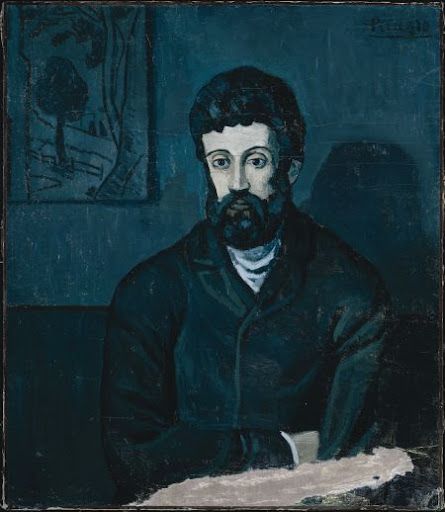貪婪房東小套房
2005年,我24歲。住在香港東區的我,在西區在一間羽毛飾物公司任職文員,每天得花一小時以上轉一次車到公司。說是文員,其實就是什麼都得做,是小公司,除了老闆,有四個同事,兩個男,兩個女,我是其中一個男,年紀我最小,當然從上至文件工作,下至碼頭收貨都是我負責的,另外一個男的是個五六十歲的元老叔叔,不是我做難道他做嗎?那他們都做什麼的?他們是負責把要做的要我做。也不打緊,多難興邦嘛,或許艱難也興人吧。
一次同學聚會,同學間談起各自的近況,男同學A說到他最近自己出來住了,感覺挺自由的,所有以往本來要在黑暗裡做的事都能在光明下做了,說得讓人羨慕,真是他XX的。在回家的夜車上,一想到那些黑暗的事就想搬出來住了,不要想歪了,所謂黑暗的事,就是在微光底下深夜看看書而已。
爸4年前逝世,姐前兩年也嫁了,媽不久就跟現在的男友一起,也差不多兩年了。他們一起不久,男友就經常來我家睡覺,我好像是個外人一樣,從身體語言來看,他們並不太想看到我在家的,媽的男友有意無意的偶爾會說他自己當年18歲一成年,就自己搬出去住了,男孩子嘛,應該要獨立什麼的。就幾年的時間,一家四口的生活就不復再了。似乎是各人有各人的生活,各自忙著。媽和姐,對於年月帶來的變化,並沒有像我一樣總是感覺傷感。
同學聚會後,我想了一段時間,終於決定了搬出去。我告訴媽我的打算,她並沒有說太多,只是說,啊,好啊,男孩子早點獨立也是好的,打算搬到哪裡啊?
於是我就嘗試在工作附近的地產代理進行生平第一次看樓。我說明要求,中年女代理就一副租也好不租也好沒所謂的態度說,有兩個類似的可以看看。說了兩通電話後她帶我到一處唐樓,走四層樓梯到一個有陰暗長通道、左右兩邊各有四個房間的單位,她打開左邊第二個房間的門,把燈亮了,一股淡淡的潮濕發霉的味道,她叫我看看,就沒說什麼。
其實吃和住,我也是個沒什麼要求的人,我認為是這樣。然而那個房間白天就像黑夜,只有一扇沒什麼光能照到的窗子小小的,不睡覺時得全時間亮著燈,十個平方左右,一個小小的浴室連廁所。雖然算是便宜,只要港幣二千元一個月,但看了一會我就說去看看另一間吧。另一間有電梯,在13樓頂層,面積和上一間也是差不多大小,也是一個浴室連廁所,但廳有一面牆是窗子,看來開揚多了,光線也不錯,樓下是個小公園,就爽快地租下了,也貴得不多,要二千五百一個月,已佔去我薪金的三分一多一點。
其後,我用了一天時間,簡單地把所有傢俬都買齊了,一張書桌、一張電腦桌、一張3尺單人鐵的折床、一個薄床墊、一個枕頭、一個住進去後是用過一次來煮即食麵的單頭電磁爐。合共多少錢沒有算,反正就是選差不多最便宜的。過幾天就到套房把兩面牆的尺寸量了,再去買些鐵架和木材,跟朋友借了把鑽,自己動手在兩面牆裝上兩行書架,一共四長行,被書本包圍是最好的裝飾。然後叫了面包車,在家裡把自己的物品一次搬到套房。媽和她的男友並沒有說什麼,只是偶爾瞄一下。
真是頗有效率的,從決定搬出去到租房、買傢俬、裝書架、租車搬東西到真正搬進去,只用了兩個星期多一點。那是2005年的夏天。
搬進去過的第一晚,我靠著窗看著小公園,十來個中年、老年的男人在那裡聚著打撲克、下棋、抽煙、喝啤酒,時而高談闊論,時而吐一口痰。這小公園似乎是中老年男人的天地,沒有女人,很偶爾會有女人路過,沒見過逗留的。這附近是挺多流浪貓的,牠們經常在木高欄上看著這群中老年男人,在想什麼呢,就不知道了。小公園似乎全日都有男人在那裡,只是有時多點有時少一點。
簽約那天,業主譚先生親自來簽,先帶我看一次套房,說明有熱水爐、小型雪柜、窗口式冷氣一部,運作正常。我順道跟他說了鐵閘的鎖是壞的,根本鎖不上,問他能否著人修理一下,他說好的,他會盡快,兩個月後我也提過他一次,他說已經叫人來了,會很快的,結果我住了兩年也從沒修理過,有鐵閘等同無鐵閘。
業主譚先生除了我住的那個間成三間套房,旁邊還有一個開放式的獨立單位出租,有人租,但從沒見過,那單位也有鐵閘,鐵閘後的木門有時虛掩,有時關著,有時裡面有黃色的燈光,有時漆黑一片。後來有次下次回家,鐵閘仍關著,裡面的木門卻大開,看進屋內,非常凌亂,書櫃倒了下來,桌子、椅子翻倒,廢紙一地,衣服和幾雙鞋也凌亂放著,明顯是帶著仇恨刻意搗亂的,也不知什麼原因。如此擱置著三、四天,一天又下班經過,裡面空空如也,剩下兩個煙蒂在地上,兩個都只剩濾嘴部份,煙絲部份一點都不剩,挺利落的。經我分析,應該是租客沒有交租就走了,是業主譚先生親自或找人破壞的,或是在屋內找尋什麼能夠找到那租客。
我住的這裡,是由一個單位分拆成三個有獨立浴廁、沒有房間、沒有煮食的地方的開放式住處。三個房間由一條短走廊連著,共用外面一個鐵閘,我的房間居中間,左右兩邊是兩個中年漢,住了兩年,左邊那個見過三次,右邊那個見過一次。左邊那個早上上班碰見兩次,兩次跟他說早安也當作沒有聽見,也不看你一眼,彷彿你並不存在。還有一次是他在賽馬日把收音機音量開得很大,彷彿整棟大廈只有他一個住,於是我叩他的門說,不好意思,我在這邊工作,能否把容量調小一點呢,他點一下頭,把門關上,確實把音量調小了。兩邊租客的說話聲音就完全沒聽過。右邊那個是不常回來的,大概一個月回來四、五天吧。有次我出門去買外賣晚餐,他門沒關上,應該是剛回來,我看了一眼,似乎是個沒有客戶的房間,即使有也很少,看見一個抽氣扇,沒有看見窗戶,也是一眼能看見整個房間的十來個平方的房間。
香港很多人稱這種住處為劏房,十年前左右吧,那時叫作套房,何以有這種稱呼上的轉變就不得而知。有時候如何稱呼一個事物,跟該事物本身無關,只是反映使用稱呼的人的某些特質,比如同性戀者,有人稱作基佬,有人稱作hehe,有人稱作同性戀者,又比如有人稱呼混血兒做雜種。是什麼類型的人,語言是一個很好的指標,當然也不是絕對的。
從開始住,我一直非常準時交租的,住了大半年,有次工作忙,忘記了,業主譚先生第二天早上九時整就致電給我,可能那時秒針也正好到九時,彷彿是靜待著九時就致電似的。他說沒收到我的租金,我說不好意思,一時忘記了,會盡快的。於是中午吃飯時就快快去匯了款給他。
不說不知,這種套房,電費是比租一個單位貴一點的,什麼原因呢?無他,就是想多賺,你們低收入的,不租這裡,也沒有太多選擇。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就是這樣來的,以往有個朋友跟我說,用八達通乘地鐵,每程是可以省下一點點,反之,用單程票就沒有這種優惠了,而我的朋友,當時窮得連買一張八達通卡也得再三斟酌。富者有優惠,貧者反而沒有,這種情況在社會上比比皆是,像我公司提供的醫療津貼,高級職員外出看私家專科醫生有全費津貼,而低級一點的就沒有了,很奇怪吧?其實這些都是小事,社會上的荒謬還有更大更大的,像是有些人傷人、虐待他人、甚至殺人也不會受到懲處的,真的挺顛覆認知。
譚姓業主會將該月用了的電以度數計乘以每度電多少錢,寫在紙條上放在租客信箱裡。租客連同租金,一併匯進業主的銀行戶口。大概每度電貴平常百分之十幾吧。 第一年的夏天,應該是八月吧,譚姓業主把度數和所需電費的字條放進我信箱,是700多元,然而我只有一部冷氣,即使整個月24小時運作也不到這個費用吧,我媽家,幾個人住,三部冷氣,電費也從沒超過700元的。於是我致電譚先生,他說沒有寫錯的,就是這個度數。只能怪我自己大意,容易信人,沒有抄下度數,也只好交了。
說也奇怪,自從我開始抄下度數後,電費就下降了,從沒超過700元。
住了兩年,媽一次也沒有上過來,我沒有邀請她,她也沒有說要想來看看。搬出去住之後,我們也很少聯絡了,偶爾會通一下電話,都是說些必要的事。一個人住沒有人打擾是挺不錯的,能聽著音樂抽煙看看書,其實挺寫意。
兩年後,有個同學說他也想搬出來住,問我是否有興趣跟他合租一個單位,我想了不久就答應了。於是跟譚姓業主說明我不續租了,他說月尾前你把東西都搬走,把鎖匙掛在門後就可以。還有大半個月時間租房搬東西。月尾東西都搬到新居後,就致電譚姓業主,他說ok。第一天早上也是九時整,他致電給我,問我是否已把所有東西搬走了,我說是的。他說,沒有遺漏了吧?有些廢紙之類的東西都可以丟了?我說是的,勞煩你了。
那天下班我想起這事,覺得很奇怪,何以他會特意致電過來這樣說呢?想不通。到晚飯時候,忽然想起,自己有一部中低階的唱機留在那裡,就在窗簾後面,所以搬東西時並沒有察覺。有幾個單位收租的譚姓業主,連這樣一部不值錢的唱機也要貪,想到就無明火起。吃過飯後,我在附近的雜貨店買了兩把螺絲刀,乘車到那單位,打開形同虛設的鐵閘,成功用螺絲刀把房間的門破壞打開,把唱機搬走,乘車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