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灣區做起了律師
不更新文章的日子裏,我成為了律師。
在通過律師執業申請的那天,我去了深圳灣公園散步,一是為“成為律師”這件事終告一段落而舒展眉頭,二是思索今後該如何展業。
不一會兒,灣區日落就出現在了眼前。翻過三十歲後,我每看到夕陽時會忽覺心生虔誠,總想來點總結陳詞,給過往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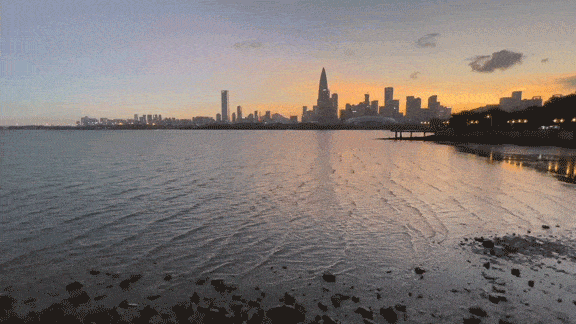
近來,有些人問我為什麼做起了律師,我敷衍地回答道:
“訴訟好比一場戰爭,參與其中讓我興奮,解決問題給我帶來成就感”
“我是個徹頭徹尾的風險厭惡者,杜絕風險發生讓我感到安寧和秩序”
“我打小就有正義之心,對世間不公之事怒不平,我用法律武裝自己”
“要不是為了賺更多錢,誰想摻和他們的爛攤子?我只想認錢不認人”
……
坦白說,我在這些回答中難辨真假,當我看著鏡中的自己時,有時覺得大義凜然,有時覺得軟弱無能,有時也覺得鑽營勢利。但是我必須得合理解釋一切內在衝突,要不然我根本就不適合參與到司法遊戲之中。
我出生在貴州省黔東南州的小鎮,那裏的人運用社會關係、暴力來解決爭議勝過依靠法律規則。在十八歲以前,我從未想過法律可以作為日後的謀生手段。時至今日,黔東南的大多普通家庭不會為誕生一個律師而感到驕傲,他們更希望家庭成員成為公務員、老師、醫生,因為法律能給他們生活帶來的幫助少得可憐。
在童年記憶裏,司法活動像一場場鬧劇。
鎮上的派出法庭設在我們常玩耍的巷子裏,常年開庭的審理案子無非是婚姻家事、繼承糾紛、相鄰權糾紛等案件。每當派出法庭開庭時,小孩子就扒著門縫往裏好奇地看熱鬧,以至於庭審給我留下的長期印象就是,先把兩撥人分開,允許他們用最難聽的話辱罵對方,法官則是憤怒無力地敲著錘子。

那時候還興搞遊街示眾,我記得他們把犯人綁起來後放在卡車車鬥,卡車繞著縣城環路開,道路兩側圍觀的人對他們指指點點,我們小孩子追著卡車一路小跑,生怕錯過每張犯罪人的臉。
總之,童年生活經驗沒有激起我對法律的半點熱情,我倒是記住了司法活動是由憤怒的臉、羞愧的臉、譏笑的臉、麻木的臉等等組成。這些經驗提醒著我,被法律捲入後,註定將帶來強烈的情感滌蕩。
青年求學時期,我想成為一名記者,那幾乎是一種傻裏傻氣的天真想法,寄希望於新聞推動社會進步,同時貪慕“著文章、天下知”的虛榮。但那時新聞界已步入黃昏,很多人都在唱衰“紙媒將死”,如今再看,死掉的並非載體,而是內核。
我甚至報考了新聞學專業研究生。幸運的是,我的導師在入學時就告誡我:要麼去輔修經濟、要麼去輔修法律,才不算虛度光陰。他說,縱使今後在新聞行業裏跑口,也能跑贏同行,若不做新聞,還能另謀出路。
我遵從了他的教導,一邊應付新聞學的課程和作業,一邊自學起了法律。那幾年,北京各大高校進出管理相對寬鬆,我也擅於和門衛們磨嘴皮子,這讓我得以流竄於各大法學院的課堂。
回想那時,仿佛過了兩倍的人生,起早貪黑只為了接近法律之門,就如同自己小時候扒著派出法庭的門縫一樣,忍不住地塞著腦袋往裏看。

有年冬天,我在P大的法理課上,聽著臺上老師講“Lawyer Personality”一課,他如時空旅行者般引經據典,從美國的霍姆斯大法官講到法國的托克維爾再講到德國的馬克思·韋伯,講“以法律為業”的人具有何種特質,講追隨自己天命(Calling)所需的激情和理性,聽得在座學生如癡如醉。
多年後,一位好友回憶起法理學課堂時感歎道,“那是理想主義燃燒的一個冬天”。如今,當我翻看當年的課堂筆記時,寫的不少隨筆都讓我覺得臊得慌,但有一句意味雋永:
法律,是一種並施熱情與眼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木板的工作。
也就是在法理學課堂上,我萌生出或許可以從事法律職業的想法。我在第二次通過了司法考試,意味著半只腳踏入了法律職業的大門。
研三那年,深圳一家大公司法務部提供一個“法律&媒體”交叉專業背景的實習崗,經幾通電話面試後,我就來到了深圳。
這是我在深圳的第五年,過去我幻想搭著大公司這艘巨輪開啟法律職業之旅,覺得一定會順風順水。但現在的我好比是荒島上的魯濱遜,剛紮好了木筏,就推舟入海。當然,這感覺並不壞,畢竟船槳在我手中,我可以選擇靠岸的碼頭。
我不再像青春年少時那樣,覺得人生有很多試錯機會,我反倒認為,其實人生能允許犯錯的空間很小,早一步或者晚一步都可能與想要的失之交臂。
疫情三年裏有一年,我辭去了公司工作,加入了一家年輕時心儀的新聞機構做起了記者,圓了當初想從事新聞工作的願望。
我也常常會想,若沒有當初導師的耳提面命,沒准在新聞行業待得更久。我那些輕盈易碎的理想主義念頭,一定會被強大的地心引力拽回地面,或者隨著蠟作的翅膀融化後,咣當墜地。
選擇做律師之後,我面對的世界變得非常具體,我面對具體客戶的具體麻煩,在他們傾瀉敘述的大海中尋找關鍵事實,從過往案例中打撈經驗,窮盡檢索所有法律規則,告知客戶在什麼情形下會受到處罰,或者會被要求將財產轉移。更重要的是,我得管理好他們對結果的期待,讓他們在絕望和希望中保持平衡。
我領悟到這份工作是如何“緩慢地穿透木板”,也時常感到如履薄冰,一方面是擔憂受託之事稍有差池,另一方面是還得顧及自己這艘小船,避免被風暴給打趴。
我不再狂妄以為自己就是風暴,而是坦然承認了我已身處風暴之中。

我常對朋友感歎道,做律師之後感覺生命都延長了。我在有限的生命裏,參與了他人生活中最為激蕩的部分,從中獲取著寶貴的人生經驗。又因長期身處於風暴之中,得以窺見人在不同考驗之下的真實面孔。所以,在道德判斷上形成遲鈍感變得無可避免,認為事實本身相對於法律規則更加重要,考慮造成的商業後果甚於法律後果。
總之,這座原本就足夠喧囂嘈雜的城市又多了我一個律師。
我想,用不了太多時間,這座城市將會塞滿律師,他們會在街頭巷尾、地鐵車廂、餐廳、咖啡館、酒吧以及無數電子螢幕中對離婚訴訟、勞動爭議、遺產繼承、民間借貸、交通事故、侵權損害、公司治理等等問題侃侃而談,那些受不了的人沒准會喊出“莎士比亞咒語”,但沒人能阻止越來越多的律師參與到個人事務和公共生活之中。
對於新律師而言,深圳是個職業啟航的好地方。這裏的每位船長都憑藉著自己所有的能力、激情以及經驗來應對生活中巨大的動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想要的也就是他們能得到的。
沒有人是大海上的孤行者,我們或將一同穿過風暴,或將於風暴中相遇。
凍櫃,常居深圳的青年律師
微信公眾號:冻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