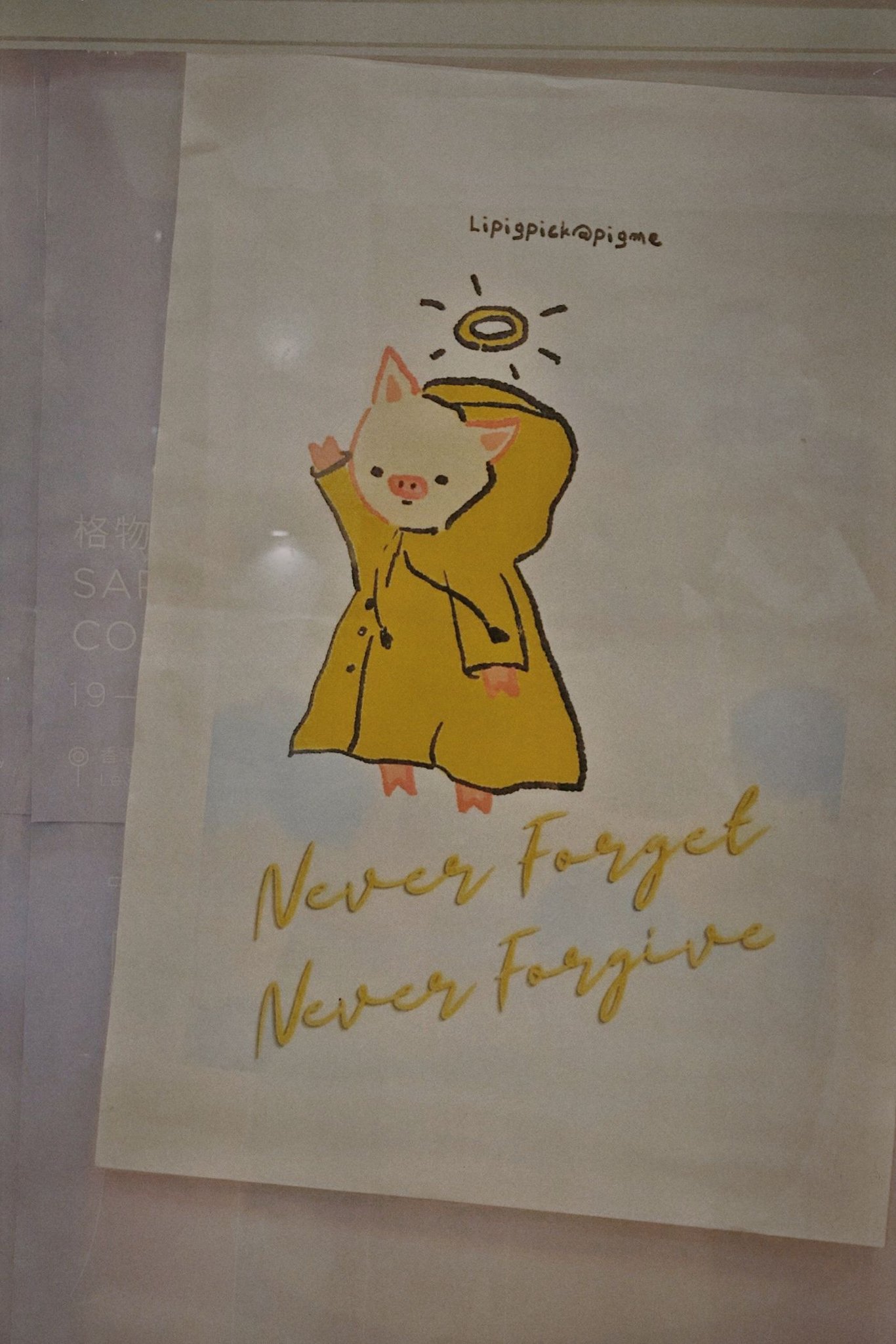中港夾縫中的情感身份:「好撚鐘意香港」的內地人
在近年的香港社會運動中,「和理非非」成為了一個重要概念,但在對於「和理非非」的討論中,我們習慣了將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為中心的動員口號視為某種抗爭智慧,其背後所附著的「渴求秩序、抗拒混亂的中產情感」(許寶強,2018)卻是不易聚焦的思考面向。到2020年的7月1日,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後當天,灣仔北海中心外的電車路上攤開一張寫著「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的大型直幡,直白的粗口口號一時間得到了城中熱烈的回應,民眾經借由這種特別的語言符號聯結起更廣泛的社群情感,亦打破了之前「和理非非」中克制的集體情感狀態。因此,當身處抗爭場域之中的民眾有機會接觸更多情感被釋放的可能,單單從語義解讀「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中包含的情感,僅做出「愛」與「超級愛」的想象或許是不夠的;同時,對香港的情感也不可以簡單地化約為殖民地主義、資本主義或其他強調本質的概念,我們可以擺脫「愛」與「恨」之類的定型,重新了解普羅大眾所擁有的感覺(呂大樂,2007)。
又在我的個人經歷中,對「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抱有情感回應的不僅有香港人,還包括有我在內的一部分人,在中國內地生長和接受教育,卻抗拒投入到集體主義想象下的共同體。我們更願意對香港社會投以期待與關注,盡管我們並未真正地與香港人同步共享集體記憶、經歷時代進程。依據Giddens的「現代自我」的啟示,全球化的現代性進一步加速把在地的影響抽離,我們很難從個人原生的地域背景來斷定自我認同( 甯應斌、何春蕤,2012)。因此,我希望借助一些情感政治的論述,關注一些身處中港夾縫中選擇「好撚鐘意香港」的內地朋友,試圖從個人反思出發,從而理解我們是如何透過這種選擇重組自我的人生故事,更新自我認同。我邀請了兩位同來自中國內地,目前分別身處海外與香港的友人H與L展開對談,我們的對話以分享19年反修例運動的記憶開始,希望記錄這些與城市聯結的個體故事,以此回顧「好撚鐘意香港」口號的背後指向了哪些或明烈或暗湧的情感關鍵詞。
壓抑之下的愛與希望
H:在中國內地的語境下,當我們說起「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就像一個暗號,大家知道其中包含著對香港這座城市追求民主、自由價值的認可,類似於「十萬個黨員潛伏各大城鎮」,我可以找到一班同路人。而且,在廣東話非母語的地區,這種口語化的表達更加地像暗號。在中國那樣「一九八四」般的社會,生活中充滿著方方面面的絕望與無力,我們已經這樣了,希望香港不要重蹈覆轍。
L:我覺得愛是要說出來的,「鐘意」需要被speak out,把情感put into a sentence。「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已經不是一句陳述句,它是誇張化和浪漫化的語句。既然如此,我們可以想想這份愛是說給誰聽,除了說給「香港」這座城市聽,更像是說給在一刹那和你共享這種情緒的人聽,說給你前後左右的人聽,所以此時的「愛」是分享和互通。又因為廣東話的粗口,讓這句話聽上去沒有書面化語言的正式,趨於日常化的表達讓我覺得這句話可以成為一種daily practice(日常實踐)。我舉個例子,當你在香港看到一棵好看的樹,你可以很自然地感歎「我真系好撚鐘意香港」,而不是高呼「光複」與「革命」。
在討論粗口以一種口語化表達聯結起社群情感之前,可以先行討論「好撚鐘意香港」的內地人身處怎樣的社會脈絡。在中國內地,反修例運動被污名化已成不爭的事實,香港成為「充滿暴力」的城市,香港人都是「暴徒」。可以說,這是國家暴力及其掌控下的媒體合力操縱的陰謀,這種陰謀壟斷了「暴力」一詞的使用權,以命名行為展對和平示威的打擊(Judith Butler,2020)。當懷抱自由信念的內地公民無法現身抗爭,一則不含「顛覆」字義的粗口也許可以成為宣泄情感的安全路徑。放諸今日香港,「以愛之名」的抗爭策略也許無奈地同樣成立。正是由於「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經由情感的範式轉移達致了新的表意,社群中的同路人因而心照不宣,這份「鐘意」仍是民心灰落之時湧動的希望。
困惑中的身份反思
H:我覺得困惑可能是每個說「好撚鐘意香港」的內地人都會有的情感,因為身份問題。第一個事情是,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我非常痛苦,家人但凡說到抹黑香港和社運價值的話,我就和他們爭辯。一段時間後我媽問我,你又不是香港人,你在這裡吵什麼吵。我知道媽媽說的是事實,我不是香港人,我沒有立場去爭辯一些事情。爭論沒辦法實現任何有效的溝通,我也幫不到香港人的忙,這樣只會讓自己不痛快,讓大家不痛快。 還有一個事情讓我困惑,我記得19年好像有黃店寫明「不接待普通話顧客」。其實我可以理解部分香港人的敵視態度,因為我覺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內地人對他們來說,都是政治立場上的敵人。但這個事情對於我來說,我不是香港人,我沒有身份上的「同仇敵愾」。關於中國人這個身份,我還想分享一些感受。我現在在國外,自我介紹從不說我的國籍。因為我並不自豪於我的身份,因為很明顯,我感覺中國人的身份被百分之八九十民族主義的國民給代表了,我並不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部分。
L:我記得有次在街上,一顆催淚彈打過來,人群散開。有一個目測比我年長,大概三十歲的男人把我叫住了,搭著我肩膀把我拉住,他因為中彈不太睜得開眼睛,想請我幫忙。當然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可他沒有叫我「小姐」,而是叫了「手足」。我覺得在那一刻,當第一次實打實有一個人在街上用「手足」這個詞稱呼我的時候,我覺得我是很confused的。因為在我當時的意識中,香港人如果分為「手足」和「非手足」,那麼「手足」是香港人的一個下位概念,你首先需要滿足香港人的身份,「手足」這個概念才可以被討論。但不管從什麼意義上來看,我都不是香港人。盡管在街頭的場合,我被他以「手足」相稱是很合理的。 還有一次,我在港大連儂牆貼社運文宣,一個內地學生非常激動地上前和我理論,態度不太友好。於是我們開始用很標准的普通話吵架,我覺得我的口音怎麼聽也不會是香港人,對方應該聽得出來。這時,身邊經過一對去爬龍虎山的夫婦,他們用廣東話問我:「小姐,使唔使幫手?」我又從普通話轉廣東話答覆:「唔使。」當時整個人十分混亂,但這件事情是confused的嗎?我事後再想,那天我感到的confused更多來自於那對好心夫婦問我需不需要幫助,這又跟被叫「手足」的情況有點類似了。但相反對待那位內地學生,我沒有confused,因為我非常深刻地知道我和他不是同一種人,不是同一種中國人,我們並不共享一個身份,這一點我自己特別堅定且清楚。
當身處不願認同的「中國人」與不能成為的「香港人」的身份夾縫之中,我們得到了一個反思的契機:政治概念中會隨附著怎樣的情感( 甯應斌、何春蕤,2012)。進一步來看,當各種意識形態已經無分內外地交織於我們的生存空間之際,我們又該如何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獨立認知框架(余夏雲,2014),如何以一種暫未被命名的身份對我們所愛的香港負有責任?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無法統一概述,因為個體會付諸到不盡相同的行動之中,比如H為社運價值的據理力爭是行動,L走上街頭和貼文宣亦是行動。此種思考進路的意義在於打破情感不屬於理性認知的偏差印象,情感身份中「困惑」的產生便是最佳佐證。
讓「整理情感」成為儀式性的行動
對談結束後,L問我為何要寫「好撚鐘意香港」的題,我回答:因為希望寫一次對香港的愛,算作對這一段學習的作結,她打笑到:「你還蠻有儀式感的。」我為何會有這種「儀式感」,我想一部分來自於《民困愁城》一書中提及Reich所持觀點的啟發:社會結構與個人心理情感相聯系,身體又是心理情感的化身與體現。當人的心理無能時,人不可能成為改變社會結構的行動者(2012)。因此,整理情感是重要的,用文字正式地記下這些情感也同樣重要,很感謝朋友們分享這些個人故事,和我一道完成了這次行動。我們可保有這副可以感知愛、恨、困惑、痛苦種種情感的有用之軀,見字飲水,同步過冬。
參考文獻
>許寶強(2018):《情感政治》,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呂大樂(2007):《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甯應斌、何春蕤(2012):《民困愁城》,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志社。 >Judith Butler,蕭永群譯(2020):《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場域中的倫理》,台北:商周出版社。 >余夏雲(2014):「後殖民」的洞見與盲視:讀周蕾的《寫在家國以外》,華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