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会的角度出发— 谈创造性的公众事件与动员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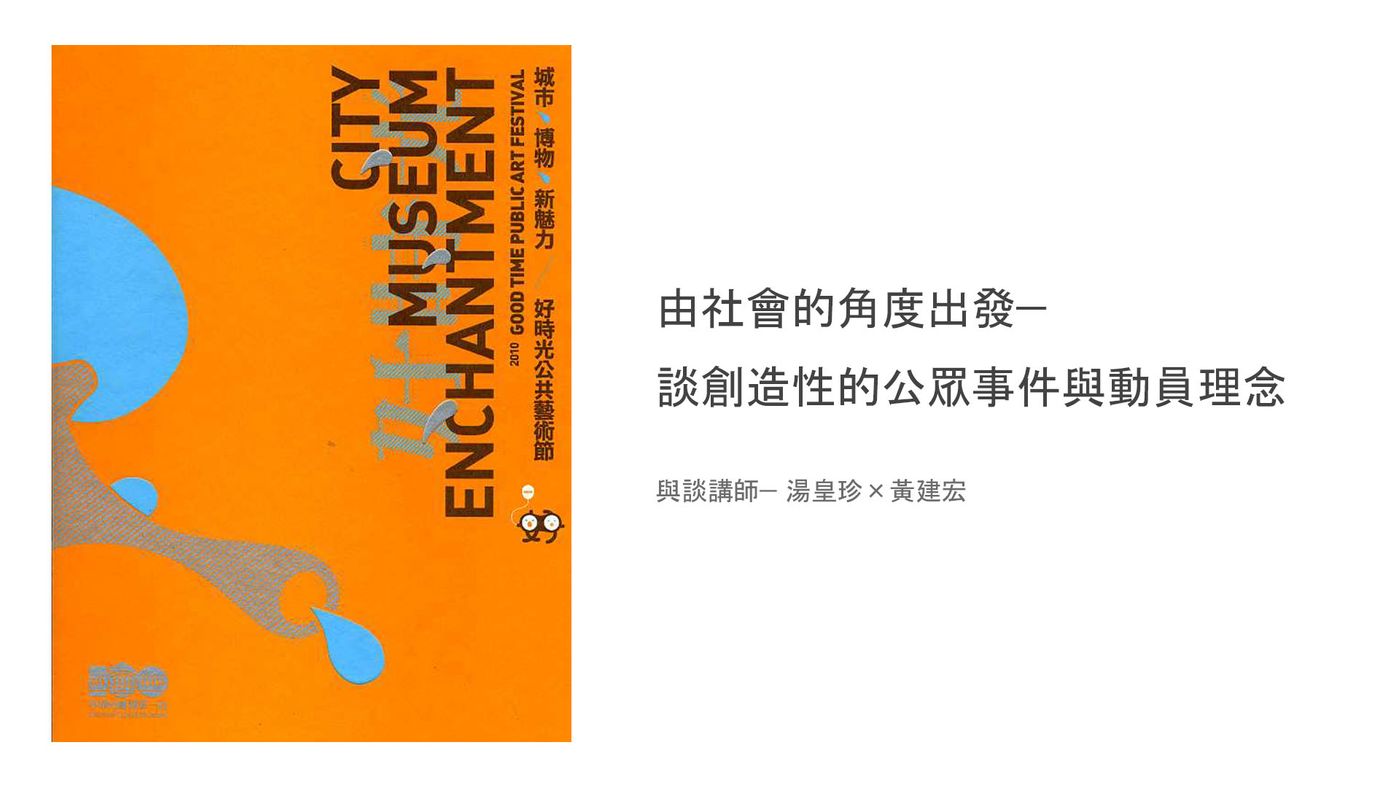
与谈讲师— 汤皇珍×黄建宏
汤皇珍:
1997到2004年我介入争取原为「立法院预定用地」的「华山特区」成为「国有艺文用地」的「华山艺文特区」,此为艺术界发动的第一个以「艺术」为议题的社会运动。在台湾,艺术长久被放逐在边缘位置,「城市中心如何(为何必须)成为全体市民艺术活动的所在」是这个运动的主要议题核心。观察文化城市,如巴黎,如柏林,「其城市中心是公众的更是艺术的」在一个文化国家形塑中的重要性,我们要求:位于台北几近东区中心的「华山」,不应沦为商人炒作的土地或是被政府机关占用,应是一处所有市民可以川流活动的中心节点,进一步更建议文化主管单位善用华山地广、通捷、对于当代跨界前卫艺术展演深具吸引力的空间优势,以此为前卫艺术创作基地,累积质量,以此为「桥头堡」,让台湾登上艺术世界地位的一个途径。
然而文建会在2006年却将华山发包商人,让商人以「文创」任务经营管理十五年。华山易「主」后,商人更名为「1914华山文创园区」,文建会以及管理单位一致绝口不提1997的艺术倡议,文创园区从此场租极高,艺术展演锐减,一笔抹除了艺术界1997以来一股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运动能量。政府交给商人的文创业务有六项:创意影像、创意演出、创意娱乐、创意市集、创意销售、创意教育,可谓「用词含糊目标无极」,只需打出「创意」二字即可入园设场, 经营单位一再号称华山为「文创世贸」,却无人告诉公民:台北市已经有三个世贸,为什么还要舍艺术基地作文创世贸?再再出现一座座巨大无比的世贸园区就能看见台湾什么?
2010年10月31日我经过华山,「华山」正在进行文建会所举办的地方文化宴飨, 我们看见贩卖食物、特产的帐棚遮住了华山开敞的正面,听见高分贝的搭建舞台正在进行拍卖式的贩卖,园里面闹烘烘的还有不知道有几个观众弄得清楚是交易什么、还是表演什么的「华山起义」?妈妈带着小孩如此过着的一个下午就是公众需要的文化生活吗?如果这是 1997年艺术社群拼命为文化台湾所争出的「华山」该担负的前景,试问分布全省的文化中心以及旧日活动中心的庙埕该做什么?商人可不可能摒除商利去设想一个社会的艺术向度?拥有行政职权与预算分配的文化主管机关可不可 能摒除政绩的算计察纳艺术公民的异议, 回归文建最基础—艺术文化的国家向度?这里的命题并无二致,皆关系着台湾的文化定位问题,能不能成为文化国家的国格问题,也正是「由社会群体角度出发的每一份子(全体)」所攸关。这是「华山艺文特区」的争取运动作为一个公众事件的立基点及其理念。
一个社会事件以艺术为议题,一件艺术作品可不可能动员一种社会命题?举两个我的作品为例。首先是发生在四个国家(韩国、台湾、法国、意大利)、横跨五年(2003~2005 年)的「旅行五/一张风景明信片」。这行动邀请当地参与者跟我进行一趟实际旅行,目的是重拍一张我记忆中的台湾老照片。吊诡的是: 记忆中的影像(照片)不会出示,代之以「我对这张照片的记忆陈述」,以文字陈述影像,陈述并流转于不同语言的翻译与重重转述当中。出发之前我与意愿参与者会先行讨论这张我记忆中的老照片,成员齐全后,约定一日旅行,到达选出的海边,参与者便在模拟人物动作的拍摄瞬间跌入「照片场景」 —我对这张记忆中照片的记忆时空。这一趟虚实互渗的旅行关系了一群人,一群四地的参与者,建构了一场由语言、影像记忆、想象与文化的集体串流,甚至充满沟通与旅行实践的历程。这其中介入了公众性,文化的扩演,更扣紧 了语言、影像、传译、沟通落在社会学面向的艺术命题。当然,这是行动艺术在公众性介入以及对意识型态集体撞击的扩张企图,其动员目的是要求艺术的。近来, 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看见艺术的能量,也纷纷借用艺术手法来行进其社会运动,然其动员目的却是要求所属社会主张的。手法互渗,但本质不同,我认为并不可混为一谈。
回到艺术作品对公众意识状态的冲撞,接着我以2009年四月迄今(座谈时间是2010年11月)所推动的「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运动以及「旅行九/远行的人」(2010 ~2011年)作品计划间相互关系,进一步阐述一件创造性公众事件的发生。我们见人常问:「你在哪里工作?」对于已有辨识度的职业:如老师、新闻记者、律师、医师等,你的回答,你的身分,你的社会位置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当一个艺术家面对「你在哪里工作?」的问题,当你回答:「我是艺术家。」这个认真的答案却让人恼怒,让人认为:你完全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对于非艺术家的「他人」而言,艺术家是一个工作吗?艺术家是一个职业吗? 艺术在工作吗?艺术家可以是一个工作吗?对应他者投来的眼光,艺术家对于自己的创作工作是怎么自我认知?是一个职业?是一份专业?是一份志业所以不是职业?艺术家无时无刻不在工作所以不需以工作来界定?有多少艺术家自然而然的回答「我是艺术家」?
政府机制怎么看待艺术家?被视同第一:无业,第二:没有在工作,所以没有「靠行」也没有「兼职」的艺术家会收到没有工作必须强制纳保的「国民年金保险」。再者,对于「工作」定义的官式界定:工作等于收入。没有收入就是没有工作。没有工作—无业,当然也就没有职业(工作)保险:没有职灾、退休金等等工作应有的保障。
「工作等于收入」是资本主义以降对于社会价值的主流思潮,资本主义要求 — 人就要工作,工作为获取有形的金钱,有了钱才能进行消费,资本家才可藉 此循环累进资本。以资本主义价值观推进的社会立基在此「工作螺丝钉」理论: 工作→赚钱→消费的循环,赚钱少就代表他的身分地位甚至才智品德的低落。以 资本主义价值观来看待艺术家,是艺术家无法陈述自己是艺术家 —这是一份专业工作的困境,因为创作不必然有收入,我们工作却不必然有实质的金钱收入。
「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运动,在此出现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没有艺术创作者、没有艺术创作这项职业、当然也就没有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没有艺术, 没有艺术创作者,怎么会有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呢?所以「远行的人」必须展开它的第九个旅行:出发去寻找艺 术存在不存在,艺术家存在不存在?
「远行的人」带着一份问卷出发去寻找艺术。她问:「为什么你是艺术家?是不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一件工作吗?艺术家在工作吗?」身为十数年创作无歇的我,借着这一系列「旅行」的命题,似乎也来到了对艺术意义、对艺术家身份的再度寻访,像一个回问,像追着一个去寻找艺术的自我背影。我,
一个艺术家,迎向社会,迎向艺术。这时候,社会运动与艺术计划相互推扩回授,真正进入我的生命内里,「艺术家是什么?艺术存不存在?艺术创作是什么?」。工会运动的成功也只有在面对了艺术才能解决。「我是艺术家」, 不只是社会学的问题,它还是个人自我意识状态的问题。一个艺术的千古问题。
「工会」运动对于「工作价值」的重新质问,对于劳动体制的突破介入,才使艺术家有成立工会的可能性。不论我们所对「职业」不典型,「工作」不典型,
「价值」不典型—这样一个追寻跟抗博,绝对不是只为艺术家。当有一天你看到一个能容多元价值以及抽象力的社会,你就会意识到我们艺术家为自我社会价值与位置身份的抗博是多么珍贵。对我们原来 (旧有)的事物产生新的思考, 对我们原来的体制价值进行抗博,艺术具有这样的创性能量,对于公众的动员不只是社会运动能做。
黄建宏:
刚在听皇珍在述说他的创作,以及她进行的运动。事实上对我来讲,她提出了一个很复杂的对话和内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艺术家对于一个问题专注的状态。如果问很多人:「艺术家是不是一个工作者?」或者「艺术是不是工作?」其实他可能会去回答,他有他的意见或是什么。但事实上, 这个问题是不痛不痒的,是工作,OK,你还是一样在做,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工作者,你还是在做。其实它本身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艺术的提问,因为她在对这个社会去问一个问题,「怎么去关切的问题」。刚刚皇珍的表达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里面最大的张 力就是「个体跟社会的张力」。对我来讲,艺术家事实上他在这个社会的重要性,是一个不断捍卫个体价值,而且也必须用他不断的能力去表达,透过这个个体价值被承认,或者说被惊起,然后让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个体都承认对方,或者是去重视对方的看法,这是我一个很基本对艺术家的某一个面向的看法。
如果博物馆谈到公共艺术这件事情上面,刚刚所提示我对艺术家的看法,到底跟公共艺术有什么关系?公共艺术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如何透过艺术的能力去讨论公共性?」这问题,之所以公共艺术在这比较概念性的思考里面,事实上是有很多开发的可能性。就台湾最 早的公共艺术来谈的话,最成功的应该就
是铜像吧! 国父和蒋公铜像总是会非常准确的选定好一个场所,在这种象征性的公共艺术中,我们对公共性的想象都还是停留在 —公共性就是大家要有共识。这个时候才会用一个具体的、固态的,甚至可以停留很久的东西,来做为公共艺术这件事情。当民主化开始(90年代之后),在民主化的过程里,这些属于社会共识,或是出现在公共空间里面的东西,很快的被引导到一个所谓健康的社会、开放的社会;可是首先的手段是什么?就是美化。在后现代过后, 艺术家在这些公共空间里面,最后设出来的美化。让大家去相信有一个更健康、更开放、更美的未来。
这次由麻粒所规划的这个公共艺术节,其实给出来另外一个想象,这个想象就像是对应了21世纪的一个民主化,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议题。谁会那么单纯地相信一个更开放、更民主、更健康的社会。如果在一个真实性的感受里面,会发现我们社会里面,世界各地都一样,充满很多的不信任,然后彼此和彼此间的生活越离越远。大家对政治的疏离,特别是公众性的事情,我们把他安排在生活之外。政治和人民、个体的生活,往往透过两个层面去进行链接。一个可能是经济上面,你可以感受到多少的压力,或舒适、或压力,这是经济的面向。另外则是感性的面向,不管怎么样都必须透过它让你愤怒、它让你觉得很美好等,让你有感性这部份的建构。
其实不管是经济,或是感性的话语,我们会发现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今天,照理说大家如果要对公共性这件事情要进行关注的话,这个面向是非常重要的。而当不管是政府或者是财团在运作资金,个体是非常遥远不可能有任何参与感的时候,艺术家在投入公共性的作为上面,有没有办法重新连接跟人的关系?这是我觉得公共艺术和这次好时光里面的项目所专注的试验。谈到公共性,或者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对我来讲比较高的期待就是公共性的创造。
公共性因为很多层面而变成一个吊诡的问题,就是公共性到底存不存在?如果以第四台、脸书和MSN的普遍率的话,那确实早就有公共性了。可是这种公共性缺乏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所有沟通和沟通的模式都局限于它接口上的语言; 而且,总是身体跟身体或是身体跟社会的联系都是有一段距离。事实上这些接口有一个问题,大家其实会越来越像生活在某种品牌里面的状态,而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公共性,也不是最迫切的公共性。因为你可以上网聊,可以交几百
个几千个朋友,但他们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公共性,或是沟通的东西出来。
今天的公共艺术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历史的阶段,就是从铜像、从美化、从互动, 一直到所谓社群,也就是沟通和参与的问题,这是目前公共艺术要特别面对的, 而且观念一定会比行政法官还来的早;因为行政法规它会限定很多公共艺术形式上的开发,相对的也限定公共性的可能,所以这是大家要努力的。
汤皇珍:
在黄老师所讲和我的意见中─其实公共艺术,被大家认知是艺术,那么,艺术比较有趣的是先把个人的个性提出来,个人不明显的时候,公众很难出现一个「公众性」。现在有一种假象,所谓的「公众性」,其实是由上而下来的,譬如说「艺术介入空间」是文建会大力推动的政策,为什么?是谁说艺术要介入空间,为什么公共艺术是美化?什么叫美,什么叫美化?为什么环境要美化? 空间要艺术介入?
好像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可能透过某一种法规、某一种文化政策的导向,或者透过经济的某一种串联,然后形成一个所谓主流,一个目标,然后下压,告诉我们公共艺术都要这样来做。我倒觉得应该反过来想,如果刚刚黄老师讲艺术是有能力帮你的个性显现出来的话,应是个体透过艺术,让大家知道艺术的个体能量;公共艺术其实是充分激发个体,充分激发艺术的概念,才能交织形成所谓「公共」意见。
艺术作品不是赶着把公众性「成果」交代出来,艺术激发每一个个人,不是 急忙去塑造所谓的公众性。诚如前述:观看的方式,不如说是思考的方式;因为思考的方式改变,观看的方式才会改变。它不是美化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美化?」「美是什么?」的思考。我觉得这样的公共艺术比汲汲营营于艺术的 公众性还要重要。
配乐「Roaming, but I am still myself」编曲: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