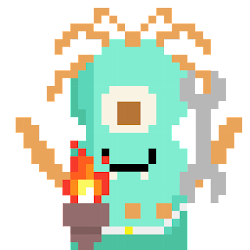兩個雙年展與兩個美術館
雙年展是否必須要回應年代?
與藝術家主題展覽不一樣,雙年展包含了不同藝術家不同年代的作品,往往是反映當下城市社會狀況。策展團隊和美術館人員設定一個題目,或挑選館藏或邀約新作,去回應特定主題。
上海雙年展由PSA主辦,題目為「宇宙電影」,策展人Anton Vidokle 提出上海這個城市分別和「宇宙」和「電影」有著莫大關係[1],甚至連結到人類時空的大主題,老實說從一個觀眾看來確實有點虛無飄渺的感覺⋯⋯

這種虛無的感官確實被策展和展覽設計團隊努力呈現出來。大廳從入口被黑布包圍燈光昏暗,剛進場的時候有點讓人搞不懂方向。進場是一個巨大裝置群組,重構各種太空衛星組建。接著的展覽裝置大多在同樣幽暗的環境下展出,跟隨規劃動線觀展的過程當中還遇上不少迷茫的觀眾開著手機小燈探路😂。當然展覽策劃設計是會有特定路線,可是這種相對不靈活的觀展經驗不禁讓人有一點不自在,也好像跟近年強調的藝術參與性有點背道而馳。
然而展覽還是充滿著有趣的作品,包括多個錄像作品也回應「宇宙電影」的主題。以建築師而不是藝術評論者的角度,我更關注的是整體空間場景的體驗與感受,而個人而言這次的焦點反而是其中一個裝置利用了美術館保留發電廠的大煙囪佈置的一個作品。這是平常不開放的區域,從展廳到達煙囪頂部入口還要經過屋頂外部空間,反而變成了展覽最獨特的風景。一月上海的天氣有點灰冷,加上非假日遊人不多,正好切合這次到訪PSA和這個展覽的體驗。

相比之下,台北雙年展則與一般沒有太多噱頭的藝術群展比較接近。策展主題是「小世界」,思考後疫情時代個人與世界以的關係及溝通等議題。同樣地加入音樂和多媒體的元素,可是在北美館這個傳統博物館展廳主體還是有繪畫雕塑或裝置作品。
美術館建築只是擺放藝術品的容器?
究竟是主題/ 場地/ 城市/天氣 還是什麼原因,進入台北市立美術館就是有一種舒適感。其實同樣是在大型開放環境的一棟獨立建築,從捷運站走過去還是有一段路,不過花博園區的攤販和練習街舞的年輕人也許讓到達過程多了一點生氣。

北美館建於1983年,正值戰後各國政府重建並開始投入公共藝術建設的時期,也是台灣第一座公共美術館。建築設計同時承接著現代主義尾聲的方正簡潔並注重公共空間的開放性,景觀四面通透的大廳在公園當中更像一個客廳,作為非付費區域公園遊人隨時隨意可以來坐。

雙年展的展品和不同展廳的空間結合得很舒服,B1層的封閉空間有音樂場地,1樓的高挑大空間是大型裝置和組團作品,還有雙年展委託創作的大幅馬賽克對應中庭。2樓的井型空間結構形成多個小空間及牆面,個人尤其喜歡的是在末端帶大窗的展廳,窗外的林蔭和夕陽正好與輕巧的藝術品互相融合,不知道是否藝術家或策展人的精心安排。

為什麼我喜歡北美館
每次去台北總是有原因到北美館走走,以前住上海的時候也經常去PSA,兩個都是相對熟悉的地方。這次正好一週內看兩個雙年展,放在一起好像還看到了兩種城市/文化空間的對比。
工業建築改造為文化建築是近十多年的大潮流,PSA也仿效Tate Modern將發電廠變成美術館,可是同樣的概念細節處理起上卻大有不同。北美館則是再早期公共建築的模式建築,沒有特別花俏的白盒子建築倒是隨時間慢慢演化。也許就是那個年代關於公共藝術空間的理念融入了建築當中,經歷不同年代美術館管理和策展慢慢滲透出來的人性化空間讓人感到舒適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