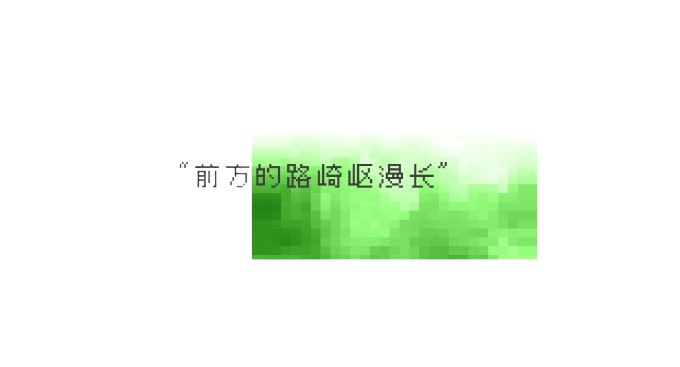让我离散的情绪漂浮在角落里
五月好。
原本的计划是把“香港篇”先写完,但是删删改改,仍然没决定好如何组织好语言把它叙述明白。而总是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一些话,想要快些写下来。
就把只言片语的零碎片段收集到玻璃瓶里摇一摇,酿成独特风味的罐头好了。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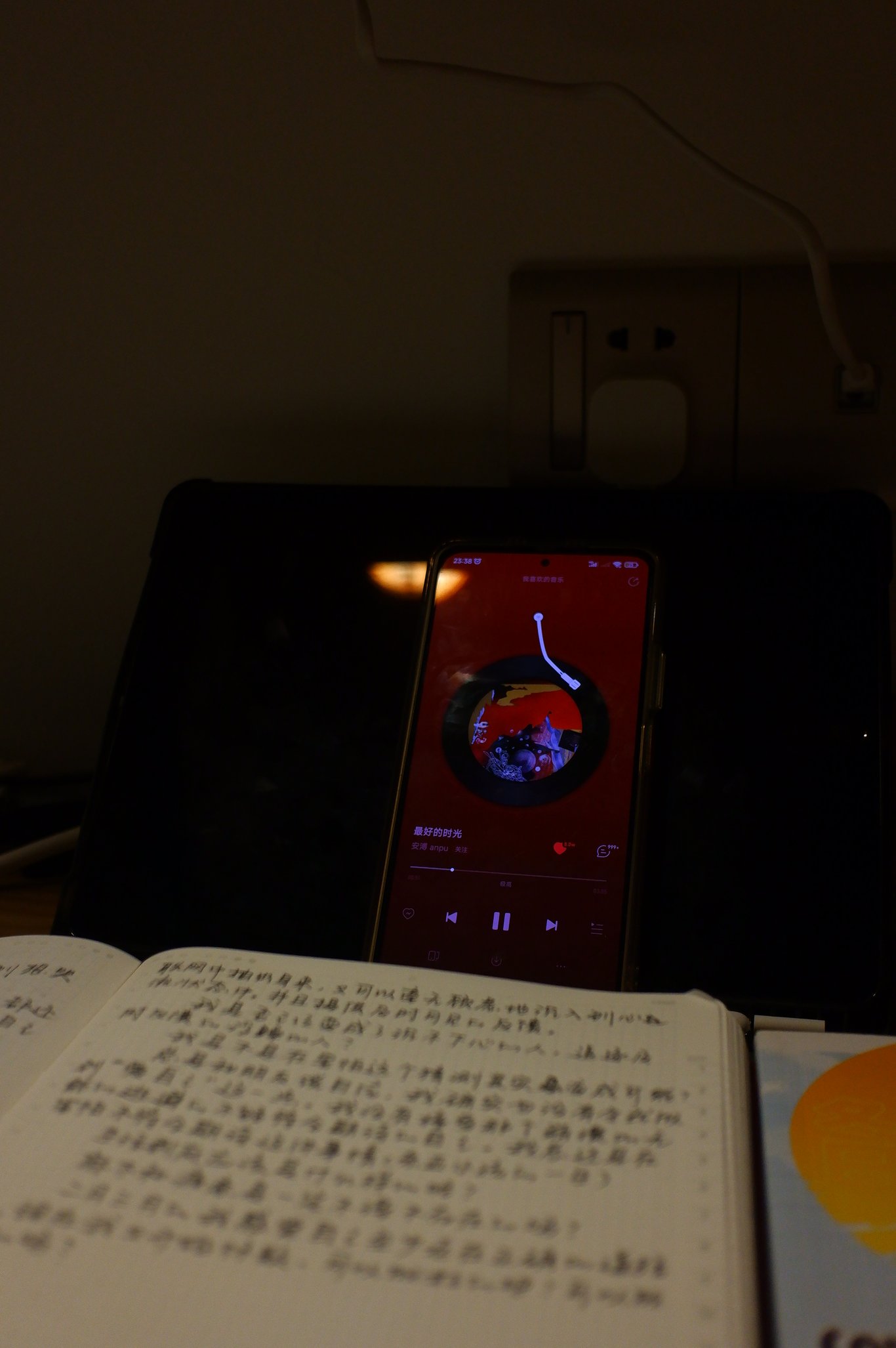
三月份是极其幸福的、“情绪价值拉满”的一个月,彼时值班的频率还没调回到现在两班倒的状态,我因此还有时间写了一篇稿,读完了四本书,和朋友出门逛公园逛展,去了老师家观影,重新磕起了影视剧cp,甚至跑了一趟香港看苏打绿演唱会。
但也正是在三月和四月,由冬转入春的过程中,我的情绪似乎也开始滑落。
或许我应该把它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广州连绵不断的阴雨天和潮湿得让人窒息的空气,归结为春天这个季节带来的百般忧愁和情绪波动,归结为工作转换交接带来的赤裸裸的无意义感。但无论如何,它是出现了。
我发现自己写不出来东西了。
我的自我价值仍然是锚定在写作上的,至少现在是如此。无论写的是什么,日记也好,同人文也罢,哪怕是碎碎念的小段落,那些“想要表达”的时刻,都会让我自在一些。但直到我发现自己“写不出来”的那一刻,自我的空虚才像烟火般在半空中炸开来。
若是单纯是无法表达出内心所想,那还好。前阵子想写一篇无限流同人文,却发现自己对于如何将传统民俗融入情节,如何渲染恐怖气氛一无所知。这种“写不出来”是能够拯救的,正如我搜起了“系统讲解中式恐怖”的视频并且还做了笔记摘录(要是我工作有这种热情就好了)。我可以靠着汲取来换取输出。
但更让人害怕的是生理性的“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失去了除了焦虑不安之外的情绪,也失去了所有感受的表达。我触碰不到它们。
在三月中旬写给佳佳的邮件里,我这么描述它:
「我仍然想要询问学习是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去学习,举目望去想学的东西要么因为太难而不想启动,要么已经短暂地掉出了“想学”的范围。我仍然不明白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爸妈打电话说让我尽快想清楚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我甚至都不喜欢写作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甚至没有办法享受写作对我的赋权了。我没有想要写的东西,也没有想被别人看到的欲望。」
恰好那阵子得知了公众号开放留言的消息,我又忍不住想,如果我当时的账号能撑到现在呢,会怎么样,会有人同我握手吗?
我记得当时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弥足珍贵的,哪怕现在看来大多是一些不知所云的情绪纾解。它们都会被我发到朋友圈,能看到朋友圈评论或是公众号后台的留言,借机和不同的朋友们聊上一两句。
而今,我就像飘浮在幽暗的空间里,蜷缩在我的飞船里,偶尔发出一段断断续续的电信号,不知道它是否会被谁接收。
我仍然是渴望交流的,渴望有人会因为某个字眼而触动,但我的记录日渐变成了向内的记录,我也发觉不会有太多人因为我的写作而停留关切,就像大多数路过的大人不会为蹲在街角看花发呆的安静小孩驻足停留。
于是过去一年我写的长文字越来越少,发newsletter变成了一件安稳的事而不是期待的事,我知道我大概不会收到任何回应。
有时候在想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读者,我也会写得更多吗?
但是让我离散的情绪漂浮在互联网各个角落里,大概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02

公司团建定在了某个强对流天气暴风雨过境的第二天,照例是去爬山,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在出发的当天决定顶着“扣钱”的代价推掉这场活动,留守在办公室值完白天的班。
值完班的时候已经有同事陆续回来了,但我的心情还是一如既往的糟糕。突然想到这一天因为团建不用准时打下班卡——这可太难得了。在经历了一上午一下午的困顿后,我决定,在晚饭前去看一场电影。
说走就走。
电影院离公司不太远,也就十几分钟路程。朋友在群里推荐了《年少日记》,我看了豆瓣的简介也很感兴趣,也选了这一部。
于是哭不出来的所有积压的情绪,都在电影院里结结实实地释放出来。
主角是卢镇业饰演,他的长相跟一位我有路人眼缘的明星相似,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他观感很好。两位小演员的对比让我觉得没有像《怪物》那么讨喜,但也还是灵动的。粤语影片原汁原味的台词舒服极了,念白里的俚语顿时让我掉落到那样一个生动的场景里,逼仄,随意,鲜活。
相较之下中文字幕的质量非常糟糕,正儿八经的表述完全展现不出粤语原句的鲜活感。甚至是不知道畏惧早恋还是恐同,把影片里高中生口中说出的“前男友”一词写成“密友”,真是令人发笑。
故事稍微有点狗血,刻板印象里的父亲和母亲、差异巨大的相处模式、被爱情救赎和在死亡前和解的老套路。不知为何我还是吃这一套,我还是会流泪。
主角郑sir的视角到故事的一半才开始真正翻开篇章。因为一封遗书,他目睹学生在隐秘的角落经历某些不可名状的痛苦,他难以获知的,就像当年的他翻开那本日记一样。
他又因此也经历着自己难以言说的压抑——看到媒体讯息下的评论会气愤地用语音回大段的话回怼,和父亲疏远甚至也变成“不乖”的小孩,和女友做爱后却无法说服自己承担“成为爸爸”的职责。(我对这一段还未ready还不戴套的情节设计耿耿于怀)
这个角色在我这里太讨喜了,他克制,大部分时间善良,他也几乎等到了所有试图和解的结局。虽然十岁的那场死亡是永远无法释怀的事。
他拥有过所爱的每一个人的拥抱,那至少是可触可感的体温,拥有过的那一瞬间无论是冷漠、误解,还是此生的忏悔、别离,都是珍贵的。
我想象过很多次我当老师的画面,不是我站在讲台上教书,而是我如何成为一个他们可以倾吐的人。电影末尾那个一边讲自己的故事一边在黑板上留下电话号码的情节,把它替换成邮箱的话,它曾经在我脑海里上演过很多遍。我也很多次写信给老师,但总觉得还是不一样。
我也想象过另一个人的样子,和电影里的河马有点像。他在初中的阶段陪过我很长的时间,让我可以好好流泪。我因此开始写日记,最初也是因为他。
一部分的我觉得,我有因为这部电影而得到一部分的替代性体验。
所以我甚至可以原谅“是死亡和爱能化解问题”的这个简单归因,可以原谅故事里那么多刻板的异性恋和东亚情节,可以原谅前述的不完美。
03

我是没想到会拖到五月份才想起来这篇未完成的文字。此时此刻耳朵里随机播放刚好又是安溥的《最好的时光》。
这几天由于崴了脚窝在家里,每天早早地自然醒来,感受皮肤上轻薄的一层水汽,听到窗外蝉鸣声起。夏天又要到了。
身体和心理还是处在好像不断掉落小石子的路途边缘,因为有太多应该去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好好地去体验它们。
四月份终于下定决心买了相机,因为不想把拍照当作负担,挑了非常轻便的一款。今天在整理照片时,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最终决定留下的,还是那种暗一些、对比度强一些、模糊的、或是聚焦在某个点的图片。
有点像我的人生底色是怎么回事。
在写作时,尤其是写日记时常常感受得到灵与肉的分离,一旦抽离出来想象出自己的外表坐在那里拿着笔写着自己心理不断往外掉落的语句,就觉得很违和且不真实。那个说着这些话的人似乎不长这样。
ta不是我,而我也不知道我是谁,这些思考又是由谁得出。安慰自己的真的是自己吗?痛苦和快乐的我是否是同一个?
朋友去了阿弥和s去过的饭店,点了他俩点过的菜,给我发来照片。“好吃。你来昆明我带你吃。”又给我发来一树的花,粉紫色轻压在灯柱上就像是把我的心紧紧攥住,让人想要掉下一些眼泪来。
我想起来五一回家时在博览馆拍的照片,有一张是叙述展览者多年来的云游历程,路标上从广州,到梧州,到合山,到天峨,再到昆明。我从相机里翻出来,发给她。
我想,我总有一天会去到一个阳光明媚气候干燥的地方。那里不要阴雨连绵,木头不会发霉,冬天可以冷一点,但也不要冷到轻易把木头冻坏。
我就去做一些木匠活儿,在蓝天底下敲敲打打。

五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