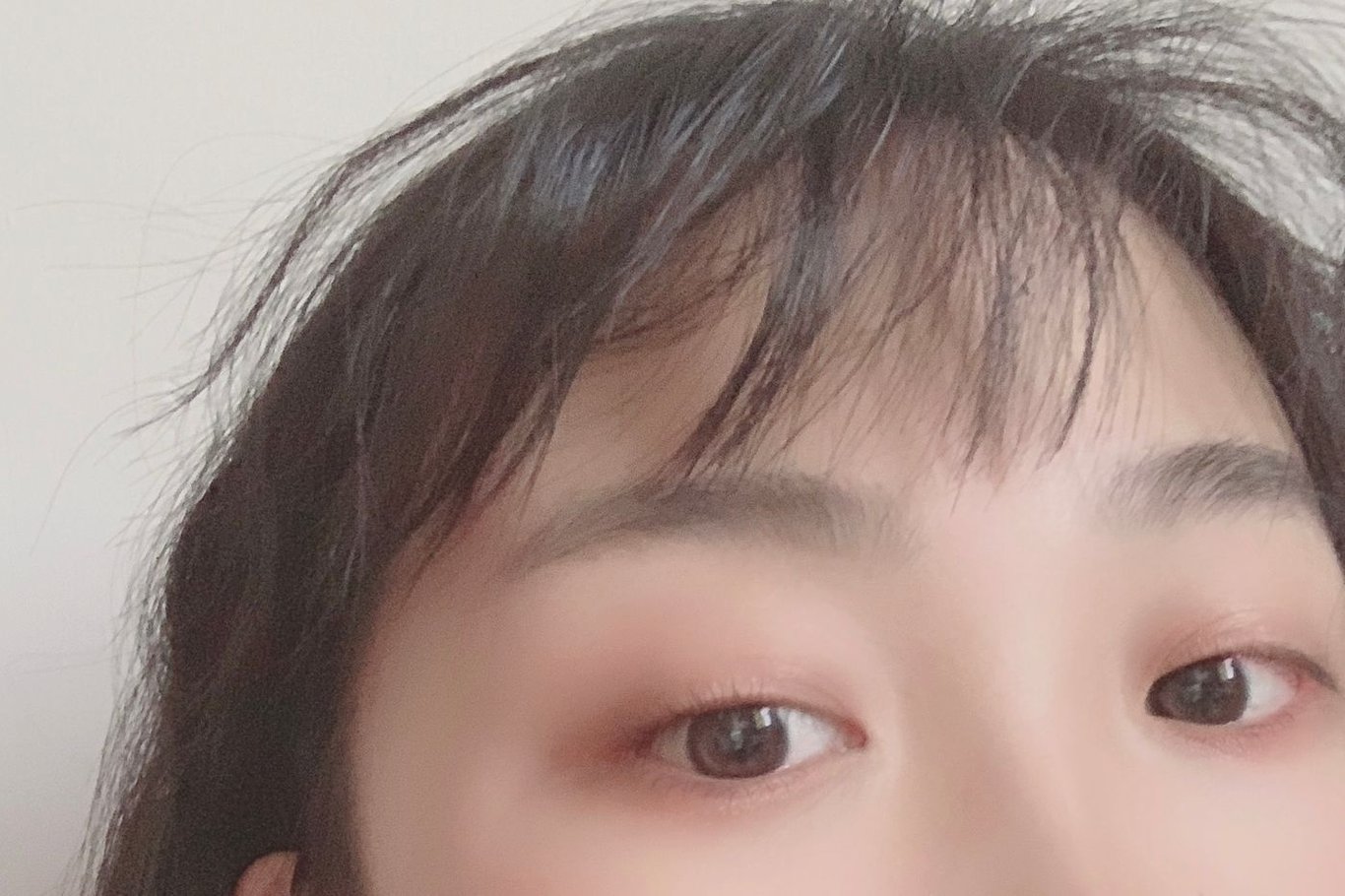我的抑鬱往事

年后的台湾,春季的实习,一切都顺利,都值得回忆。
6月,天很高,云很厚,日日阳光普照。我还能跟同学在4号看纪录片,能读懂杨德昌电影里潜藏的细味,能到财新峰会做志愿者,听人们议论一河之隔的那边。能琢磨“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能在周五的晚上享受一次奢侈的晚餐。
在19年的前半个夏天,我是一个健康且“健全”人。
开始的样子
7月11日
精神的孤寂让现实生活变得凋敝
毫无归属感 我失掉精神的坐标
这次的断档掉线又会持续多久
然而好景不长,在7月到来的第11天,我的心情如同对岸的局势一般急剧恶化。持续六个月的浮沉接踵而至。
又是一年暑假,同学实习的实习,回家的回家,白日的寝室里空空荡荡。除了复习一切的业余生活都被斩断。久而久之,我失去了独处的能力。
堂哥跟我一个学校,之前父母常说家里就一个小孩,亲戚要多走动。然而大多时间都是各自忙碌,在我们大学生活重叠的3年里,也就见过一次面,再无更多交集。
如今他毕业了,我才反应过来,有个哥哥在同个学校多好,需要人开解陪伴之时,他总不会吝啬时间,我也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打扰他。可是他毕业了。
我记不太清滑进情绪漩涡的开始。光记得人一旦陷入情绪会变成满肚牢骚的哲学家。
“希望就像猎人手中的红肉,连蒙带骗地勾引你。像宗教里的上帝,正因其不可证伪而无往不胜。总是有希望的,不试怎么知道?”
7月我还在寝室复习。湖北在清嗓子,湖北在看电视,湖北不给开空调,我快热死了。她做的一切我都好讨厌。其实犹豫了几天,最后还是漏夜收拾行头,第二天清早六点回了家。
一回家倒好,楼下的雨污分流管道在年复一年地施工,小区对面新花园的地桩像盘古开天地一样不舍昼夜地敲击地面。我实在没有心情把这种反人类的轰鸣比作所谓的“交响乐”。
地铁终于修到城市的边缘,郊区的房价开始急剧上升。经济不见发达,楼房倒是一幢一幢拔地而起。旧城区被划上大大的拆字,城市更新终于提上了日程。

拜他们所赐,我的小学同学摇身一变成了富翁。正如那些有点语病的标语所说:“城市每天一个样”。而在他们的眼里,普通人的努力是那么的轻易。
我是那个被抛下的人,意志日渐消沉。复习进展变得缓慢,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也似乎注定无法走远。严密的计划不断被自己毁约,信心在不断的透支中被摧毁。学科和应试的特性让我开始怀疑当初的决定。
黑夜不再瑰丽
它转而死寂 压抑 让人透不过气
夜晚所有感官统统关闭,只留我赤条条地与自己独处。我的脑袋空无一物,却又急于从里面掏出一些治疗的药方,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于是我白天什么事也静不下心做,夜晚整晚整晚地失眠,只有在思绪跑到筋疲力尽的间隙,才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废柴
鸡汤式的安慰被编成咒语一样的短句,在恐惧趁虚而入时扮演思想的卫队,反复在脑里回响,扫荡。
我开始对一切漠不关心,提不起兴趣,书也看不进去。终日不是瘫在床上就是瘫在沙发上,眼睁睁窗外亮了又暗。我讨厌天空的放晴,讨厌所有人就连太阳的心情都变好了。
食欲不佳,还缺乏锻炼,爬一段楼梯就喘,蹲下站起会眼前发黑和头晕,就连拿筷子手都会不自觉的抖动。周末看到最喜欢的海滩我不再像十几岁时一样兴奋地大叫,而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没有知觉。

渐渐地,我失去对美的鉴赏力,失去写文字的能力,失掉我所视为珍贵的和骄傲的,畏首畏尾,患得患失。
其实我一向不相信心理医生,认为只有自己把心里的结解开了才能恢复元气。后来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以再持续。于是准备死马当活马医,在医院预约了精神科医生问诊。果不其然,确实没有毛用。
医生翻出一本厚厚的大书,指着书让我做一套心理测验。又抽一张白纸让我遮住评分标准,把答案写在上面。其实我早就看到了评分的标准。
写完两套题他又把白纸收回去,戴上老花眼镜煞有介事地算了算分,宣判:“这是轻度抑郁。”
每次我爸在医生面前都尊重得有些局促,又担心一本正经地谈论会加重我的心理压力,在我讲症状的时候,他只好笑笑又着急地补充,生怕遗漏会影响诊断一般。
医生倒见怪不怪地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最后开了安眠药和一点什么药。然而那安眠药并没有什么用,没吃两次我就不吃了,谁知道这些药吃多了会不会病没治好,反而把人给吃傻了。
九月
9月9日
在与时间赛跑的路上踽踽独行
在无边的寂寞中与无数个分身厮杀
欲言又止 欲言又止
“预想的创伤”统治我对未来的想象
我担心 害怕 焦虑 躁动
像搁浅的鱼 拔去氧气面罩的病人
直到九月仍然没有救回自己。眼见离期限只剩短短三月,日期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催命符。我每天挣扎,焦灼,我劝自己为什么就不能随便一点,不再忧郁,捏着鼻子跳入海里。
那段时间,“一手好牌打的稀烂”的谴责在心里不断地循环。我不是不知道这一年的决定会使同龄人在若干年后拉开多大的差距,我要强,我害怕落后。但我在打退堂鼓。
朋友圈常常是我心情的晴雨表,半年来,我的手机里的照片不超过100张,朋友圈动态一条都没有。
又开学了,我在路上害怕遇见同学触发任何我不想讨论的话题,朋友圈的功能早就关闭。即使这样,那些同学的喜报仍然有意无意地塞到我耳朵里。
人家在高歌猛进,我在原地举棋不定。
更恐怖的是,那些旧账全部沉渣泛起,我想起小时候上过的书法课、外语课、舞蹈课、钢琴课统统是三分钟热度。这是真正的心理危机。
我在质疑我这个人,为什么总是做不到坚持、为什么总是“迎难而退”?究竟这次的退堂鼓,是因为我不喜欢而放弃,还是迎难而退?
进与退两种力量在体内撕扯。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风平浪静又暗流汹涌。多少人的命运在不知不觉中被注定,在这个岔口分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早就计划周全的人现在担心,担心自己是被落下的那一个。
迷航
我一如既往的颓废。是个人就跟他掏心掏肺,问些正常人寒暄不会问的问题。白天扎进人堆里游荡,晚上只有跟妈妈一起才能安心的睡上几个小时。
每天唉声叹气,常常感觉有大石压在胸口,仿佛长长地吁一口气才能够排解心中的郁结。
从小到大我算是个比较有主意的人。父母从来只是默默地陪伴,基本不会过问我的决定和思考。一天躺在床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好”。我妈很认真地问:“你告诉妈妈,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曾经赖以生存的基点早就崩塌,往日的意气风发早就了无踪迹。我像在汪洋大海中迷航的一叶小舟,一掀就翻,手上连一杆桨都没有。
连月来的失眠没有好转,我人生的命题也找不到答案,睁开眼睛又是跟昨天一样的一天,我对自己失望,失去耐心。每天都在担惊受怕,心惊胆战,找不到情绪的出口,活着不过是一场再清醒不过的噩梦。
早晨睡醒家里又一个人也没有,仍然习惯性地竖起耳朵听外面有没有凤凰卫视的声音,我爸每天早上吃早饭都要看的。
然而屋子里静悄悄,窗帘轻轻地飘动着。床头柜上摆着的全家福在晨光的映照下显得温馨。岁月静好。此刻我的心里却晦暗无光,万念俱灰,只有凭借对家庭的责任和理智勉强苟活于世。

返校
那时唯一我能确定的,是要脱离心灵的囚牢。我开始找实习,试图用无意义的劳动占领我的脑筋,至少把自己从无边无际的胡思乱想中解救出来。
9月底我回到寝室,湖北还在实习。
湖北比我大一级,生过一场大病,结果化险为夷。休学了一年,才跟我们一届上学。据说那场病也没有多痛苦,但是很严重,能置人于死地。
除了开过光的脑袋头发还有点稀疏,每天戴个帽子之外,她跟普通人没什么差别,该上学上学,该熬夜熬夜。在床头还贴着一张用彩笔写着“不许熬夜,生命只有一次”的A4纸。
我问湖北家里有几个小孩,问她万一她去世了那她爸妈岂不是会很伤心。又自言自语那我们家就一个小孩,万一我出什么事我爸妈一定也会很难过。我盯着楼下的羽毛球场出神,盯着乔苑的楼顶出神。
后来还真有学生从那个我仰望的天台跳下。第二天黄昏,我走在小西门的天桥上,愣愣地看着夕阳出神。
夕阳橙色的光晕笼罩着所有归家的人们。有人要去聚餐,有人要去打球,而那个昨天从世界上消失的女生再也看不到今天的光景。
这样的崩溃经历我不是没有过,高三有过,大二有过,大三一模一样地又来一次,只是这次似乎是“毁灭性”地打击?总之溃烂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我像一滩烂泥扶不上墙。像一个跛脚的人,走没两步路又重重地跌在泥里。
过往的经历告诉我做决定一定不是光凭一个脑袋,这样永远找不到我要的答案。
其实不愿意跟亲戚谈论到这些。但理智驱使我不得不这么做。实习完的晚上,我开始请教别人,而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求救。
我咨询做法律顾问的伯伯、在做人力资源的姑姑,但就像我之后在学校做的心理咨询的结果一样。我感谢他们的包容。但他们听不懂我,我也不能听懂他们,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一向不干涉我选择的爸爸此时也见缝插针地提出他的建议:考个公务员多好。亲戚劝我别多心,专心复习就是。于是微信里出现一大堆考公考编的公号,手机的首页多了几个求职的软件。可这一切让我不再纯粹,也无疑是让我离自己越来越远。
失去指南中轴之后,我被各种外界力量撕扯扭曲,成为大众的傀儡,毫无反击之力。每天游走在崩溃的边缘。
实习
新的实习是做政务新媒体的编辑,这个名衔集齐了本科四年来最厌恶的元素。在四年里不知不留情面地嘲讽讥诮过多少次的工作,到了大四的暑假,竟然这样鬼使神差地接受了。
跟电视台的实习不同,编辑成天成天地坐在办公室里头。办公区只有一层楼,除了人就是电脑,人们自顾自地干自己的活。就算聊天也是讲些“李佳琦”、谁又上了热搜这些我不关心的事。
上班时间除了楼梯间和卫生间没别处能去。楼梯间的禁止吸烟标签下放着一盒将熄的烟头,卫生间也有股悠悠的烟味儿。办公室从早到晚开着白炽灯,不上洗手间都不知道窗外已经日落西山。一天坐下来腿麻的要退化。
写字楼的电梯早午晚高峰常常爆满,而且是不把人塞满到电梯嘀嘀叫都不关门。有一天跟同事下楼,被挤在电梯最角落,真真是肩肘相接,我在夹缝中拿起手机,跳出屏幕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某写字楼电梯超载坠落。
当时还是流感季,办公室咳嗽声此起彼伏,整个房间就靠中央空调换气,平时一包冲剂就能好的感冒一个星期都没好,好了又复发了一次。
编辑的工作无非是复制粘贴,排排版式,排排海报,天天跟几个行距字间距较劲。加之我又只是个实习生,根本接触不到设计、策划的活。这份工作很轻松,按毛姆在《刀锋》里传递的观点来说,偶尔的体力劳动有助身心健康。
但这样的工作内容实在无脑的令人警惕。每隔两三个小时我就要去洗手间怀疑人生。
“努力又是什么
如果目标已经出错
这里有没有人清楚
越努力越错的多”
我似乎习惯了复制粘贴,丧失了思考的人格,变成我最讨厌的人。我不清楚她是认真的,还是戏谑,一次一个编辑教育我,做新媒体就要懂得自嗨,还一本正经地传授我新媒体的套路。
政务新媒体
四年里从书本从老师得来的知识远不如这三个月亲身经历得来的生动。我了解了所谓新媒体的内容生产过程,即使是这样的政务新媒体,也只能微信不能全信。
举个例子,卫生监督的科普内容十之八九从健康中国、丁香医生一些稍显正规的网站复制下来。审核也都是行政审核,没有专业审核的环节。
更糟糕的是,所有内容都是无本之源,我从一个可能的内容生产者变成内容的搬运工,这样极不安全,因为你可以使用的永远是有限、受制于人的。
再扯远一点,现在的政务新媒体我看顶多是姿态性融合。从机制上就可以看出,机关单位的人领着一份工资,却无端端多了工作内容,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现在有这种外包的工程。
即使说“新媒体”是一块蓝海,没有教材历史可以参考,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书写历史,我依旧不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尤其是政务新媒体。
因为公号运营的好不好,不仅是编辑一个人的功夫,还要跟甲方(机关单位)协调。加之其“政府”的属性,内容上局限较大。在形式等其他不触及底线的方面也最终取决于主管人的个性和风格。
也就是说,这样的体系之下,虽然温饱是牢靠了,但最根本的个人的发展则会受到数不清的限制。这棵树倒了,除了看起来“光鲜”的简历之外,我一无所获。
不管怎么说,这段时间还是有意义的,至少把我捞出了水面。
下班吃完饭我总是一圈一圈不知疲倦地绕着操场走路。同学实习结束也回学校了,也和我一起不知疲倦地绕着操场走路。归属感也在回来的路上了。我终于稍微提起精神,回归正常生活节奏。
复原
在19年的年末,我的元气开始复苏。
12月18日
我像被遗忘在深海潜水球里的潜水员
求生的绳索被扯断,再也不可能被拉出水面
而现在那根绳索再次向我伸出援手
我回到了我自己。所有的决定也变的不再艰深,不再斤斤计较,瞻前顾后。身边的人们不再像是布景里的傀儡,我也不再跟布景格格不入。
心脏健康而兴奋地扑腾,我能看进去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能看一部接一部地看李安的电影,能继续在周五的晚上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再买一块蛋糕上书店看画册看到书店关门。我该有的想象力跟活力都被全数归还了。

我一个人躺在夜里,感觉得到被子和褥子是软绵绵的。六个月以来,今晚第一次自己睡。
其实当然是一个人睡自在。之前在妈妈身边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是因为信心被击碎,脆弱的不行,企图用人类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换取一点可怜的安全感罢了。
快到圣诞节了。实习结束之后快乐指数也高了不止一点点。那块大石头也在变小,消失。虽然每天早上还要病态的反复检查,自己是不是放心过头了。但我能没由头地哼着小曲儿,恐惧在下降,勇气在复原。
19年的跨年,我和同学上塔门岛去露营。去程有海鸥绕着渡轮来回飞翔,我叉着腰在山坡上面向无敌海景刷牙。返航的渡轮在青山迷雾里有条不紊航行,它自有它自己的导航系统。

总之,成长是一次跳水,起初奄奄一息,就快窒息溺水。可是慢慢扑腾,总能找到合适的泳姿。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度。小时候参加的管乐团小喇叭吹来吹去,长长短短也吹了七年,直到上高中解散了才放下。初中的长跑我也能一鼓作气冲过终点。大一读书的习惯也不知不觉持续到今天,变成类似一日三餐的习惯。
无怪乎有些事情我没法坚持。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