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翻書寫作練習:夢想、愛與怯懦,就讓蟲子去處理
我從桌邊的小書架上拿下久違的,娜妲莉·高柏的《直到死亡貼近我》,在取下來的那瞬間,我便順勢翻開某一頁,於是我就看見這句話:「讓蟲子去處理。」,通常,我會打算寫點什麼心底有關這句話的感受或小故事,卻感覺到內心一片空無。
像是把石頭扔進池塘裡,卻沒聽見「噗通」的聲音一樣。

我得承認我對蟲子這東西有點反感,甚至我很想要他們可以離我遠一點,此刻我想起前天晚上打開租屋處房門後,看見那隻正好在公共走廊閒晃的蟑螂,我怕得立時關上門,轉頭便抄起垃圾桶旁的殺蟲劑,殺氣騰騰地整裝。於是再度打開門後的,不再是怯懦、恐慌、害怕小蟲子的我。
我已從獵物被轉化成獵手。
後來,它逃進了某間沒有人住的房間裡,我在附近用殺蟲劑佈下「結界」,使他再也不會出現在我的面前。
蟲子,我真的很不喜歡他們。
但此刻我又開始想起,今天拿起的這本書《直到死亡貼近我》,想起自從我母親離世後,我彷彿把死亡拋諸腦後,這半年間我已經經歷太多的分離、死亡。
想起去年冬天夜晚從竹東殯葬處走出來,撲面而來的涼意讓我發抖,我把外套拉得更緊了些,想起爺爺躺在冰櫃中那個枯槁的臉龐與寧靜的面容,想起小時候他帶著我從北埔騎車到新竹市區,想起他在暑假時的一大早,特別去市場幫我買的漢堡包。
爺爺都沒說,但才國小的我就知道,這絕對是「特地」的,因為爺爺從不吃這些東西。想起他特地從街上帶回來的菜包,還有黑糖味的九層糕,我咀嚼到的是爺爺的關心與愛。
但此刻我只能透過冰櫃的玻璃看著他,靜靜地看著,聽著外面親戚們一邊吃便當一邊閒聊,我只是靜靜地站在爺爺面前,想像我走過阿太(客語:aˊ tai,曾祖父母)家的池塘邊,看見他在菜園裡掀開藍色大水桶,站在瓜棚下,並用紅色塑膠水瓢澆花的畫面。
已經是好久好久以前,就連爺爺的去世也已經是好久以前。

緊接著春天,我的母親就過世了。
我很難說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有多大的轉變,但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放下了這麼多年間,我與她之間的侷齬。那天在得知這個消息的夜晚,當我坐在奔襲中的高鐵上時,看著窗外的我,看著我的臉、我的眼,以及我眼中的驚駭與悲愁,我彷彿透過自己的眼神看見我的母親,然後⋯⋯在這一刻我便放下了。
畢竟,不論是愛與恨,都將在死亡的那一刻被斬斷,斬斷所有的連結與思念。
我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遇見了兩次死亡,而此刻我再度看著這個書名《直到死亡貼近我》,我才驚覺其實死亡一直都距離我不遠,但也許是經過練習了,我似乎已沒這麼驚慌。
想起幾年前,在閱讀此書的那段時間,在夜晚睡覺前,我甚至會偷偷地觀察早已熟睡的伴侶,觀察他是否還有呼吸,直到我發現他的胸口因為呼吸而起伏,或突然動了一下,我才感到心安。
「他還沒死。」
我在黑暗中看不見他的臉龐,妄念會在夜半時刻鑽進我的思緒,侵蝕我的感官,使我開始想像——他毫無回應的身軀是否已經冰冷又毫無知覺,是否在我伸手碰觸他的指尖的那一刻,感受到的已經不再是溫熱的體溫,只剩僵硬又冰冷的身軀。
我閉上雙眼,順著床的水平線探索,直到我碰到他的指尖。
「呼!還是熱的,他還沒死。」
我非得要這樣做才可以心安,我非得要這樣做才可以讓自己可以安穩地睡著,我很怕死亡突然降臨,然後從我身邊帶走他,我怕被留下。
只剩自己留在這個又小又空蕩蕩的房間。

飛蛾在窗外撲騰,躲過壁虎的追擊。
他逃離死亡,用盡全力。
在我母親與爺爺都離我而去後,在他們都已無法繼續欺騙死神的目光後,我竟變得比較淡定,我開始思考這件事情,思考若有一天我真的被留下,真的只剩我一個人時;更開始思考,若我即將死去,我該怎麼做?
或是說:
「我還可以做些什麼?」
前陣子「夢想」這個詞不斷出現在我的生活中,不論是在站上留言區或敘事團的討論中,夢想這個語詞不斷出現,我也重新揀回來問自己:
「我的夢想是什麼?」
我曾在心底想著,既然要寫作,既然我都想要一直寫下去,那不如就許個大願望吧?於是狂妄地想著:「何不拿個諾貝爾文學獎呢?」
哇!當這個念頭出現的那一刻,連我自己都被嚇到,我竟對文字有這麼巨大的野心,不只是可以溫飽就好,不只是可以賺到一點錢就好,居然還貪心地想透過文字在這世間博取名氣,博取大家對我的奉承與喜愛。
我真是狂妄。

但此刻,經幾年的寫作生涯後,我又再度問自己這個問題:
「我的夢想是什麼?」
我卻好像已經沒有當年那樣驕傲的心,我不想透過寫作改變什麼宇宙規則,不想透過寫作讓大家「知道我是誰」,但這答案卻明晰無比:
「我想寫到生命的盡頭。」
如果今天我被宣判還有幾天即將死去,我想我將會做的是:
「打開電腦,然後開始寫點什麼。」
我想要紀錄下一切,寫下死亡的過程,寫下專屬於我獨一無二的經驗,寫下我的這輩子,寫下我人生的全部。
或只是,寫下今天午餐有多美味,或我已經毫無味覺而味如嚼蠟。
我想這是最浪漫的一件事情。
「寫到生命的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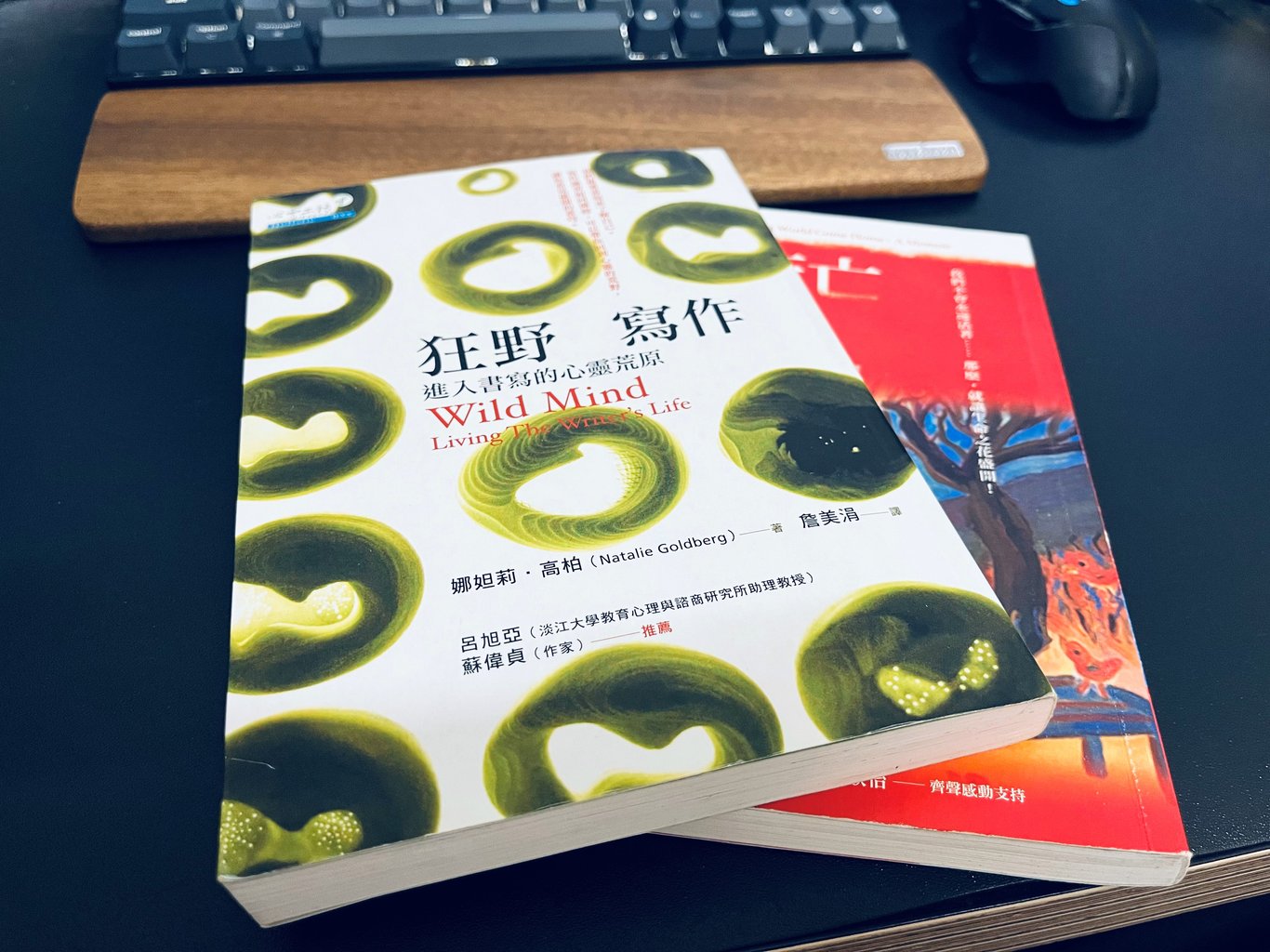
我想起曾在《狂野寫作》中看見的故事,娜妲莉寫下自己跟隨禪師前往另一位同修的家中,她的師傅在病榻前擁著另一位禪師,問他在死前還有什麼想說的。
她原以為會聽見什麼超脫死亡的語言,或禪意的回應,卻只聽見他說:
「我不想死。」
是的,就這麼簡單。
死亡讓人恐懼,面對未知的恐懼,面對別離的恐懼,即便是擁有多年修為的禪師,盡力參透世間道理的人,面對死亡都會恐懼,於是在生命結束的前一刻,留下的遺言就是這句:「我不想死。」
多麼言簡意賅,面對死亡的逼近,如果真有這一天,如果我真得在清醒時面對死亡朝我迫近的那一刻,也許我也會發狂地在紙上寫下「我不想死」,藉以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大聲宣告我也並不是這麼大無畏的人,我也只是一個庸俗又倚賴物質世界生存的凡人。
此刻,我又想起這句話:「讓蟲子去處理。」,這句話出自娜妲莉的女友玉光,當時她被醫生宣告罹患乳癌,在經歷短暫的打擊後,她決定不能坐以待斃,打電話給附近幫人剃度的僧侶,述說自己的狀況。
她說:「我覺得我得主動出擊,在癌症奪走我的秀髮之前,搶先一步。」
最後她在親友的見證下,在家中後院完成這項「儀式」,把她由及肩的黑色長直髮剃成大光頭,也把她由一個凡人轉變為一個直面死亡的勇者。
她面無懼色,也一滴淚都沒掉。
最後,當有人問她那些頭髮怎麼辦?玉光只說:
「就讓蟲子去處理。」毫無留戀。
我不知道該怎麼評論這一段故事,但我從玉光那面對死亡挑戰的態度中,感覺到豁然,感覺到勇氣,但更想問自己,若真有這一天,我可以如她一樣這麼坦然嗎?
當死神站在床頭的那一刻,我可以淡然地與祂打招呼,並邀請祂坐下喝杯茶,等我把這一則故事寫完,接著在完成後安心赴死嗎?

我想起我的母親,想問她在倒下的那瞬間,在她意識到自己即將離世的那一刻,她在想什麼。也想問問我的爺爺,當他在醫院裡終於闔上雙眼的那一刻,他看見了什麼。
但我想這些問題在此刻都已毫無意義,而我也沒有機會得到答案了。
不論是那年暑假,我緊緊抓著爺爺白色薄內衣的衣角,坐在後座順著道路前進時的回憶,還是總在要從老家離開的時候,爺爺從菜園摘了滿滿兩大箱的蔬菜水果,希望給我們這些孫子帶回家吃的回憶;
又或是小時後與母親在籐製梳妝台邊,一邊聽著母親閱讀國語日報的《小球姊姊說故事》專欄,一邊讓他教我認字的回憶,還是那年離家出走,在母親終於在路邊發現了我後追上來,在我宿舍的停車棚旁邊對我說:「這麼多年的媽媽,難道就可以這樣放下了嗎?!」。
我記得在夕陽下她的髮絲在微風的吹拂下顫動,也看見她眼神中強打精神的憔悴與眼淚。
都回不去了,無論歡喜也好,無論煩憂也好。
都回不去了,也都回不去了。
「就讓蟲子去處理。」
我剪下這些回憶,讓它們在我心底的堆肥箱裡發酵、分解、昇華,隨著蟲子的啃食逐漸轉化,就讓名為時間的蛆蟲去處理吧!
消滅殆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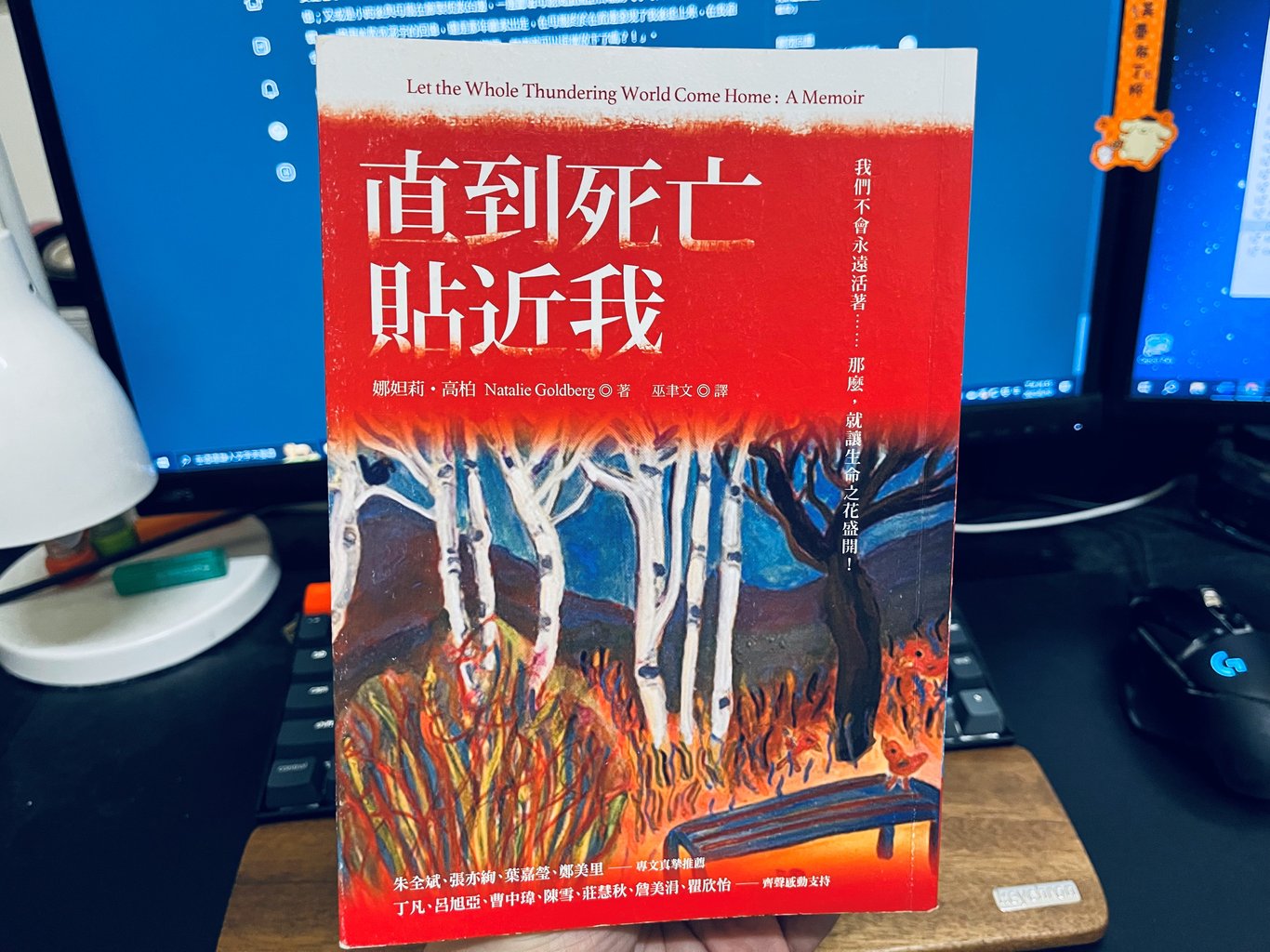
本文關鍵詞句:「就讓蟲子去處理。」,出自娜妲莉.高柏《直到死亡貼近我》一書,第13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