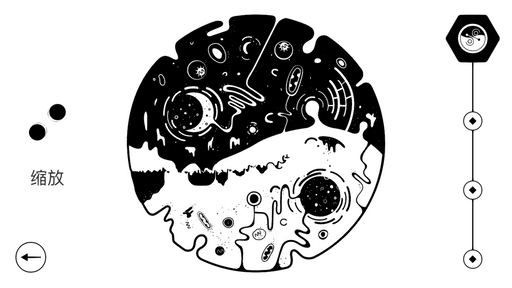华语语系文学刍议——以史书美,王德威,黄锦树为中心
随着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的不断升温,关于该概念的质疑和争论也越来越多。本文希望通过对华语语系文学中两位重要评论者,史书美,王德威的观点进行分析,试图厘清华语语系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和关键问题,同时通过分析马来西亚旅台作家黄锦树对华语语系文学中的个案马华文学的论述,来揭示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问题和迷思。
一、华语语系文学与“反离散”
史书美是最初系统阐释华语语系文学的学者[1],她的观点偏向于后殖民理论。在史书美看来,华语语系文学“包括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地缘政治之外的华语群体,他们遍及世界各地,是持续几个世纪以来移民和海外拓居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同时,它也包括中国域内的那些非汉族群体,由于汉族文化居于主导地位,面对强势汉语时,它们或吸收融合,或进行抗拒,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回应。”[2]如果追溯定义的源起,不难发现,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的定义,是在效仿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等带有殖民色彩的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潜在的“侵略者”和“受害者”的角色,虽然史书美的初衷是为了彰显边缘文学的个性特征,但是二元关系的设定导致她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华人文学的现实。她认为中国概念不过是近代产生的,在和世界其他地区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对于中国和汉人而言,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至少出于三个不同的意图:以统一的民族抵制20 世纪早期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主义;践行自省(self- examination),这是一种将自我(self)这一西方概念内在化的努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给部分少数民族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之外,还要把少数民族的国家诉求和爱国奉献精神调适到中国这一国族身份上。”[3]
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存在很大问题。史书美承认,中国人的概念是由于外国侵略造成的,但是却把汉族描绘成了压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的凶手,似乎汉族将其他非汉族作为一种对外抗击的策略。但实际上,西方侵略才是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关键之处,史书美的阐释却将这一点轻描淡写,导致她的论述更像是逻辑自洽的语言狂欢,而没有深入到华人文学的现实之中。特别是史书美提出的“反离散”的概念,更印证了她与现实的隔阂。
她认为“离散中国人研究界提供的证据却充分表明,这些移民在他们移居的国家里寻求地方化的意愿非常强烈。” [4]并举了马来西亚的海峡华人以及新加坡移民的例子。但是正如马来西亚旅台黄锦树反驳的那样, 史书美忽略了这之中的复杂性“中国认同,甚至华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都被视为原罪,不被那些单一语言国家接受。终结离散并不是无条件的,经常是暴力的过程。轻者用消灭语文教育的方式(菲、泰、星、缅、韩等),重者就是大屠杀(如印尼)。”[5]史书美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但是实际上真正排斥华人的却是等级森严的当地社会。“离散”或者是“反离散”根本不是华人自动选择就可以解决的,这其中是政治与力的角逐。华人接受的中国概念,也并不一定对应真正实在的中国,而是一种想象的存在,这是一种源自祖辈的文化记忆的遗留,它以语言,文字或者习俗等方式流传下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称其为中国性不过是为了指代的方便,但实际上,它只是某些细小的文化静脉的碎片而已,它更像是不断传递的内在个人经验,并不是宏大叙事中的中国。
二、华语语系文学与“华夷风”
真正使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为人所知的是海外华人学者王德威,他也是第一个将sinophone literature译为华语语系文学的人。王德威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处理和史书美并不相同,首先,他在史书美“反离散”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民主义” 的理论“后移民、后遗民、后夷民。有的移民是迁移到海外的移民;有的是移民到了海外心念祖国,年深日久仍然不能忘怀祖国一切的移民;还有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两代,一旦到落迹在英国、法国,他们如果忘掉了语言的源头,生活的习性,他们就真的变成了洋人了。” [6]不过王德威的“三民主义”似乎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诠释“反离散”,虽然他否定了中国作为侵略者殖民者的角色,也没有将华人文学无家可归的状态归结于“问题在于,谁在阻止他们成为一个泰国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或是新加坡人,和其他的国民一样被认为仅仅是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居民,只不过恰好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祖先而已。”[7] 但王德威实际上坚持了史书美“离散有其终时”“语言群体是一个处于变化之中的开放群体。”[8]的观点。虽然年轻华人对当地文化有更多的感情,但是国家和社会还是会将他们区分出来,区别对待。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黄皮肤的祖先,而是当地社会过于不宽容,这两种情况之间确实有本质的差异。
另外,王德威认为,应该将中国大陆文学,或者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加入到华语语系文学的谱系之中,让不同的声音进行对话。另外王德威又援引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根茎学说,“我所期望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不是差异的轻易确立或泯除,而是识别间距,发现机遇,观察消长。”[9]
我很同意让不同的华语文学对话形成谱系的做法,但是,如果想要得知距离,却还是绕不开本土性和中国性的问题。因为就算是对话,也并非毫无偏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国家支持,在华语语系文学中必将处于中心位置。实际上,评论者稍不注意,就会因为缺乏对对方的了解和认识,陷入到离谱的偏见之中,然后又会回到本土性还是中国性的争论。当然对此王德威也试图去解决,他的方法建构一种新的审视文学的标准。他强调华语语系文学中的时间性,也就是“势”,“ 如果 ‘根’指涉一个位置的极限,一种边界的生成,‘势’则指涉空间以外,间距的消长与推移。前者总是提醒我们一个立场或方位(position),后者则提醒我们一种倾向或气性(disposition/propensity),一种动能(momentum)。这一倾向和动能又是与立场的设定或方位的布置息息相关,因此不乏空间政治的意图。更重要的,‘势’总已暗示一种情怀与姿态,或进或退,或张或弛,无不通向实效发生之前或之间的力道,乃至不断涌现的变化。”[10] 在“势”的基础上,王德威试图将华语语系文学重新翻译为“华夷风”王德威的论述明显受到布迪厄场域学说的影响,他试图用趋势而不是固定概念去建构文学理论。提出“势”的概念弥补“三民学说”(其实也是“反离散”)中对更多可能性的忽略,理论阐释的空间变得更大。纵观王德威的理论路径,会发现他其实改变了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意图和方向,从关注边缘文学的特质到关注汉语文学内部的张力和变化,这里又回到了那个问题,话语语系文学究竟为了什么而存在?它是为了凸显大陆之外的文学书写?还是将所有的文学合并在统一的体系之中?
三、华语语系文学的现实:马华文学
虽然不管是史书美还是王德威都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建构颇费心思,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都像是为了使逻辑自洽的权宜之策,但是如果真正进入华语语系文学的现实之中,却会发现错综复杂的关系并非“势”所能涵盖的。马来西亚旅台作家黄锦树,就对于华语语系文学有很多质疑。黄锦树本人在《乌暗瞑》一书的自序《非写不可的理由》中这样写道“祖父母自中国大陆南来,父亲是土生土长的一代,而我则是国家独立后出生的一代,各自铭刻著不同的时间性。因为某种缘故,父母亲一直都住在胶园,以割胶维生,守著祖父母毕生劳力和血汗结晶成的一小片胶园,孩子一个接一个生下。毫无例外地,我们的童年都在胶园的阴影里度过,一直到学龄了才走出胶园。”[11]黄锦树的话,确实能够证明王德威的观点有合理之处,时间性确实在阐释海外华人的作品时有重要作用,华人和华人之间有着非常不同的记忆,这种记忆会让他们面对同一事物(如国家性)时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但这个特征也可以用来反驳王德威的“三民主义”,海外华人文学的复杂性,并非“三民”概念能够涵盖,而可能出现更加复杂的似是而非的答案。
对于黄锦树来说,中国性和本土性是双重资源,更是双重压迫。诚然,中国文学可以作为丰富的写作资源,用于弥补地域劣势导致文化养分缺乏,本土性则提供了特殊的热带视角和语言风格。但同样,对马华文学中国性的争论,却也意味着马华文学要不断去和这种强势文学对标,或许只是无意的比较,但压力却是不言而喻的。黄锦树曾这样感慨道“犹如马华文学单凭蕉风椰雨、方言土语、热带故事是不足以让它在现代中文文学的战场里找到位置的,它必须更激进、更全面的调动世界文学的资源,甚至开展出完全不一样的叙事形式。” [12]王德威借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去形容黄锦树的面临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恰当。“‘异托邦’是一个具体或想象空间的存在,被社会所命名,所树立,却被作为“境外” 处理。异托邦折射一个社会的欲望或恐惧,规训与包容的空间,但也因为其另类的位置,形成与主流权力既联合又斗争的微妙互动。马华文学让文学的中国性或马国性不安,因为它在‘国家文学’的旗帜下经营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叙事逻辑——像一面镜子里左右对调的反影。”[13]马华文学实际上是一种逃逸的文学,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确定的谱系,但却因此能够吸收所有不同的资源。关于黄锦树本人如何看待中国,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他对史书美的反对可以和他对龚鹏程“文的优位性”观点的支持做对照,实际上,我认为不管黄锦书如何批判那些对中国怀有乡愁之情的作者,他本身也隐含着这种倾向,虽然并不是在感情意义上,而是一个严肃文学家在文学质量上给出的价值判断。
不妨将马华文学和犹太文学做一下对照,犹太人可能是任何国籍,他们可能熟悉不一样的语言和文化,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但他们依然认同自己是犹太人。当然海外华人并不具备像犹太民族一样严整的血统和宗教联系,但是他们面临的情形却有一致之处,那就是无论在何处都很难被认可。作为作家的黄锦树,用极其敏锐的直觉抓住了马华文学这种“逃逸”的特性,所以,他的选择是抛弃中国性和本土性的双重资源,以另外的方式靠近文学,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强调“文的优位性”[14]也就是说,在国家,文化之外,建立一个形而上的文学王国,这个王国的第一标准就是文学。同样因为“文的优位性”这一原则,黄锦树重新衡量和建构了自己的文学谱系。不管是他强调用现代主义的方式看待马华文学,还是激进的想要借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语言传统,其实都是出于对马华文学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判断。黄锦树同样要求要实践,如果缺少对文学的原则,那就自己创造不同的原则。如果说史书美和王德威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建构,处于理念上的设定,那么黄锦树,则是在目睹马华文学现状后,对矛盾重重的现实进行了挑衅。可以说,黄锦树强调“文的优位性”,重新整合资源的方式,倒或许成为华语语系文学沟通不同文学的方式,因为以“文”作为衡量标准,可以公平的看出不同地区的文学的不同。
撇开文学议题上的讨论,我认为马华文学的问题,恰恰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甚至是后现代)民族的问题,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样,现在的文学以及它所属的群体,都有很强的流动性,不能按照原有的方式进行固定化的分析。如果用更为直接的问法就是,现代人认为的共同体是什么?在原子化的人中间,何种经验才是共同的经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然也关系到和政治密切相关的文学。
花絮:
机缘巧合这学期有马来西亚的同学来我们学校做交换生,当她得知我在做马华文学的问题的时候,给予我了很多的帮助,然而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她说:“来大陆只是学校安排,我对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对我来说,马来西亚才是我的乡愁”。听了这话我有点感动,相比于宏大叙事以及理论阐述,个人的经验和记忆,反而是最为真实和宝贵的。换句话说,人永远不可能像理论中想象的那样,生活在失去归属地的痛苦中,相反,他们在那缺失处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生活的答案,即使他有追忆和乡愁,那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不可被通约为某种特定群体的感情。
参考文献:
史书美著 赵娟译《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王德威《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6年第1期
王德威《 “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刘俊 《“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
黄锦树《乌暗暝》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版
黄锦树 《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年版
[1]据学者刘俊的考证,“sinophone”一词最早是华人学者陈鹏翔在1993年的《文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世界华文文学:实体还是迷思》中提到“sinophone”但是史书美是第一个将sinophone这个概念进行完整阐释的人。但是华语语系这个概念则是由王德威翻译的,但是也得到了史书美的认可,这里用华语语系文学代替“sinophone”,是为了行文的方便。
[2]史书美著 赵娟译《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第5页。
[3]史书美著 赵娟译《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第6页。
[4]史书美著 赵娟译《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第7页。
[5]本文原题《这样的“华语语系”论可以休矣!──史书美的“反离散”到底在反什么?》,刊于书评网站〈说书Speaking of Books〉2018年1月2日,本文是《近代文学研究》转载版,有删节。
[6]文段引自王德威2017年6月7日在“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人物盛典”上的演讲稿《何为中国?何为华语语系文学?》
[7]史书美著 赵娟译《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第7页。
[8]史书美著 赵娟译《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第11页。
[9]王德威《 “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第13页。
[10]王德威《 “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第12页。
[11] 黄锦树《乌暗暝》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12] 摘自2014年7月28日黄锦树在吉隆坡书展推介《火,与危险事物》上的讲稿。
[13] 王德威《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6年第1期第13页
[14] 这是黄锦树对龚鹏程“文的优位性”概念的借用,具体可以参考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一书,这里仅对黄锦树的观点简要概括。.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