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有四种似是而非的罪名,并不构成犯罪
政治自由”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多次讨论到的问题,他认为立法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一个国家,无论它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只要能保障自由,便是理想中的“宽容政体”;而如果无法保障自由,那便是暴政了。
在那本名著的第十一章中,孟德斯鸠指出——
“自由是一种权利,能做法律允许的所有事;若一个公民能做法律禁止的事,那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权利,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要保障自由,就应当用法律来限制权力,规定公民们都只能做法律所允许的事,不能超出法律的限制之外。但是,孟德斯鸠发现“一切手握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且一直要用到极致才肯停下,这点已被从古至今的经验证实。”这种滥权现象容易冲破法律的限制,因为各国的君主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随意修改法律——既然法律约束不了权力,于是孟德斯鸠创造性地主张“用权力约束权力”,提出了分权制衡理论。当最高权力受到约束之后,暴政就减少,民主就会增加,自由也得到了保障——这是从政体方面来捍卫政治自由,在第十二章,孟德斯鸠又从公民方面来探讨如何保障自由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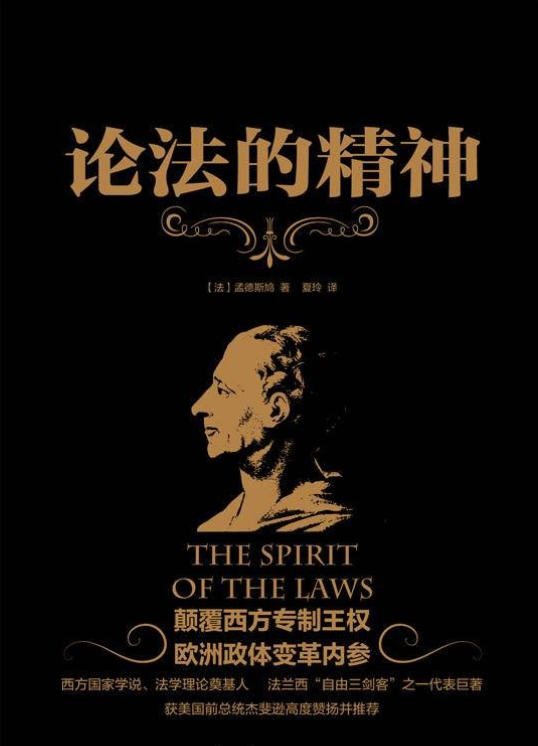
有政体自由,不一定有公民自由
在孟德斯鸠看来,“政治自由”有两层含义:第一,能够做法律允许的事,或者拒绝做法律没有规定的事;第二,处于安全状态之中,或者觉得自己处在安全之中。
一个公民生活在社会中,他如果不能做自己应做的事,或者拒绝被强迫做自己不应做的事,那他必然感到不自由。所以才需要建立一个分权制衡的政体,把各种权力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没有人有权去强迫别人做不该做的事,也没有人有权去阻止别人做该做的事——国王若想增税,得先得到议会的批准,他无权违背人民的意志悍然增税;当国王否决某项法案之后,议会如若通过多数投票,再次确认了法案,则国王无权阻止法案的通过。在这种政体中,即使国王存在,但政体依然是自由的。
公民有权利做法律允许的事,这是实现政治自由的第一步,但还不代表完全实现了。孟德斯鸠就指出存在“政体自由,公民不自由”的情况——古雅典是一个自由的政体,但是苏格拉底却不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哲学理论,他被控诉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腐化了青年以及伤害了雅典人的感情,最终被处死——也就是说,雅典人苏格拉底并没有享受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在这样的城邦里,很容易就会因说错话而被指控犯有亵神罪,遭受迫害。各种潜在的禁忌使雅典人感受不到安全,即使他们享有自由的权利,能够参加公民大会,发表政见,可是一旦出言不慎,冒犯到风俗或神学,就会有灭顶之灾,要么流放、要么处死。
因此,就算人们拥有自由的权利,可是如果感觉不到安全,那么他们也不敢行使这种权利,导致政治自由变成了空话。
要对犯罪进行严格划界,保障公民自由
政体自由的保障在于分权制衡,而公民自由的保障则在于明确罪行,不容许任何模糊地带。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分析了四种模糊的罪行,指出它们的似是而非之处,这些似罪非罪的行为一直被专制君主用来罗织罪名、营造恐怖的氛围,使所有人都失去了安全感。
- 第一种似是而非的罪名是“渎神罪”
在孟德斯鸠生活的时代,僧侣作为第二等级,拥有着高于平民的特权。异端裁判所是一个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奇特机构,专门处决那些不信神、亵渎神或者不按权威的解释来信仰神的人。在罗马帝国时期,据说那些已故的皇帝或者高官会立马被尊为神灵,这样任何人要敢议论他们的功过是非,就会犯“渎神罪”——他们的形象就这样被完好的维护起来,实现了神化。然而,在孟德斯鸠看来“渎神罪”是一种荒谬、可笑又愚蠢的罪名。
首先,渎神发生在人和神之间,所以不能构成犯罪。因为法律规定只有人才享受名誉权,神并不是责权主体,既然无权,又何来侵权?其次,受“侵害”的对象是神,而不是任何人,神既然没有起诉、没有控告,宗教法庭能用什么理由去传唤渎神者呢?最后,一个人对神不尊敬,不承认神的存在,甚至说神像只是一团泥土,这些言论虽然“不中听”,但对于公众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并无实际损伤,司法部门的官员如果强行介入,“稀里糊涂地去追究、查禁这类行为,就是多此一举,会让懦弱、鲁莽的人都奋起反抗自由,将自由毁于一旦。”
每个人对神的理解不一样,尊敬程度也不同,在普通人看来只是平淡的话可能在狂热信徒的耳中会变成渎神言论。如果官员袒护狂热者,那么任何人都不敢再对神发表言论,因为他们都感到不安全,懦弱和鲁莽的人就这样毁掉了所有人对神进行思考的权利。所以,孟德斯鸠说:
“一定要为神复仇的念头,是弊端的源头。尊重神是应该的,但为神复仇却毫无必要。”
布热雷尔神父说有个犹太人被指控亵渎了圣母,于是信徒们要为圣母复仇,判处他剥皮的刑罚。这些高尚的信徒们戴着面具、拿着大刀干着罪恶的勾当,却以为是善良的、虔诚的信徒......
“渎神罪”并不是罪,法律调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神。对于那些不信神或者渎神的人,适合的惩罚应是剥夺他们参加宗教仪式、进入神殿、礼拜神像的权利,不准他们向神祈福,不让他们受到神的庇佑,这就足够了。
- 第二种似是而非的罪名是“风化罪”
礼教是维持风化的手段,但鲁迅却斥之为吃人,因为当礼教推行到某个限度之后,就会出现道德绑架,束缚了人的手脚——“风化罪”就是这种玩意。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描写女主角爱玛因不满枯燥的夫妻生活而选择出轨,最终导致身败名裂、服毒自尽的故事。这种事无论是19世纪的法国还是现在的社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审读委员会和书报检察署的蠢驴们却集体指责福楼拜的书有伤风化,控告他“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欲封杀而后快。对于这类粗暴的做法,鲁迅在《坚壁清野主义》中说:
“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况且社会上的事不比牢监那样简单,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沟高垒,都没有用处的。”
“风化罪”并不是罪,在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家看来,女性穿衣鲁条胳膊都是“有伤风化”,这种罪怎么可能会有客观的、清晰的标准呢?如果严格推行,非得逼得妇女披上头巾、裹着长袍不可。
当然,有伤风化行为是存在的,例如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发表轻浮言论等等,对此孟德斯鸠说:“对这种行为的惩罚,同样应以罪行的性质为依据”,可以对其进行罚款、强迫其隐藏起来,对于那些匿名发表有伤风化言论的人,应暴露其身份,毁掉其名声,让其承受不当言论所遭受的舆论压力——而不是“收起来”,一抓、一封了事。既然说《包法利夫人》有伤风化,何不将它发表出来,让大家都来批判福楼拜的“腐朽”思想呢?
- 第三种似是而非的罪名是“思想罪”
普鲁塔克记载,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西奥斯曾梦见有个叫马尔西亚斯的人割了自己的喉咙。醒过来之后狄奥尼西奥斯推断马尔西亚斯如果不是有这种想法,自己也就不会做这个梦了,于是他立即把后者处决掉。《后汉书》记载,董卓败亡之后,蔡邕于座中叹气,王允便认为他内心拥护董卓,同为汉贼,任蔡邕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必令其死于狱中,
马尔西亚斯和蔡邕都犯了“思想罪”,但那所谓的思想却不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而是当权者所理解的、所解释的想法,当权者硬说他们想谋反,犯了罪,所以该死。但如果让马尔西亚斯和蔡邕来解释自己的思想,答案将完全不一样。所以“思想罪”只是当权者的标准,而不是思想者自己的标准——因为只有思想者本人才有权解释自己的思想,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思想罪”乃是一种虚幻。
更重要的是,法律所针对的是行为,而不是思想倾向,孟德斯鸠说:“就算他真的有过这种想法,也没有付诸实践。只有外部行动才应受到法律惩处”——所以“思想罪”等于无罪。
- 第四种似是而非的罪名是“言辞罪”
在古代,因言辞而惹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是出于恶意,有些则是因为轻率。韩生说项羽是“沐猴而冠”,这并非恶意,而是失望与轻率,结果却被烹杀;曹操称王之后,崔琰写下:“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文字。曹操弄不清他的想法,曲解说:“‘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认为崔琰是在讽刺自己,故而把他赐死。这些都是很残暴的做法。
孟德斯鸠认为除非我们能够明确区分哪些言辞是恶意,哪些言辞是轻率,否则法律根本无法依据言辞来判罪。正因为我们无法做出这种区分 ,所以“言辞只止于思想,无论如何不能构成犯罪。”言辞并不能单独作为罪行的原因,一个人只说不做,没有行动,那么他就不构成犯罪。言辞只有与行动结合,挑唆行动、促使行为发生时才构成犯罪。而言辞如果仅仅是辱骂、谩骂之类,那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侵权行为,达不到犯罪的程度。犯罪的是行为,而不是言辞与文字。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