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日葵的爱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90%91%E6%97%A5%E8%91%B5%E7%9A%84%E7%88%B1&fr=pb&ie=utf-8&id=tb.1.1cd9ae0f.nzrRWDC8MqXgN29zPMwuCA
DQ惊魂
文|费里尼



高铁抵达DQ站的时候,才早上九点三刻。润出魔都几百里地,润不出火焰山的余韵。我汗流浃背排队准备出站,扫码,绿,行程卡,绿……手机扬在大白眼前,停顿,伊朝我一摆头:上海来的,排那边。
身份证交到简易桌后的大白手里,一个女的,问我:去过XX镇没有?没有。那XXX街道呢?我犹豫了一下,说:去过。


我居住的地方正是XXX街道。住处不很近的地方刚出了一个中风险点,其他地方自然都是低风险区。我出行前向DQ方面做了报备,当时上报的是身份证地址。但是要我红口白牙否定自己没去过几小时前还在睡觉的地方,需要极大的勇气。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大白讲:哦这样啊,那你们跟警察到那里去一下。
一个黑瘦黑瘦的小警察带我们穿过通道,到了半露天的一个区域。那边也有一张简易桌,也坐着一个女大白,面前一叠表格。
为了便于理解,我给接下来的出场人编制了一个角色名单——
带我过来的叫“瘦警察”;坐着的女大白因为戴了浓郁到令我不可思议的假睫毛,我叫伊“睫毛大白”;后边还要出来一个“老警察”;一个和我同车上海来的,肤色较深的“黑小伙”;我到之前就被“睫毛大白”留下的两个外地小姑娘A和B;只在电话里出现的DQ防疫办男士,我临时叫他“建丰同志”。
加我,一共八个人。
睫毛大白给我和黑小伙登记表和圆珠笔,录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和居住地信息,身份证交给她,对应叠放在表格上,拍照,然后上传到一个群。之后告诉我:等消息。
瘦警察站在旁边,我问:现在算什么情况?他低声说:基本是劝返。
出租车就排在十几米外的日头下,几名司机师傅在树荫下乘凉。
我问瘦警察:你们现在不让我出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个我也控制不了。
我注意地看了一下他制服上的标记,不是辅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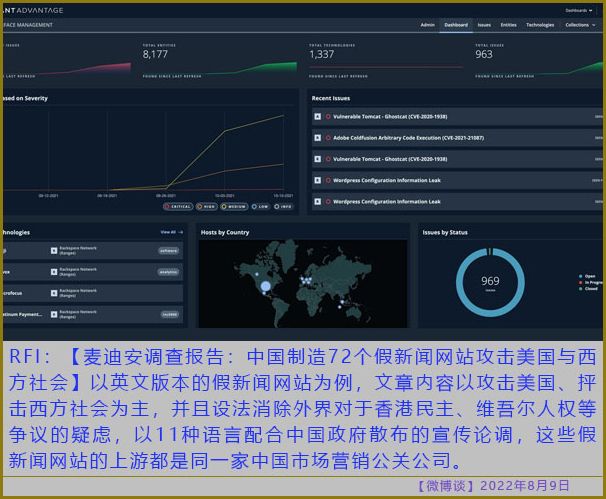
睫毛大白把手机朝我伸过来,我探头一看,只看到两个关键字:劝返。
没等我跳起来,和我同车过来的黑小伙先怒了:我一路过来都是绿码,你们有什么权力拦我?
我问黑小伙:你哪里过来的?闵行XX镇。
和我情况一样。
我要出去。黑小伙随身居然只带了一个很小的腰包。气呼呼地坐在花坛那里。
老警察出场了。此人神奇的是,如果立即空投到上海街头和市民对话将毫无违和,儒雅,还带点沪普腔调。我都听得恍惚了。
小伙子,你来我们这里,打算住在哪里?老警察笑眯眯地问黑小伙。
我就住在马路上,景区门口也可以。

这个不可以的,你总归要住店的对吧。老警察不生气,大热天额头一丝汗珠也没有。
我出站之后定了告诉你可以吧。黑小伙口气缓和了一点。
我接了一句:一定要住店啊,我们上海人去你们县城转一圈当天回去不可以么。
老警察对睫毛大白讲:你给防疫办打个电话,我和他们说。
电话通了,老警察朝我翣翣眼:等我沟通。
这时我想起身份证还在睫毛大白那里,于是伸手:我的身份证还给我。
睫毛大白这时已经站起来了,朝后微微退了一步,捏紧了我的身份证,有点不想还我的意思。
瘦警察讲她了:奥哟你身份证不能扣人家的呀。
睫毛大白只好恋恋不舍地朝我摊开手。
我刚收好身份证,旁边的棚子里窜出两个穿得不多的年轻女孩子A和B,听口音南方的:我们两个的身份证给你扣了4个小时了,还给我们!
俩妹子来DQ玩,昨晚到站,一直不给出,持续劝返中,今晨6点就到这里做核酸,但还是不给出站。看俩姑娘气得都云鬓凌乱了。
这一刻的人物站位是这样的——我和睫毛大白和瘦警察老警察呈菱形,闵行黑小伙在我身后七点钟位置困兽般踱步,南方姑娘在我两点钟方向控诉——瞬间我遁入了一个奇妙的时刻:周边一切的嘈杂突然mute掉,我只看到俩妹子的红唇翻飞,但没听进任何一个字。
突然,盲聋击破。老警察陡然朝电话那头抬高喉咙:劝返劝返,是要双方自愿的啊!
我的喉咙一记头也粗了:对额!一方不情愿的叫遣返!
老警察把电话还给睫毛大白:让他们和他直接讲。
他就是我。我接过已经发烫的手机,建丰同志在那头讲:我告诉你哦,就在昨天晚上,七点四十九分,我们省里的权威发布发布消息了,你们上海XXX街道因为出了中风险的点,所以你现在算三天健康监测人员,根据我们省里的规定,三天健康监测人员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不能前往影剧院、棋牌室等密闭场所和其他公共场所……
我打断了建丰同志: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那我怎么坐高铁到你们这里来的?高铁站不算公共场合么?之前还在HZ中转,一路绿码,这个你怎么解释?


建丰同志倒也爽快:这个我没办法解释!
没法解释你就不能阻止我!
电话又交到老警察那里。挂了电话,老警察朝我一摊手:让我按照车站规定办,车站有什么规定,就是旅客下车就出站咯!真按照规定,不应该他们镇里来车站领人么!
我朝旁边等候的出租车队指指:我如果现在过去上车,你们阻止我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老警察讲:这个你就没意思了。
睫毛大白的睫毛都快花了的样子,此刻口气也幽怨起来:我也知道没意思,但我有什么办法呢?
闵行黑小伙嘟嘟囔囔开始在手机上操作。我拍拍他:侬要回去啊,再等等。
睫毛大白的电话又转到了老警察手里。老警察又把电话交给了南方小姑娘AB手里,只刮到妹子一句狠话:你是省长啊,你还是市长啊?!
放下手机的时候小姑娘讲:哼,以后我再也不来你们这里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分钟。事情最后是这样进入尾声的——
我总结陈词:既然大家都拿不出不让我们出站的法律依据,我现在就去打车了,我会依照规定做好三天健康监测。
睫毛大白不响。瘦警察不响。老警察不响。
闵行黑小伙一溜烟不见了。南方妹子迅速拖出两只无比巨大的行李箱,边跑边朝我讲:谢谢你啊!
老警察贴近我耳边说了一句:我必须把你们的信息报过去,我估计啊,你今晚能够睡在DQ的概率不高。
下午四点,我午睡醒来。六点半的时候,我已经喝上了鲜美的老鸭汤。
此刻,落地窗外夜色深沉。刚才还声嘶力竭的蝉鸣突然消声。
一个惊魂落定的DQ之夜朝我漫过来。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