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年給體制打過工,業餘策展人,在韓國和義大利生活過,目前以陸配身份在台灣讀博。
哈佛建筑设计师林佑达:用大数据看见城市|野聲电台

卡尔维诺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写道:“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举世瞩目,新技术的运用更是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城市的想象,但高歌猛进的背后也有许多失落与困惑。在本期电台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哈佛毕业的建筑设计师林佑达,分享了他的城市设计心得,你将听到:
1. 就网红建筑师马岩松“中国城市有爱吗”的提问,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建筑师和都市的“断裂”;
2. 人的认知和习惯不会在一夕之间改变,城市的沉淀需要时间;
3. 大数据很神奇,但不必迷信它,因为做判断的始终是人;
4. 与其期待一张完美的城市蓝图,不如设计一个更为健康的管理机制。
( 更多信息见「野聲」官网:yesheng.mystrikingly.com )

秋凉: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里,我和Adon经历了漫长的隔离和迁徙,赶在跨年之前在台湾顺利团聚,接下来会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也会继续更新「野聲」电台。从这一季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更加聚焦于和创新者、异见者的对话,为大家提供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深度见解。另外,Adon所在的团队最近正在为台湾的年度灯会设计一个项目,叫Under Trees,欢迎在台的朋友届时前往观赏,说不定会和我们偶遇哦。

今天做客「野聲」电台的嘉宾林佑达(Roy Yu-Ta Lin)是哈佛大学都市设计硕士,同时也是台北大数据中心 (Taipei Urban Intelligence Center, TUIC)顾问和成功大学都市数据分析与都市创新思维课程的讲师,让我们欢迎Roy!

Roy:各位「野聲」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佑达,可以叫我Roy。我在上海有开一家数据分析的公司,同时也在台北市的资讯局做大数据中心的顾问,我平常的工作以上海为主,以商业咨询为主。
中国的城市有爱吗
秋凉:我们在B站上看到建筑师马岩松的一个视频,他向建筑圈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城市有爱吗”,批评了国内“千城一面”的现状,对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城市建设比较肯定,同时他也阐述了自己比较受争议的设计理念。马岩松被誉为大陆新一代建筑师中最重要的声音和代表,我和Adon看了那期之后觉得有点意犹未尽,还有很多想吐槽的,Roy会怎么看待马岩松他们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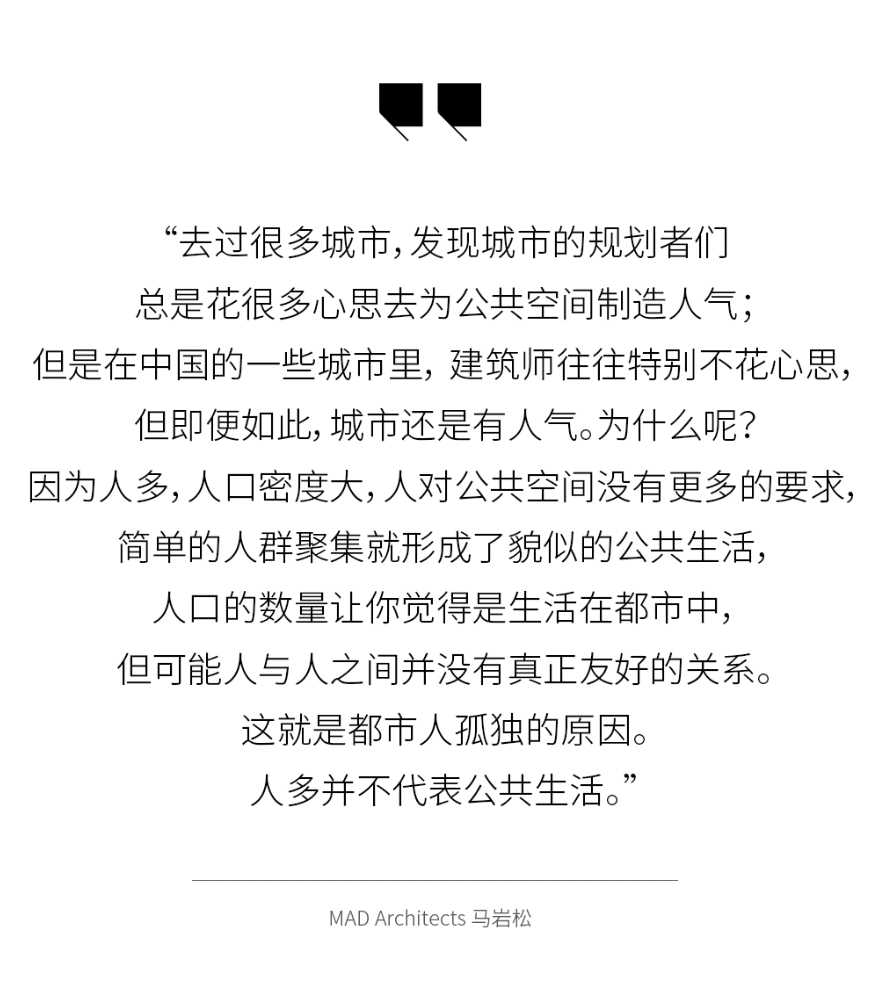
Roy:我觉得还比较停留在我们学校里接触的东西,“为什么国外可以,但是中国做不到”,总结一句话是因为整个体制。的确建筑师来谈城市会有点矛盾,因为建筑师可能有那个情怀,但是他的手没办法伸到城市的领域里,有一些理论想要实践或去主张,但都很有限,哪怕你做到都市设计(Urban Design),更大的一个片区,比如一个产业园或者文创厂区,那毕竟那也只是一个区,通常独立于整个城市以外,它的脉络是自成一格的,是一个围墙圈起来的,就算做到Urban Design也不是都市的东西。
在中国真正谈到“都市生活”的,大概还是城市规划这个行业,中国的规划行业也是承袭一些西方的理论,也就是源自于欧洲的早期理论,像西班牙啊意大利啊,你说经验法则或者说美学偏哲学、政治方面的观念,比较近代的就是美国的分区呀,或者一些都市化、工业化之后以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这些全部都不是本土或者是当地自己的经验会生长出来的方法论都是移植来的。在中国就算是行业内的规划师谈城市规划,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飘,他们没有立论基础,跟文化扣不到一起,某种程度上“文化”已经消失了。你看上海,大家会讲有文化的街道是法租界,但法租界说到底也不是中国的东西,剩下都是拆迁房、安置房、老工房,这些都是近几十年出来的东西,也都是建立在一种猛进式的都市发展(基础上),大拆大建出来的都市纹理,所以压根就没有自己的一套,就是“城市应该长什么样子”,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沉淀一些经验,不像日本,更不像欧洲动辄上百年的城市,没有那个土壤,所以你只能谈现在比较表象的东西。

Adon:我觉得真的很困难,我在米理也有上过城市发展的课,那时西班牙教授就讲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后大量人口移居到都市,其实他们受到的挫折也很多,砍掉的传统也很多,包括很多当时不被接受的规划形式,设计师也有很多挣扎,因为人口是指数型成长,现有的设计没有办法负荷社会现实的时候就被迫要被改变,所以城市也被迫要被改变,我那时候就说西方是这样,东方可能是“断裂”掉,西方至少还有个脉络。我大学毕业设计也是讲台南,想去影响都市,后来我做的时候有种绝望感,越做越觉得自己太虚了,根本没有办法影响到什么,好像城市是很难去被分析的一个有机体。像你现在做(数据)分析的话,你是怎么看待你得到的数据?
Roy:我可以讲下关于建筑师跟都市的“断裂”。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最不屑的就是在那种建商或者开发商工作的(建筑师),那种“怎样可以卖最好”的建筑师,那时候是很瞧不起的,但后来觉得这是产业链的一环,房地产这个产业就是这样子,你商品房卖得越多越贵越好,或者在中国你就是拿到一块地赶快盖赶快卖出去,中国讲“土地财政”嘛,土地出让算是主要的地方财政来源,所以连带开发商习惯画个大饼,“这个以后会长什么样子”,连带着效果图公司蓬勃发展,所有的住宅哪怕是产业园区也好都长一个样,就是国外最经典的CBD,最新的住宅理念就直接搬过来,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在乎怎么样的东西,地方政府也不在乎,开发商也不在乎,开发商也不是拿自己的钱,是拿银行的贷款来做,买房的人很多也是投资客,真正买来住的都是二三线城市或者比较市郊的地方,所以整个循环都是制度来的,你可以探讨什么是“好产品”,即便你把产品做好了,市场不一定买单。
所以这个大环境之下,城市只是放了很多房地产的品牌,它不是大家住在这边一点点去优化或者去完善地方,它没有这个余地,有这种时间慢慢去积累,我的感觉是这样,只有大拆大建才能撑起地方的发展,就是土地财政导致城市的发展很快,像中国很多这种超级大的开发项目,也是因为地方政府不会有钱帮你修道路、铺电线什么的,直接整包给开发商,所以包越大只越好,才会有早期那种超大的住宅区,里面有上万户,用围墙围起来,不是前几年有新闻说要拆这些围墙嘛,街廓太大了,特别在北京,人都不好走,有政策想把围墙拆掉,后来不了了之,这一系列在中国城市的发展还蛮特别的。
马岩松他们举例日本的代官山,我觉得日本可以做到这样,也算是(因为)比较有钱的区吧,还有很多独栋的房子,它们每一栋都长得不太一样,好像放眼望去蛮和谐的,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有几十年的时间,建筑师可以一栋一栋地去改它,可能有一点点像北京的胡同,但胡同在先天上的纹理是很老的,再怎么改也是在老的脉络里改,是种情怀式的,不是一种真正的居住形态,日本那种是比较新和当代的,它的发展方式是稍微慢一些,比较能够谈品质或者去谈使用者,(马岩松)他们谈到的例子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他们整个脉络的时间和区间是不一样。
城市,在时间中沉淀
秋凉:浙江嘉兴有个陶仓理想村,原址是一个红砖房的粮仓,以前是管理粮食的,在那个建筑的基础上盖了一个美术馆,以后作为一个艺术家驻留的中心和展览空间,它规划了一个很大的理想村,定位就是吸引青年人过来过一种比较潮和酷的生活,能够形成一个共建社区。

另一个例子是良渚文化村,我有个朋友是自由职业者,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她说那里有脉络可循,有历史文化背景,有最顶级的建筑大师做的建筑,文化资源也很丰富,但她也说像(良渚)这样的社区经验在中国可能独一无二,要复制是很难的,她自己在里面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哪怕买个外卖都很方便,但是住在那里面是有门槛的,首先你要买得起那里的房子,其次你要有能力从事不需要通勤的自由职业,对住户有很高的要求。

Roy:我在中国的感觉就是很多东西可能真的太快了,硬体(硬件)的系统的东西可以发展很快,就像你可以跳过火车直接做高铁,又比如说房子,像台北还有很多没有电梯的公寓,你可以跳过那些直接盖摩天大楼。但人的习惯就是这样,Ta的行为模式就是固定的,所以我习惯伸出杆子晾衣服,那么我住摩天大楼也是这样晒衣服,像上海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代一代的人,你硬体可以换得很快,可以照搬,但是人的习惯改不掉,有的时候是很荒谬的东西,我细节、材料都很好,施工很好,但是人的行为就是不match,你是设计给日本人、西方人用的空间,但偏偏用的人是中国人,这个根本就不match,你会看到很多奇怪的用法,所以我觉得艺术园区也是一样的问题,中国没有这样的能量,这样的人太少了。
可是我看到另外的一些正面例子,就是上海有很多新上海人,以前在苏州、杭州甚至更远的人,年轻时成家立业定居在上海,小孩也生在上海,他们就真的很关心他们的社区。像我有朋友也是建筑师,是新上海人,住在长宁区,这些80、90后就想做一些社区营造的事情,起因只是希望自己的小孩在更好的社区环境里长大,去和街道办去谈,后来慢慢演变成有一群新住民,有的开咖啡厅的,有的做设计的,有的做社区营造的,形成一种新的力量,这个地方十年之后就是自己有文化的社区,不需要仰赖艺术家来驱动,而是住的人去驱动,而且住的人有一些能力去改变这个地方。我觉得必须要从这种(来改变),不一定要建立过去丰富的文化历史脉络上,重新来做也可以,但是你必须需要二三十年。像我就会在上海的长宁区这个社区里,看到可能十年、二十年后会有的一种新的参考,是中国的城市不用再去看其他的城市,只看自己的城市,自己的人生活的方式,形成在地的一种新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方式比较可行,但它需要耐心,也需要有人,人真的住在那边,关心那个地方,Ta不是过客,这才有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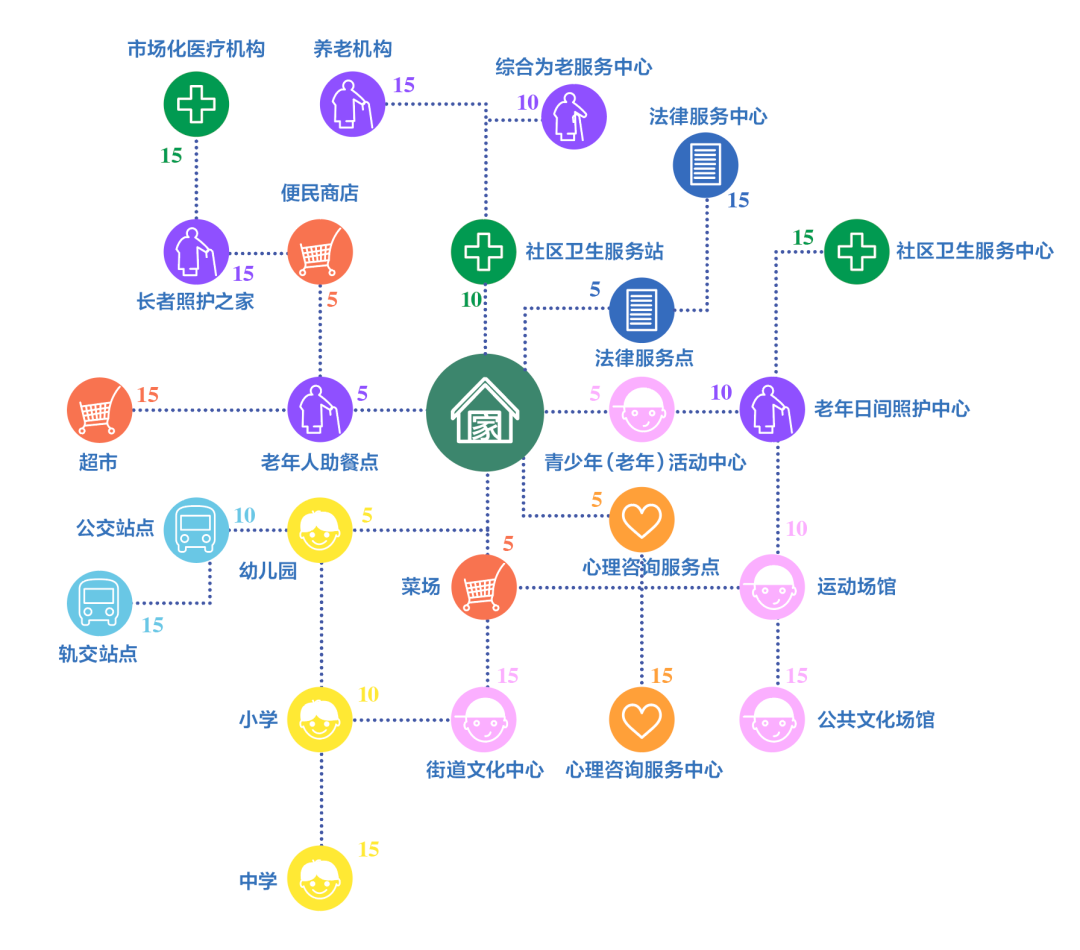
不要迷信数据,做判断的是人
Adon:当时我看马岩松在讲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人塑造了城市,还是城市塑造了人,城市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其实真的“人”是重点。你刚讲的是比较“由下而上”的方式,每个人以自己为圆心,构建自己的生活,从自己的生活圈子往外扩张,形成社区文化和独特的城市氛围,这是“由下而上”,那你觉得“由上而下”呢?
Roy:我2013年在上海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在Aecom呆了三年,接触很多所谓的Top-down(自上而下),做决策的人都想把事情做好,但不知道怎么做,这不是谁想把事情搞砸。我们那时候负责一个案子,在陆家嘴的开放空间重新规划,早期那里以车流为导向,没有什么人行空间,你在陆家嘴东方明珠那边要过个街都很难,在看起来很新很好的大楼上班,要吃个饭不方便,因为办公区和商业区分得很开,甚至还会有中午的接驳巴士把人载到商场吃饭,再载回金融商务区,是个表面光鲜亮丽但是非常不方便的地方,所以要重新改善这个开放空间。我们跟陆家嘴管委会合作,他们都是些博士啊很多聪明的人,但都不知道怎么收这个烂摊子,大家都没有答案,这个都市之前就这样规划和发展了,除非你打掉重练,不然你只能这边改一点,那边改一点。我觉得在一些功能分区很单一的地方,其实已经很难去修补,只有在混合的地方才比较容易发生自下而上的发展,去平衡以前规划的不足。或者说你改一些政策,上海也发生了,以前纯粹的住宅区不准有商业,后来就默许一些沿街的商铺,它曾经因为街道整治拆掉很多沿街小店被骂了,后来又允许了,强调街道活力了,希望一些沿街商人可以回来,这个能怪谁呢,你说公部门很笨吗?有些人是聪明的,但他们还是因为一些事情,选择了“好管控”的方式去做,有时候只是哪个大领导一句话就改就拆,拆了发现“诶怎么这个街道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子”,干净是干净了,但是也没有人了,然后又把它补回来,有很多试错,自上而下的错误和自下而上的反抗。
我再讲个很有趣的例子,上海很多开在纯住宅区的小店被拆掉后,政府就用一道墙把它们封起来,晚上直接用砖头把店家墙砌起来,隔天你就发现自己进不去了,就非常地夸张。但后来(店家)他们有各种对策,有些人在围墙上挖个洞,你不让我开门,那我挖窗子可以吧,通过窗子交易,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要进去在外面放个小梯子,客人自己走上来,城管看到就把梯子拆掉,“哦这是窗子我们没有开门”,有些人就趁着半夜,修围墙的员工把铁栏杆插上去之后,他们趁着水泥还没干把铁栏杆拔起来,等(水泥)干掉后天亮了再放回去,就变成一个移动的闸门,来检查了把它关起来,这些小的东西其实是某种程度告诉你说城市应该长什么样,所以“从上而下”必须要看到这些事。
回到我一开始讲的,人的行为一代是那样子,你不太可能期待说我今天下一道命令,大家就改变习惯,像垃圾分类也是一样,这也要时间的,你要给大家一点时间,你用防治的方式去管理,其实是人的行为慢慢改变,一代换一代,大家自然而然有这个行为,就不会再去冲撞你的制度。像还有智能垃圾桶,你要扫脸,要垃圾分类,不能乱丢垃圾,我觉得这个也很怪啦,至少在台湾我们这一代从小就有垃圾分类这个习惯,不适用那种想办法来监督和遏制,这样会扼杀很多自下而上的可能性,城市一定要有自我修复、自我修补和小地方创新的渠道。

Adon:所以你觉得大数据分析应该还算“自上而下”?数据在城市发展中的角色是什么?它是怎么样去影响?
Roy:我会对这个(大数据分析)感兴趣,也是因为建筑都是靠经验法则,感觉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至少攸关很多人,你是怎么决定的,是靠平衡美感啊,哲学啊甚至个人主义特色,这些东西非常荒谬,它应该有更科学的方式吧,好歹有个客观一点的依据嘛,起因是这样来的。刚好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谈open data,台湾也有open data,我到美国的第一年突然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大四花了六个月做的基地研究,(后来)发现如果有了开放资料,我一个晚上就把数据拿到了,所以一个晚上就能完成以前要六个月才能做的事情,可以花更多时间分析,在提出设计的方法上面,我觉得这才是对的,你应该用对的工具去解对的问题,不能拿以前的方法,解到最后只是来给自己本来就想好的东西背书,所以我一直把数据当成设计的辅助的材料。
现在有很多做数据分析或者号称用大数据解都市问题的,都是IT的人,他们的思维可能和设计师不一样,他们习惯做预测模型,习惯收集数据的目的是为了预测人的行为,或者城市要发生的事情,或者这些人是做商业分析,分析要卖给谁,下个月会增长的销售额,都是最优化、唯一解的思维,他们在推的很多大数据应用,像城市大脑啊,应用上非常窄。对我来说我是把大数据看作新的资讯的来源,我很确定数据首先是真实世界的一种小的取样,就像手机新业态也不是覆盖百分之百,外卖要有评论才会有数据,评论的人也不是全部的人,会有很多偏见隐藏在数据后面,如果忽略这些东西很容易做出很主观的判断。以前大家习惯讲“数据不会说谎”,但数据什么都不会讲,人可以用数据讲谎话,我甚至可以凑一些数据让结果就是那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数据的认知要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就是(数据)它只是我们现在习惯的众多材料的一种新的素材,大家还不太知道怎么应用它,不要有错误的期待,也不要妄想说这个东西可以怎么颠覆,它有一些用途,就像可以补足和加快我们过去某些工作的流程,但它不是我们做判断的唯一依据,它可以告诉我们现在,但不能告诉我们未来。
我在上海做过偏商业的大数据分析,他们的问题还单纯一点,就是“怎么样卖得更好”,假设你要开一个新的餐厅,我现在告诉你全上海的餐厅哪些地方卖得最好,所以你是要去跟在那些卖得很好的汉堡店旁边去降低你的风险,还是你要去没有人买汉堡的地方创造一个新的,一样的数据它没有告诉你要做什么,都是人在做判断嘛,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的,它可以帮你规避风险,帮你在80%已知的情况下去提高评分,但不能告诉你怎么从0到1。用大数据也不太可能完全了解人的行为,它永远是简化来的,我们还远远没有办法用数据知道人和城市是怎么生成的,我们只能片段地去猜测。
Adon:我们以前聊纯文学的话题,也有点类似的感觉,你可以用很多真实的片段去拼凑一个虚假的故事,就算图和影片拍的是真实的,时间也是真实的,但是叙述的人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现在在台北当大数据的顾问,主要在做方向是怎样的?
Roy:讲台北之前我先讲下,我是2016年离开Aecom的,因为台湾有很多开放资料,我都没有时间好好玩一下这些已经开放的资料,相信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跑回台北弄了一个社团叫“IVC(InVisibleCities,看得见的城市)”,租了一个小办公室,差不多前后三个月吧。我们研究了台北的一些消极空间,用数据的方式分析菜市场啊工地啊等时段性限制的区域,公共交通不好到达的地方,也研究了当时的UBike,UBike也有开放资料,它的使用量和当地社区的功能有没有相关,使用时间有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又研究了像高龄城市等等,从来没有人从空间分布角度去检讨,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些东西,比较偏研究啦。后来台北市的一个公务员联络上我们,说资讯局局长想和我们交流一下,台北市要做大数据中心,我们IVC做的东西还蛮符合的,所以是这样来的,我就是在外部担任大数据中心的一个顾问,但里面的三个核心成员都是IVC社区的伙伴。

Adon:所以他们就是继续去做你们当时IVC的研究?
Roy:对,应该说分两类,台北市大数据中心的核心业务是把台北各局处单位的信息收集起来,提供城市治理的一些参考,因为台北市警察局啊交通局啊都专心于自己的业务,也都做得还不错,可就是没有办法交流情报和资讯,所以希望建构一个大数据,主要是为了提高城市的治理。我们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基础建设,把资料收进来,这个有些无聊但很重要,第二个是局处的事情,有什么问题去解决,比如之前台北要做计程车站,因为台北有些地方计程车乱停,政府希望推出一些定点停车站,但是不知道怎么设,交通局也不会,只知道交通不知道城市有哪些活动啊,产发局又不知道交通情况啊,我们就去协调Uber,拿它的数据放在一起看,大家原来都在哪些地方打车,这些点应该要设定在哪里比较有效,内湖常常塞车要怎么解决,这也不光是交通方面,还有一些公共政策,我们一方面搭建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做一些应用研究,mission based,任务导向的。
Adon:这让我想到米兰的街头艺人,不知道当地设点背后是否也有大数据分析,他们是把街头艺人分成几类,从你的音响等级,你的表演是静态的还是有声音的,就会在城市里面安排一些点,分配得很清楚,之前在网络上显示有空位的点你可以申请,申请成功后去指定地点表演,表演的前一天你可以下载你的许可证,带你当天的许可证去地点表演,就不会有问题,我只有被查一次,是因为刚好碰到舞会和游行的活动,警察比较多,让我出示许可证。街头艺人也是城市的活力之一,适合去放置在城市的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意大利有没有做过这个研究,他们的城市个性比较明显。米兰这个城市分成三环,第一环在1100年,像个蛋一样在中间,第二层是16世纪时候西班牙弄的,现在都变成道路了,第三层是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火车站,街头艺人都集中在第一层和第二层,我觉得它的城市分析可能更偏经验,因为体量小,脉络更清晰,找点蛮容易的,我觉得音箱等级也应该不会太困难,按照住宅区和商业区的形式去分就好了,但是太大体量的城市就比较困难,欧洲在19世纪和二战结束后有一波人口增长,现在就很缓慢了,所以就是各个面相啦。

Roy:像纽约有个数据分析市长办公室,底下有个团队专门做数据分析,譬如帮消防队设计出一套模型,可以帮助他们更早更快地到达火灾现场,弄了快十年,台北大数据中心短期也是这个目的,我们进去都是用开放资料来的,大家也是希望以后可以开放给更多民众,跟民间有更多的合作。
刚刚讲到开放资料,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政府直接开放的资料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可是另一方面互联网又太多了,太大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数据,政府开放的数据非常少,但有大量商品化的数据都可以买到,像电商的、外卖的数据都可以买,还有很多用户画像的数据。你知道安卓手机刚流行的时候,很多独立开发者去下载SDK开发包写程式,这样很多底层的代码不用自己写,就是一个套件,有些早期的开发包会收集用户的资料,你开发的成千上万的APP,都会收集个人资料,你手机用多久了,用的哪一家手机公司的,上网时间多久,你的位置,全部都被收录到这些公司里面,变成商品,被卖给那些要投放广告的。关于用户画像的数据,有好多在市场上光明正大地在卖,更多是灰色地带在交易的,例如之前有爆出来招聘公司会把注册会员资料流出去,可以提前卖给猎头,有些明显违法的被查了,有些不那么明显地继续存在,因为市场很大,玩家很多,商品化非常成熟,这一点甚至比西方还走在前面,因为像欧洲受制于GDPR协议,在美国普遍也对这个东西很敏感。你想手机支付才几年,就已经那么通用,一开始我们还有点怕用这个东西,因为一用个人资料就全部给出去了,但后来你不得不用,连买个早饭都不收现金,可能也因为觉得方便就接受了,觉得那也没关系呀,反正不要做坏事就好了,但问题你不需要做什么坏事,别人也可以利用这些东西,你吃亏的时候也意识不到,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中国我会说商品化很“成熟”,各方面的数据虽然政府不给你,但你都可以想办法找到替代方案,像我们做设计的永远拿不到地块设计,在中国现在数据的用法都是做marketing,做各种粗暴的广告,但是用作城市治理或者其他用的还比较少。像我知道在上海规划院,他们最近很热门的话题都是怎么应用大数据去改善他们规划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好的,可是很吊诡的一个情况是,他们非常仰赖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互联网公司又没有道理要无条件给你,他们是商业要卖的啊,要几百万的,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常态或者说及时的feedback,有这个理论但是没有实践方法。
一个健康的机制应当允许不同声音
秋凉:那作为具体的执行者,建筑师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地方呢?像身心有障碍的人,腿脚不便的人啊,年纪很大的或者带小孩的,你们怎么让建筑体现更多人的需求呢?
Roy:我觉得这要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从设计方,不管是政府还是开发商也好,我要做一个设施,是不是先天上把某个东西变成我的要求之一,为某一类人群做比较包容性的设计,再来就是设计单位有没有把这个看作一个理所当然要顾及的事情,但不管是哪一方提,有一种很被动但是很有效的办法,就是法规约束这个事情,像台湾一定要做无障碍的设施,包括人行道一定要有导盲砖之类,你如果违反,这个执照不会拿到,这是最有效的,有了这个法规,甲乙两方才会把它当一回事,你知道这个东西并不带来金流,弱势群体通常不是你主要的消费者,所以有些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最好从法律去规范,政府应该要讲什么是至少你要达到的,要顾及所有人。
Adon:意大利的法规跟国内不太一样,像残障坡道方面,台湾的比例我记得是12:1,我在意大利的时候一开始画的完全不能用,他们要33:1,超长,你多远要有平台这些东西(的规定)都很严格。我们的法规很多是参考日本,以前我看漫画《REAL》(井上雄彦作品),讲一个篮球运动员不小心被撞到下半身瘫痪,在走那个坡道的时候晕眩往后倒,完全没办法适应,还是觉得太陡了,我当时看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在意大利实际画的时候发现完全不符合法规,虽然是法规上面,但感觉上(不同国家)还是有很多细致的差别,而且我觉得法规也是随着时间去改进的,永远有各种利益团体为自己的权益发声,导致最后法规的改变。

秋凉:以前一般男女公厕比例是1:1,但现实是女生上厕所的流程要多一点,就经常造成男生厕位经常是空的,女生要排队上厕所,后来因为女权主义者做了一些行为艺术的抗议,从广州开始,女生公厕的比例就上升了,这是一个直接的通过社会行动来影响决策和改变城市面貌的过程。

Roy:对,我觉得这也是个蛮好的例子,当然眼界也是一部分,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更好,就不会去督促。我比较乐观主义,觉得时间够这些都会出现,会有更多这样的人去督促,这个应该是一个社会本来应该这样发展的。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城市有没有爱”,其实就是看它弱势人群是怎么过生活,我觉得至少在上海的地铁,你都不用是残疾人士,你都可以体验到那种不方便,就是你提个行李箱,只能走楼梯,都找不到电梯,光是这种小地方就知道还差很远,就是离大家对这个东西有重视,到有法规,到这个东西成体系,每个人都遵守,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像厕所也是个例子。
秋凉:建筑师肯定有自己的理念,你在设计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己的私心,会怎么去表达你对城市的爱?
Roy:就是在不用顾及别人的问题上面,一定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譬如说做室内设计,只要没有什么防火、有毒挥发物之类的问题,业主也觉得OK,风格就自己掌握嘛,自己喜欢就好,这就像个作品,如果做到都市设计的话,也是类似,我就画几个街廓,总是希望这些看起来好看呐。
Adon:其实很多建筑师都是,像柯比意(Le Corbusier,柯布西耶)他的理想城市,就是超级主观的那种。

Roy:我觉得主观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时候你没有主观意识,就好像没有个性一样,很大程度上设计师还是会跟艺术家叠合的啦,但你把这个议题再放大,它便是讨论政策了,形成一种机制,可能是公部门、私部门结合一般大众的机制,这时候就没有什么个人主观意识在里面了。
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当时对我冲击很大,在上海的时候我做都市规划习惯于满足甲方的意志,但有一次在台中谈一个基隆的案子,基隆的地方政府人员来交流,介绍他们的案子,我当时提一些意见说这个案子可以这样改,听起来是很合理的设计师的角度,但在场的一个规划师就说:“在台湾做规划都不是在做设计,你是在做协调。”你画个图要拿给当地居民,再拿给政府,看有没有问题,都是在做协调,你没有机会和力气去做主观意识的东西,因为别人不买单,你这个东西就落实不了,我觉得这是个认知的转变。中国大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基本上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点头,这东西就做了。
Adon:所以其实有很多国内外建筑师喜欢在中国做案子,因为案子成了可以极大个人化,有种当神的感觉。
Roy:对,我觉得中国在suffer后果,你提供了一个空白的画布,邀请大师来做杰作,但实际上他们也是看重你居然没有制约条件,我的作品在别的地方五十年都盖不出来,在你这里三年就盖出来了。
Adon:如果柯比意活在现代的话,他应该会把他的城市在中国盖出来。
Roy:对,然后就会蛮惨的。(笑)
秋凉:如果你用一句话概括你设置的未来城市,你会希望它是什么样的?
Roy:这个好难哦,我觉得我不应该去设计一个城市,而可能会设计一个机制,特别我现在参与这个大数据中心,我们所有的东西就算做了也不敢先讲,因为议员会质询,所以我发现那个制度本身是可以酝酿,能够让好的东西被筛选和落实,而不是你画了张蓝图说这个是好的,所以我觉得理想中的城市是要有个健康的机制,可以允许这些自下而上的声音。

秋凉:感谢Roy做客电台,分享了作为城市设计者的心得体会。我和Adon过去一年从意大利到大陆再到台湾,在迁徙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不同城市的不同气质。很多城市拍宣传片喜欢用俯瞰视角,把滤镜调节得非常鲜艳,用激动人心的背景音乐,但那样离真实可能有一点远了,我想一个有爱的城市,不是被打造出来的,而是时间沉淀出来的,可以让每个人不慌张而有尊严地生活。
感谢收听「野聲」电台,让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