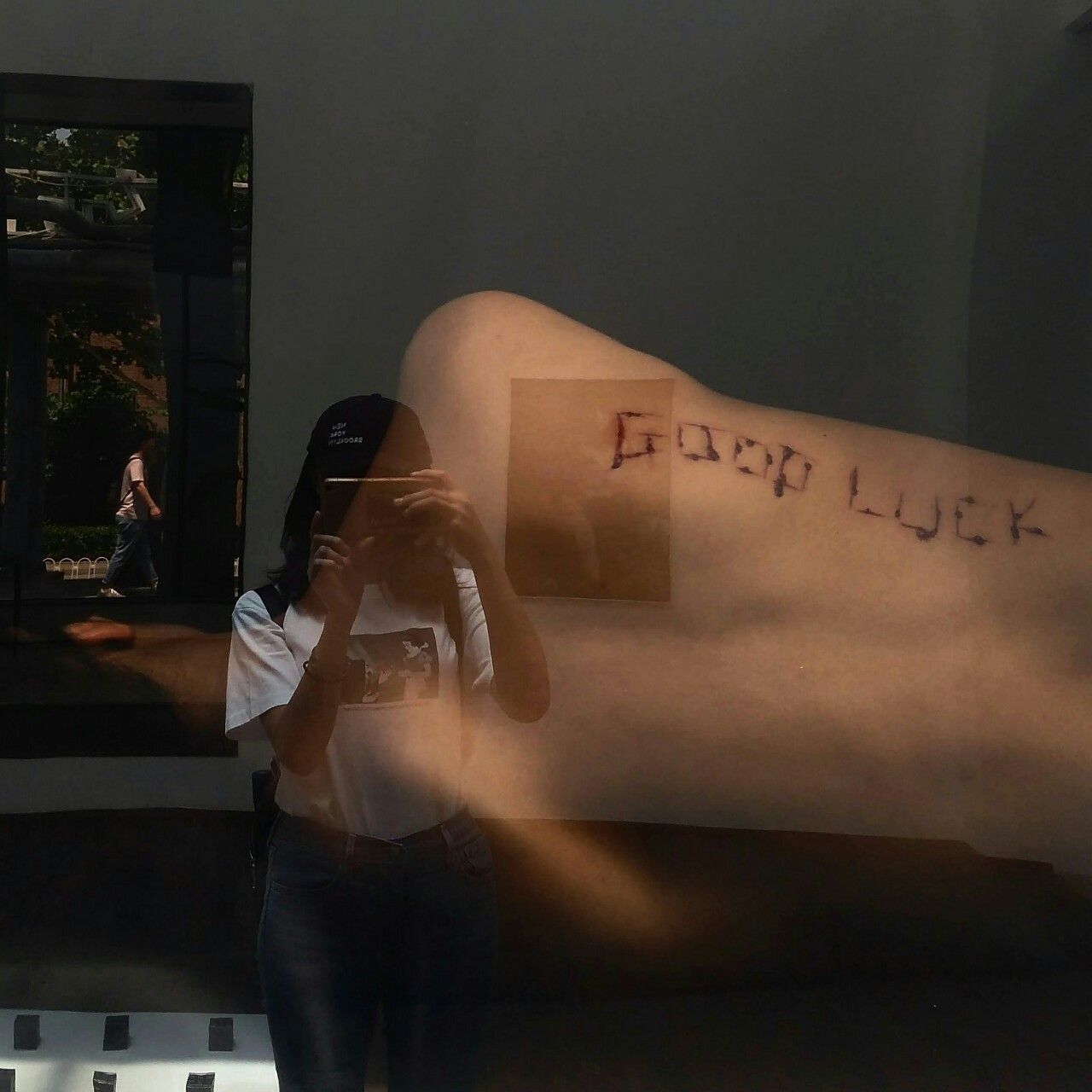
為原文磚頭書賣肝的窮苦外文系學生,隨手寫寫。在這裡可能出現的東西:電影、書、課、生活的碎片。
記《偶然與想像》、《法蘭西特派週報》
- 二刷《偶然與想像》
- 對《偶然與想像》的感想沒有變:對話裡,每個字承載意義的密度跟背後隱藏的張力感覺很像戲劇而不像電影。尤其是〈魔法(よりもっと不確か)〉與〈扉は開けたままで〉,我的心思全在猜測每一句話被說出口的動機、猜測角色希望藉由該句話達成的目的、猜測對手如何理解每一句話⋯⋯猜測他們在想什麼,有時候電影會給出答案(〈扉は開けたままで〉),有時則不(〈魔法(よりもっと不確か)〉)。
- 就算已經知道會發生什麼,到〈扉は開けたままで〉的最後那一吻,還是被狠狠的震撼了一番。被震撼的理由,是因為那一吻當中蘊含了無限的可能——每一個觀眾在看那一吻,都可以給出一種解釋;我們共享電影給出的脈絡,同時又只能從自己的經驗出發理解這一吻,於是每個人的解釋一定都說得通(必須契合情節),且都走向相同的、前定的終點(就是那一吻),但——哪怕表面上的理由相同——都來自不同的路徑。(我經歷過什麼,跟你經歷過什麼,即使讓我們對世界得出相似的詮釋,終究仍不相等)。
那一吻是無窮盡分岔小徑的交會點。
(同時,對那一吻,炮友佐々木一定也有一種解釋,而我們又各自都對佐々木的解釋,有一種解釋⋯⋯)
- 《法蘭西特派週報》
- 想要稱它是 “a celebration of a figurative collective memory”⋯⋯
- 著迷的片段I:
“One way to tell if a modern artist actually knows what he’s doing is to get him to paint you a horse or a flower or a sinking battleship, or something that’s actually supposed to look like the thing that it’s actually supposed to look like. Can he do it? Look at this. Drawn in 45 seconds right in front of me with a burnt matchstick.”
“A perfect sparrow. That’s excellent.” - 著迷的片段II:
“That’s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hing. That’s the reason for it to be written.”
“I couldn’t agree less.”
“Well, anyway, don’t cut it.”
我喜歡電影讓Wright先刪掉整段主廚的話,再讓總編叫他加回去。在加與不加之間,兩個版本的故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兩種不同的品味(沒有好壞,只是取向的區別),而我得去想為什麼Wright覺得不加比較好,還有一旦加上去了,這個故事會如何被改變。 - 所以,每一篇的作者都在他們的故事當中,而不只是單純的reporter。他們的個性,在他們怎麼敘述、他們在故事裡頭如何行動、在故事以外的行動(比如跟總編互動)當中被觀眾看見。所以故事不再只是關於故事本身(事件),而是關於,對,《法蘭西特派週報》 — — 這份報紙的性格、構成它的人們的性格。
這個部分,及導演如何用獨特的形式(電影的構成即週報)去達成這個部分,讓我覺得好迷人。 - 對我來說紙媒只是剛好被選中成為這部電影形式上的載體。我不願意把它讀成對紙媒的致敬、悼念、致敬、悼念、迷戀、懷舊⋯⋯我想要稱它是 “a celebration of a figurative collective memory”。而當我說figurative時指的是:報紙、Ennui的過去、畫家、學運、綁架案/移民/黑道 — — 這些東西在週報中被刊出的方式,是週報讀者的世界裡確實發生過的「現實」(電影中人的collective memory),在我們的世界裡它並沒有發生,但透過比喻或者戲仿,這些故事用充滿愛意的眼光重述我們的世界、喚起我們一些印象(我們的collective memory)⋯⋯
(這部分我還沒辦法好好說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