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
723日记 | 悲伤旅程: 寻访40位动车事故遇难者(2)

(2011年)8月2日 周二 晴
一
晨7时起床,收拾行李,退房,打车到奥利匹克大酒店前那条街,定下了我昨晚看中的那间旅馆的房间,交了押金。给我办手续的是旅馆老板娘,我没有告诉她我的身份,也没说是因何来温州。
之后,我到医学院育英儿童医院,到小伊伊病房门口,门卫告诉我,只有小伊伊的一个姨妈或是姑姑在里面陪护,不会出来,因为离开了人,小伊伊会哭。我便先离开。
打车到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在住院楼7楼,应该是普通病房,41号是曹立衡的病床。曹立衡就是潘约翰外婆曾给我讲到的那对遇难的美国华人夫妇的儿子。他也是美籍,这次是与父亲曹尔星、母亲陈曾容一起从美国回来,回福建老家。他的父母不幸遇难,他也受重伤。
在曹立衡的病房门口,我让护士帮忙叫了曹立衡的亲属出来,是个年轻女性,我想她也许是曹立衡的爱人吧,但她没有接受采访,留了我的名片,说以后再说。
打车到双屿客运中心,其附近的金园宾馆三楼,302房间,住的是遇难的D301次动车司机潘一恒的家属。潘一恒生于1973年,事故发生后,他被发现时,胸口已被操纵杆捅穿身亡。据他的同事分析,在动车相撞前的电光石火的一瞬间,他曾拉紧急制动进行刹车。我进到302房间时,见《xx周刊》的张x正在采访一个老者,应是潘一恒的父亲。正采访时,来了一个男子,问我们来历,张x自我介绍了,我则没有说话。其他几个房间的人,据说也是潘一恒的亲属,但他们不愿谈。我便坐到张x的旁边,不说话,等他采访。那男子也坐一旁,有些不安,还递烟给我、张x、潘父。后来张x说他习惯一个人采访,让我们出去一下。我出来,那男子也出来,对我说:“原来你们不是一个报社的。”他到楼梯口打电话,我听到他说:“你给xx汇报了没有,这里有两个记者,我看不过来。”我想他应该是工作组的成员。
这是我来温州后第一次遭遇他们,心想要小心了。我下楼。二楼是个餐厅,我点了东西,准备吃午饭。坐在窗边桌位上往窗外看,发现百米之外,低矮破旧的房子之上,就是动车高架桥。
一辆动车轰隆隆驶了过去。
二
刚才又去金园宾馆302房间,找到潘一恒的父亲潘邦瑞,拍了潘一恒的照片。潘一恒的儿子翔翔画了一幅画,曾被人发到网上,在这幅画中,年龄只有7周岁的翔翔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了动车事故现场的情形,特别是D301第四节车厢挂在高架桥上的样子,像新闻图片中的那节车厢的形象一样刺目。潘邦瑞告诉我,这张画是出事的次日——那时翔翔已经和他的家人一起来到温州了——在宾馆房间里根据电视新闻里的画面画下来的。这张画被他的家人过了塑,保护了起来,我想,它会是给这个家庭的一个特别的纪念吧。

上午从金园宾馆出来后,又曾回到302室,在《xx周刊》张x跟潘父聊完之后,我跟潘父聊。这两次到潘父那里,总可见那个40多岁的高大的中年男子,一看即知他是在防备潘家人对记者多说什么的。上午张x采访完后,我对潘父说:“老人家,我也跟你聊一聊。”这个中年男子轻声对潘父说:“行啦!行啦!”意思是想让潘父拒绝我。我们问起潘一恒的爱人现在哪里,那男子说潘一恒的岳母扭伤了腰,昨天就把潘一恒爱人和岳母送回福州去了。但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托词,是为了不让我们采访她他才这么说的。尽管有此人尝试阻挠,潘父还是愿意跟聊。我就和他聊了近一个小时。
潘一恒的尸体目前还存放在温州市殡仪馆,潘家尚未签下赔偿协议。上午在与潘父聊完之后,离开前,我对潘父说我会在温州待很长时间,还会再来找他,对于潘师傅的后事以及后续赔偿问题,我会一直跟踪,如果有需要,我会进行披露。
下午3时左右我再去潘邦瑞处时,发现那名中年男子又坐在一楼的厅堂里,我跟他聊天,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跟上面的一样。”上午我即听他对张x说他是潘的远亲,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我对他说:“没关系,我知道你的身份,你们也很辛苦,大家都是一份工作,大家互相体谅一下。”他笑笑。
每有大事发生,无论是发生在哪个天涯海角,前去采访,都可以遇到同行。上午采访完后,近12时,与张x一起出来,到附近一个牛肉拉面馆,我陪张x吃饭,他吃面,我喝水。聊起来,才知道他之前在《xxx周刊》工作,这次来温州前,他正与女朋友一起在厦门玩,发生了这件事,便过来采访。不一会,他的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工作的女朋友也过来。他们就住在对面的锦江之星酒店。
天气很热,跟张x他们分开后,我去边上一个网吧,上网,也休息一下。这个地方距离动车事故现场不远,我决定去看看。
三
动车事故现场是在距离双屿镇客运站三四公里的下岙村,位于双屿镇的西南角。15时许,我坐摩托车过去。摩托车先是在一条公路上行驶,离开公路,往西一拐,是一段通往现场的石子路,有人告诉我,原先这里是泥巴路,工程车、救援车根本开不进来,在事故发生之后,“一夜之间,”就铺好了这段石子路。
摩托车在动车高架桥下的一个大坑边停下。那大坑正是被疑为要掩埋破损的动车车体才新挖的,它被一圈木栅栏圈着,不知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被填平。木栅栏上,还有几处挂着“危险”字样的警示牌。出事桥体的正东面,约20米开外,有一个面积约一亩的荷花塘,荷花绿油油的,一簇簇高擎着,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动车早就恢复通车了,每一二十分钟,便有一辆从头顶呼啸而过,声音不算太响,我没听到在经过这个路段时有哪辆动车会专门鸣笛。我听在此处逗留的当地人讲,动车的车速比之前要慢了。
大概是因为这个事故影响太大,“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且溫家宝又亲临过这里的缘故,在我到达现场的这天,这里似乎成了一个旅游点,不时有车子开过来,有些人甚至连车都不下,车子开到“温家宝讲话处”,稍停一两分钟,就掉头开走了。还有些人是步行过来,三三两两的,一看就是来“观光”。

我在现场和几个人聊了起来。一个江西人,在1998年就已来温州打工了,他说,7月23日那晚,他正和人一起打牌,当时雷大得能吓死人,雨下得也很大,听说发生了动车事故,他在晚9点多也跑过来看。当时,在下岙村打工的人都过来了,另一边的上岙村,村里人也全跑过来了。当天晚上,往医院送伤员,有的是本地人的小车,有的是外地人的小车,都是免费送。
听围观者聊起这些,我也说:“我记得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说,为什么要埋车头,是为了填池塘。这里还真的有一个池塘。”查网上的新闻报道,我的记忆没有错。7月23日晚,在温州召开的一场关于这个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为什么要掩埋车体,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答说:事故现场有池塘,车头埋在里面是为了尽快填满池塘。他还说:“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
因为目睹了事故当晚现场救人以及运送伤员的场面,这位江西打工者对温州人的印象很好,其实他在温州打工这么多年,对温州人的印象一直都很好。他说:“如果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其他地方,说不准那地方的人就会趁火打劫。温州人很好。有的地方的人,卖了地,收租,就不再工作了,不是打牌就是嫖。温州人不是这样,他们很勤奋,能吃苦,有的已经是老板了,做事还能做到夜里一两点,有的还能睡地板。在其他地方,我没见过这么勤快的人。”
吴先生是温州本地人,他已是第三次来这个现场了。他注意到,动车高架桥上的护栏,本来是水泥做的,因为发生事故时被撞,毁掉的部分就临时用木头当护栏,今天他再过来,发现那木头已被水泥换掉了。
“这个事情,说到底,就是因为铁道部,”吴先生说,“我感觉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特别傻,好像一点都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只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方法做,比如开新闻发布会,请的是一个傻子讲话,如果请一个好一点的,还能说清楚,在比如,网上舆论,都已经把铁道部推到一边了,它也不第一时间澄清,都是过了一两天,才不痛不痒来一句。”
吴先生早年在杭州读书,他说,当年没有动车,从温州去杭州,坐车需要8个小时,后来情况好一点,还是得要4个小时。前两年,开通了动车,就方便多了。但是,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他还会继续去坐动车,“出一次事情不会再出第二次,一个雷打到了一个树坑里,不会再打第二个。”但是,想起那些遇难者,他就会感到心酸。他老家村里,就有一家三口在这个事故中遇难。他虽然跟遇难的男主不熟,但知道他在村里人缘非常好。这一家出事前是在温州下属的瑞安市生活,他曾和人一起去看过他们的家人,男主的父亲教过书,比较开明,对于这件事,“他说人毕竟都会死,没事了,”他已经看开了。
事故现场所在的下岙村,有很多工厂。来自江西的那位围观者说,“下岙这里的小工厂,主要是做鞋底。我认为,住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外地人。本地人有的进城了,有的在外地经商,还有的,是到外国打工了。”
他还记得,这座动车高架桥是在2008年前后才建起来的,“记得那时候,桥上修水泥墩,还掉下东西砸死过人,砸死过人的那地方,距离这里大概一公里。”
四
我看到动车事故现场南面不远处好像是一个小工厂,有几个人正坐在门口乘凉,便走过去,找他们攀谈。就这样,我认识了老任。
这是一个做鞋料的小工厂,像这周边的小工厂一样,它就像是一个小作坊,规模非常小。来自重庆梁平县的老任夫妇也是在这个小厂做工。他们是动车事故的目击者。老任今年60岁。他们一家已经来温州七八年了,“都是这个厂做几个月,再到别的厂做几个月,哪里工资高就在哪里做。”到这个厂,是7月5号才来的。
老任回忆,7月23日晚上,7点多开始下大雨,8点多就停电了,房子的灯,路灯,都停了,一停就是一天多,到了24号下午才恢复通电。那天晚上,因为停电,他们就下班了,步行回住处。回住处要经过动车高架桥下,当时他们看到一辆动车正在高架桥上,车速非常慢,比他们步行还要慢,虽然车速非常慢,但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直在慢慢地往前面隧道方向移动。老任夫妇刚走到下岙村里的113路公交站,这里距离出事的动车高架桥那儿约1里路远,老任夫妇发现,后面一辆车速较快的动车开了过来,“砰”地一声,就撞到了前面龟速前进的动车上。老任夫妇看到,一股带着火花的烟冒起来,车厢就像是冲天炮一样,先朝天空上冲,然后下坠,有车厢掉到了桥下,另有一节车厢一头栽到了地面上,但仍斜挂在高架桥上,没有完全跌下。

见动车出事了,老任就开始喊人,“见一个人就喊一个人,”很多人赶去现场救人,这当中有他的儿子任勇,据老任说,任勇救了10多个人。在发生动车相撞时,老任看了一下手机,时间是在晚八点半,他们赶到现场救人的时间是在20:40左右,到了20:50左右,消防、医生等才赶来参与救援。
“太惨了!”回忆起那晚的场面,老任说。
但是,在我见到老任时,他正在生气。“说了也没用,”他说,“我们救人了,但是话都没有人说一句。”老任的意思是,事后没有人对他们表示过感谢。他说他曾把他的经历对四五个记者讲了,也把他的名字告诉过他们。但是,我在网上检索,并没有找到记者写的关于这个场面的报道,老任的名字,也没能在网上检索到。
“现在我们家还有我儿子救人时的衣服,上面有血,没有洗;还有一个消防用的手电筒,”老任说,“这都是我们救人的证据。”
“白发送黑发,真的受不了!”
讲述:潘邦瑞(遇难者潘一恒的父亲)
时间:2011年8月2日
地点:温州市双屿镇金园宾馆302房间
一
我平时都会看新闻的,在电视上看新闻联播这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7月23号晚上却没有看,早早地就睡觉了。凌晨2点,一恒的一个堂哥就跑过来告诉我,动车出事了。他的小孩在香港,是从香港打过来的电话,问一恒是开的哪个动车,他的动车是走哪条线,他堂哥接电话时也不知道,他家小孩就说你赶紧去问,动车发生事故了。他堂哥就打电话给一恒的爱人,一恒的爱人说一恒的同事也给她打电话了,他的同事告诉一恒的爱人,说一恒走的不是这趟车。现在看,他的同事之所以这么说,也许是出于安慰吧。
一恒的堂哥告诉了我,我不放心,就去了一恒家。我到的时候,一恒的单位的人已经在他家楼下了。一恒的同事说,一恒出事了,但是没有说其实他已经没有了。他们应该是怕我们伤心过度。我们知道一恒出事后,就坐上他单位的车,到温州来。到温州的时间是24号上午11点。到了后,也没有让我们马上去看一恒,可能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安排好吧,就先把我们安排到这个宾馆住下了。从福州一起到温州来的,有我,我爱人,一恒的爱人,一恒的儿子,还有他单位的领导。
在过来温州的车上,一恒的领导也不敢给我们讲。我一看这种情况,心里其实就已经有数了。我给一恒打电话,一恒一直都没接,也没有回复。平时我打给他,他要么是马上接,如果当时有事没有马上接,也是过一会就打过来的。这次我一直都没有接到他回复的电话,我就觉得也许是他受了重伤,头脑昏了。我估计是出大事了。
到温州后,他们说,你们先住下。一安排住宾馆,我就估计一恒是没了。如果他还有生命,哪怕是重伤,我们一到,就会马上把我们送到医院去,怎么会先住宾馆呢?
是在我们住下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们才跟我们明说。来温州后的那一天我都很揪心,我一直问他们一恒在哪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他们一直没明说,只是说动车追尾了,生命可能有危险。我自己也知道,汽车追尾都受不了,何况是动车呢。我就更觉得没希望了。第二天上午,他们坦白了,就安排我们去殡仪馆看一恒一眼。
在知道确切消息之前,就一直都处在悲痛当中,因为,来温州了,也没有看到人,又没有去医院,我自己也就能够确定了。他们告不告诉我确切的消息,也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后来,我们被带到殡仪馆看一恒。一恒穿着他的工作服躺在那里。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像是在挂念着什么。我感觉他死的时候,还有一个意念在那里。但他挂念的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好。
二
一恒是家里的独生子。
我们家在福州市晋安区的郊区。那个地方,原来是农村,离市区只有一两公里,后来,开发商征收,国家也征收,早就没有农田了。我今年64岁,早年做过木工,现在年龄大了,也早就不做了,她母亲今年57岁,也没有工作。
一恒属牛,今年39岁。他小时候学习成绩好,后来考上了广州铁路机械学校,学的是内燃机车专业,是中专。我们家没什么背景,他能考上学,靠的是他的真本领。他毕业的时候,只有20岁左右,毕业后就到福州机务段开内燃机,一直在福州机务段工作到现在。

我家是个大家族,我的兄弟姐妹有十几个。一恒有很多堂兄弟。按照当时的水平,他能去福州机务段当司机,能有这份工作,在他的同辈中,算是最好的,很多人都羡慕,都说一恒刻苦读书,又有了好工作,说他很有本事。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能赚钱的人多了,和他同辈的,有的人开工厂,有的人成了大老板,有的人出国了,一恒还是拿一份工资,人家就都赶到他前面去了,但在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是铁饭碗,是最好的。
一恒成家晚,差不多30岁了才结婚。他开始工作后,一直都是住在家里,他的单位离我们家很近,每天,他都是骑自行车去上班,下班再骑自行车回来。那时候,我们还住的是老房子,和我的兄弟几个家庭一起住在一个旧的大木房子里。也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但是人家第一个就会问:你还住在这个旧房子里啊。看到这个情况,人家就不给你再往下谈了。他在家里住了近10年,一直没成家,就是因为我们条件比较差,如果有两个人排在那里,我们就比不上。
一恒的爱人是闽侯人,是别人给他介绍的。她是农村的,结婚前只是做些小工,好像是在玩具厂,结婚后,就不再做什么了,生了孩子,就照顾孩子。一恒只有一个儿子,叫翔翔, 7周岁,现在刚刚读完小学一年级,是在福州金山区一个小学读的。现在他们家在金山区。一恒靠公积金在那边买了一个房子,70平方米。
到他出事,一恒已经在福州机务段当了大概18年的火车司机了。一开始,他是开绿皮火车,跑的是福州到鹰潭段。这几年福州有动车了,他就成了福州第一批动车司机。他开动车,有个路线是从福州南站到厦门,还有个路线,是从福州到杭州。他出事的这个车,是回头的,他在杭州接下来,回福州。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恒的工资好像只有100多块钱,后来慢慢涨,现在每个月能拿六七千。我记得,他第一次上岗赚工资,好像是赚了160来块钱,他第一时间就拿给了他妈妈,自己只留个零头。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基本上全靠他。我还记得,他上班没多久,给家里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台洗衣机。
三
现在说起来,真是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一恒很能吃苦,在生活上,他没什么嗜好。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一点,不喜欢夸夸其谈。不工作,就是在家里,帮家里做家务,有时候老人家煮饭,他也参与,让老人尽量多休息。他不会经常到外面玩。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他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他很节约。几千块钱的工资,如果不节约,根本不够家庭用。他就是要把这个家照顾好。
在工作上,他也能吃苦,每个单位都会有坑坑坎坎,但是,我从来就没听他讲过什么不满意,他从来不抱怨。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也没必要搞吃吃喝喝那一套,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来跟人交往。你对家人好,人家就会对你好。他的朋友还是很多的,主要是同学和同事这两层关系,都处得很好。
在孝顺方面,他也是没得说。比如我的牙齿都掉了,10几天前,他还讲,等有时间了,就带我去把牙齿做一下。他还说过,等他再做几年,就带我们出去玩,现在是没有时间。他说,先去我们附近的地方,出省的,比如到北京去看一下,以后再讲。现在,这些都没办法实现了。
出事那天上午,他妈妈还跟他通过电话,他是要到晚上才下班,他说明天会带我孙子过去,一家子在一起。后来就再没接到他的电话。真没想到,见到他,就是在温州殡仪馆了。
有的亲戚朋友上网,他们看了,说你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紧急刹车,如果不这样做,损失可能会更大,他们的意思是说你的孩子有这种表现,你老人家应该感到欣慰。如果一恒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做老人家的,还是感到很欣慰。
现在,就是让他走得安心,就是看怎么把这个家庭撑起来。现在没有退路了。他单位的人也是这么讲,我的亲戚也是这么给我讲,就是说你老人家现在自己要保重身体,下面的事情还很多。如果你身体不行了,下面的事情靠谁做?其实,我的身体平时很差很差,我爱人也是这样,她经常感冒,她是早年操劳过度,到了老了,身体就很不好。
我跟你讲,虽然一恒一直都是在铁路上工作,但是我没坐过动车,连火车都没坐过,他母亲也是这样,最远的地方,我们就是到闽侯这些地方晃晃。一恒以前也邀请我们坐坐火车,我们就不肯,怕他单位上会有人说,说你把家属带到什么地方去了,说你对家属有优待,当时就是担心,怕别人讲,也许去坐坐也没什么,但我就是没有。
温州这个地方,以前也没来过,真想不到,会来温州送我儿子。
白发送黑发。真的受不了!
8月3日 周三 晴
一
今天上午9时许出门,到市三院七楼病房,让护士叫曹立衡家属,出来的是个女看护,向她要了曹立衡爱人何女士的电话号码,女看护说曹的家属都是住在医院门口的总商会大酒店七楼。
从市三院出来,到总商会大酒店,在酒店大堂,我看到手机显示下岙村的老任在8时许曾给我打过电话,我打过去,老任问我还去不去下岙村,我说一定去,“一两天内吧。”接着我上楼去找曹立衡的家属。七楼一位女士告诉我,七楼住的几乎全是家属。服务员帮我问曹的家人是住哪个房间,我也打电话给前台,前台告诉我,这都是曹家统一登记的房间,登记的房间是712。我便到712,见有四五个穿戴整齐的男女在房间里,一问,原来是工作组的,他们问我干什么,说别在这里找,要去宣传部。我便先退出。在一楼大堂,我打电话给曹立衡爱人何女士,她说要照顾她先生,要我过几天再打电话。
我又打电话给另一位遇难者家属王惠。王惠的丈夫郑杭征在这场事故中遇难。王惠说今天要忙着签协议的事,没有空见面。又打电话给另一位遇难者卓煌的姐夫陈先生。曾有媒体报道,陈先生是几个遇难者家庭的“联合发言人”。他对我说“很忙”,现在火车站接人,明天要火化,然后就回福州了。我说过几天可以在福州见面,他说好。
二
关于昨天去的事故现场附近的那几个村庄,我很好奇:住在这些村庄里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它的人员构成是什么样的?破破烂烂偎依于动车高架桥下,动车在这里的通行,对这些村庄及住在里面的人都会有什么影响……
昨天跟着老任通过下岙村的街道去找他的儿子任勇,我才发现这个村庄其实更具城中村的味道,街道两边都是小商铺、小饭馆,我还在一面墙上看到“下岙基督教堂”的字样,字是红色的,竖排,字的上面是个十字架。在穿过街道走了一段长长的路后,终于到了他儿子做工的地方。一个抱着男婴的年轻女性,是他的儿媳,她打电话给任勇,意外的是,电话那头的任勇听说是记者,拒绝了采访。我让老任再打电话给任勇,老任怕儿子埋怨他多事,没有打。在出村的路上,我告诉老任,过几天请他们父子吃个饭,好好聊一聊,也算是交个朋友,老任说好。

我昨天到事故现场没多久,心里感到失落,因为现场恢复得太正常了。若不是被告知,没有人能看得出这个地方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灾难。人们太擅于遗忘,从灾难发生到现在,还不足10天时间,很多人便已经不再提起它了。但是,灾难又一定会以某种形式,保存在某些人生活的某个角落里。昨晚将要离开下岙村与上岙村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名叫叶豪平的江西打工者,叶豪平在温州打工已经10多年了,事故发生的当晚他不在现场,但次日上午他曾到现场看,他的手机里就保存着几张他拍的现场照片和几段视频。我正好包里带着电脑,便到他做工的小屋,把他的照片和视频拷贝到我的电脑里。叶豪平告诉我,当时村里很多人都拍了这样的照片和视频。
三
昨晚有人发给我一条信息,我把它发到微博上,催泪无数。这条信息是这样写的:
讣告:先父母项余岸、施李虹原系瓯海区教育局、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职工,因意外事故不幸罹难。谨择定于2011年8月4日(农历七月初五,星期四)上午7时00分在温州市殡仪馆5号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届时敬请亲邻戚友莅临执绋,存殁均感。孝女:项玮伊泣告
项玮伊就是小伊伊。我明早会去这个告别现场。
8月4日 周四 晴
一
昨天很累。23时许开始睡。定的是晨5时的闹铃。5:10许起床,不到6点即出门,打车到温州市殡仪馆。我到殡仪馆的时间,约在6时一刻,见殡仪馆门口站着很多学生模样的孩子。到二楼的5号长安厅,这里是小伊伊父母的告别现场,已有很多人,现场也已布置停当,项余岸和施李虹的遗像置于大厅的正中间。按原定程序,告别仪式要在7点开始,但6点30分左右,他们的一个亲属,是个中年妇女,已到遗像前大哭,几个人搀扶着,哭倒在地。不到7时,告别仪式正式开始。先是大家默哀,三鞠躬,然后由项余岸、施李虹所在学校的两个领导先后致悼词。第一个致悼词者是项余岸生前所在的任岩松中学校长,他满怀感情,声泪俱下,他在悼词中说,不相信这样的灾难会降临到项余岸身上,也不能相信这样的灾难会降临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余岸你走了,带着你的爱人一起走了,却留下了亲爱的小伊伊子独自伶仃地在这个大人都无法理解的世界里……”最后由项余岸的弟弟项余遇致答谢词。在这之后,先是他们的亲属绕着遗体走了几圈,接着全体到场的送别者也都列队绕行过去,把手中所持白玫瑰放到他们的遗体旁。
这个早晨,我到现场后,先在门口的签名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领了一支花。我随着人群绕到他们的遗体边上,把手中的花献上,鞠了一个躬。
追悼仪式结束,在穿着白色制服的礼乐队的吹奏声中,项余岸夫妇的棺木被抬出告别厅,出殡,然后送到火化间。两条生命就这样化作一缕青烟。
在殡仪馆,遇到了来拍纪录片的杨荔钠女士,她说,拍《铁西区》的王兵也在温州。
二
从殡仪馆出来,我坐车回市区,在一个繁华地段下了车,然后走进一个酒店,在大堂里坐着休息,同时给手机充电。在这期间,我打电话给遇难者家属王惠,她没有接电话。我从酒店里出来,准备坐车到市二医院去看看,在路边问路时,发现这里居然是“鹿城后巷”。我记得王惠在电话里曾告诉过我,她们就被安排住在鹿城路后巷的威斯顿酒店。我问人,这个威斯顿酒店果然就在附近。从“鹿城后巷”公交站往东行不到50米,在一个大树旁的小巷口往北折,就见到威斯顿酒店的招牌了。我记得王惠曾告诉我她们是住在306房间。敲开306的房门,王惠的父亲在,但他并不愿意多谈。“这边情况很复杂,”他说。他告诉我,他的女婿郑杭征今天中午一两点钟即火化,他在等他的小外孙女,过一会也要到殡仪馆去,今天火化后,他们即带着郑杭征的骨灰回郑杭征的老家福建连江去了。我说那我过几天去连江找你们,等你们稍有心情了我们再聊,然后告辞出来。
知道王惠的丈夫郑杭征的遗体也要被火化的消息,这个过程似乎是冥冥当中受到指引。王惠昨天下午5点多才签了协议,网上有消息说,她当时知道丈夫并没有被冷冻,而是“冷藏”,大伏天,遗体都要腐烂了,在这个情况下,她立即决定停止抗争,把协议签了,以把丈夫遗体尽快火化。

在威斯顿酒店附近的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打车去殡仪馆,12时许就到了。中午的殡仪馆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影。我的手机没电了,二楼的过道里坐着三个志愿者,他们本是做金融行业工作,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去做志愿者,被调配到殡仪馆。他们告诉我,二楼最南端的接待大厅可以充电,我便去接待大厅。接待大厅很宽敞,开着冷气,里面有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工作人员躺在沙发上小睡,另一个则坐在一张桌子旁翻报纸,那张桌子上有写着“媒体接待处”的标识牌。大厅里有五六张桌子。我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写日记。杨荔钠和摄影师陈荣辉一起走了进来。他们又去了事故现场。
三
王惠亡夫郑杭征的告别仪式从下午2时开始,来的亲朋并不多,但场面催人泪下。首先是在我进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披着黑纱的小女孩,我问那中年妇女小女孩是谁,中年妇女指着远处悬挂着的郑杭征的遗像,说是他的女儿。这个中年妇女告诉我,小女孩名叫郑xx,才1岁4个月大,不会说话。显然,对于父亲的死亡究竟意识着什么,她仍一无所知。那中年妇女让她拿着手中的电话,说:“打电话,打电话喊爸爸。”中年妇女这样说了好几遍,小女孩都没有理会,反而冲我一笑。我把她披着黑纱,被那妇女牵着手在大厅里走路的背影照片发到微博上,催泪无数。
这个仪式很简短。亲友先是默哀、鞠躬,然后由郑杭征的父亲讲话,讲话毕,即告别、出殡、火化。郑父的讲话也很朴素,他说:“杭征吾儿,你生前事业有成,爸爸高兴,妈妈也很高兴,生前你对爸爸妈妈非常孝敬,爸爸妈妈满意了。今天你走了,爸爸妈妈悲痛欲绝,你的朋友也非常的悲伤,今天他们都来了,见你送你,你一路走好。你给家庭带来的不幸,爸爸妈妈全部承受了……爸爸妈妈会永远想念你的。”
第一次见到王惠。她很年轻。她很伤心。她大哭。家人大哭。她的女儿也开始大哭……
很遗憾,那个晚上因为与《xx晚报》的几个同行吃饭喝酒,我爽约了,没能去找王惠一聊,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要回福建连江了。我想,我会很快去她的家乡找她。她是这个事件里很重要的一位当事人。
四
从殡仪馆与杨荔钠、陈荣辉一起出来,上了杨荔钠他们从北京开来的车。见到了拍《夹边沟》、《铁西区》等片子的纪录片导演王兵。王兵43岁,是西安人。跟他们一起到酒店。后来和杨荔钠、陈荣辉以及《xx晚报》的一个小女生到楼下咖啡厅聊天,王兵则没有下来。聊天中,杨荔钠讲到的一点颇给我启发,她说她想拍一个《大桥底下》,到大桥下的形形色色的人很有意思,用一个长镜头,定格在那里,拍那些闯入镜头的人。
杨荔钠原是某剧团演员,在贾樟柯《站台》里演过跳西班牙斗牛舞的女配角钟萍,我看过很多遍《站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杨荔钠在电影中的那段西班牙斗牛舞跳得艳光四射,印象非常深刻。
明天是动车事故的“二七”。我会尽早赶到现场去。
五
补记昨天下午的事。
昨天下午我又坐车到了双屿下岙村。我先去找到打工者叶豪平。叶豪平现在一家小五金厂打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那间简陋狭小的工厂里忙碌着,他在制作一个机件,手中作业的机器时而发出刺耳的噪音。这个工厂的规模很小,老板是温州本土人,据叶豪平告诉我,忙碌的时候,他的老板会雇佣五六个工人,但是等不忙了,为节约成本,就会把工人辞退,只雇两三个工人。叶豪平是江西乐平人,他到温州已经12年了,但是,他在这个老板的小作坊里打工,已经差不多10年了。温州小作坊里的工人流动性都非常高,都是哪儿工资高就换去哪儿做工,像叶豪平这样,能在一个小作坊里工作这么多年的,当属少见。

叶豪平打工的这个五金小厂,原来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双屿镇边上另一位置,大概3年前,老板才决定搬迁到下岙村,叶豪平也就跟着一起来了。这个小工厂现在下岙村的位置,距离发生动车事故的高架桥,约一公里,走出门,抬眼就可以看见那座高架桥。叶豪平回忆说,动车出事后,“一节车厢挂在高架桥上,从这里,也全都看得很清楚。”
叶豪平今年45岁,他的爱人也在温州打工,是在一家服装厂做活。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2岁,现在杭州工作,从事通讯行业,小儿子16岁,在江西老家读书到小学6年级,就不再读了,他们夫妇就把他带在身边,但是小儿子来温州,也只能是每日玩耍,叶豪平说,小儿子还不能进厂,因为没人敢收童工,他又不放心把小儿子放在老家,怕他在老家学坏了。现在叶豪平每月能有3000元钱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比之在他的江西老家,也是赚得不少了。提及他的老家,叶豪平说:“我们那里都是种田,每人只有几分水田,种水稻,也有旱田,可以种蔬菜,种芝麻、花生,棉花也种一点。吃起来够用,但赚不到什么钱。那里也发展不起来什么工业。”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老家的年轻人都远走他乡,出门打工去了,“就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
下岙村属于双岙行政村。双岙村有包括上岙、下岙在内的多个自然村。一位下岙“土族”告诉我,双岙约有几千本地人,像叶豪平这样的外来打工者,则起码有几万人。现在双岙一带,本地人主要以出租房屋为业,一是出租厂房,一是出租住房。这个村原本也有农田,后来土地被一点一点征用,就完全没有农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要建一条从温州通往金华的金温铁路,先是征去了一部分土地。现在这条铁路仍在使用,它就在动车事故现场不远处穿动车高架桥而过,站在在动车事故现场,时而可见那种老式火车鸣着长长的汽笛声轰轰隆隆驶过。在建这条铁路线征地后,又因治理瓯江河道,征去了一部分土地。最近的一次征地,就是修建这座甬温线动车高架桥了。这座桥在叶豪平打工的小作坊刚刚搬迁到下岙的那一年才开始修建,“大概是前年十一期间通的车。”这样的征地,富了一批当地人,“他们的房子,有的补了几十万上百万,就发财了,当然,因征地发财的,只是少数人。”
我在叶豪平的打工工厂里和他聊天时,一个在隔壁工厂做管理的本村“土族”走了进来,也跟我聊天。他说,更早几年,下岙这里几乎全都是小工厂,很多小工厂都从温州其他地方搬迁到了这里,原因有二:一,这里房租便宜;二,村里想拉活经济,有意而为之。但是,近几年这种小工厂又变得少了些,原因也有二:一,租金涨高了;二,管得严了,“以前这里是农村,没人管。”但是,即便如此,这里的小工厂至今仍是鳞次栉比,一间接着一间,行业以做鞋居多,像叶豪平做工的那种五金厂很少,也有一些是服装加工厂,“前几年下岙有一个工厂着火了,就是服装加工厂。”
搬到下岙村后,叶豪平见证了甬温线动车高架桥的从无到有。动车事故发生后,有一件往事屡屡被这里的村民及打工者提起,就是在修建这个高架桥过程中,就在动车事故现场不远处,曾死过人。叶豪平也说:“这里出了不少事。就在建这个高架桥的时候,离这里大概两公里路,建桥板,铁架子塌下来,死了几个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有去看,我的老板去现场看了。”叶豪平还向我讲起另一件“有点迷信一样”的事情,他说:“有当地的老人说,以前这里发生战争的时候,一架飞机就在这次动车出事的那个地方坠落过,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7月23日晚上,雷雨交加。叶豪平回忆,当时他感冒了,没有出门。当动车事故发生后,他听到了动静,“警笛很响,到半夜都吵得睡不着觉。”但是,他仍是没有出门看。大概是晚上9点多,他的老板曾给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动车出事了。当时他的老板已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了动车出事的消息。叶豪平对他的老板说,他听到了,但是停电了,蜡烛都买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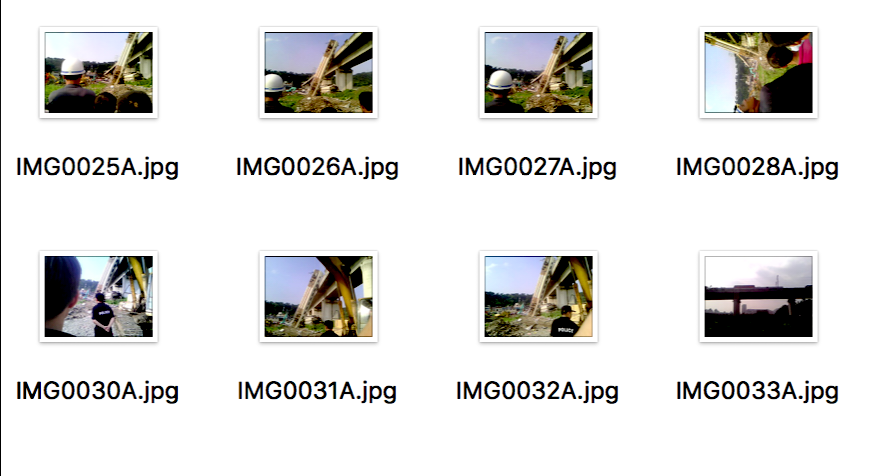
过去这几天,村里参加救人的人会经常聊起他们的所见所闻。叶豪平说:“他们说当时很惨。有些过去救人的不懂,连玻璃都砸不开,听说砸玻璃的四角就可以砸开了,他们说车里有人在招手,隔着玻璃,喊也听不见,有会砸的,就把玻璃砸开了。听说他们抬出来的人,有的已经死了。”
六
我从叶豪平处出来,穿过下岙村中嘈杂的街道去找老任。老任正和他的老伴一起在动车事故现场南边不远处的那间鞋料加工厂里做工,他说要等下午6点才下班。我便又到事故现场。大桥底下仍旧不时有人过来“观光”。
33岁的李小冬在深圳从事银行保险工作,他在8月3日这天早晨7时在深圳坐飞机,9时许飞到温州。上午,他和他的一位在温州工作的同乡一起,去医院看望小伊伊,他们给小伊伊买了一束鲜花,他还打算在见到小伊伊后向她捐助500元钱,但是,由于小伊伊要动手术,而且病房门口有保安,他未能见到小伊伊,只能让人把鲜花代送进病房。下午,他又和他的这位同乡一起,打车到了动车事故现场。
我和李小冬聊了一会儿,他这样告诉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偶尔看到这个事情,看到大家讨论得特别多。郭美美事件刚刚过去,又出现了这个事情。平时遇到这种事情,我也都会很关注。这次动车事故,前一周时间,大家关注得比较厉害,晚上也不睡觉,耗得精力也比较大,后面看到家属抗议啊什么的,网民的表现也很热烈,但是实际上到这边支持的不是很多。我就想,与其在网上耗精力,还不如到现场,如果能做,我就做点事情。所以我就到现场来了。能到这里来看看,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对我个人来说,也能使自己的内心能够平静。”
在温州职业技术学校读大三的一位姓肖的女生在这个下午也到了现场。她说,自动车事故发生,她一直都在微博上关注这个事件,但是前几天,现场封锁,来不了,现在能来了,她就过来看看。动车事故发生的那晚,她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号召去献血,献血点离她的住处不远,她也走过去献了血。她回忆,“我去得比较早,当时排队献血的人还不是很多,后来排队的人就很多了,挤得满满的,工作人员都忙不过来”……
下午6点,我打电话给老任,他还在厂里,过了一会儿才坐了一辆摩托车过来,我们一起往村里走,他边走边说:“手机卡里只剩2块钱了,”“打不出去了,”“儿子去找钱了,好给人发工资”……反正全是钱的事。我说请他父子吃饭,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后,他却又推脱了……
傍晚我再到大桥底下,这时遇到《xx卫视》在采访一个来自河南的打工者,他在动车事故发生的那晚参加了救人,我要了他的联系方式。之后,我又遇到来自安徽的小伙子刘磊。刘磊开一辆货车,在温州做废品生意。动车事故发生时,他的货车就停放在事发现场附近的桥下躲雨,他当时则是在驾驶室里给他爱人打电话,发生事故时,他看到大桥上突然冒起一个火球,他还看到有一节车厢挂在了大桥上,他想是有车掉下来了,立即就赶过去救人。
刘磊身高1.74cm,体重170多斤,看上去很强壮。按照他的描述,他应该是第一个冲到现场救人的人……
救人者的回忆(1)
讲述:刘磊
时间:2011年8月3日傍晚
地点:动车事故现场大桥底下
我是安徽宿州人,1986年生,2002年就出来做事了,这么多年,搞过电焊,搞过钢结构,还去沪杭高速嘉兴段架过桥。最近几年,我收废品,就是别人打电话叫了,我就开车过去拉废品。
今年7月初,我才来的温州,之前在江苏南通待了一年多了,这边的朋友打电话,说这边生意可以做,我就开车过来,也是哪里有人叫我,我就过去拉废品。
动车出事的那晚,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几个人有两辆车,一辆大货车和一辆小货车,雨下得很大的时候,就把这两辆车都停在了出事的动车高架桥旁边的另一个高架桥下,那个高架桥就在这个动车高架桥的西边,大概距离50米吧,那也是火车桥,但是很少见有火车跑,你看今天到现在了,我还没有看到过一辆。当时,雨很大,我就把这个大的货车开到那个高架桥的最里面,想着少让雨打车头,就等于是避雨。
刚下大雨的时候,我去买了饭,买了回来,我就在那辆大车上吃。吃完饭了,这时雨也小一点了,应该是在晚上8点钟,我老婆给我打电话,她在江苏南通,那边没有下雨,我接了,就在车上跟她说话。

我们的那辆大货车和小货车是背对着放在动车高架桥旁边那个高架桥下的,大车的车头在桥底下,小车在它后面。大概在晚上8点15分,我从大车上下来,跑到小车上去了。我躺在小车里给我老婆继续通电话。当时我就很纳闷,我说动车高架桥上那辆动车今天怎么那么慢呢,我就觉得它是停了四五分钟。当时它车上的灯都是亮着的,如果车上的灯熄灭的话,我躺在小车里也就看不到它了。当时这辆动车的车头已经快到隧道口了。突然,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火球,像打闪一样。我是用眼睛的余光看到的。再看的时候,就看到有节车厢挂在那里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原来这辆动车的后面追上来一辆车,因为我是躺在那辆小货车里的,我的视线,只能看到动车高架桥上前边那一段,后面再远,就看不到了。
当时我看到一个阴影,在高架桥上竖着。我就想,完蛋了,动车掉下来了。我就把货车的门打开了。我对我老婆说,那边可能有个火车从高架桥上掉下来了。然后我马上穿上衣服,一边给我老婆打电话,一边朝掉下来的动车那儿走。
这时,基本上已经不打雷了,如果还在打雷,我就不敢接电话了。雨还有一点点,很小。我边打电话边朝那边走,我就看到你找人的南边那个小厂门口站着几个人,他们都没有过来。我走近掉下里的车厢,只有一二十米远了,我根本就听不见车里有人喊救命之类的声音。我还以为是空车呢。我就大呼了一声:有没有人?我这么一叫,就听见好多人在回应,特别是女孩子,声音很大很大,好多人都在喊救命,说:“这里有人!这里有人!”
当时从桥上掉下来的,有车头,一节车厢侧翻,一节车厢挂在桥上,还有一节车厢是正面朝上的,这节正面朝上的,应该是第三节车厢。车里喊叫的声音,我听到的,主要是正面朝上那节车厢里传出来的,侧翻的那节,基本上没什么声音,在桥上挂着的那节,应该是离得比较远,有几十米,基本上也听不到声音。
我就先到正面立着的那个车厢那里救人。
第一个出来的是个男的,他是从我的背上滑下来的,我扶着他,他从车上下来。第二个,在他的后面,好像严重一点,他说腿不行,腰也不行了,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也到了,我们把他拖着,放了下来。
上面还有几个女的在叫。我看到在这节车厢的最南头,应该是厕所那里吧,东南角,卡住了好几个人,他们什么姿势都有。再往中间一点,有两个人,是头脑清醒的,我就帮着把他们放下来。上面还有人叫,我就爬上去了,爬上去后,我用脚踹卡住他们的那个铁梁子,实在是踹不开,我说我先到后面救人吧,我就下来了。
下来后,我看到厕所后边第一扇窗户的玻璃破了,就从那儿爬进了车厢。当时过道里有几个人,我就都放出来了。他们有的下来时,不知道该怎么下,我就抱着他,把他的腿抬上窗户,往外面放。当时外面很快就来了几个人,帮着把他们放下来,但是没有人进到车厢里。我一个人在里面待了有20分钟。
那辆车是卧铺车厢,都是小包厢,一间一间的,包厢里都在叫,我就挨个拉包厢的门。拉到后面时,看到一个女乘务员,胖胖的,她当时还是比较清醒的,她说你把我放到卧铺上面去,她肯定是知道我一个人是搞不出来她的。她说腰不行了。她当时是靠在车厢上的。我就把她拖到里面卧铺上。
当时我的想法是先救活的。我进去车厢的时候,看一个窗口下面躺着一个人,还看到再北边一点,也躺着一个,因为他们一动不动,我当时认为他们应该已经死了。还有一个,是卡在东南角那一窝人中的,应该也是已经死了,我看到他时,他的头耷拉着,小手臂上的骨头有长长的一节露在外面。当时他们已经好像是没有生命迹象了,我觉得再救也没有意义了。
我在车厢里面,基本上就是重复同一个动作,就是把人扶到窗口。他们在里面的时候,都在叫,我说不要着急,不要慌,一个一个来。我一个挨一个把门打开。受伤严重的,我就把他扶过去,受伤不严重的,我就是搀一下。他们当时都是摇摇晃晃的,都是受了惊吓的。从那个窗口往外下的时候,他们有的可以自己翘腿,很多都是我抱起来,外面再接住。

从那节车厢里出来的,基本上都经过了我的手,我觉得应该有40个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靠近厕所的那个窗户出来的。
到了晚上9点10几分,我就从车厢里出来了。当时,除了在东南角那个角落里卡的人我搞不出来,里面能救的人全都救完了。等我把里面的人快救完的时候,还有一个包厢的门搞不开,这时有两个消防员进来,他们用斧头砸那个门,也没能砸开,车厢外的西面有个土堆,后来有人站在那个土堆上,用大斧头砸玻璃,才把玻璃砸开了,把里面那两个人救了出来。他们是卡在卧铺包厢里的最后两个人。我在车厢里的时候,通过那个包厢门的一点缝,看到他们一个坐在卧铺上面,一个躺在地上。
我从这节车厢里出来后,又到侧翻的那辆车厢那里。侧翻的那节车,当时是把玻璃砸开,放个梯子进去,然后把人救上来。此时消防员已经来了。因为有人出不来,我还下去这节车厢,用肩膀把他往外扛。在夜里10点多的时候,有个人,应该是现场指挥,他拿着一个喇叭,说群众救援的撤出去吧。
这时,我一看,已经好多人了,救援的人已经全部到位了,我就走了,去洗澡了。
晚上10点多,我还过去现场围观。那天晚上围观的人非常多,有骑摩托车过来的,也有开车过来。我一直围观到凌晨3点。
第二天早上,现场已经封锁了,我要把货车开走,当时我说我要把车子开出去,他们说,可以开出去,但是,开出去就不能再进来了。这样,好几天我都没有回来。到了7月29号,“头七”那天,我才又把货车开回了下岙。
对于救人这件事,我的感觉,就像是捡到钱还给人家一样,就是觉得是应该的。换个位置想一下,如果你坐在车里,别人不救的话,你是什么感觉。不过说实话,当时心里还是有一点害怕的,因为之前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以前哪见过那么多人受伤啊,还死了人。但是,一听到他们叫救命,就完全顾不得这些了。
另外,现在回看那天的事情,还真有点害怕,因为毕竟有那么多人死在了那里。当时,车厢里的味道是很难闻的,呼吸都困难,我在里面,差点都要吐了。因为有人流血了,车子还几乎是封闭的,里面很腥臭,又热,又闷。
这个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不会晚于晚上8:31,因为我是在8:31挂断的我老婆的电话。我手机里有通话记录。那天晚上,我老婆给我打电话的时间是在晚上8:01,我们通话半个小时。挂了她的电话后,我到掉下来的车厢近前了,还曾经给110打了一个电话,我110的时间是晚上8:32。
我这个手机的时间是比较准确的,我曾经跟电视对过时,它只比电视上的时间慢六七秒钟。
(未完待续)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