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漢書》裡的偽辭賦家枚乘傳記及東漢出現傳佈佛家“要言妙道”的《七發》
談《漢書》裡的偽辭賦家枚乘傳記及東漢出現傳佈佛家“要言妙道”的《七發》
在西漢這個時代,承續著秦的政制,不設史官。整個西漢王朝的史料只靠著有識之士的記錄(也包括了別有動機的偽史),當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記載到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的《史記》。史官的重新設置要到西漢末王莽時代始創設之。東漢承襲莽制,故在東觀設立史官,記錄政治事件。但是《漢書》是東漢班彪、班固父子所主筆,其時所寫的西漢故史,很多都是據後來增益的文獻,其中不乏誇大不實及偽史料,班氏父子也未費心斟別,以致於一部《漢書》,其中偽史之遍佈不堪。此吾人已有如《兩漢經學及古文偽經偽史考》一書已就其學術面的虛妄不實的學術經學尤其其中的古文經學的偽經偽史加以釐正。
至少在《史記》所述之武帝時代以前,因為有司馬遷以其史筆實錄所見所傳之近史,一比對數百年後班固的《漢書》依誇或偽史料增益者,即可以比較分析斟別出來《漢書》增偽的部份。
像是在文學史上很有名的,被號稱其人寫了《七發》一賦而開創漢賦脫離楚辭體的先河及創散體大賦及“七體”的枚乘其人,後人全據《漢書》枚乘傳的偽史來敍,且並不察《七發》一賦根本非枚乘所著,於是張冠李戴,迄今之中國文學史裡都還弄錯了漢賦的發展歷程,實是誤信《漢書》及文獻內不實記載,不仔細察證之過。
枚乘的活著的時代是司馬遷《史記》可以完全完整覆蓋的,因為他死於《史記》成書之前些年。但是《史記》對於他的敘述,因為他實際上並不是什麼重要人物,因此司馬遷《史記》內,不但不專立列傳,而只在《司馬相如傳》裡述及枚乘的『遊說之士……淮陰枚乘』及《魯仲連鄒陽列傳》裡的講『淮陰枚生』幾個字:
《司馬相如傳》裡言: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按,司馬遷對於文學人物,都會在傳記裡陳述並把其代表性作品列入,如屈原、賈誼等楚辭賦家在《史記》裡都有其名作載入,但是對於被後世偽史虛稱的枚乘其人,司馬遷與其幾乎同時代,對於枚乘竟不知他寫過了什麼《七發》的代表作,更不知他寫過什麼名賦,甚至沒有記載他有會寫什麼賦的經歷,而只是說枚乘此人是諸侯王梁孝王的『遊說之士』。而且依《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與枚乘這些遊說之士還相處過,使司馬相如反而後來寫出了名賦《子虛賦》。枚乘的真正一生可稱述的只有這幾個字而已。
與梁孝王同遊的諸生遊說之士裡,反而鄒陽比枚乘更有名,司馬遷反而替鄒陽寫專傳《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漢書‧賈鄒枚路傳》裡,講『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造了一篇鄒陽上書吳王濞的文字。
傳中對於枚乘,則言:『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漢旣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賔,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皐。』
在其間,又造了《諫吳王書》及《重諫吳王書》兩篇。按,其實,在《漢書》裡的枚乘《重諫吳王書》,有人認為係偽作,此余冠英《中國文學史》裡就指出了:『《重諫吳王》一篇,是吳王已反後勸吳王罷兵歸國的上書。這一篇內容有不符合史傳記載的地方,後人懷疑它是偽作』。但是班固的《漢書》的枚乘傳記裡就堂而皇之視之枚乘之親筆而收入,若此篇係偽作,不就坐實班固《漢書》的枚乘傳記內容裡有虛假不實之存在其中歟。此篇為偽,則班固所記『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全係謊言偽史。
而且《漢書》還說,因為枚乘上書勸吳王濞歸順,於是在平七國之亂後,『由是知名』,但如此『知名』之事,何以司馬遷不知此有功於大漢之偉業而沒有大筆一書呢。可見此『由是知名』四字就是偽史之筆。
而且《漢書》再筆景帝派官給枚乘,枚乘不樂而以病去官,此任官之事,司馬遷自當記上一筆,但不料《史記》全無影無響,一字不見枚乘此『功』及此『官』,終枚乘一生死於司馬遷寫成《史記》之前,司馬遷對其評價是“遊說之士”及因為在辭賦上並未太出色,不夠在《史記》內記上一筆,故亦不提。
為何知司馬遷亦知枚乘會寫辭賦呢,因為司馬遷在《司馬相如傳》裡提到了景帝不喜『辭賦』,所以司馬相如一見梁孝王之門下如枚乘、鄒陽、嚴忌等同好,『見而說之』,『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可見梁孝王這些門下都是好『辭賦』的,司馬相如與他們相處數年。但司馬遷並不認為這些門下包含枚乘在內,有何辭賦出眾,故沒有提到,雖然班固《漢書》講『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抬高枚乘的辭賦高於其他門客,但司馬遷即便知枚乘為辭賦,但也沒有稱道之,此亦間接可以證明了在司馬遷那個枚乘死去後的初期,並無看到有所謂什麼《七發》此一驚天偉作由枚乘寫出來,不然,司馬遷豈不要像是對賈誼列專傳,並且收入賈誼的名賦《弔屈原賦》《服鳥賦》的一樣來收作枚乘的《七發》並讚歎一番了。
故可知道,後世所謂枚乘所寫的《七發》其實不是枚乘所寫。真正出世的時間,依吾人所考乃在東漢末年,有某信佛道的文人為反對傅毅《七激》而寫成《七發》,命名“發”字正為了正面對沖“激”字。從佛道觀點來批駁傅毅非道宗儒的立場。此吾人另有文剖露之。
而且在《史記‧吳王濞列傳》裡,根本沒有什麼記載枚乘其人會二次上書給吳王之事。依《史記》,枚乘一開始就在梁孝王門下。相同的,像是鄒陽此人也在《史記》裡只是『游於梁』的遊說之士,但到了《漢書》裡,把枚乘及鄒陽都加上了曾在吳王濞門下的經歷,以便插入偽作的鄒陽及枚乘上吳王濞書,而且枚乘及鄒陽都分別給吳王濞上書,枚乘還寫了前後二篇,第二篇在離開後,聽到吳王濞反漢而上書。
在《漢書·藝文志》裡載枚乘賦九篇,此九篇內並無《七發》,不然班固豈不亦會將此名賦加以介紹或全文載入,但並沒有啊,只在《漢書》裡提到他的辭賦在梁孝王的門客裡是最佳的,但是不是天下最佳的,沒有提到。因為沒有《七發》在東漢班固那個東漢中葉的時期出現啊,《七發》出現在佛教以黃老同質的面目進入中土時中期以後,故其末所謂“要言妙道”就是指的是傳入中土的佛法。世人怪《七發》之篇為何狗尾續貂,最後的解答只是“要言妙道”,沒有舖陳詳述“要言妙道”的內容,因為,此一偽托枚乘寫《七發》的信佛文士,在東漢末年,還不是可以倡言佛法而不受排斥的時代,才以“要言妙道”打發全篇,讓有領悟力的讀者去領悟此四字的要言及其中的妙道了。(劉有恒,2020,9,21於台北)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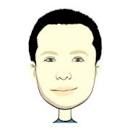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