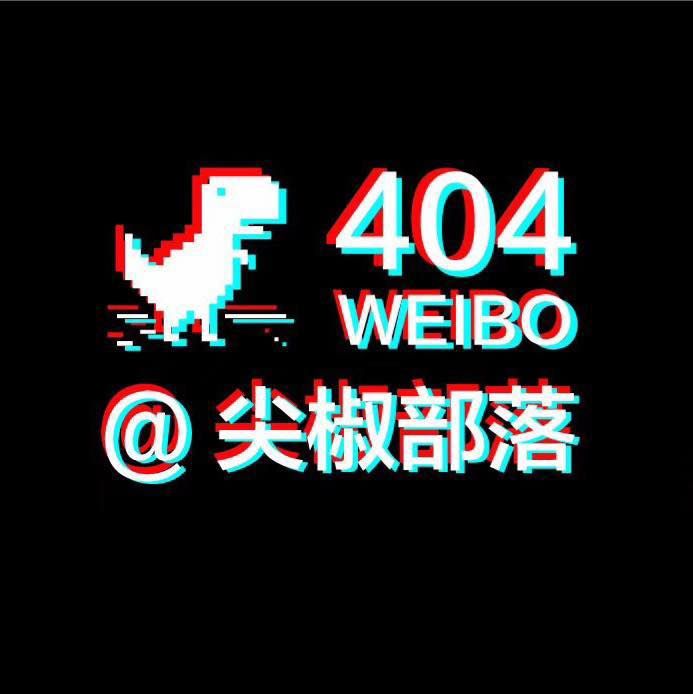
此處收錄了女工權益與生活資訊平台--尖椒部落--在七年中發布的女工原創作品精選。她們通過作品展示了各自人生路途中的思考、心境、掙扎和探索,以及在彼此的經驗中獲得的啟發、連結和印證。 尖椒部落雖已退出歷史舞台,女工的創作卻不會止步。 完整網站內容請見: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715122223/http://www.jianjiaobuluo.com/
家里家外两头挑:她们的担子更重了,也没有转身的空间
小马 · 2020-05-30 10:01 · 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姐妹,你复工了吗?孩子复课了吗?你的生活复苏了吗?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你过得辛苦吗?
广东番禺的欢姐觉得自己比往年都辛苦。因为丈夫收入减少,两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又在家上网课,她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还抽不开身出去工作。四月刚从湖北回到深圳的女工小文,则因为老家的父母和哥哥觉得肺炎“没啥”,一个人为全家囤粮囤药孤军奋战了三个月,还被父亲和哥哥打骂。
来自四川的兰姐和来自湖南的月英本来都在广东打工,可是有好几个月都是房租交着,人回不来。经济不好,兰姐厂里严重亏损,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失业。月英和丈夫则是双双失业,可上有老下有小,两岁的孩子只得断奶,改吃米饭了。在北京做小时工的河南人芳姐也险些失业,雇主不放心她进家,怕有病毒。可是日子过一天,钱就要花一天,为了还房贷,她已经欠下两万的债。
疫情冲击了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有些积蓄的人还能挺下去。可对基层女性来说,本就脆弱的生活,似乎轻而易举地就被击垮了。而重回疫情之前的生活状态,也许要花费她们好几年的辛苦,甚至,就再也回不去了。
快要失业的兰姐已经40多了,也不识字,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工厂能要她。“真不行就只能回老家种田了。”在三个月没有收入之后,芳姐终于回到北京,扯了各种各样的通行证和健康证明,做回东家跑完西家跑的小时工。可是算一算,她今后两年得继续有活干才刚刚能还上过去三个月的债。月英还没找到工作。“你觉得这样下去还能撑多久?” 她不知道。
她们都有家。在无法复工的日子里,家人的饱暖、营养、健康,是欢姐每天操心的事。家居的整洁、消毒,是月英维系的日常。家人的相处融洽,是小文挨打完偷偷哭泣时,最想要的东西。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她们的难处却个个不同。
一、家外:钱与命的选择
月英已经失业3个月了。她算了一笔账,因为疫情在老家跟长辈亲戚总共六七口人一起住,老人家没有收入,她每天买菜要100元,一个月就是3000元。在广州的房子虽然回不去,但也得付房租,每个月1000元。她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本来一个月喝两罐奶粉,一罐300元,现在疫情不喝了,省了。尿不湿一包100元,能用20天。平均一个月4000多元的花销,她和同样失业的丈夫经历了整整三个月只出不进的状态。
月英是做特殊教育康复的,丈夫做房产中介,本来收入可以支撑全家老小花费。但疫情影响,她工作的特教学校不能开张,丈夫也卖不出房子。“如果再这么不工作的话,这样花下去,还能花多久?”她感觉问了自己一个可怕的问题。不能这样。她决定重新找工作,可是湖南老家的农村,只有超市和餐厅服务员可以做,月收入也就一两千,根本不够用。她还是回了广州,想找一个稳定的,收入跟之前差不多的,但至今没有找到。
“着急,在家多着急啊,经济压力太大了。”老家的米涨价了,肉也吃少了。
跟月英一样上有老下有小的,还有兰姐。她运气好一些,没失业,停工两个月后,又回到了深圳的玩具厂工作。可是玩具厂本来做的是出口生意,疫情影响国际航运,货出不去,好多订单都取消了,厂子亏得厉害。老板灵机一动,又改做口罩,兰姐也做了一阵,可是国内口罩价格上不去,出口又没有证件,还是亏。
她身边许多工人都失业了。“我们楼下一个工厂,前几天还好好的,昨天就停了,本来那些人上班上得好好的,把货做完了,就没有货了。老板不可能来养你个闲人。”还有的厂,老板没有钱,跑了。她也怕哪天轮到她自己。
她在深圳十几年,知道40几岁的女工,很难再找工作。“稍微好一点的,都不会要我们这些老年人了,一看身份证就不要。”她没上过学,不识字,自然没有签过什么劳动合同,也不懂去要什么五险一金、失业保障。
她的工资是按小时算,本来是每小时13块,现在减到12块,晚上也不加班了。从住处到工厂要40多分钟车程,其中一段只能坐电动车,车费就要10块钱。以前厂里有10块钱的交通补贴,现在也没了。午饭之前也管,现在也没了,要自己带饭。她就每天五点多起床,先给自己和孩子做饭,孩子出门上学,她就出门上班。收入减少,开销增加,就是这么熬着。
往年这个时候,她给孩子交完学费,交完房租、水电,还能剩下一点。可是,“今年实际上还没看到钱。”她想过回老家,可是老家农村没工厂,“回去就是种田,去挖泥巴了”。挖泥巴自然更没有钱赚,可是留在深圳,“连水都要钱”。
前几个月孩子还没复课,要上网课,可是上网课要用手机,去厂里上班看健康码也要手机。怎么办?最后决定丈夫去上班,她跟手机一起留在家,孩子上网课,她就不能复工。但没有钱,吃什么呢?她就接一些零加工的散活,坐在家里做,3分钱一个,一天做1000多个,赚30多元。不多,总比没有好。四川老家的老人都80多岁了,三个孩子,两个还在上学。“老的也要钱,小的也要钱。”
同样因为孩子上网课而不能去工作的,还有番禺的家庭主妇欢姐。她有一对小学二年级的双胞胎女儿,天天在家上网课,又打又闹,拍视频作业、跟老师连线、吃饭穿衣洗澡睡觉,根本离不开大人。丈夫做厨房,本来月收入有6000,可是疫情期间餐馆不能开,家庭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欢姐想过在社区的卖菜点帮帮忙,赚点钱,可是她最多只有半个白天能抽出身来,实在没法工作。
为照顾家人而差点放弃工作的,还有在深圳打工的湖北人小文。
武汉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小文老家大年初一就开始封村。好多同乡都说,这星期要赶紧走,再不走就走不了了,就不能回去上班了。“但我想的是什么呢?”小文说:“老子的工作不要了,我也不走。我就要在家里陪着家人,我哪都不去。”为什么呢?“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肯定还是想跟家人在一起,要保护他们啊。”
这一留,年假无薪假都被扣完了,整整三个月,厂里只给了一千多。好不容易回到深圳,她结束隔离,赶紧去复工,但厂里效益不好,加班费没了,只剩下每个月3000元的底薪,吃饭住宿还要另外花钱。
小文的母亲有心脏病,父亲在疫情爆发前才刚做完脑血栓手术。花钱大手大脚的哥哥肩负着父母传宗接代的希望,交际多多,却存不下也借不出一分钱来。小文掏出仅有的积蓄付了爸爸的手术费,到疫情爆发,又赶紧给父母囤了两个月的药量。“别人那是一盒一盒地买药,我们家那是一条一条地买啊。”父母抵抗力都不好,她还狠狠心,花了500多买了好几罐蛋白粉,全家人早晚一勺。零零总总加起来,小两千块钱又花出去了。可是她还庆幸自己买得早。“到后来别人去买药的时候,每种药都涨价了。”
湖北老家里种了点菜,可是肉还要买,新鲜的肉都留着给刚做完手术的父亲吃。即使现在复工了,小文也还是省吃俭用。“8块钱一斤,10块钱一斤,你见过这种水果吗?你猜是什么水果?”她揭晓谜底:“就普通的苹果。我吃不起。”西红柿、黄瓜便宜,她就当水果吃。 她怕,怕疫情再来个第二轮,自己家人到时候拿什么吃饭呢?她也怕父亲母亲身体再出什么问题,觉得自己不能毫无准备。可是哥哥不这样想。“他再没钱不能委屈了他自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存钱只能靠她。
“你要钱,还是要命?”那时候,她选择留下,保护全家的命。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才明白命和钱常常是绑在一起。没有钱吃饭看病,也一样会没有了命。
同样的难题,也困扰了在北京做家政的芳姐好几个月。她年前回到河南老家,本打算2月初就回北京,在她已经工作了7个月的雇主家继续帮忙带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可是疫情一来,她想回北京开工,雇主也不让了。“人家也害怕你身上有病毒。”家政工要进入雇主的家庭,密切接触,就算芳姐不怕,雇主也怕。
可是每个月房租2000,加上吃饭水电,怎么也要3000块钱,再加上每个月3000元的房贷,本来就是月光族的芳姐也顾不得什么病不病毒的,只想早点开工。丈夫劝她看开点:“要是你赶着去复工,坐车感染了,本身就没有钱,那咱们的经济负担会更加重的。不让咱上班,就不上了吧。”可是,芳姐问:“咱一直不上班,咱俩吃啥?”丈夫说,实在不行就找人借吧。她和丈夫两人坐在河南老家的房子里,每天到处打电话,丈夫早她一个月复工,可是房贷还是还不起,只能借了两万块钱。
芳姐是小时工,没有合同,雇主说不要她来,她就立刻失业了。好不容易等到雇主说,可以来了,却因为经济不好,人家雇主也想省钱,四小时的小时工变两小时,收入减半。她只好多找了两家,同时在三家人里做,到处跑。每天都很累,可是一想到欠的那些债,她不敢休息。
二、家里:看不见的女性劳动
芳姐这样的家政工,今年普遍少了收入。不仅是因为这份工作特别的进入家庭,让人害怕感染,还因为许多女雇主也没有复工或是收入减少,就选择自己在家做家务、带娃。原本被分担给芳姐的家务劳动,因为疫情,又回到了女雇主自己的手上。
芳姐说,以前她做小时工,要负责做饭、搞卫生、带孩子,现在人家只让她做饭,其他事都自己来。雇主节省了开支,可是,家务劳动却没有减少,甚至因为全民居家防疫而增多。而对本就没什么经济能力的基层女性来说,每个人都一直是家庭里的那个芳姐,那个无薪的家政工。
困在湖南老家两个多月的月英,每天要和婆婆一起负责六七口人一日三餐的饮食。疫情期间,外面餐馆开得很少,也怕出门感染,大家都在家里吃。有的人负责张嘴,就得有人负责做饭。包括老人小孩在内,每天的柴米油盐、生活用品,都是她们在张罗。买菜、煮饭、洗碗、擦桌子,还要隔三差五地打扫卫生,还要照顾两岁的孩子。出门采购也是月英的事,村子里没有渠道能买到口罩,她在广州生活过,会网购,全家的口罩都是她在买。
欢姐也面对类似的情况。稍微幸运的是,她父母跟哥哥住,她只需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庭。可是两个不能回学校的双胞胎女儿,让她在小小的厨房客厅卧室厕所里,忙到几乎崩溃。
每天,她一大早先张罗两个女儿起床、吃早餐,然后就要拿出手机打开直播,陪女儿上课。“必须全程看着她们,不然她们就会乱按很多东西,要么去搜百度,要么去看抖音。”学校给低年级孩子安排的网课也考虑了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所以上20分钟就休息20分钟。可是这也把欢姐的时间,切割成了20分钟、20分钟。上午的课结束了,她要赶紧做饭,两个女儿在长身体,可是又挑食,她必须变着花样地做。吃完饭,洗了碗,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会儿,两个女儿就开始吵吵闹闹,不能出门让孩子的精力无处发泄,加剧了彼此的矛盾,总是打架,还曾经咬过对方的脸。欢姐只好呵斥女儿:“不可以打头打胸口,打死人的。”
下午继续上课,课后又要交作业。每天的写字作业都要拍照发给老师,朗读作业则要拍视频发给老师,手忙脚乱之下,又要煮晚饭了。晚上则要打扫卫生,帮两个女儿洗澡,再坐下来休息一下,等到丈夫下班回家,已经十点多。
疫情最紧张的那几个月,她每天看新闻,越看越紧张,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卫生没做到位,怕自己带了病毒回来,传染家人。“睡不着觉,觉得自己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强迫症,老是觉得这里那里都不干净的。”出门买菜远远遇到一个人,她也像是做贼一样闪开。只要出门回来,她就让女儿站到阳台上去,不要靠近,自己立刻去洗澡换衣服,才能到客厅坐下。换下来的所有衣物她都要当天洗,早晚还要两次用消毒水拖地。
丈夫有阵子工作减少,也整天在家,可是也没有帮忙做家务。欢姐看着,也发过脾气,忍不住一直大声骂孩子。孩子还小,玩抖音很厉害,可是手机网购口罩就完全帮不上忙。做厨师的丈夫更是完全不会弄,连健康码也是她帮着申请的。她在微信朋友圈跟有门路的朋友买了50个,怕不够用,又在番禺当地的预约口罩APP抢购,可是一次也没抢到。
“他们三个都摊在那里,等于他们三个没有事情做,只有我在那里做。好像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不是他们三个的事。”那丈夫和孩子怎么反应呢?丈夫有时还是会帮忙照看一下孩子,做一顿饭。更多时候,她得到的回应是:“妈妈发火了,我们快走开一点。”
那有没有人体谅一下妈妈呢?“我就觉得没有了。” 她说。
要一个人负责全家防疫物资的还有湖北女工小文。她不是武汉人,但老家有不少亲戚在武汉工作。老家的父母哥哥和亲戚都不把疫情放在心上,老想着出门,说她吓唬人、晦气。隔壁村天天有人偷着过来打麻将。小文觉得,自己留下来保护家人,完全是在孤军奋战。
她几乎是全家唯一的资讯来源,不仅追看新闻,还和深圳的工友互通消息,又加入各种本地的小区微信群,“就能第一时间知道哪个小区,多少米以外又有人被拉走了。”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她哥哥还一定吵着要去市里,她劝不住,只好利诱,让哥哥既然都去了就顺便多买点口罩带回来,“卖了赚钱”。那时还没有人抢购口罩,他们一下子买到了500个,真在村子里摆摊卖了好多,剩下的自己戴。
但她妈妈还老是要出去摆摊卖东西,爸爸和哥哥也总想出门溜达,还跑去亲戚家串门。她哭着求妈妈不要去了,给家人看新闻,看最惨的画面,也没有多大用处。“你让我干活,累,我无所谓。但是你要出门感染了死了,可怎么办?”后来疫情蔓延到全国,家人还说都是她乌鸦嘴害的。
她急了,只能使出绝招,大年三十的晚上,把家里前后门的钥匙都偷出来,直接锁上,谁也别想出去。“门一锁,我就不信了,你还能翻窗户出去?”爸爸骂她作妖、不要脸,哥哥骂她小题大做,各种不好听的话都往她头上扔。她不怕。有一次她爸爸终于找到了钥匙,开了后门出去散步,就老有邻居要过来搭话。她只好站在门边看着,有人过来就说:“爸,你回来。”大年初三,哥哥偷偷去亲戚家玩,她知道了,气得在亲戚群里大骂:“你要是敢把病毒带回家,我就跟你绝交。”
坏人就让自己做吧,得罪人的话,就让自己来说吧,小文想。“反正我将来是要嫁人的,不像我哥,还要跟他们做邻居。”
四个人在家关了三个多月,家务活自然是她和妈妈干,哥哥和爸爸偶尔动手,“就像是要人感恩戴德的,特别得意”。“这就好像是老板本来就应该给你发的工资拖欠了很久,终于有一个月,居然准时发工资了,你对他又谢又拜的那种。”她觉得让她干活可以,楼上楼下搬东西,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她都能做,但这不是活该她做的。“我爸我哥有一种思想就是,女人干活是应该的。”
在这样的观念下生活了一辈子,她妈妈也觉得干活干习惯了,都是自己该做的。可是疫情期间家务更多了,再加上父亲手术后本来情绪就不好,一下子从在外面讨生活的大男人变成了吃饭都能吃到衣服上的老头子,就把情绪都发泄在家里。比如小文刚拖完地,她爸爸就能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瓜子壳全吐到地上。第一天她扫了,第二天爸爸又吐,连续这样四天,她干脆不扫了。“我扫一次你吐一次,垃圾篓就在这里,你不放,你想干啥?你上天是不是?”
这样突如其来的紧密相处和情绪发泄,也严重影响了她父母的关系。眼看疫情缓解,自己和哥哥都要离家复工,她做梦都在想,怎么才能让爸妈不吵架。从小在强势爸爸的棍棒教育下长大,她为了帮爸爸恢复信心,找回做长辈和一家之主的成就感,心甘情愿地坐着,被爸爸的拐杖打了两回。“疼啊,那是木头的棍子。”她也不停劝说爸爸不要再对妈妈发泄情绪找茬,“妈妈也有自尊心啊。”小文觉得,这比做家务更难熬,为了爸妈,为了家,她愿意受这些委屈,可是有时候还是忍不住趴在床上偷偷地哭。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中,她不仅承担了家务劳动,还有繁重的情绪劳动,为了维系家人的生命健康和家庭关系和睦,她也做出了种种努力。芳姐和兰姐的丈夫都愿意分担家务,也会一起承担防疫物资的采买。可是,仍有不少像小文、月英和欢姐这样的基层女性,在面对经济难题的同时,还要一力承担家中的劳务。而令小文最寒心的则是,这些劳动在许多人看来都不算劳动,而是女人天生就该做的。
三、更密集的照顾责任,家里家外的搏斗
疫情明明冲击的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与生活,女性的家务劳动也不是第一天存在,为什么她们还会面临这样特别困难的处境呢?
有学者认为,其中原因是,在疫情防控期下,女性在履行母职时,承担的照顾职责比平常更加密集。研究发现,一直以来,无论是在多么民主和平等的家庭,女性还是承担家庭照顾的主责。而这一代中国女性从没有跳脱传统规范对我们的束缚和影响,绝大部分女性都不自觉地去承担主要的照顾职责。
疫情期间,因为照顾职责高度集中,方方面面都在挑战女性怎么把一个家庭照顾到最好。而这当中的底线和标准就是,这个女性要保证自己的家人不可以有任何生病的风险。在这个标准下,女性就得为家人考虑基本的防护、物资和食物,保证健康有营养的饮食,有作息的安排,还要让家人运动,让家人的情绪疏解。除了关注自己的核心家庭以外,她可能还会分担娘家的照顾,不能让娘家有食物、物资匮乏的情况。而一些关注疫情的女性,会更容易看到这种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面前生命呈现的脆弱。她会对各种反应机制的迟钝感到愤怒和失望,例如欢姐的“强迫症”和小文的偷家里钥匙。这种双重的拉扯,会再加深当事人的焦虑。
除此之外,许多受疫情冲击的家庭女性,虽然有强烈的就业需求但外出工作仍然举步维艰。社会学研究指出,她们工作的脆弱性与背后整个劳动的主妇化倾向有关 。
这种家庭主妇化的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玛利亚·米斯提出,说的是资本主义利用那些在乡村地区没有进入到市场体系当中的女性劳动者,让她们从事零碎的加工劳动,赚取计件工资。这就像是因为孩子要上网课而不能复工的兰姐,虽然她一天在家做3000个零件,但这并不是什么正式的职业,没有市场认可的劳动价值。她打零工挣钱,但也只是补贴家用的,不作为家庭收入的主体,所以在家里必须有一个人不复工,留下陪孩子上网课的时候,出门工作的那个就是她收入更高的丈夫。
玛利亚.米斯很早就批判,资本主义把生产劳动和生计劳动分开,主流经济学只探讨了生产劳动,而冰山下没有被看见和认可的大量劳动,其实是生计劳动。什么是生计劳动呢?生养孩子、照顾家人、煮饭烧菜、洗衣打扫,这些日常生活的维系,占据了女性大量的时间,就是没有市场价值的生计劳动。所以也有学者指出,随着疫情减缓,社会各界在复工复产层面对女性进行的一些支援,例如帮忙找工作等,其实还是针对生产劳动层面的,并没有支援到生计劳动受影响的部分。
社工学者梅若曾帮助过许多基层女性。她说,在经济危机或是大的灾难来的时候,家庭里就自然而然地会做一个优先顺序的分工,一般丈夫的工作可能更稳定,收入更高,那么妻子就自然负责家庭里面的责任。可是,这种分工确实加重了女性的劳动,对还需要打零工赚钱的基层女性来说,就是家里家外双重的劳动压力。
当家庭变成应对灾难的最小单元,家庭安全的责任,保命的责任,大家同舟共济省钱的责任,都压在女性身上。“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女人应该负责给家人买菜做饭,一顿饭都不应该去外面吃,这样既安全又省钱,但结果就是,女性会很辛苦。”
可是如果不把这些责任往身上揽,女性又怎么面对他人的目光、社会的要求呢?“所以我们还是挺需要一种能量去对抗,要持续不断地搏斗。”梅若说。可是对基层女性来说,家庭温饱已成问题,要先去搏斗外面的部分,才有空回来搏斗家里的部分。所以,“有文化有经济能力的女性还可以通过经济解决一部分问题,可是像这些非常艰难的劳动女性,转身的空间真的不多。”
这就像是芳姐这样没有合同保障的家政工,或是像兰姐这样大龄不识字的女工,她们是复工复产的各种推动政策所触及不到的人,随时都面临失业和再失业的风险。她们的生活本就脆弱,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大变故毫无抵挡,而求助,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大量的基层女性都是流动人口,户籍都在老家。“那她到底该找谁呢?如果是在当地,还可以找村委会、居委会。在外地,她都不知道可以找谁。”
梅若发现,对她们来说,能拿起电话去求助是很困难的事。“因为你要通过一些救助途径去真的争取到一些东西,是要做一些努力的。可是她们有时自己会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很难跟别人解释清楚自己的困难,一上来先说我情绪怎样,不说事实怎样。”她常常都要在一大堆话头中找出线索,才能捋清楚对方到底遇到了什么难事,需要什么帮助。所以她觉得需要专门的机构,熟悉她们说话方式的、有经验的人来协助,才能真正帮到她们。
此外,各个可以求助的部门和渠道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谁能帮你做什么,要理解这些事情,对一个基层女性来说,也不是很容易。在网上搜寻,各种心理辅导、政策讲解、就业培训的讲座不少,可是梅若说,她们还是觉得很难。“她会觉得,我听这个讲座,对我有啥用呢?她现在的焦点不是这些东西,她需要的是现在就能找到一个工作,月收入几千块的,然后她就可以干,就可以有现金。”
而这种事,靠听几个讲座是很难解决的,反倒是跟姐妹们互相打听商量,还更有用些。基层女性彼此间的社区网络,成了她们脆弱时的依靠。社工学者梅若还发现,稳固的社区网络,可以让参与其中的女性建立个人价值感,在遇到问题时也更愿意主动表达、求助。
芳姐的新工作是在微信朋友圈找的,处境差不多的姐妹们互相帮忙,有谁家要小时工的,就互相介绍。买不到口罩的时候,她的口罩也是在北京的工友姐妹给她寄的。小文是全家消息最灵通的人,在封村之前,不仅为两个长期服药的长辈提前囤好了药,还提前囤好了口罩。这也得益于她在深圳认识的那些工友姐妹们,消息互通。
小文觉得,今年的这波疫情,是她人生中的一个大波折。她帮着全家人扛过来了,可是日子艰难,所有的努力都太杯水车薪。“我在一步一步地努力,就像蚂蚁在爬一个火焰山一样。”她苦笑着说,“我的四个蹄子都快烫熟了。”
(文中受访者名字皆为化名)
参考文献:
【德】玛丽亚·米斯:《可持续发展社会中的妇女与工作》;
魏开琼:《玛利亚·米斯和她的主妇化概念 ——兼论广义社会 主义女性主义视角的必要性》
本文来自尖椒部落-中国唯一女工权益与生活资讯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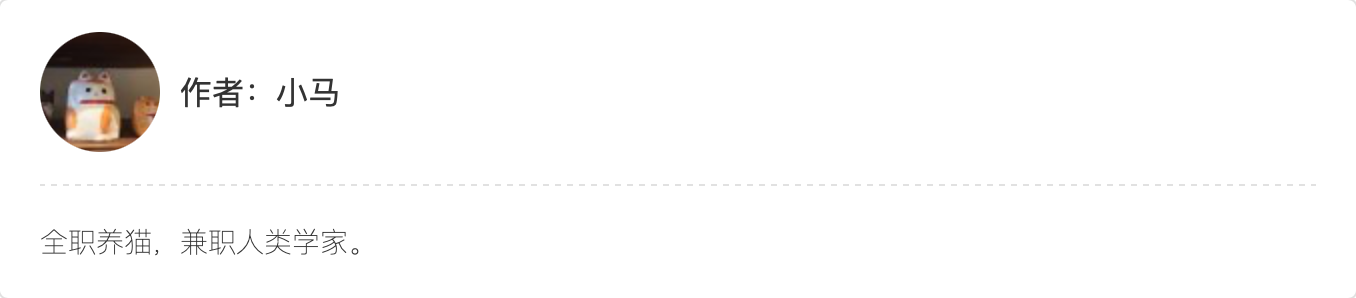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