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anotherland.org
唐冠华:探索人类摆脱金钱束缚的可能性

阡陌交错,鸡犬相闻;春花秋月,芳草萋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在媒体的渲染下,类似“李子柒式”的田园隐居生活勾动着在钢铁森林中那些不安的心,流于表面的美好也引起了阵阵回音。
种地开荒,建造实验。蚊虫叮咬,蟑螂相伴。
这是唐冠华的“隐居”——早在还没有互联网喧嚣浪潮的2010年,唐冠华就带着他的睡袋躲进了位于青岛的崂山。
2014年前后,他被媒体吹捧为“隐居打造桃花源的先锋战士”,登上了电视台,连国外媒体都为他做过采访。
但相比于“隐居”这一词的宽泛含义,唐冠华更愿意将自己山里的生活描述成一场“生存实验”。
他给这里取名为“自给自足实验室”:盖房子、种菜、挑水、做实验,他甚至还造了一个自行车发电机。
他告诉笔者,这是“家园计划”的第一步。
在他的描述中,“家园计划”像一个理想国。这将是与城市完全并行的、健康交流的另一片土地,有完善的医疗、教育和生产规划。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在这里,互相扶持,相伴终生。
而现实残酷,在第15个年头,“家园计划“无家可归。
唐冠华向笔者讲述这些时,2023年的春天已经悄然而至,百花开始绽放,曾经的“家园”却一度荒芜。
一批又一批人梦碎于田园净土,而逃离大城市的人依然不绝如缕。
田园将芜,胡不归?
只是,在这样一个商品社会、物质时代,吾谁与归?
文:三伏

2010年,山东青岛,崂山的清凉涧来了个“奇怪”的年轻人。
他带着一只睡袋,钻进了一个破房子,一住就是几个月,还准备在旁边的地上再盖个房——只是他看上去就不是专业人士,敲敲打打了好些天,房子的雏形也没见着。
来往的村民们好奇,问他来这做什么,怎么不雇个人来干这些活。
年轻人笑了笑,开口是亲切的青岛话:“没事,我边学边干。”
村民们又纳闷了,该不会是有钱人来体验生活吧,遂旁敲侧击,还有人摸进去,把这座破房子看了一圈。
最后得出结论:干干净净,穷鬼一个。

山中村民淳朴,怜惜之心顿起,看年轻人过得拮据,偶然来送点菜,问他有没有收入来源。
年轻人又笑了笑:“我花得少,吃得也少。”
村民们抬眼一看,这年轻人整天窝在破房子里敲敲打打,要不就到处捡些“破烂”,衣服也没见换几身,确实也没见花钱的地方。
看得多了,也就熟视无睹了。
几个月之后,陆陆续续有人上山一起盖房。两年半过去了,一座由轻钢、木头、竹子、布匹,以及足足1.5万个饮料瓶组成的房子,竟然真的盖成了。
与此同时,山上也出现了媒体的长枪短炮,突然间,这小屋谈笑有鸿儒,往来也有白丁了。
等到报纸卖到了村里,村民们才知道,这年轻人一声不响,成了名人——
所以这唐冠华,到底何许人也。

被媒体关注,唐冠华似乎早有准备。
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来到世间,就是要获得影响力,要有名,要引发社会的争议。
“有影响力、有名气,我的作为才能被世人知晓,得到更多的支持,以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社会在不断争议、不停反思中,才有进步的可能。
“虽然这将面临繁重的工作,但只有这样,牺牲才有价值,才可以为后代留下坚实的前车之鉴。”
他将这次在山上的生活定义为一场实验,还给住所起了个名字:“自给自足实验室”。
顾名思义,他的目的就是:探索人类能否摆脱金钱的束缚的可能性,实现自给自足。
在他原本的计划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只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刚上山的那几天,因为没有锅,地里种的菜也赶不上收成,他吃的是生食,“看有什么生的东西可以吃,其实非常多,水果都可以生吃,蔬菜里黄瓜、生菜甚至白菜都可以直接生吃,就靠吃这些东西来过渡”。
那菜是如何得来的呢?唐冠华的回答是村民送的。
随后,唐冠华的“自给自足实验”渐入正轨,却也意外频发。
首先是技术上的难题。
唐冠华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工科男,在那个流媒体视频还未得到普及的年代,他想要制作一些生活工具,主要途径只能来源于“搜索”。
“就是在网上查资料,会得到好多答案,我需要重新做好几遍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
他因此受过伤,失败的次数也要远远高于成功的瞬间。
比如焊接金属时,为了能更清楚地观看熔点细节,在没有预算购置优质防护面罩的情况下,他只能用眼睛直视火光,最后弄得眼睛通红,流眼泪流了一个多周。
他形容自己:既是“小白鼠”,又是“实验员”。
再比如,他急需做一口锅,满足自己吃熟食的需要,但锅怎么也做不好,他只好从外面找来一口别人不用的旧锅,“至少能够有一个温饱的状态,再去做一个个的研究,研究出来这个锅之后再替代上”。

其次是人员的配备,他意识到,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独自上山两个月之后,唐冠华在网上发布了“招募令”,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这项实验,效果显著。
先后有2000多名志愿者来到这里,其中也包括唐冠华的妻子邢振。
唐冠华与邢振在几年前相识,彼时邢振的父亲是位艺术家,与唐冠华更早结识,随后两个年轻人缔结缘分。
在唐冠华上山之后的那段时间,邢振时不时会来探访他的实验进程,也是确认丈夫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否认真——2011年,在唐冠华独自上山一年之后,邢振决定放弃自己在城市的工作,追随他一起踏进了这场实验。
在一篇夫妻共同接受的访谈中,邢振提到过自己父母对她这个选择的支持:“妈妈在我辞职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太好了!我的女儿可以去过她想要的生活了,这也是我年轻时想过而没敢做的。’”

家人的支持让唐冠华再无后顾之忧,他对笔者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连续提到了一个词语:“急切”。
“我需要证明这件事能行,因为我在网上查资料,没发现有人做成这些事儿,只有一些国外电影(展示过),国内要不就是在终南山隐居,苦哈哈的,实现不了一个比较舒适又能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能实现一个样本,大家就能够从过去的下沉生活中走出来。”
他还告诉笔者,这只是“家园计划”的第一步。


“家园计划”出现在唐冠华的脑海中,是在2008年。
彼时他只有19岁,已经工作多年。
在唐冠华的叙述中,他与所谓的主流观念始终有些水土不服,当笔者问他是否与他游离的童年有关时,他没有否认。

1989年,唐冠华出生在山东青岛。
他讲到自己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没有再写过作业——学校里老师不管他,父母离异之后,也有些顾不上他。
唐冠华是跟着祖辈长大的,在爷爷奶奶家住一年,再去姥爷姥姥家住一年。
双方老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无形中引导了他第一次有关“共识”的思考,他说:“就比方说我奶奶家这边是一个月才洗一次澡,但我姥姥那边一天要洗两次澡,他们就说对方是错的。到底哪边是正确的,在当时还困扰了我一段时间。”
后来他想,或许本就没有对与错吧,“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他们是有一种共识的,对于他们来说,共识能够让他们生活下去,组成一个自己的家庭或者社区,这就是一个共识社区,他们就可以可持续的运行——当然基础是你不能去影响和伤害其他人”。
上了初中之后,唐冠华被阴差阳错地划进了青岛市最好的中学,升学率稳居前列,素质教育也热火朝天。学校里应声开办了有关机器人编程的兴趣小组,唐冠华眼前一亮。
有人告诉他,这个兴趣玩好了,要是能获奖,可以保送高中。
他一听,干脆课也不上了,整天泡在兴趣小组里,于是,当保送的讯息变成乌龙,结果就显而易见。
他落榜了。
没考上高中,父亲告诉唐冠华,要不然你想办法创业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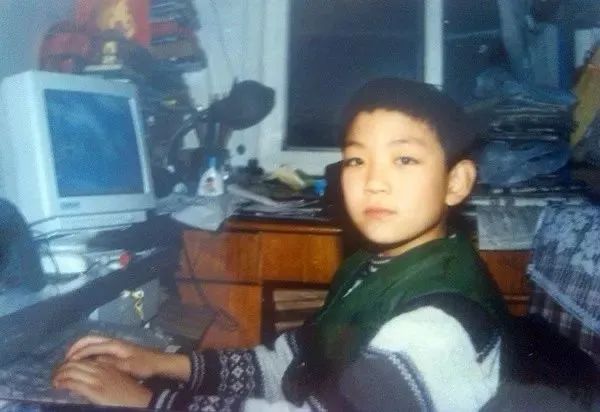
根据唐冠华描述,他的父亲曾是个诗人,后来下海经商,彼时在给企业做管理顾问。
他给唐冠华买来一些书籍,唐冠华至今对书名还有印象:“什么17岁,什么百万富翁,什么总裁,就说你看这个,这也是条路。”
似乎一切都有迹可循,唐冠华走上了创业的路,那一年,他只有16岁。
他开了一家小型的广告设计工作室,卑躬屈膝的“乙方”做久了,内心想要表达的欲望也就越燃越烈。
偶然间,他接触到了一种名为“观念摄影”的艺术形式,“就是通过计算机做一些后期的特效处理,把想象中的画面塑造出来。”唐冠华解释道。
又能表达自己的观念,还能通过后期的收藏等活动产生一定的收入,唐冠华因此入了行。也因为“观念摄影”,他结识了一圈玩艺术的朋友。
2008年,19岁的唐冠华在青岛美术馆对面租下了一间房子,开了一个名为“馆子”的艺术空间。
“只要想在青岛做一些创作,我就接待他们,提供住宿,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天南海北的创作者汇聚到这里,各显神通:有的创作文字,有的从事画画,有的人想要拍摄一个电影……但无一例外,都没有钱——连住宾馆的钱都没有。

穷困潦倒的他们在“馆子”的院子里开办了一场场小型演出,燃烧着一份份怀才不遇的梦想。
唐冠华看着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当下社会的荒谬与割裂,有些心事,就在这间小小的院子里酝酿。
他想到了之前去过的澳门赌城,只要有钱,就可以“购买其他人的尊严”,“把钱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东西,大家为了获得它,趋之若鹜”。
他开始越发清晰地感觉到:一些事情,不太对。

也是在2008年,因为一次探亲的机会,19岁的唐冠华去到了日本。
日本的城市化与人群的麻木性让他难以忍受。
他走在街上,看到每个人都长着一张相似的脸,“这里的人们随时有可能爆笑,随时有可能肃穆起来,有的人脸上时常呈现一种火山爆发前任何方式无法惊扰到的宁静安详,似乎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有房子、有花园,但没有个人时间,花园几乎荒废。他们有工作、讲礼貌,但更像是浮于表面,竞争的暗流在私下里涌动。

在日本期间,唐冠华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很大篇幅叙述“电流与灯泡”、“货币与交换”、“道家”、“粒子”等等复杂高深的名词,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是平衡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社会需要改变。
他洋洋洒洒写下了自己的计划,展开了对未来的种种想象,并阐明了自己的目标——
既然金钱支配着城市里人类的生活,他就要以自我为试验对象,“自主开始对私人生存能源的实践和计划,重点根据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提出并且加以验证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简单来说,就是他想要验证,金钱不是生活的必需条件。
他给这篇文章起名《家园》,在文章的最后,他写:“家园终将还给所有本该属于人的权利和良知”。
回国之后,他开始践行这个计划,后来,他将脑海里的规划加以完善,命名为“家园计划”,共分为三步:
第一步,用5年时间,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
第二步,用 20年时间,吸引一定数量的人在一起生活,分担生活中的必要工作,形成社区。
第三步,让家园与城市形成良性的、健康的交流对话,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至于为什么第一步计划只有5年?因为崂山的房子唐冠华只租了5年。
在这五年里,他收留接待的流浪者、背包客数以百计,来往的媒体更是数不胜数,作为主人公参与拍摄的海内外纪录片十余部,还受到了国际影展的提名。
他在采访里表示,自己已经完成了生活上70%的自给自足,是时候进入到下一阶段了。
于是,他有意识地向前来采访的媒体透露,2015年之后要找一块更大的地,让更多的人一起生活。
在媒体的密切关注下,这个愿望很快得到实现。

2015年10月,在一家基金会的帮助下,他们一行人来到了福州市闽侯县关中村,基金会授权唐冠华可以以“实验”的名义使用一块位于村里的,面积约500亩的土地。
唐冠华与同行者就这片土地未来的发展展开了讨论与规划,在这个阶段,他们有意识地放弃了“自给自足”生活理念的必需性,更想要达成所有社区居民的“共识”。
三个月后,其中七、八个人决定留下来,共同建设社区,他们给这个社区概念起名为“共识社区”——一群有共识的人共同组建的反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正式的称呼是“南部生活共识社区试验”(以下简称南部社区)。
这一年,唐冠华仅仅26岁。


试验的开始,听上去比较顺利。
2016年,在社区正式建立的第一个年头,唐冠华累计接待了上百位慕名而来的访客,尽管最后能长期留下来的人屈指可数。
离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多是因为“失望”。
唐冠华告诉笔者,他们在传播时会特意提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这里就是“建筑工地”,但还是挡不住有些人就是抱着逃离城市的避难态度,迎面撞上这里的毒虫与荒凉。
“落差感是必然的。”唐冠华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在建设,到处都是废墟一样的地方。我们甚至吃饭都没个正八经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忙碌,谁也顾不上,所以说这根本就不是想象的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安居乐业需要你创造,可能十年以后才行。”

此外,要想变成南部社区的“居民”,也需要一定的门槛。
社区的创始人唐冠华对访客没有身份与年龄上的限制,但要想变成所谓的“居民”,则需要该人在社区里累计生活超过一年,才有资格提出社区居民身份申请。成为“居民”就有了对社区建设的责任与义务:“要参与表决,参与决策,投入一些公共资金……”
所以,尽管这里人来人往,生活在此的长期居民最多也不超过十人。
2018年是唐冠华口中南部社区的“高光时刻”,“达到了最融洽的社区氛围,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社区价值”。
所有人各司其职,不再需要沟通分配工作:有人负责盖房,有人喜欢种地,有人在搞教育活动,地里有成熟的、可供食用的庄稼,山上有搭建完成的、充满艺术感的穹顶房屋。
居民们彼此了解与爱护,有许多对恋人在南部社区定情——甚至在去年,还有孩子在这里降世。唐冠华形容彼此是“没有血缘的家人”。

有网友在网络上分享去到社区生活的感受:“这里确实没有任何人来充当指挥者的角色。我需要依据自己的兴趣去安排每一天。当然也可以选择去协助其他伙伴,参与他们的劳动,但更多的情况下,还是需要我自己来发挥创造力。”
当然,没有创造力似乎也没有关系。
比如在这位网友到达社区的下午,就有居民说要在公共空间——当地废弃的半成品房屋——的五楼做一个天台酒吧。
几根粗糙的破木条随性地架在一起,就是窗户;麻布胡乱地挂在墙上,就是壁纸;原来脏到海绵都漏出来的破沙发被套上布套,就是酒吧里最温暖的座位。
看上去,城市的内卷、竞争、攀比等负面情绪在这里得到了消解,但矛盾依旧肉眼可见。

因为素质教育的特殊意义,社区里的孩子一般要去村里的小学上学,尽管社区里开办了织布课、音乐课等多种特色课程,但这些课程更像是主流观念里的课外拓展——事实上,确实会有附近学校组织学生来此学习体验,社区内也经常会组织给村子里的留守儿童上课。
“那如何解决生病就医问题呢?”笔者问。
“社区内就医还做不到,但我们离医院很近,我们也有了解针灸和中草药知识的人,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自己会用一些中医的方式——大家也都比较尊重这种中医的方式,但是如果骨折了,或者是负伤了,我们也还是会去旁边医院搞一下。”唐冠华碎碎念着,随即又补充道:“我当然希望教育、医疗、养老全在社区内解决,我很期待有这样的社区,我想创造,因为我没找到……”
只是,意外远比创造更早到来。

2018年,他们突然被告知南部社区所使用的土地属于一类耕地,上面的所有建筑在法律意义上不被允许,他们被迫停止修建。
那天之后,他们被迫撤到村中,租住在村民的房子里,思考接下来的前路。
2022年,资助他们的基金会资金短缺,土地被村委会收回,土地上的建筑被拆除。
许多常住居民因此离开,其中包括唐冠华本人。
“家园计划”至此,无家可归。
从2008年唐冠华执笔那篇《家园》开始,这个著名的计划走到了第15年,倒在了寒冬中。
理想、家园、家人、感情,很多东西他依旧在苦苦寻觅,但有些东西,他也确实无能为力了。


2023年3月,辗转多地之后,唐冠华来到了云南昆明的大墨雨村。
这是一个有些特殊的村子。
大墨雨村本是昆明西山区的一个传统彝族村落,据资料显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约有70%的本地村民外迁,这里一度成为“空心村”。
近些年来,有许多新村民来到此处,对当地民居进行改建,据唐冠华介绍,目前该村子里,将近有一、二百人都是迁居于此的新村民。
新居民中有建筑师、艺术家、软件工程师等等,大多在这里实践着“半农半X”的生活理念——一边进行简单的农业种植,一边根据各自特长开展着手工工坊、民宿餐厅、自然教育等各种活动。
这里是理想的过渡地。这也是唐冠华选择来到这里的原因。
“我的考虑就是得找一个可能在发展中的社区,它有一定的潜力。如果让我重新创造一个社区也可以,就是挺难找到一个合适稳定的土地,在国内,我觉得几乎是非常难了。”而如今的大墨雨村人才济济,唐冠华企图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好友,继续他的“家园计划”。

但与以往相比,他的“家园计划”似乎又有了些变化——他将自己的计划重心转移到了为“少数人群”发声的领域,在他看来,这也是“家园计划”的理念之一,殊途同归。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从小就不同的,他们是独立的,有独立思想的,一出生就决定的,城市不培养这样的人,城市淹没这样的人。”他在一部纪录片里说到。

上图为“大喜哥”参加“家园计划”活动
十五年前,唐冠华给“家园计划”起了一个英文名字:anotherland,中文直译是“另一片土地”。
他告诉笔者,对应着目前已有的这片土地,“家园计划”要做的事情就要一直去开拓在已有的空间之外的,其他的生活选择。
“它是一个持续的工作,没有止境。”
他如此告诉笔者,又似乎在告诉自己。
此外,如今34岁的他,也坦率地说道:“我现在怕是买不起一张车票……”
他最想要的,或许还是那张通往梦想的车票。




唐冠华向笔者讲述这些时,2023年的春天已经悄然而至,百花开始绽放,曾经的“家园”却一度荒芜。
一批又一批人梦碎于田园净土,而逃离大城市的人依然不绝如缕。
田园将芜,胡不归?
只是,吾谁与归?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