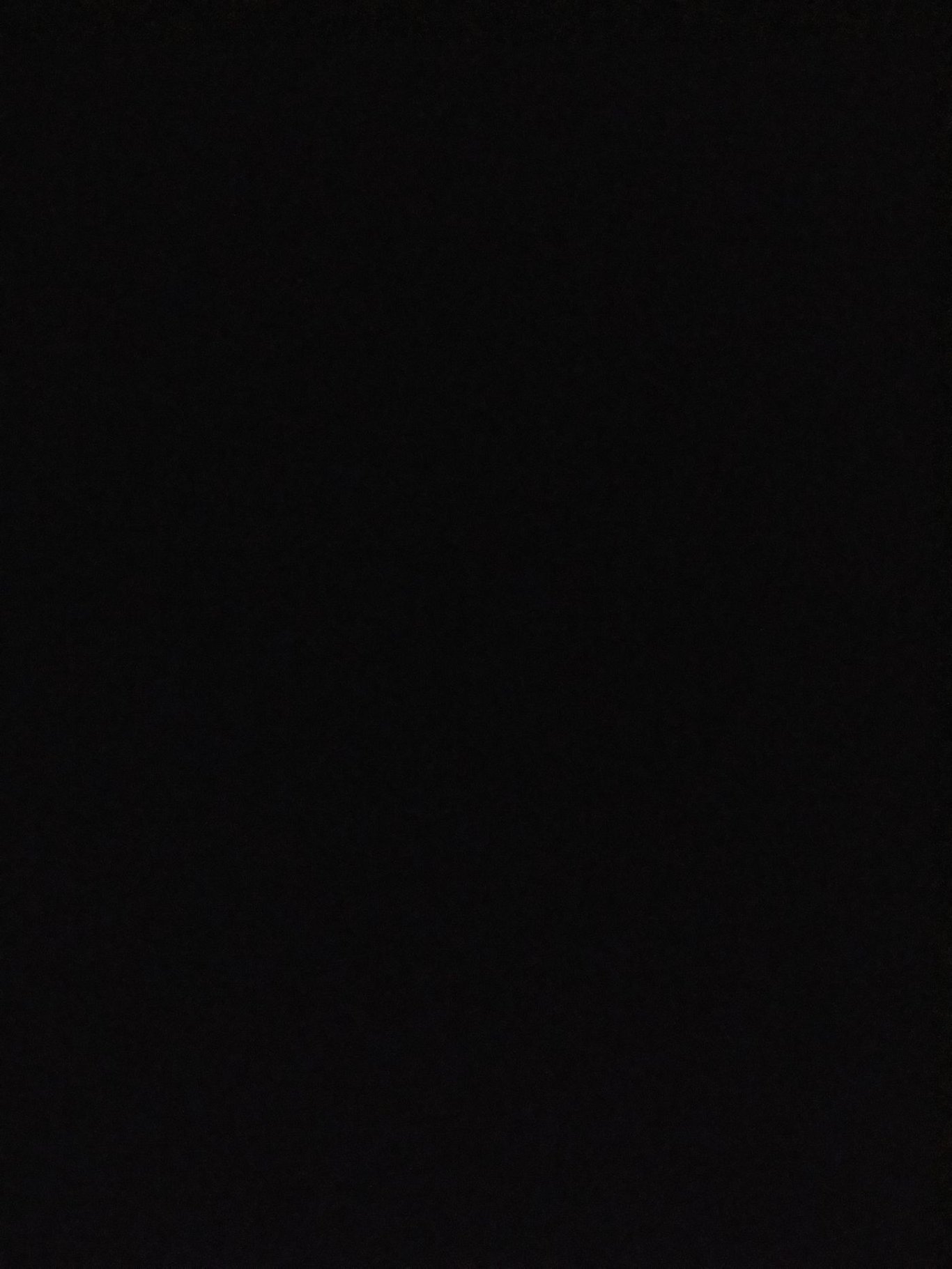
写点小说
隐身术
我的客户终于从大楼里出来。
那是一位高个女孩,年纪没比老李那个正上高三的儿子大多少,穿着夏天才能见到的连衣裙。她在大厅的玻璃墙里给我打电话,我冲她挥手示意了一下。她一路小跑出来,看了眼手机说,今天比平时快多了。我从电瓶车后的箱子里取出一盒寿司交给她,她说,谢谢师傅。我锁好箱子,刚想说“不客气”时,她已经重新退回到了写字楼的玻璃墙内。
时间还早,我坐在电动车上抽烟,看着旁边两个园林工人修剪绿化灌木的枝丫。一个人拿着一把电动链锯,端平锯子的刃齿,横扫过错综复杂的冬青树丛;另一个人拿着一把扫帚,把切割下来的碎叶和木屑聚拢成一堆。他们缓缓行进,没有说话。两人走过,身后的冬青树冠留下崭新、齐整的切口,像一条刚刚铺好的微型马路。
这时,一个男人拎着两杯饮料被保安从我面前的大楼里赶了出来。这里一到五楼是一家购物中心,五楼以上是写字楼,两者像两家长年冷战的邻居,互不干涉。入口、电梯各自独立,只是都在大楼的同一侧,经常有人走错。
我家的寿司店在三条街外,开了些年头,附近一带的外卖骑手,我多少有些印象,眼前这位瞅着生疏,难怪认错了路。他在大门前跟保安嚷了几句,骂骂咧咧走开了,路过我面前时,见我看他,回头吐一口唾沫,说:“呸!”
我说,门在那边。
他没有理我,却在我身边站住,从塑料兜里拿出一杯果汁,噗呲插入吸管,旁若无人地喝了起来。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没几个来回,杯底发出嗤嗤声响,菠萝外形的塑料杯在他的手中坍缩成一枚干瘪的果核。他把果核甩进绿化带里,在电锯的激烈亢鸣中,它很快被断枝和碎叶掩盖。
这样的事过去并不少见,我接过许多客人的电话,通常是抱怨外卖盒里的寿司数量变少,有时候甚至连盒子一起消失。起初,一周内只会发生一两起这样的事件,后来渐渐失控,每天都能接到新的投诉。留意了几天,我基本推定:问题出在那些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的外卖员身上。出于担忧,也可能是猎奇,我曾尾随过一个外卖员,试图抓住他偷吃的罪证。那天,天气似今天一样炎热,我们从寿司店离开后,就在城市里绕着圈。他沿途在一间螺蛳粉、一个烧烤摊、一家麻辣烫短暂停留,接收打包好的餐盒后,骑着电动车径直往城北驶去。一路上,我骑车跟得很放松。我经常走同一条路线回家,非常熟悉,只要他不在我的视线里彻底消失,我都能轻松咬住。十分钟左右,他在城北公园的正门口停下。
公园里走出一个酒糟鼻,他们攀谈了几句,外卖骑手把车钥匙交给他,翻身下车。酒糟鼻跨上他的车扬长而去,而骑手拐进一条石子小路,转眼不见。我把车停在路边,紧跑几步追上,走上同一条路。
正值盛夏,公园里草木繁莘,至深处遮天蔽日,甚是凉爽。我来回荡了一圈,终没再见到人。准备回去时,听见路旁的竹林里传来人声,热闹非常,仔细一看,林中竹枝上挂着几只电动车头盔,越往里走,挂的东西越怪,钥匙串、手机、毛巾、半满的矿泉水瓶、脏污的皮包,拉链豁口里挤出折皱的纸币一角。地上散落着数不清的拖鞋、沙滩凉鞋、皮鞋、运动鞋,像一副洗完的麻将牌,正在等人码好。
我侧身钻过面前一道缝隙,蛛网落在头上也浑然不知。眼前是一片空地,被竹林环抱,这里正在举办野餐会,有男有女,许多男人打着赤膊,他们的上衣铺在地上,拼出一幅斑斓的地毯。
一些人已经喝多,他们合抱在一朵云的影子里。旁边,一个眼镜男盯着手表正在倒数,五、四、三、二、一,点火!抱在一起的人们就地倒下,纷纷睡去。另有四五个人围绕他们站立,抬头看着天空,依次报道:助推器分离;火箭第一级分离;第二级分离;整流罩分离;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太原监测站跟踪正常;青岛监测站跟踪正常;太阳帆板展开正常......
这时,有人带头鼓掌祝贺,是带我来到这里的那位。他走过来和大家握手、问候,到我面前时,吃了一惊,说:“你不是刚才那个做寿司的老板?”我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说:“我不是老板。”他把我拉出人群,来到一方小餐桌面前。绿茶和巧克力两种颜色的小蛋糕在桌上堆起一圈矮墙,正中心摆着一只镶边平底大银盘,里面有一只被拼凑起来的奇怪动物,骨肉缝隙间用牙签连接固定,细长的脖子被一面竖立的半人高的化妆镜斩断,头已不知去向。在银盘四周还摆放着生煎、蒸饺、卤猪脚、烤串......它们被分门别类地装在一个个塑料方盒里。他取来一副碗筷,示意我品尝。我推辞几下,接在手里。
火箭发射中心传来骚动,一名宇航员在地上痛苦地扭动,双目紧闭,大叫:“不好,舱压出现异常!”人群哗然,不知所措。
我问:“怎么回事?”
男人说:“闹着玩的,别当真。对了,我还没问,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想了一下,说:“就是路过,在外面听见动静,进来看看。”
男人安排另一名宇航员展开救援,然后跟我说:“你还是头一个外人。”
负责救人的宇航员匍匐爬进故障的活动舱内,把一个蓝色头盔套在伙伴的脑袋上。痛苦的人重新安静地睡去,不再挣扎。地球上的人们看到这一幕,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溢出他们的眼角,他们的手紧紧握住另一个人的手,好像彼此从来没有分开过。
这一幕把我也鼓荡得心潮澎湃。我说:“有点意思,你们是演员?”
男人说:“不是,我们都是送外卖的。演员我也干过,在横店跑过龙套。”
我看了看地上的衣服,黄色和蓝色最多,扭头问他:“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有时候玩穿越,从镜子里去另外一个世界,有时候也给这个世界下点诊断,比如上周我们刚审判过马云。”
我说:“什么镜子?”男人指了指餐桌上。我又问:“什么马云?”
男人说:“审判。判的结果我给忘了,得问问那个戴眼镜的,当时他是马云的辩护律师。”
我说:“那扮马云的人是谁?”
男人很惊奇,反问:“为什么要扮马云?”
我问:“不是审他吗?”
男人说:“审的就是马云本人。”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也喝多了。
我又接着问:“那你干了什么?”
“那天我没在。”男人把我重新带回餐桌,说,“那天我在卡宴。”
“4S店?”
“一个外国地方,《加勒比海盗》看过吗,在加勒比海的南方。”
“还有这地方?”
“不信你查地图。”他从大银盘里的动物身上,撕下一只烤鸡翅膀,摆在桌上,说,“看见没有,翅根那段是北美,翅尖那段就是南美,胳膊肘里就是加勒比海,往下数一个小指头,对,就到了。”
“到那干嘛去?”
“旅游。”
“好玩吗?”
“地方小,要啥没啥,一条毛巾被都得靠进口。我没算好日子,正赶上人家闹罢工,城里乱糟糟的。超市、饭馆都不开张,景点也没人玩,我找到当地的华人公所,干脆打了份短工。”
我猜他在吹牛,于是问:“打工能干啥,你懂外国话?”
“送外卖。街上那么些游行的人,不上班也不回家,吃饭喝水都得要送。不会外语也没关系,你就是在国内送,来回颠倒也只用得上那么几句,现在手机上都有翻译软件和导航,非常好用。”
我又问:“去时坐的飞机还是轮船?”
男人说:“飞机,国际航班还真比国内的舒服,连座都软些。”
我说:“机票怕不便宜吧。”
男人说:“买什么票,我不买票。”
我问:“空姐不把你赶下来?”
男人说:“他们看不见我,我会隐身。”
话到这里,越说越离谱,我抱以微笑,伺机离开。突然,手机里进来一只电话,狂欢的人们听到铃声,纷纷扭过脸来。尴尬中,我一边挥手致歉,一边退入竹林。
电话里,一个女人说:“你知道我一直在等吗?”
我说:“你谁啊?”又看看屏幕上的号码,确实陌生。
电话里的声音开始飘渺起来,时断时续,好像有无数话语要诉说,我没有办法听清,“喂”了两三声后,只好踩着厚厚一层腐败的竹叶向林外大步而去。
往外走了一会,信号好了一些,女人的声音终于清晰起来,她又问:“你能帮我找到吗?”
我说:“我不在店里,你打美团上的座机电话,店里有人。”
电话里的女人还在问:“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有毛病。”我挂掉了电话,走出竹林,顿觉天空开阔,世界好像要翻转起来。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