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是列车 日子是症候 灵魂是休止符
与历史争夺记忆
“危机是不受人欢迎的。但残酷的是,人类通常只能通过危机来省察自身与社会的真实形态。”
——孙歌《常态偏执与当今世界》
上上周的某一天,下班路上正在边走路边神游,路过国贸附近一个十字路口,被不知何处来的便衣和保安拦住,语气粗暴,和其他的行人一起愣住然后等待。大意是,不要再走了,所有人都得等着。行人中偶有几个外国游客,也一副摸不着头脑的疑惑样子。我观察了一下马路对面,同样的,所有的机动车,行人全被拦下,一时间,形成一种诡异的寂静,仿佛都在等待什么人到来,什么事发生。
实际上我已经大致有了猜测。路口离国际会议中心很近,我估计是有政要或者贵宾要来,大约等了两首歌的时间,果然有车来了。领头是两排六辆警用摩托,后面陆陆续续跟着十多辆黑色轿车,我没仔细看是什么牌子的车,大致是红旗一类的。一辆接一辆,这些车通过后,四个路口的安保人员一齐放行,人流立刻涌动起来,外卖的摩托车也轰鸣起来,人流涌进地铁站之后变得非常拥挤,大排长龙。
我回过头去想所有人等待的那几分钟,真的太诡异,太安静了。光天化日,每一个人,如此听话,端端立在路边,不发一言,不敢拿起手机拍摄,那一刻我的耳机里还在播oscar jerome的新专,吉他和鼓刷混杂在一起,产生一种混乱的秩序。然后当安保一声令下,当所有人动起来,大家又开始谈论今天的项目做了多少,回家吃什么,仿若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更让我心惊。这感觉实在难用语言描述,只觉得大家都不想过多转动脑筋,只想快点回到日常秩序中去,回到熟稔的常态中去。
这疑问时常回到我脑海中,我一般会忽略它,例如,“难道人们真的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了吗?”直到今晚我重新翻开书架上孙歌那本书(《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读到其中一篇,她讲:
”对于常态的偏执性依赖,使得人们能够以平常心态生活在非常现实中,并且不会感觉到任何矛盾。这也正是现代社会可以化荒诞为神奇的社会基础。“
我感到很神奇,这篇文章于2013年发表,当时正值日本福岛核辐射危机余波未消,孙歌作为研究日本问题和东亚社会的历史学者,以女性平缓的笔触,剖析危机面前,政府与民众的相关现象。但读来读去,这文章处处没写中国,却又处处像是在写中国。
我惶惶然发觉,现如今发生的一切都是注定的,因为沉默的大多数如此。想来2022年是多么疯狂的一年,健康宝被发明出来,成为现代社会良民证,核酸几乎一天一做,与此同时我还要时刻担心,我的狗是否会被“无害化处理”,我爱人出差之后能否正常回到北京,进入小区甚至要填写一个详细到把祖宗八代都报上去的个人信息表。到年底十一月,又是铺天盖地的白色,乌鲁木齐,上海,瑞丽,一切的一切,我无法再去坦然谈论,因为我们已不被允许书写,也不被允许铭记。
联想到我个人经历的,与历史无比接近的时刻,也不止这些。大学本科期间,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上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举黄雨伞,戴黄头盔。的确,混乱中有许多芜杂的声音,每日每日,学生把林郑月娥的头像打印出来贴满地面,供人踩踏(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可说名字的人)。学生直接要求与政府和校方对谈,痛陈自由与民主之可贵,毕业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崩溃而泣,质问校长,我们的明天在哪里,香港的明天在哪里。面对这一切,大部分内地学生选择离开,有的人甚至联系了能够从珠港澳大桥一路开回内地的黑车司机,但一个亲密友人在ins上给我发语音,说,我不想走,走了便不是亲历者,便无资格再讨论和记住。我当时捏着手机说好,那我也留下。
几年之后,又一次的,整个社会恢复了常态。这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政治面前,不是理智才有权利存在。情绪同样具有正当性,仇恨并不可取,仇恨指向毁灭。但愤怒不是,愤怒是失望的体现,它是我们清醒的另一种形式。
前天晚上睡前读了杨显惠《夹边沟记事》里面的第一个故事,叫上海女人。我起初无心恋战,读的很慢。在这个中性的书名下,拼凑的却是一段无疾而终的历史。亲历者的记述,多声部的交响曲,杂乱而震耳欲聋,每个人都有血淋淋的痛苦和恐怖。这一章和下一章,连绵不断,拼成一座呼吸剧烈的劳教农场,末日中的无声抵抗,没有被死寂掩埋,全部复活。
只看了一章,我的心里堵得慌,关灯睡了。
很巧,我前段时间看了王兵的《死灵魂》。全片长达八个小时,我分了四次看完。纪录片里是对于夹边沟以及高台明水发生过往亲历者的采访。大多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事发地离兰州不远,有人还操着兰州方言的口音。说到58年后接连大饥荒开始死人,人吃人的部分,人们并未有战栗和恐惧,大都是麻木和空洞,甚至苦笑。
全部过程里,让我胆战心惊的,是谎言。国家的谎言,强权的谎言,历史的谎言。在谎言中濒临崩溃的服役者,无望的等待,驱赶别人同时献祭自己。他们重复着谎言的指令,接受谎言的吞没,有的人临死前还在抵抗,但无济于事,直至噩运将他们拦腰斩断。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在我们的时代,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一分一秒,正在发生什么?我关掉视频,合上书,这样问自己。但我清楚,我只能做个无力的好人,时刻准备被徒劳裹挟,预知今晚,将和明晚一样,以失败告终。在这以后,天亮之前,借由文字吸入一点自由空气。
黑夜过后,只有谎言能够活到明天。
高中时早自习,出去到天台上背政治书。人民当家做主,公民具有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选举权,制度自信,权利和义务具有广泛性和统一性。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制度真好啊,当权者高瞻远瞩,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我甚至还在2017年暑假去支教的时候专门给10个孩子讲了一下,中国的执政者要真正开始管理之前要经历多少考验,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现在看来,我只觉得如鲠在喉。
体制就是秩序,没有非常明确的命令,一切按部就班,不会有丝毫改变。每个人都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但是里面没人敢说,没有人有权利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任何变化。暴力机器和乌合之众,本质上都是一体的,但个体被孤立,声带被切割,方向被剥夺,全然没有和集体协商的权利和经验,只剩下在危难面前高歌猛进,众志成城,悲剧情怀。许多人悼念,悲伤,焦虑,苍白又无力。
我不知道他在怕什么,他们在怕什么。
在我眼中,他们也只是权力的傀儡,权力的奴隶。想尽一切办法堵住悠悠众口,想尽一切办法延续统治,主流压榨少数派,只顾着自己头顶那片云。权力为何可憎,因为当职责缺席,唯独权利在场,剩下的不过是假借权力之名的恶。暴风肆虐,谁都不能独善其身。悲情与愤怒席卷,是民意的浪潮,我不知道接下来还要牺牲什么才能够得到真相,才能够警钟长鸣,或许再下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人道将至,何以鸡鸣。
我看着历史,却不曾拥有那段历史。如今我感到被车轮碾过,因为只能眼睁睁看着它重演。我们肝脑涂地的代入,更加悲哀地进入历史遗迹,彼时的发生,则是活生生人民的生死与存亡。
家乡的平原与河流,溢出我们共同经历的生活,超过了苦痛与爱的一切限度,最终由它界定了分离及归来的一切行迹,无处可寻。那纠缠又无法脱离的爱,你与我,今生今世的关系。爱上你之后,我连同爱上了这片土地上所有微小的事物,可我望着星空,却无法成为那个温柔的巨人,为你提供安全一隅的庇护。
公权力粗暴的刀刃剜开那具被抛尸荒野的尸体,屁股和腿上的肉都被人吃了,饥饿恐慌的人民。我伸出手去,摸到那个医生腥热的心跳,感官复活的刹那并非由黑到白,它更像破晓时分的宁静,雷霆万钧的撕裂。他和一些声音的消逝,加剧了整个时代的不安全感。忽又想到那个被消失的清华女生,她喊:“不要再为公权力口交”。
事实上更多时候我也不想想起这些来,我也是有惰性的,我也想沉浸在自己建造的小世界里,无需面对时刻到来的危机和炸弹,单纯因为这样太累。四季流转,绿色断流,生活被重新塑造,拿捏,把玩,凝视,然后成了灰白色,我不再鲜活。25岁已过,我心底只留下一个强烈的声音,去探求一种脱离常态的生命维度,其实简单来讲,我只是想看看人有没有别的活法罢了,而不是陷在“什么年岁干什么事”的悲剧循环之中,做那井底肥硕的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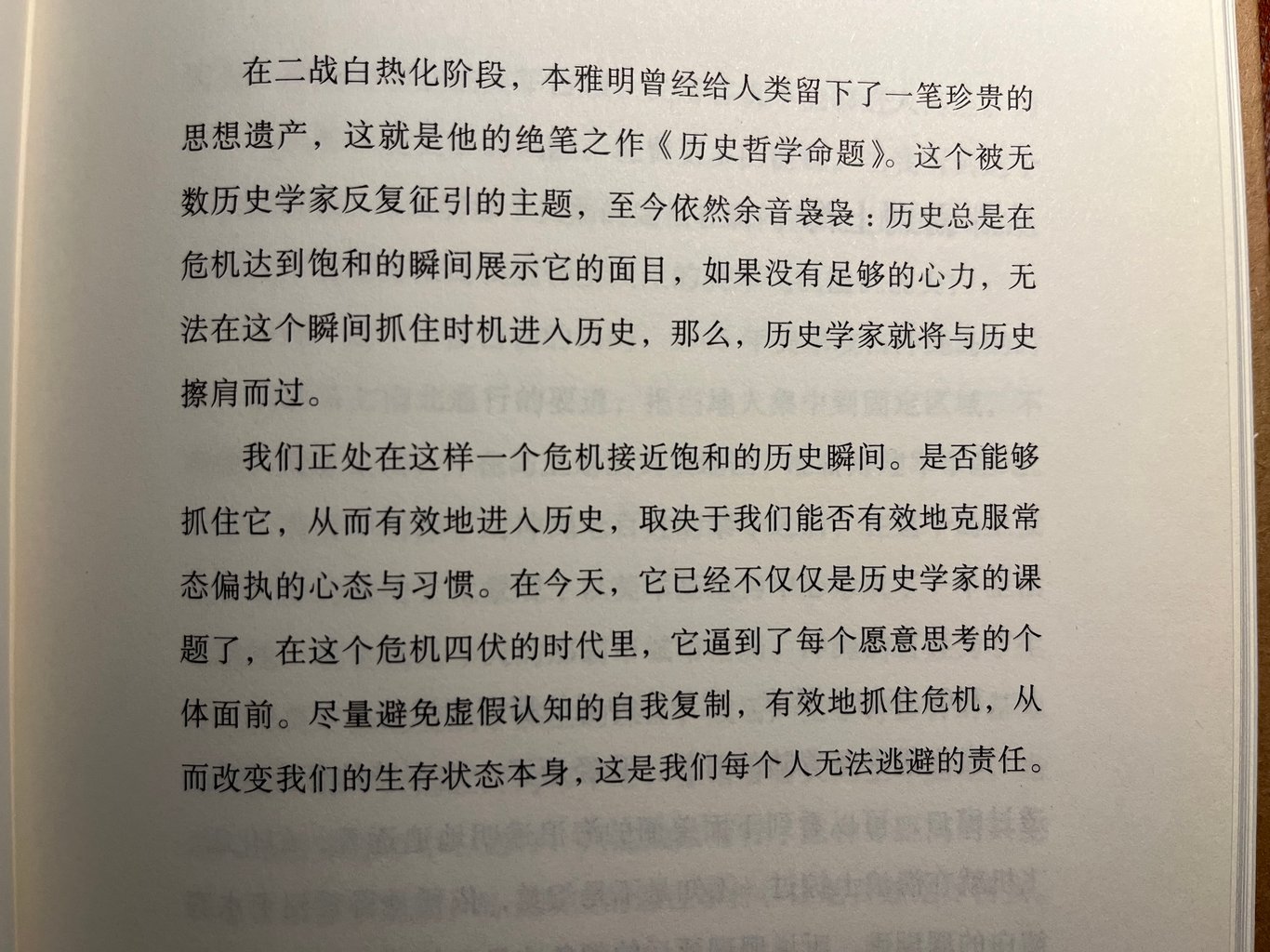
脱口秀,像我们此刻的相遇。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