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讀葡國史所思之三個基本歷史事件問題(包含政治、貿易與社會結構三個方面)

(一)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的產生與反宗教改革浪潮之間有何聯繫,對葡萄牙在十六世紀後的葡萄牙在人文和社會領域方面有何影響?
伊比利亞半島上宗教裁判所的出現要早於反宗教改革運動(1545年—1648年)。但兩者之間在國家宗教取向與涉及教權與國家利益妥協形式上存在着緊密的關係。
羅馬教廷為應對「異端」的增長與後來宗教改革浪潮波及歐洲,急需强化宗教裁判所來提振教廷在宗教司法與基督宗教唯一標準的權威。因此,教廷需要尋找一個可結盟並堅持天主教獨裁治理的對象。
在一四九二年攻陷格拉納達的西班牙王國是良好的結盟對象,鑒於西班牙王國在當年已經取消除基督教(羅馬天主教)之外的一切信仰;相對地,葡萄牙比西班牙稍晚設立宗教裁判所,并且直到一四九七年都對在商業、文化和航海事業上卓有貢獻的猶太人群體加以寬待。然而,葡萄牙第一所裁判所在一五四七年成立起,就下令國内的猶太人在十個月内離境,或儘速接受洗禮,信仰天主教。教會在十五世紀初利用葡萄牙民間的反猶情緒與在航海探索活動上對葡萄牙的支持,成功將反猶太人和教廷的精神權威植入到十五世紀的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地中。
此外,宗教裁判所也成為教會和葡萄牙王室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鎮壓葡萄牙人文主義者的工具,宗教裁判所十六世紀中期時先干預葡萄牙人文主義者的活動。他們對從法蘭西、英格蘭、蘇格蘭和意大利等地留學的學者加以恐嚇與警告。一五五五年葡萄牙國王若昂三世應王室成員、樞機主教恩里克的要求,將發表過人文主義和有利於新教評論思想的學者或解職、或驅逐。以清除異己,但同時也造成此後數百年内僵化的宗教思想與緊綳的社會氛圍,阻礙了學術自由和學術人才引進,深深影響了葡萄牙的國營大學事業,使得葡萄牙在其鼎盛期時,大學教育規模無法和西班牙、英國、法國甚至仍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等歐洲政權相比。此外,宗教裁判所的設立還使得耶穌會士在兩個多世紀内成為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無可爭議的代理人。
推動反宗教改革的耶穌會士通過葡萄牙的保教權(Padroado)參與葡萄牙在十六世紀,由澳門到巴西的殖民地帝國的教育事業、貿易和城市管理和慈善產業體系中。使得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浪潮或多或少在長時間内滲透到這些殖民地的文化環境中。由於耶穌會的反宗教改革議程,導致葡萄牙本土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都少有科學相關的專業和啓蒙哲學方面的著作大量流通,而由於耶穌會士的嚴格管控和葡萄牙發展重心始終注重於由里斯本控制,純粹的商業貿易,因此其所有海外殖民地在除神學院外,沒有一所正式的綜合性學院 / 大學。
宗教裁判所和耶穌會還對自然科學發展亦加以打壓,一五三四年作為葡屬印度首席醫官的葡萄牙猶太人加西亞·德·奧爾塔(Garcia de Orta)出版了一部集研究印度醫學、南亞醫學臨床實驗和針對亞洲霍亂疾病研究的名著《關於印度草藥以及藥物的對話錄》(或譯:《印度方藥談話錄》;Colóquios dos simples edrogas ne cousas medicinas da Índia)[1],卻因秘密堅守猶太教信仰而被迫逃離里斯本,前往葡萄牙在印度的首府果阿。即使在奧爾塔死後,其妹也因猶太人身份和包庇罪人而在火刑架上被燒死,一六三六年成立的果阿宗教裁判所也將其遺骨挖出焚毀。

(二) 葡萄牙具備哪些開啓海外擴張活動的條件?
一些觀點認為葡萄牙在海上擴張方面始於十五世紀中葉,且是一整場持續百餘年的擴張戰略計劃,以傳播天主教信仰和奪取香料產品、為西方征服亞洲政權作準備。
首先,我認為葡萄牙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與長期商品貿易路綫的有利變化是導致其鼓勵發展航海技術的重要因素。
1.貿易網絡與航海-製圖技術
葡萄牙面朝大西洋的優勢體現在國内遍佈良港和連接城鎮與大洋、地中海之間的河流網絡。且葡萄牙在十四世紀後期為控制貿易和擴張領土向卡斯蒂利亞、加利西亞等地擴張失敗的情況下[2]。遂完全將開展貿易與擴張中心瞄準大洋。在此之前的三個世紀,由於地中海港口之間的流動性,連接着伊比利亞半島與地中海世界的貿易,葡萄牙得以參與鏈接西北歐和法國、意大利的海上貿易網絡已經融入了海上貨物運輸的經濟體系;其航海技術也在十五世紀以前三個世紀的時間内被改良精進。葡萄牙吸收着從東北方的畢爾巴鄂—布爾戈斯方向的運輸的羊毛產品和鐵礦石[3]、并通過南方運輸和出售小麥、葡萄酒、水果和海鹽等物產。由十三世紀起,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塞維利亞、畢爾巴鄂與卡塔赫納這三個港口城市已然成為航運貿易的外圍中心。
通過這些河海相通的貿易綫路,形成了一個集造船、捕鯨、煉鐵與羊毛生產為交換產品的大西洋東岸貿易網絡[4]。以水手、船長和商人為主的人員流動更促成了葡萄牙王室對海上貿易及其貨物運輸利潤的重視,並招募來自熱那亞和西班牙東北部的水手以改良製船技術。葡萄牙與卡斯蒂利亞船隊已在十四世紀後半葉起分別通過援助英、法[5]而檢驗戰力和戰爭技術。航海技術的應用除了放在戰爭領域之外,葡萄牙人的漁業與商業也更直接推進了對大西洋及沿海島礁、駁岸與各處海上自然條件的認知。得利於葡萄牙王室對商業船隻及軍事戰艦行業之間的干預,葡萄牙從事商業的船隊得以配備船艦製造的新技術,在減少外國水手競爭的情況下發展出最先進和適應地中海近海航行和大西洋外海航行的技術[6],這使得葡萄牙在技術上獲得主動地位。
2.亞—非海上貿易路綫的短期震蕩與穩定
歐洲國家依賴從亞洲向西,經印度洋、波斯灣與紅海和地中海的貿易路綫比較明顯的時期可以着眼於十三世紀,蒙古帝國一路向西的征服對陸上貿易綫路造成巨大破壞,而蒙古帝國的驛站體系與廣泛的交通—經濟網絡則打開了海上貿易的通道。歐洲國家之間為追逐貿易利潤與扼守重要港口和航綫的穆斯林政權結盟。十四世紀中葉由於波斯的分裂、蒙古各汗國的崩潰和明朝的海洋封鎖措施,商人們更為依賴海上貿易。但是,通過《加泰羅尼亞地圖集》的證據顯示香料沿着紅海(Mar de Roxo)和埃及亞歷山大港這條路綫流動;此外歐洲經濟史的研究表明十四世紀後期的胡椒價格在歐洲既比起該世紀中期上升了一倍;而英國胡椒價格上升的時間卻在十四世紀中葉,對應蒙古—韃靼政權的内戰和崩潰,但到該世紀末到十五世紀已經下降,保持廉價。可見,從中世紀到近代早期的貿易路綫和商品貿易更為靈活,戰爭固然在一段時間内破壞長途交通,但總會帶來新的商貿運動熱點,東方帝國的重建使得貿易在更高利潤,更高水平上帶來市場上價格和供需的平衡[7]。
3.恩里克王子的擴張及動機:擴張計劃的準確範圍與動力
恩里克王子是十五世紀中期開展葡萄牙航海學校、將國策定於海上擴張,通往印度次大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這老生常談的説法顯然誤解了葡萄牙海上擴張——直開闢新航路為止,世界近代史標誌性事件及海上擴張的實態。
須注意,恩里克王子領導下的擴張動力中既有財富考量、也存在宗教因素,有關後者,他一度構想從葡萄牙佔領下,位於摩洛哥的休達或菲斯直接經陸路通向位於埃塞俄比亞的約翰長老(Priest John)處[8],而1455年羅馬教皇的聖諭中卻提到其目的地是位於「位處被認爲是尼羅河,某條大河上的敵人處」。同時代的《加泰羅尼亞地圖集》將「印度」標注在非洲上,而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史官的直接記錄則聲稱恩里克王子和摩爾人爭戰的二十多年裏,從未得到其他基督徒的幫助,因此他想在這些地方(從西非沿海)尋找是否有一些基督徒王公援助他作戰。教皇聖諭中還提及探索西非的恩里克竟然「已經到達了『尼羅河』」,此「尼羅河」實則指塞内加爾河和岡比亞一帶的土地。這些線索都暗指恩里克王子主導的海上探索的計劃只會限於沿海地理信息尚未明朗的西非到埃塞俄比亞,卻不可能涉及亞洲甚至印度上的穆斯林政權。
然則應肯定以恩里克王子為代表的上層貴族對於葡萄牙的航海擴張起到主要的政治號召作用,那麽,設使葡萄牙航海事業的贊助方有計劃、有部署地將航海探索的戰略,直到開闢新航路時的成就,就應該從經濟和利潤層面考量;葡萄牙早期的史官表明恩里克在對航海探索服務於宗教活動的態度十分狂熱[9]。其王弟佩德羅也認爲同異教徒和平進行商業來往是合法和合乎美德的,這些精神層面上的考量乃是構築葡萄牙海上擴張貿易的最根本的動力。直到十五世紀中期,位於大西洋上的馬德拉群島和亞速爾群島都提供製造葡萄牙船隻的原材料和船舶停靠,補給的天然港口,島嶼之間不同的自然環境與土壤使發展農業、畜牧業和奴隸貿易成爲發展殖民點經濟的選項;馬德拉群島提供甘蔗、糖、樹膠、原木;亞速爾群島則運送大量小麥、肉類、葡萄、粉彩、原木、蠟和蜂蜜等產品前往里斯本和葡萄牙的各大城市。馬德拉群島甘蔗的引種來自於恩里克王子的嘗試,並一度成為全歐洲糖的重要產地,涵括農業機械、城鎮建設和勞動力引入的工作都是恩里克王子為榨取殖民據點利潤和發展造船業,提供天然的經濟服務空間,由上層貴族主導的官方給予運輸、轉口貨物的商人許多優惠政策和特權,一方面擴大了貿易的原料儲備和增强海上擴張的動力,但另一方面卻加重階級矛盾和生產者的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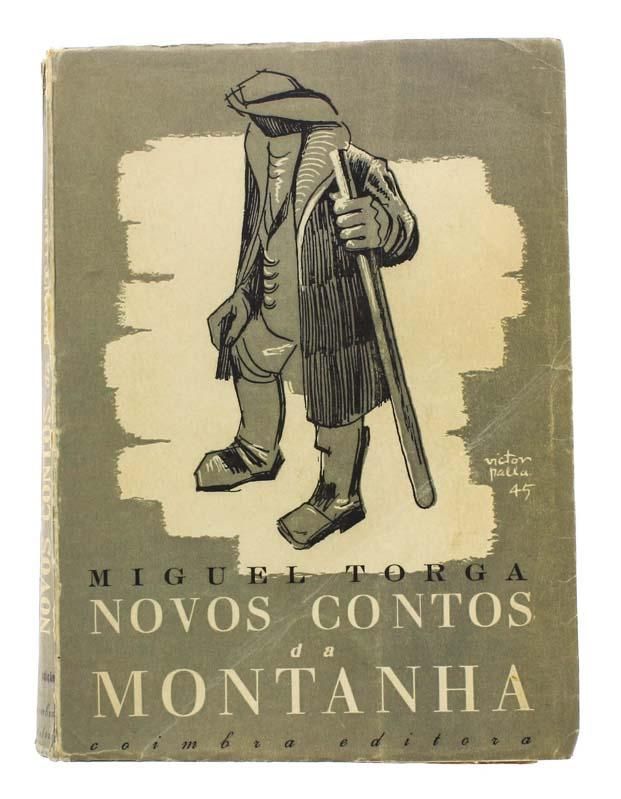
(三)阻礙葡萄牙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纪初實現工業革命的因素有哪些?
葡萄牙以引入工業設備,改善農業生產環境與增加可用國内資本為目標的工業的工業革命浪潮始於十八世紀中後期,經歷挫折後在十九世紀末仍未成功。制約葡萄牙完成工業革命的因素既有在歐洲具有普遍性的因素,亦有因其歷史文化鋪墊與經濟模式、社會思維等因素所造就的獨特問題。
基本而言,制約葡萄牙工業革命的内在原因包括地理問題與脆弱的農業體系;與外部環境相關的因素則在於其强烈而模糊的重商主義及經濟領域過於依賴大城市,在以上兩種因素外,加之葡萄牙過早發展殖民主義,由此造成明顯的人口分佈失衡與男性勞動力持續流失。天主教文化在葡萄牙又適應環境並演變出一種强調等級位階的封建秩序,導致進一步壓抑社會佔比不高的第一產業。在經濟生產的條件中,缺乏生產資本和新商品的動力,數個世紀以來,從亞洲、巴西的消費品和英國在十八世紀工業產品直接在葡銷售,更進一步壓制了各階級對國家工業化的需求(粉飾了國家工業化的急切性)。
一種可行的思考路徑是結合葡萄牙在經濟、社會和聚落形態的長期延續性,以及留意特定區間中的轉變,將各領域的因素用結構分析的視野與心態看待。
一、人口方面:里斯本的人口虹吸、增長的緩慢與城市規模
葡萄牙勞動人口及其增長在五個世紀以來長期處於低位,人口增長相對遲滯且緩慢是導致無法發展出有效的第一、第二產業基礎最重要的因素。葡萄牙的人口在十六世紀只有140萬,而直到十八世紀初仍只有210萬人口。葡萄牙人口增長同樣存在明顯的不平均性,據研究,十六世紀末葡萄牙的人口密度係數(人/平方公里)處於16.7至19之間。在海濱大城市和南方沿海以外的中部與北部區域的係數區間則是7.7-35不等;而里斯本和海濱城市則集中了全國從十五世紀起,人口在城市分佈的特點也隨着行政規制、就業機會的緩慢變化而變化[10]人口自然增長的緩慢減少。人口分佈不均的問題在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城市體現為中型城市與省級大首府的缺失。小型城市的勞動力通常在前往殖民地和功能相對完善的首都里斯本謀生。因而,儘管葡萄牙在十五、十六世紀已經建立了世界性的海洋商品聯繫網,但葡萄牙本土多個體量薄弱的城(市鎮)卻無法體現專門、僅供自給之上的生產功能。限制了大農業的發展與封建地產制度的退潮[11]。
二、社會方面:三等級制與封建特權,重商主義與文化工具的改變
葡萄牙國内,移居海外,人口流出最多的地區在不同時間段上有一定的相似性。移民發展到十九世紀中後期,基本每幾年就有數萬至數十萬人離開,十八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中期人口最主要的流出地主要是農業—鄉鎮地區和馬德拉(Madeira)群島和亞速爾(Açores)群島。這些人通常都在由於貧窮和社會等級難以獲得上升而離去,而葡萄牙社會上的嚴酷的封建社會結構無疑致使這種現象的一大主因。葡萄牙的社會分別在十五、十六世紀被《律例》(Ordenações)分為以教士、貴族與其外的人群組成的三個等級。第一等級司法獨立,并且國家不得對教會徵稅,只向國王呈上資金奉獻。教士的地產擴張早在十五世紀已不可置信地在數量上「等同於城市的其他房屋的數量」。神職人員的特權與豁免權貫穿及作用於葡萄牙和海外殖民地的社會與人口結構之中,他們利用法律要求教區内的居民繳納涵括在定期、節期或不定時繳納的實物和現金,以及教會確實地徵收了佔國民生產十分之一的什一稅[]。另外葡萄牙的教會分佈在各地的濟貧院和「仁慈堂」(Miséricordia)將死者的財產保管起來,在死者無繼承人或繼承人短期内不能作證以繼承,教會就將這些富商巨賈的錢藏於聖庫。
貴族階層主要也依靠社會階級上與教士階層關係緊密的網絡[12]與血傳承的土地財產——這種收入方式與法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的貴族階層有可見的分別——葡萄牙的貴族階層在土地上對農業和畜牧業生產的干預直到十八世紀仍在持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半島上超過95%的土地屬於貴族與教士[13];葡萄牙貴族收入的一大來源是參與全球海上貿易與海外殖民地的皇家職務(如二十世紀前的葡印總督都由貴族家庭成員擔任)中,通過豐厚的本薪加上賄賂、有時在當地科徵宗教稅項獲得大量商品、奢侈品和黃金貨幣。部分大商人或業務超群的商業經理人,在委托照看大貴族的海外貨運生意下,也在法律上被認證為貴族階層。然而,鑒於葡萄牙國内生產根基不穩,還需考慮直至十八世紀中葉前仍沿用的嚴苛封建特權法例,成為貴族家庭的大商人和原貴族反而助長了階級固化,堵塞階層流動的通道。
在葡萄牙、第三等級儘管在十八世紀的發展中有所變化,但其基本規則仍然不離中世紀時期的分類框架。主要分為耕種私人和他人土地的農民、商人和貿易商、從事手工業和工業活動的商業性佃農與機械師,不久之後漁民、水手和批發商都被納入其中。葡萄牙第三等級的分類與法國最大的不同點是,由於葡萄牙的教育事業不足以培養起龐大的官僚隊伍,有學問而從事公務或王室任務的的群體都基本被納入貴族的幕僚中,其身份自然也升為小貴族。而三等級制度從中世紀到十九世紀葡萄牙的模糊很大程度上投射在第三等級的定義中。國王可以隨意因爲某項航海任務或功績、總是給從參與商業的人封賞。在獨特的架構和社會心態中,顯現出貴族重商化的風潮。
三、長期的收入來源:移民使僑匯作為財政補充,以及人口的「逃逸式」流出
葡萄牙的移民現象應該在結構性分析中單列,這種做法是為抽出長期移民潮與財匯流動之間的緊密聯繫。移民現象脫胎於葡萄牙的政治—人口問題中,卻在經濟—財政層面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移民從十五世紀至今都流轉在前葡屬領土的世界範圍之内,到十九世紀結束時,他們基本上在五個大洲中都建立了自己的社區。十九世紀移民流入數最多的地點是巴西,而移民數量又在一八八八年奴隸制廢除,巴西帝國政府需要更多勞動力和商業人員時繼續其盛況:當年葡萄牙就有131,268人移往巴西居住。巴西迎來二十世紀時,已接納了五分之四的葡萄牙移民。
葡萄牙海外移民回國後通常置辦土地產業,將部分資金投入繼續投入海上商業活動中。這種現象同樣自新航路開闢前後已蔚然成風。流動的資金發揮則在十九到二十世紀逐漸醖釀出巨大的能量,從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一年間,葡萄牙歷史學家埃庫拉諾(Alexandre Herculano de Carvalho)和奧利維拉·馬丁斯(Joaquim Pedro de Oliveira Martins)稱從移民從巴西寄回葡萄牙的款項由三千康托上升到15,000康托。移民對葡萄牙本土的私人資金轉移與來自外國商人——尤其是英國商人的外國資本流入一度挽救了葡萄牙政府的財政,冲抵了貿易持續不景氣下的負收入。十九世紀時,隨著工業化倡議的深入,葡萄牙現代化工程的改革者依靠這些資金投入到公路、鐵路建設,改進防止金和科學種植等活動。一定程度上幫助了葡萄牙的製造業。
四、結語:葡萄牙工業化的「不可能」與封鎖力量
工業革命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形式,稱為「資產階級社會」。這種社會將經濟杠桿交由中產階級的上層群體主導。葡萄牙從人口結構、社會及文化結構與經濟視角上來看,看似是由於不適合耕作的地貌、天主教傳統的守舊和移民僑匯天降一般的援助,葡萄牙社會得以在幾個世紀内拒絕工業化議程而維持表面繁榮。但若我們不一味套用英、法工業化路程的公式與充斥其間,歷史中巧合的事件及將葡萄牙的在不同領域上展現的情況與其海上擴展的文明—政治—經濟戰略以結構分析的方法思考,便不難發現,在一個充斥着商品(包括貨幣商品及其等價物)流通和模糊、不完全的重商主義——它最終也沒有使葡萄牙國民在海上獲得的財富與資金放在投資、儲蓄和機械發明這些領域上。原本應在生產力角度扮演推動角色的工匠與農民截至十九世紀都處在貴族、教會利用特權和政商關係與三等級傳統壓制之下。
這個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阻止發展出成熟資本主義的結構,實際上發源於葡萄牙人口與城市受地理環境影響,另一方面又從葡萄牙探索前往黃金之地和印度的一刻起就已經為葡萄牙產業部門的失衡與不良的膨脹埋下禍引——作為舊資產階級,為利潤而生產,為流通而銷售的大商人們占據主流,中產者滲入上層,預示著中產階級而凋零,而農民和城鎮的工人又由於貧窮、饑餓和封建制長期規限完全失去活力,甚至組成移民大軍遠離國土。歸根究底,正是不重視基礎產業和城市組織—經濟領域自有和現代化,葡萄牙擴張的慣性本身導致其無法擁有完全工業革命的先決條件。
註釋(附參考書目與論文)
[1] Baudry Hervé, 'Medicine and the Inquisition in Portugal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eople and Books',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23, 2018. pp.93-95.; 顧衛民:《葡萄牙海洋帝國宗教裁判所的歷史(1536-1821)》,《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9(01), 2017. 第68-69頁;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澳門三種民間草藥》,《文化雜誌》,澳門:澳門文化局,1990年。
[2]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Vectores do descobrimento do Atlântico'', A Expansão Quatrocentista Portuguesa. Lisboa: Dom Quixote, 2018, p.224.
[3] Ibid, p.225.
[4] Ibid, p.225-256; 'As maneiras de sentir e se pensar e o comportamento económico', p.123.
[5] Ibid, p.230.
[6] 'Condições culturais da navegação oceânica e génese da náutica astronómia', p. 256-257.;顧衛民:《15世紀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前西歐主要的幾種地圖式樣》,《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20-05。
[7] 儘管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擴張確實一度影響義大利方面的黑海貿易,但奧斯曼不久之後,於十六世紀初已然重新促進過境貿易,對黑海貿易造成打擊的反而是葡萄牙艦隊在一四九八年越過好望角直接通印度洋建立交通,從胡椒原產地販運胡椒時開始。那麽,在這樣一個貿易網絡之下,葡萄牙人新航路的開闢與奧斯曼帝國的興起之間就不存在必然的聯繫,穆斯林君主之間的戰爭與軍事威脅相當程度上指向於經濟和貿易財富上。奧斯曼帝國在十四世紀遭受帖木兒帝國的打擊以後,迅速開始對巴爾幹地區進行擴張,占領了位於地中海東部的羅德島,一度剝奪了熱那亞商人所有的貿易特權,但不久之後就恢復了同佛羅倫薩等國的關係,鼓勵商業活動。 Jaime Cortesão.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2 vols.), Lisboa: Circulo de Leitores, 1979;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Os Descobrimentos e a Economia Mundial, Vol. I. Lisboa: Editorial Prensença, 1981. p.236, 238, 260, 265. 又見於: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Economy', Review, p. 331-339.
[8] 顧衛民:《若奧二世時代(1481-1495)葡萄牙海洋帝國的擴張事業》,《歷史教學問題》,2017(05),第15頁。
[9] 十五世紀葡萄牙史官有關恩里克王子的記述業已提及恩裏克王子與其弟佩德羅之間在攻佔北非的穆斯林城市丹吉爾這一戰略決定上存在理念上的分歧,前者認為武力征服北非穆斯林的手段合乎美德;而後者則認爲和平與人類的良知揭示了以戰爭手段迫使摩爾人投降並改信天主教,已經違反了基督美德中排在首位的人類良知與兄弟之情。
[10] 什麼應該被認為是「城市」?在不同的時代、環境下,自有不同標準。儘管總是有一個雙重標準——數字和功能——來區分「鎮」和「村」。就其功能和性質而言,一個城鎮必然是商業和工業活動的中心,有時至少也是行政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其人口(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以這種方式間接謀生。量化標準更依賴於時間--一個中世紀的城鎮在今天不過是一個村莊。然而,重要的是要強調,超過一定的數字閾值(因此,根據所考慮的時期而變化),一個定居點必然具有我們所列出的城市功能。在我們的時代,所謂的農業城市,即人口致力於農業的城市中心的形成,只是明顯地掩蓋了這種聯繫:在今天的規模上,它們更應該被稱為農業村落;而且只是在今天,由於新的運輸手段和農業機械化,它們才成為可能。
[11] 1527-1531年,葡萄牙首次對住宅(住房單元)進行了全面普查。在葡萄牙海洋帝國的鼎盛時期,就是當我們高祖父與高祖母為塑造現代世界,為全球規模的商業資本主義做出巨大貢獻時。然後,有91個城鎮的檢察官被記錄在王家議會中;他們共有63,572戶,占大都市280,528戶的22.6%。但在這些城市中,並非都是城市群:有37個城市的火災次數超過500次,而這個門檻對於定義城市化來說是很低的,即使是在16世紀;但請注意,這37個「市」和「鎮」加起來共發生過52,111起火災,因此,占總數的18.5%。每個住宅我們平均可以計算出4.5人(在4到5人之間),因此,500個住宅的門檻可以起到區分「城市」和「農村」的作用,但不是城市本身。在十六世紀的規模上,這一資格實際上應該保留給至少有4000名居民的城市群,也就是說,如果不是1000個住宅,也應該有900個以上的住房。在900到2000個住宅之間,也就是4000到10000個居民之間,我們發現有14個聚集區:三個非常接近最大值——聖塔倫(Santarem)、貝賈(Beija)和埃瓦什(Évash),有四個市鎮少於1000個住宅——阿威羅(Aveiro)、埃斯特雷茲、維亞納和(Viana)維拉多孔德(Vila do Conde),其餘七個城鎮在1000人到1600人之間——塔維拉(Tavera)、吉馬良斯(Guimarães)、科英布拉(Coimbra)、拉各斯(Lagos)、波塔雷格雷(Portalegre)、塞圖巴爾(Setúbal)和奧利文薩(Olivança);它們共有18749個住宅,人口大約為85000人。超過一萬人的居住區,如埃武拉,有12660人;波爾圖,有13500人;里斯本,達到7萬人。這樣定義的城市人口只佔王國總人口的12.7%。在西班牙,沒有一個城市可以與里斯本相提並論——塞維利亞是最遠的城市,只有45400名居民;但在2萬到5萬之間,有不少於6個(本世紀末有8個),而葡萄牙沒有這個類別的城市;在1萬到2萬之間,有7個(本世紀末有10個),而我國只有2個;在這以下,但也以4000為下限,有13個,比葡萄牙少一個;城市人口一定占總數的8%左右。見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 Evolução Demográfica e Urbanização', A Estrutura da Antiga Sociedade Portuguesa, Lisboa: Edições 70, 2018. 09, p. 15.
[12] 1715年,莫奈修道院院長為法國陳言,神職人員擁有王國2/3的財產;葡萄牙的教士階級沒有達到這個比例,但他們在土地財產中的份額在1/3和1/4的比率間搖擺不定。那麼,教會收入相對於國民收入而言又是什麼呢?1537年,它們達到了100萬金克魯扎多;1632年,它們超過了184萬金克魯扎多;換句話說,在95年裏,它們以穩定的貨幣將收入增加了84%。在第一個日期,國家收入(不包括商業合同和海外收入)不會達到40萬克魯扎多,但加上「商業」條目,可能達100萬;在第二個日期,包括所有的收入來源(海外除外),會達到200萬金克魯扎多。舊政體時期,人們認為在【伊比利亞】半島,「收入」(被理解為超出生產階級直接生存需要的一切生產資料)被大致平均分成三份:一份歸國王(國家),一份歸神職人員,第三份屬於貴族。轉引於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A Estrutura Social do Antigo Regime'. p. 29.
[13] 神職人員上層與貴族緊密相連,在伊比利亞半島,貴族們能夠從教堂、修道院和各種虔誠的基金會的收入中抽出可觀的份額。巴托洛梅烏-多斯-馬爾蒂斯修士打算在他的大主教職位上將他的財產歸還給它的主人(國王),他對別人表示「他正在與王國的大部分人和王國的所有貴族進行公開的戰爭,他們的主要收入就包括capela和comendador」;這些教會收入的擁有者認為他們是所有者,而不是用益物權者。(《大主教生涯》,第三冊,第七章)。
[14] 不論他們是直接領有土地抑或接受名義上由國王受封的「騎士賜地」「王家產地」等,貴族在後者仍然擁有收取土地稅收和直接控制生產資金的權力和眾多額外特權。
主要參考文獻與書目:
[1][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全球通史》(下),王昶、徐正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美]唐納德·卡根等著:《西方的遺產》,袁永明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美]R.R.帕爾默等著:《現代世界史》,何兆武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版
[4]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Os Descobrimentos e a Economia Mundial, vol. I a 4 vol. Lisboa: Editoral Presença, 1981.
[5]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A Expansão Quatrocentista Portuguesa, Lisboa: Dom Quixote, 2008.
[6]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Estrutura da Antiga Sociedade Portuguesa , Lisboa: Edições 70, 2018.
[7] Pierre Chaunu. A America e as Americanas, Lisboa: Edições Cosmos, 1969.
[8] Jaime Cortesão.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2 vols.), Lisboa: Circulo de Leitores, 1979.;另有中文版,[葡]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二、三卷部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7-12。。
[9] 顧衛民:《葡萄牙海洋帝國宗教裁判所的歷史(1536-1821)》,《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9(01), 2017. 第60-69頁。
[10] Baudry Hervé, 'Medicine and the Inquisition in Portugal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eople and Books, '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23, 2018. pp.93-95.
[11]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Economy,' Review, p. 331-339.
[12] 顧衛民:《若奧二世時代(1481-1495)葡萄牙海洋帝國的擴張事業》,《歷史教學問題》,2017(05),第23-32頁。
[14] 顧衛民:《15世紀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前西歐主要的幾種地圖式樣》,《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20-05,第129-142頁。
[15] 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澳門三種民間草藥》,《文化雜誌》,澳門:澳門文化局,1990年,第22-30頁。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