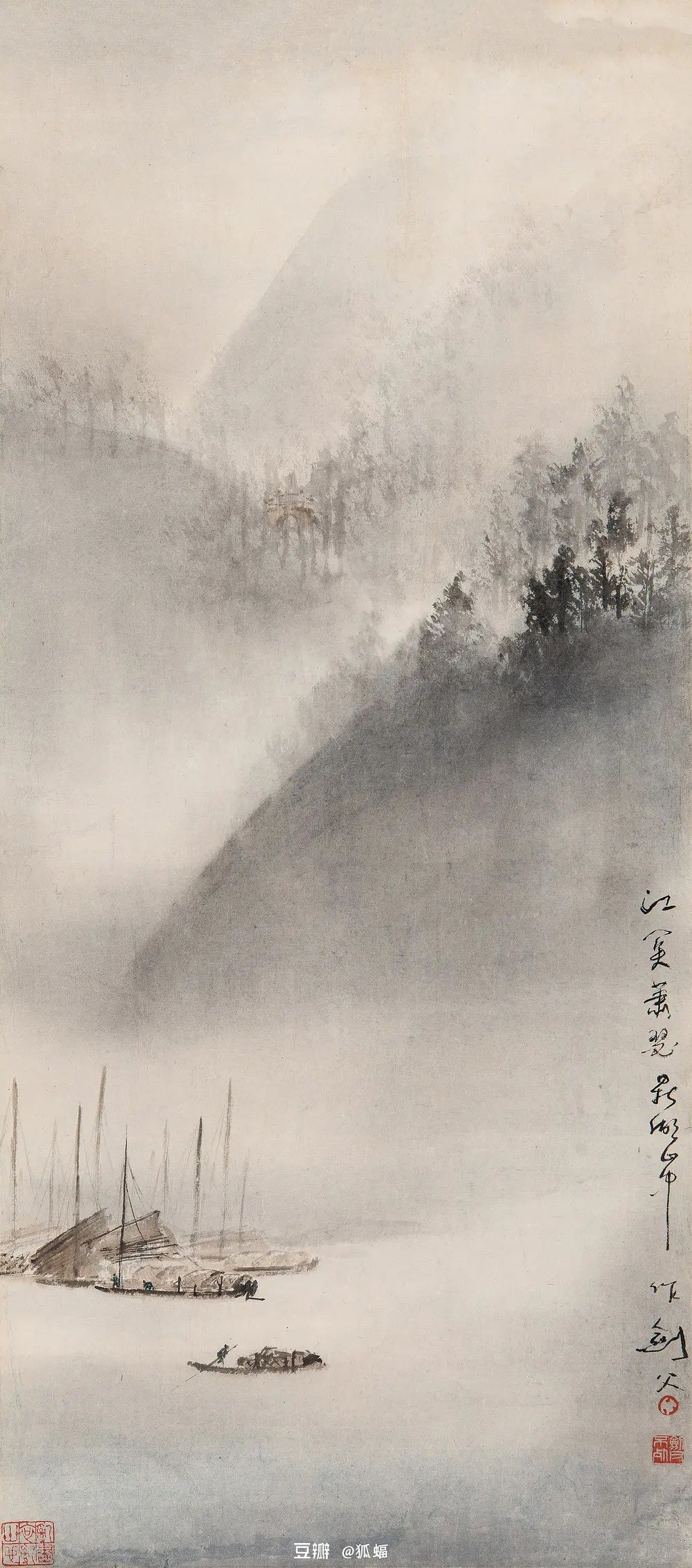
语言学小学僧,论文废晚期患者,社评见光死选手,白日梦爱好者。拥有翻译中埃及象形文字的技能,但正在遗忘的边缘徘徊。 奢望某一天可以从事甲骨文和音韵学研究。
记一次失败的田野经历
我虽然是语言学学生, 却辅修了一门人类学。课上老师聊到自己的田野经历时,不断地强调个人立场与田野的碰撞,以及自我在深入田野时那种那以避免的割裂感和价值观冲击。我一直以为自己并不是那种喜欢把个人立场强加于他人身上的人,田野中的人以及人们的认知于我而言是独立于我的个体,而别人的立场又关我什么事?于是便一直以为田野带来的冲击可能并不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事实证明,我似乎是错的。
前几天和我的死党讨论大陆围绕个人健康产生的一系列社会规则,以及普罗大众对疾病的一些看法。因为了解到,如果某人身患某些疾病,那么那个人很可能因为责任等问题而被一些公司拒绝,如果运气不好,也许就与心仪工作无缘了;更有甚者,这可能就是一个致命打击。当时我很疑惑,我在澳洲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社会机构以及社会群体不该应为疾病或残疾而将一些人推向社会边缘,而是应该尽可能完善各类public accessibility。残障者权益也许是呼声较大的一个话题,但在残障者之外的,与疾病相伴一生的人的声音似乎非常少,以至于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网民似乎根本不会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 (如果身边没有这类人群的话)。
简单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体检报告如果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必要的证明而存在的话,它理应服务于个人健康和公共安全,而不是将个人驱逐出社会。如果入职所需要的体检报告是为了公共安全和进入一个集体所需担负的责任,那么患有某些疾病的人在保证对自己的疾病负责的同时,公司是否也应该对其一视同仁,而不是因为一些潜在利益矛盾而一刀切地拒绝对方呢?的确,并不是所有公司和集体都有这个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于疾病的社会属性似乎并不是特别了解,针对一些疾病的歧视和污名化也的确存在,因为一些疾病而改变人生轨迹,打乱自我实现路程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但毕竟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国了,对于国内的现状不是特别了解,想着这似乎是一个绝佳的锻炼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机遇,将课上学的东西实践一下,若有可能,还可以期盼一下对现状做出一些改变。
我最先想到的是在豆瓣建立一个话题,通过话题引起公共讨论,这样就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及人们如何与异见者辩论或撕逼。然而这个话题并没有通过豆瓣的审核,这第一步似乎就受到了媒体自我审查的否定。之后我又换了一个封闭性的社交网站,得到了几个回答。回答主要有那么几种:1)同意疾病具有社会属性,并且告诉了我一个他身边的因为疾病无缘工作最后自杀的案例;2)认为我的担忧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认为疾病是公平的,不管什么阶级都需要面对疾病,认为我的担忧是鸡蛋里挑骨头;3)认为当下的社会虽然有对于疾病的歧视,但是路有千百条,此路不通还有彼路,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遭,社会上依旧有正能量;4)认为我不应该在这里批评,与其跳着脚批判,不如去提意见,去进入行政系统做出改变。
这些回答中不免有价值观不同而引发的冷嘲热讽,事实上,在我收到的仅有的几条回复中,大部分回复夹杂着我看不懂的敌意。当然啦,在当下的简体中文网络世界中,党同伐异实在太普遍了,尽管我觉得他们的一些看法不无道理,但这种交流的氛围实在是无法令人接受。而几条仅有的回复更加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测:因为疾病以及疾病的社会属性所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也许一直处于失声的状态,而大部分或许认为疾病事实上是最公平的东西(这点我保留意见)。
最后,当田野与我所牵挂和担忧的集体重合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老师所说的“割裂感”。一方面我明确告诉自己,疾病不是公平的,疾病有它的社会属性,围绕体检报告的规则虽有它的必要性,但似乎再正义的社会规则到了现实中都会变成强者的武器、弱者的牢笼。一方面我又需要提醒自己,必须听到不同的声音,听到人们心中真实的想法,并且要理解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导致它们的权力结构,只有听到普罗大众如何理解这些规则,才有更好的方法改变这一切。然而听取不同声音过程好比油煎火熬。互联网中低效的沟通、因为意识形态而产生的分歧,以及一言不合就开撕的风气将我从田野中拉了出来,再一次投进了那个吵吵闹闹,叽叽喳喳的网络空间。
这个时候才明白所谓人类学的视角:投入又抽离的视角实践起来是多么困难。当你真正成为田野的一部分的时候,当田野不再是异化的他者的时候,田野带给你的会是无尽的撕扯,于我而言,还有无尽的失望和无力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了所谓的家国情怀也许是最大的束缚。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