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夏的回忆文字四篇
转贴者曰:按照龚本人的时间顺序进行了排列。
从城市到乡村:我的小学生活
2009-03-11 20:48 星期三
最近到美国的一些地方组织上去谈教育改革,经常会说起中国教育的情况。去年曾经应蒋保华之邀,在他的“我的小学生活”系列中写过下面这篇文章。人们谈教育改革的时候,经常会遗忘像“春耕小学”这样的学校里的学生。
************
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我的小学生活是1966年结束的。不过对于我来说,更值得回忆的是飓风降临之前的一年。我作为小学生的生涯在那一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我今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65年,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中国南方沿海进入了战备状态。当然,对于居住在离香港一百公里的广州市的人们来说,战备早已是常态,只不过有时候看上去更加紧急一点而已。这年夏天,上面的领导人号召市民将年幼的子女送到乡下或者内地,以减轻大城市的负担。这也就是所谓“战备疏散”。于是,父母将我送到了湖南省长沙市的祖父祖母处。
我当时九岁,刚刚读完小学三年级。我就读的学校是广州东山区的寺贝通津小学,是市里很少的几间五年制实验学校。学校的设备、教材、师资在当时都算得上是一流。如果按照正常的进度,我十六岁就可以从中学毕业去上大学了。然而,生活这时却出现了个人无法控制的急转弯。
到长沙的新学校入学还没有几日,祖父有一天回到家里,闷着头一句话也不肯说。几天后,父亲从广州赶到了长沙。孙儿辈并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却看到大人们都在愁眉苦脸地收拾行装。很快,我们不过的行李被搬上了一辆长途汽车,祖父祖母和四个孙儿一起被父亲送到了车上,开始了我们的长途旅行。
后来我们知道,祖父因为说话不当、做事不小心,在“四清”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为此,阖家老少也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祖母和我们四个从三岁到十一岁的兄弟姐妹不得不中断了学业,跟着祖父回到了老家益阳县的一个村子里面。
村子里有一家小学,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我们就被安排到那里去上学。
从广州最好的小学被“下放”到这家叫做“春耕学校”的地方读书,是我人生中最奇特的经历之一。
学校在村子的尽头,从家里走过去大概两个华里。路途虽然不远,但是在经常雨雪纷飞的冬天,孩子们走到学校的时候穿的棉鞋都会湿个透,因此人人脚上都长着冻疮。那个年头里面,橡胶套鞋是非常稀罕的东西,在田里干活的大人都轮不上一双,更不用说孩子了。学校的房子里当然也没有取暖设备。家境比较好一点的学生,都会提着个叫做“烘笼子”的东西——一个外面套着竹篮子的铁皮罐、里面烧着少许几块木炭、能维持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暖炉。在冷得直哆嗦的那些日子里,保暖比读书对孩子们来说重要得多。
学校一共只有两间教室和一男一女两个教师,大概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他们教的只有语文和算术。像音乐、体育这些课程,大人小孩都没有听说过,那绝对是城里人的奢侈享受。这里四个年级的学生只有两间教室,因此每两级的学生共用一间。每间教室都带着一个小小的耳房,那就是老师的寝室。每逢中午下课,两位老师就各自回到屋里去做饭,飘出的香味让留在那里的学生馋个不行。我的那个课上,一边坐着二年级,另一边坐着四年级。老师轮着教两个班,一个年级上课,另外一个年级就做功课。
课本都有点破烂,原来都是过去的学生留下来的,开始时这让习惯了在书本上做标记的我很是为难。我从小就很爱读书,自从离开广州之后,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正经读过书了。拿到课本之后,我迫不及待地翻了开来。一看之下却大失所望——原来这里所谓四年级的课本中大多数的内容,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读过了。这里的学生也买不起作业本,人人都用一块石板代替。老师也不改作业。需要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个答案,大家自己去对。至于学生在课堂上听懂了多少,作业做对了多少,老师并不太关心,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关心。据说这两位老师的“成份”都有点不好,但人们似乎也不怎么在意。
虽说是在广州长大,我在学校中学会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并且非常以此自豪。可是到了这里,普通话却根本派不上用场。老师上课用的是当地的土话,我几乎一点也听不懂。听着同学们在用益阳话背诵《乘法口诀表》(这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背会了),我真是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哭。
说起同学,那也是一个不同的概念。班上的男孩子们年龄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可是不少女同学却看上去已经是成年人的样子。原来,这些女生的确也已经有十五、六岁,零零碎碎地在上着学,也不过就是为了认识几个字。四年级以后的学校——这里叫做高小——在她们那里几乎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当地人都说,女孩子反正最后是要嫁人的,还是学点种田的活计或者女工针指才是正经。
其实,所有学生的课程也都断断续续。本来每天就只上半天课,在学校里也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听课,因此每天上课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两个小时,根本不能和城里的全日制小学相比。而一到农忙的时候,学校统统放假,大人小孩一起要到农田里面干活。大学教育对于这里的学生来说比月亮更加遥远,能够去上中学已经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即便是上高小,也要走上十多里的路。在“春耕学校”读书的孩子,对未来很难有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梦想。
学校的条件虽然尔尔,湖南却是个有读书传统的地方。村里如果有哪家的子孙通过教育远走高飞,那在多少年里面都会是人们的骄傲。“大学生”的头衔,就跟以往的进士、状元一样风光。至于那是北大、清华,还是湖南师范专科,人们并不太计较。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之类更是闻所未闻。 “春耕学校”为学生们铺下的,仅仅是通向农田的道路。
2008年,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我讲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历史。有一位学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带着浓重西班牙语口音说:“教授,可以给我们说一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吗?”
我告诉他们说,在上大学之前,我只有四年正式的小学教育。而最后的那一年,我学到的是农村孩子的生活。我给他们描述了“春耕学校”。
“听起来和我们危地马拉乡村的学校一样,”提问的学生若有所思地说。
“所以那里的孩子将来未必就不能上哈佛,”我很高兴能为学生们作出这个结论。
不过,身在地球另外一面的我经常会猜测,今天的“春耕学校”及其学生们,比当初会有了多少改进呢?
http://blog.tianya.cn/post-1020111-16729243-1.shtml
我的体育爱好(及照片)(照片略)
2008-07-22 00:39 星期二
按:腾讯网在组织一批怀旧的稿子,命题作文,这是我写的第二篇。由于写到了在世界各地旅行,所以附上一些照片。
==========
1965年,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由于祖父被打成反革命,孩子们都跟着被赶下乡,从此以后也就失去了正经读书的机会。十四年以后的1979年,我从一家工作了多年的工厂里考入了北京大学,和那一代的许多幸运儿一样,又重新过起了学生生活。
刚开学不几天,就要上体育课,那很是令我为难了一阵子。虽然当时只有二十三岁,但是因为我在工厂里已经有了“老工人”的身份,能够对徒弟们指手划脚,所以心理上早就自觉是饱经沧桑的成年人。跟十几岁的小年轻一起蹦蹦跳跳,总感到有那么点不对劲。
第一次上课,老师发下一张简单的表,让大家填写体育特长。我横着竖着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写什么。球类是一概不会,跳远跳高大概只能给地上砸个坑,跑步肯定赶不上别人。思量再三,我写下了两个字:拔河。
体育老师看到之后,对我皱起了眉头:
“拔河算什么特长?”
“需要点力气”,我辩解说,在农村工厂劳动那么多年,力气自然不小。
可不是,当年在农村生活,十三四岁我就可以一气挑上四块泥砖,每块三十斤,远远超过了我的体重。在工厂工作,机器模子七八十斤,轻轻松松就能搬起来。不仅如此,在农忙或者工厂旺季的时候,每天都要工作十至十二小时甚至更多。练出来这点力气,用在拔河运动上难道不是正好?
其实后来才知道,那个时代体力劳动锻炼出来的真正本事,是负重和长途跋涉。这些年来,每逢年度休假,我就会和朋友 一起走到世界某个人迹罕至的角落里安营扎寨,融入大自然的和平与宁静之中。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名川大山中都有我们的足迹。背着三十多斤重的背囊,里面装上帐篷睡袋和两个星期的食品衣物,我一天能走上十几二十公里,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
有一回,我们漫游来到了希腊的奥林匹亚。在古人留下来的体育竞技场面上,有全身穿着沉重的盔甲、手持庞大的盾牌的武士在比速度。那全副武装,至少得有四、五十公斤,名副其实的负重行走。
于是我就想,当初北大的体育课怎么就没有这一项呢?否则,我也不至于总是那么丢人现眼地不及格呀。
http://blog.tianya.cn/post-1020111-14631219-1.shtml
弹指三十年……
2009-03-02 23:01 星期一
几天前接到广州一位老朋友的来信,问我是否记得二月六号是我们平反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忽然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我的确忘记了。不仅忘了,而且是这些年从来没有想起来过。于是赶紧打电话过去,才知道当年“李一哲集团”的人不久前还聚了一趟,只是少了几位已经去世的长辈和朋友,特别是郭鸿志和李秀芳,当然还有几个身在海外的人。到网上去查了一下,发现广东的地方报纸居然还有一些报道。看来,三十载沧海桑田,仍然有许多人记得当年的往事。
1974年,在卷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事件的时候,我刚刚十八岁。在现在的人看来,那时候的我们是一批非常奇怪的人。明明在工厂做工,在农村耕田,却总是一有机会就讨论国家的前途和世界的未来。其实我们未必知道多少,只是从有限的几本书里面拼命汲取能够得到的人类文明的养分。后来我常常跟人感慨说,读《马恩选集》连脚注都能背下来的,大概也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我之所以成为那里面的“黑干将”(这是当年“运动办”给的头衔,并非自诩),纯粹出于莽撞。那年的夏天,我从朋友处借到了一本手抄的《民主与法制》,看得欣喜若狂。之后开夜车转抄了许多份送人,并且打听到李正天(“李一哲”之“李”)的地址,上门给他送去了一大叠印刷用的白纸。正好我在早些年里因为油印上诉材料,学会了刻钢板。这时候手艺也就派上了用场。有经验的人都警告说,这么干最终是要掉脑袋的。
虽说有可能掉脑袋,但是卷入后动里面的人们却义无反顾。脑袋如果不能用来思考,那也不怎么值得留恋——起码当初我们这些年轻气盛的人都这么感觉。况且,那篇《民主与法制》激励了千千万万受尽委屈、满怀痛苦的人。全国各地雪片也似地飞来的信件,让我们感受到了与整个民族心的相通。我们觉得自己在创造历史。
后来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顺理成章——我们一大帮人被扣了个“集团”的帽子,被关了起来,过后又被平了反,大家散伙各奔前程。我离别了当年生死与共的朋友到北大上学,这一晃三十年就过去了。如今回忆起来,七十年代的那段生活仍然令我觉得充满了意义。也许可以说,十八岁那年的冲动与莽撞奠定了我日后人生的哲学基础。
其实我是个不喜欢怀旧的人,虽然我最热爱的专业是历史。尼克松在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接受记者采访,说“人生到了我这个年龄,就只有未来可看了。”三十年后,我的未来已经系于太平洋西面的这块土地。在这里,民主与法制不再是理念而是实践。我想,我如果能够用自己的经验来为这些理念未来在中国的实践提供一点有用的脚注,当年吃的那点苦头大概就不算白费。
http://blog.tianya.cn/post-1020111-16638970-1.shtml
没有房子住的回忆
2008-07-19 00:03 星期六
按:腾讯网约稿,要写一点八十年代的事情。第一个专题讲的就是房子。这是我写的当年的故事。
================
1983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在上研究生前夕和在中文系的男朋友结了婚。
婚礼是借二十八楼研究生宿舍的会议室举办的。买糖和茶水,我们一共花了十五块钱。云翔在上研究生,四个人一间房子,空间比八人一间的本科生多一些。他们宿舍的另外三位男生搬到外面去住了三天,将房子让出来,我们就算是结完了这个婚。三天之后,我夹着枕头又回到自己的宿舍去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房子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研究生宿舍当然是没法容纳新婚夫妇的,只好到附近去找农民房。先是找了一间不知道原来是用来装煤还是装砖的六、七平方米的黑糊糊的小屋,旁边住着哲学系的甘阳夫妇。当时北京的房屋奇缺,就这么间房子,记得还要花十五块一个月,让我们这些阮囊羞涩的措大心疼好半天——当时的研究生助学金只有四十六块钱。后来还算我们运气好,通过朋友介绍,借住到圆明园一户人家。他们家有一间用来养鸡的旧房子,这时候鸡不养了,就让给我们住。而空出来的那间房子,国政系的刘苏里夫妇立即欢天喜地挪了进去。
圆明园的房子虽然旧,但是毕竟有了自己的小窝,我们对房主人很是感激。夏天窗外一片蛙鸣,池塘中布满了荷花,给读书增添了几分古朴的意趣。到了晚上,却经常听到顶棚上有沙沙的声音,我们以为是老鼠。
在圆明园快乐地住过两年之后,人家要拆房子,我们也只好搬回学校来。拆房子的时候,人们在顶棚中找到了三条蛇。原来它们才是这些年真正的同屋。
云翔留在中文系教书。青年教师,两个人一间房子。同室是好朋友,不时给我们让地方,但却不是长远之计。最令人沮丧的是,当时北大的青年教师们完全看不到解决住房问题的前景。1985年,北大曾经召集一批青年教师代表开会,由校领导向他们解释住房状况。当时分房子是按点的:级别、工龄、年龄、学位等等全都要计算在内。我们算了一下,要挣够一间单间的房子的点数,我们必须等到四十一岁。在那以前,如果自己想不出办法来,就只能住集体宿舍。
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在面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在找分配单位:有没有房子是优先考虑的条件。我们既不会拉关系也不会走后门,就会读书。我们想,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读书无用论总不能永远应验。
于是,我们开始了准备托福考试和申请美国学校的漫长过程。说是漫长,也就是花了一年多时间。当时两人只有三十出头,比等那间房子还是快了十年。
也就是这样,云翔和我后来分别拿着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
http://blog.tianya.cn/post-1020111-14602960-1.shtml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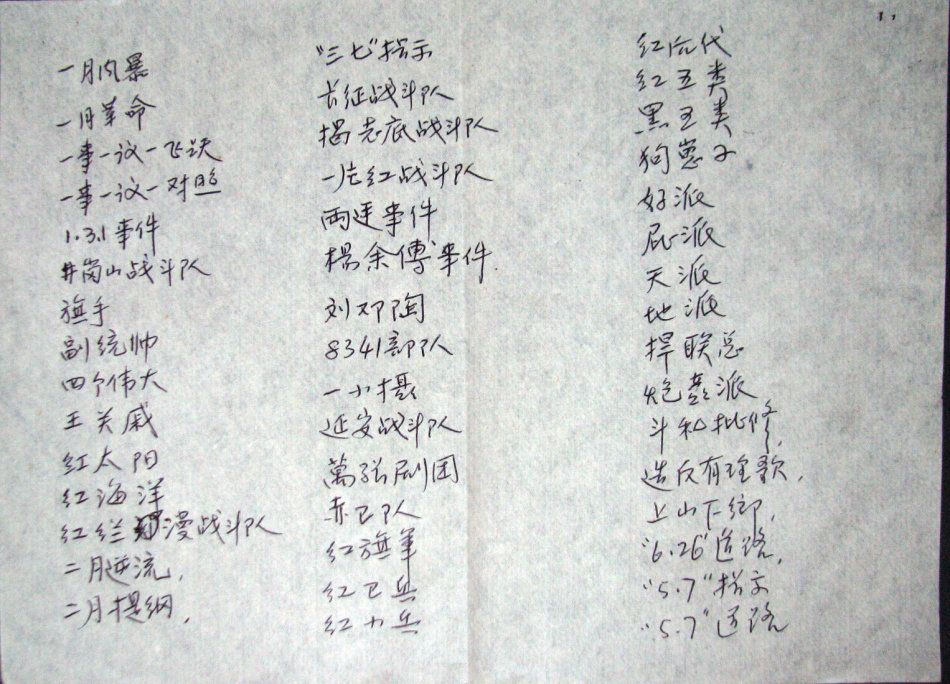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