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论|被争夺的场域:心理治疗的源流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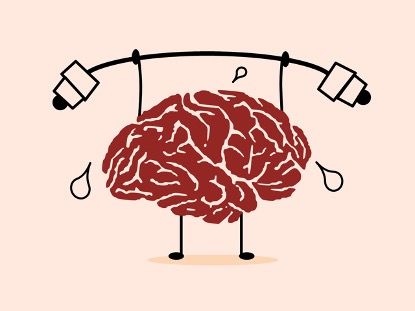
文|日鸣
什么是心理治疗?
近来,“精神健康”议题越来越受关注,而“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在公众心目中则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在生活中不时听到,“陌生”是其实又不太了解,大抵是有个印象,觉得是当人有一时之间无法全凭自己走出的“情绪困扰”、甚至受“情绪病”以至“心理病”或“精神疾患”折磨并阻碍日常生活的时候,除了吃药之外的另一个选项。
人们可能觉得“心理治疗”就是“找个(心理)专家聊聊天去解开心结并得到一些建议”,但这个“专家”究竟是什么人,以至究竟“心理治疗师”、“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辅导员”、“社工”和很多不同类型的所谓“心灵导师”等这些名号之间其实有什么分别,也未必有很多人能分得清楚;当然,也更少人会去追问,这些名号的区别究竟纯粹是在特定脉络下的社会建构,还是有充分理据的概念区分,以至这些区分究竟怎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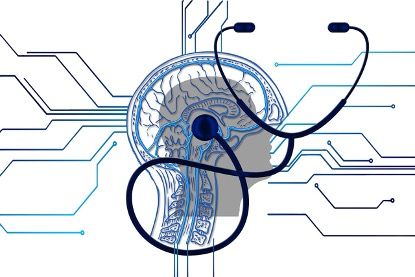
这些概念区分和论述,同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和定位自己“内心”的问题和困扰、以及这些问题或困扰可以怎样跟自己所参与的社会生活挂勾(或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连)。假如我们对它们根本没有觉察或不清不楚的话,其实就等同于把自己对“自己的内心状况”的诠释权交出而不自知,在懵懂不知的情况下被夺去了对自己最私密的领域的自主权。甚至,我们对私生活领域人际关系的理解,以至对于种种切身的生活体验、问题的划分与定位都失去了诠释权和参与的主动性———例如哪些状况是精神健康问题,哪些状况是教育问题,哪些状况是成长问题,哪些是工作问题、家庭问题、人际相处问题、个人问题,以至哪些是社会问题等等,也只能等待专家或权威告诉我们或替我们作标签,并交给他们处理。
例如现在很受关注的“学习障碍”和“特殊学习需要”(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究竟是教育问题、精神健康问题或者个人问题,以至这“问题”需要或应该得到怎样的处理或支援,不同的解答足以对面对着这种状况的人以至其身边的人的生活,有着全方位的影响,不管这人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自己的子女;又例如,我们在某些情景或某种生活中感受到“失落”、“沮丧”、“愤怒”、“委屈”、“恐惧”、“担忧”等情绪,究竟纯粹是个人困扰还是社会问题,究竟是合乎情理的反应还是病态/病症,究竟是需要治疗照顾、教育培训、个人成长还是普通的亲友支援陪伴,都受上述那些概念框架左右。
所以,所谓的“心理治疗”,不只是一些治疗实践的技术和跟治疗实践有关的知识,更是一套或一组影响力超出了“治疗室”而广及日常生活不同层面的思维方式或视野。
科学还是经验?心理治疗的源流
对“心理治疗”进行更深入的追问和探索,有着超出“精神健康”范畴的社会意义,并且与一个人作为“公民”和“行动者”的身份和权利/权力密切相关。如上所述,一般人对“心理治疗”的印象很可能是“找个(心理)专家聊聊天,去解开心结并得到一些建议”;若追问下去,让他们描述得更详细的话,这个说法可能可以进一步扩充并厘清为:
在“治疗室”(一个暂时跟生活隔离的安全空间),于“治疗时间”内,跟一个有着“治疗师”身份的专家“谈话(谈自己的事)”,或跟他/她“互动”(不只是“谈话”),以求在这“过程”之中,发现并超越某些“盲点”(或“自我限制”),得到解开一些“心结”的“启示/指引”,让自己转变到“更好的状态”,并寻获或得到进一步“改善”自身或自身的状况。

若这一描述(不是定义)大抵可以被接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心理治疗”可被视为不依靠“物理介入”(如手术、电击等)或“生物化学介入”(如药物)的手段,在一个特定的(体验)情景中,在另一个人(一个被信任为“专家”的人)的支援下,试图让自己因得到某种解放而有所改变,并进而引发更深远的个人转变。而所谓的“物理介入”或“生物化学介入”,则往往是“精神医学”(psychiatry)这种着眼於“作为生物体的人”并标榜其“科学性”的专业实践所使用的主要介入手段。[1]
通过“谈话”和“人际互动”,去引发或支援另一个人的转变,企图让他/她生活得更好,其实并不是什么现代的新发明。这种实践在世界各种古文明皆有踪迹,由一些有着“巫/萨满/祭师”、“精神导师”以至“哲学家”[2]身份的人来进行,是苏格拉底、孔子、耶稣、佛陀等人经常做的事,是古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苏菲教派、基督宗教的神父牧师、佛家赟师或上师等人会做的事。
那么,这些过去的实践与我们今时今日所说的现代“心理治疗”究竟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又有哪些相通的地方?
一些当代的“临床心理学家”(clinical psychologists)可能会通过媒体或他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此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心理治疗”是依据“现代科学的心理学”去进行的谈话治疗或非物理、非生化治疗介入实践,而过去那些人生导师所根据的是玄想、人生体悟或神秘体验。
可是,这说法其实并不准确,甚至有点本末倒置之嫌:例如,佛洛依德及其“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是“现代(学术)心理学”总是不想提又往往不得不轻轻提一下的人物和学说,虽然他经常被视为“谈话疗法”(talking cure)的先驱,或现代“心理治疗”的起点,但他建立其学说和治疗技术所实际依据的,绝非什么学院心理学(academic psychology)或实验心理学(experimental psychology)的理论或知识,也不算通过什么严格的科学程序(如果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所得出的成果——尽管佛洛依德本人一直很希望自己的“精神分析”得到“科学”的名衔和地位。不只是佛洛依德及其“精神分析”面临这样的批评,甚至是其后诞生和崛起的各种心理治疗流派,其实大都不是根据所谓“科学心理学”的实验或科学方法而发展出来的;就算是发展出来之后,也大都没有花太多功夫去进行符合实验室研究标准的验证,它们的验证和修正发生在其每一刻的实践过程中。尤其那些在实务前线进行治疗工作的治疗师们——包括那些因其技艺和实务功力而得到名声和地位的治疗师——根本就很少依靠科学化的心理学知识或心理实验的成果,来进行治疗或发展他们的实践技艺。毋宁说,他们的“心理学”或心理治疗“学说”(即真正指导他们实践的概念框架和原则)主要都是从他们的临床实践经验甚至试验而来的,是他们对自己(及其前人)经年累月的临床心得所作出的整理和总结,是一些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建构和修改的参照图像。[3]
这里并不是要把“心理治疗”和“(学术/科学)心理学”完全对立起来,因为事实上某些心理学研究成果也会对心理治疗的实践和更新有帮助。但这里要厘清和强调的是:“心理治疗是依据心理学研究和知识所作的实践”,甚至说“心理治疗是由心理学研究和知识发展出来”,这些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可说是言过其实,因为心理治疗的临床实务知识有更大部分跟这些科学知识并没有关联。即使如今往往有一些“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的确会这样宣称/相信,但这跟“心理治疗”实务的真实状况实在相去甚远;此中有两点值得留意甚至作出批判性的反思:一是事实上在历史上以至现今很多地方,“心理治疗”的执行也不是由一个单一专业所垄断的专利[4],而这些专业之间往往存在着竞争角力的拉锯关系,它们各自向公众和官方体制以不同的论述为自己定性和定位;二是关于知识的构成,从实际情况可见,“临床实务知识(既来自实务经验又直接用于实务实践的知识)”和“科学知识”两者构成其实有着不同的途径和准则,但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后者往往会垄断了“知识”之名,或把自己/被体制定位为“最高的知识”或“最可靠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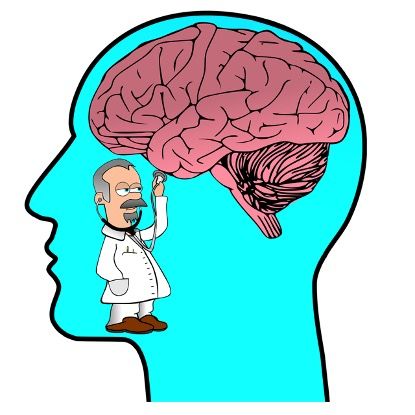
现今大部分的心理治疗方法和学说,其实是根据临床经验(而非实验或科学研究的结果)整理出来的实践知识或参照框架,而普罗大众一般笼统地说的所谓“心理学”知识,其实混合了分别来自至少两个不同源头的“知识”,它们之间未必真能相互沟通或统一成一个知识体系:一个来源是治疗的临床实践经验和反思,另一个来源则是学院/研究所的科学化研究(即依靠统计学数据处理方法和人为建构的实验情景去收集数据和有系统地整理数据并从中建构理论再加以验证的程序)。若以知识社会学的眼光,从历史发展脉络看的话,此中还可说有第三个源头,那就是跟“应用心理学”紧扣的种种“心理测验”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分类模型建构”[5];不过,现在的学院心理学往往把“心理实验”的知识跟这些“心理测验”的知识包揽在一起,但从知识建构方式和源起方面看,后者其实不一定等同于前者,而在发展过程中后者往往是一种依据其于“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工程”方面的实用需求而被接纳和广泛使用的“知识” [6](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就业领域,种种“考试”和“评核”都跟这种心理学关系密切 )。
也即是说,跟作为自然科学或严格科学的“物理学”或“化学”相比,“心理学”一词其实既不代表一个大致上统一的知识体系,也不代表一个至少在研究方法或规格方面有大抵一致标准的学科[7]。如果“心理学”这名号如今已被“学院心理学”所垄断(把“心理实验”和“心理测验”两方面的实践集合起来),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心理治疗”根本可算是另一个领域,而不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们之间只是刚巧名字听起来有点相近而已,因为即使回溯它们的发展历史脉络,其实也没多少交集的地方。也因此,“临床心理学”其实既不等于“心理治疗”,“心理治疗”也不从属于“临床心理学”,而“临床心理学”关于“心理治疗”的定义也无法代表实际上在临床实务层面的所有“心理治疗”实践[8]。
这些听起来有点混乱的奇怪现象,可以通过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得到更充分的了解,一旦追溯起来就会发现是个非常复杂曲折的故事,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和探讨:
- “心理治疗”领域和笼统而言的“心理学”领域的知识或论述方式是怎样建构起来的;
- 这个知识/论述建构的过程怎样跟相关专家的专业身份形成过程挂勾;
- 当中专业阵营之间的竞争角力怎样影响这些知识/论述的建构,在同样被视为会去处理人们的个人烦恼、精神痛苦、心理问题或情绪困扰的几个专业之间——即“精神医学”(psychiatry)、“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y)、“心理治疗”(psychothe rapy)以至“心理辅导/咨询”(counselling)之间其实一直发生着非常激烈的拉锯、合并、分裂和重新定位的动荡过程,它们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争夺对于“人的内在苦难”的“处理权”和“发言权”。
被争夺的场域:心理治疗背后的权力与利益
这情节多变的故事只能放回到历史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即使这故事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但对于一个具批判意识的“公民”和“行动者”来说,有一些重要的事实是非常值得知道和注意的,例如:

- “精神医学”(psychiatry)在所谓的“药物革命”之前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虽然它一直依靠官方体制的力量及官方于社会控制方面的需要,在“人的内在苦难”这个领域维持着最高的权威,甚至到了现在由于精神健康问题大受关注而极受重视,但实际上在20世纪中叶“精神科药物”有大突破并使精神医学跟制药业(pharmaceutical industry)的利益链连成一体之前,精神医学在医学界的地位(相对于其他医学专科来说)可说是最低的,甚至经常被其他专科的同行瞧不起;而精神医学在“药物革命”之前所用的种种疗法,一直都既缺乏医学界所重视的科学性和实际效果,也常常被批评为过份残酷,而当时精神病院的管理方式也不时被外界评击为极不人道,所以精神医学可说是有着一段极为黑暗又尴尬的历史。
- 精神科药物的突破、制药业的全球崛起及与此相关的利益链的形成,直接影响了“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分类和诊断方法”的知识建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很大程度地主导了这些“科学”的发展走向和实质内容。
- 虽然“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y)现在宣称“心理治疗”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但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都不是以“心理治疗”为其主要任务的,而且它在精神健康领域主要从属于“精神医学”之下,扮演的是一个辅助角色,直到后来跟当时新兴的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至认知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认知革命”,让学院心理学研究有了新的方向,进而在治疗方面发展出结合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一些疗法或治疗策略,如“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CBT)或与之相近的“理性情绪行为治疗”(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al therapy,REBT),“临床心理学”才明确地在医疗体制中得到了以(科学化的)“心理治疗”方法去承担治疗任务的角色和地位。
- 上世纪中叶起,在欧美地区开始陆续展开的精神医疗“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或“社区化”运动,让“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方法在短短十年至二十年之间急速发展(可说是以几何级数增长),并变得非常多样化,尤其是对于以更人性化的治疗为宗旨的种种人本取向治疗方法/学派来说,这运动是个极大的发展助力。从一方面看,这些“去机构化”和“社区化”的政策改革,的确以“人道精神”和“更人性化的医疗照护服务”为旗帜;但另一方面,种种事实却也揭示了,这个运动背后的动机其实并非如其宣称的那么纯粹,当中很大程度上也涉及了政府当时希望紧缩医疗开支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以及制药业的崛起、医疗界和政商圈子的利益瓜葛等黑暗面——亦即是说,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始终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 精神医疗的“去机构化”和“社区化”运动,推动了心理治疗的发展,并催生出心理治疗流派的多样化。但与此对应的,是精神医疗照护服务的“私营化”和“市场化”趋势,以及保险业于其中的角色也变得日益重要,精神保健及医疗越来越倚重仿佛比较易于量化管理的“市场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让心理治疗领域由一度百家争鸣的发展重新趋于单一化;而“私营化”和“市场化”亦令心理治疗学派之间的竞争涉及更多的商业因素,产生更严重的利益冲突,也间接令各学派的专业认证制度渗入了更多与监督专业服务品质无关的考量和决策。
- 即使“心理治疗”在精神医疗“去机构化”和“社区化”的过程中,开始摆脱“精神医学”的制肘,而逐渐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性,但由于“心理治疗”始终跟医疗健康有关,不论是公众还是官方都会特别关注其“安全性/风险”,所以“心理治疗”无论是向官方体制靠拢,还是走向市场,它都得建立种种认证监管制度,一方面试图以此让公众安心(即使实际上监管质量和力度往往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借此保障自身的特权和利益。这些认证制度让“心理治疗”领域形成了一种相对保守甚至权威层级式的生态,即使某些学派的理念或学说于理论上很着重“人的解放”、“反思批判”和“社会脉络”等概念,但实际上,心理治疗的专家们在公共社会层面和专业领域内部都相对保守,甚至会倾向跟社会事务保持距离。
“人的内在苦难”似乎无可避免,对于这种状况的关注和种种需要,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一个被不同“专家”或“特权阶级”去争夺话语权和掌控权的场域,在种种看来条理分明,甚至宗旨纯粹的学说或解释背后,其实渗杂了许多混合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竞争和角力,而“心理治疗”也不例外。这不是说“心理治疗”因此就毫无价值或完全虚假,重点是无论作为实践者还是服务使用者,乃至作为“公民”和“行动者”,我们都需要带著一种社会视野和批判意识去对“心理治疗”作出反思。
[1] 即使现在不少精神医师或在历史中某时期的精神医师并不完全排斥“心理治疗”甚至有时也会亲自执行“心理治疗”的操作,但实务上--尤其在医院中--这始终不是精神科医师的主要治疗方式。
[2] 在今时今日现代化了的大学体制中,“哲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在批判性反思中通过抽象思辩去进行理论建构/重构的纯学术活动,但其实在大学现代化之前,在世界各地凡古代传统中(包括如今所谓的“西方文化传统”),那些如今被我们叫作“哲学”的东西,大都并不是纯理论或纯理论性的思辩,而是跟“生命转化”有关、以“生命转化/安身立命”为目标的精神活动(spiritual exercises)或曰疗愈行动/互动。即使这种观念已非当今学院的哲学的主流,大学所教的哲学史也早已根据现在的主流标准被重构,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哲学学者把这种古代的哲学面貌重新疏理出来,例如Pierre Hadot所著的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和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还有Martha Nussbaum的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等等。
[3] 最大的例外也许是现在于大部分地方成为主流、大受临床心理学家们拥护的“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CBT)或与之相近的“理性情绪行为治疗”(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al therapy;REBT);说它们是个“例外”,不是说CBT或REBT这种心理治疗方法真的已经充分得到实验室科学研究验证为最有效,或真的在实务上比其他心理治疗方法显著地有效很多,而是说这方法及其实践者往往会特别声称自己是根据以实验为基础心理学或认知科学发展出来,也特别强调其疗效最经得起实验验证的方法。(但现实是,例如有一些比较符合实验科学规格的研究指出,认知行为治疗其实没有比其他一些心理治疗方法更有效;也因此,研究者们尝试改为尝试筛选出这些不同的治疗方法所共享的有效治疗因子。)
另一个值得提的“例外”现今非常盛行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对心理治疗(以至大众的心理学知识/论述)的影响。这个跟科学研究关系比较紧密的学说,虽然没有直接发展成一套新的心理治疗方法或学派,但却很广泛地影响了许多既有的心理治疗方法与实践。
[4] 这些专业例如包括“心理治疗师”、“临床心理家”、“精神科医师”、“辅导员/咨商师”、“职能治疗师”甚至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社工”和“精神科护士”等等,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权限划分。
[5] 关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这三个源头,详细可参看Jens Bergmann所著的《失控的心理学:心理学如何成为赚钱的产业、当代的信仰?》第一至三章;当中关于“心理测验”在历史脉络下作为“心理学”的发展与盛行的主要线索之一,有一些有意思的整理,是现今的心理学教科书未必会提及的。
[6] 从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更清楚,“心理测验”的技术和知识的发展其实一直跟社会管理/控利挂勾,军方、企业和同政府政策相关的行政管理是背后主导的推动力。
[7] 正如《失控的心理学》的作者在该书的前言说:“心理学是一个一般化的概念,原因在于这个学科可区分成为数可观的分支学科及学派(而且“非常亲密地”维持着对彼此的厌恶)。”
[8] 当然,一些相信“科学至上/只有科学才是真理”的人、“精神科医生”或“临床心理学家”会说,正因为有很多心理治疗方法依然没有科学根据或不是由科学理论发展出来,所以不可靠,而这正正就是心理治疗领域迫切有待改善的地方。但不少“心理治疗师”则会反对这个说法,会强调不能把“治疗”化约为“科学的应用”,“人”也不能化约为“科学研究对象”;好些著名的心理治疗师甚至会指出,其实“治疗”更接近“艺术”而非“科学”(如Jeffrey K. Zeig),对于心理治疗来说“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素养是比“科学”知识更重要的基础(如RolloM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