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3時代的內容與matters——與劉果的暢談
主持人
這次邀請劉果老師來GreenPill中文社區分享,也是因為近期兩個社區之間合作很多。我們在matters上面也開了官方賬號,matters 也請了我們幾個社區小伙伴,包括k 和York 去他們的學習會上交流。所以我覺得咱們可以線上加深一下聯繫。
關於matters,在2018 年剛創立的時候,其實在我們媒體圈其實引起蠻大的一個震動,一個是因為張潔平老師的個人品牌,一個當時是建立在區塊鏈基礎上的一個去中心化的內容生態,對當時人們來說還是蠻新鮮的。但當時我離區塊鏈圈子挺遠,而且看他的整個使用的界面看起來就像一個Web 1. 0 時代的論壇一樣的,後來也沒有繼續很深地關注。後來到了美國,在洛杉磯跟劉果老師有幾次交流,其實也沒有太看懂。這兩年隨著web3的概念的推出,其實我感覺matters 也在逐漸的有一個轉型,逐漸跟Web 3 領域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它作為一個承載Web 3 信息的一個內容平台,一方面跟麥克盧漢說的一樣,媒介即信息,他本身作為一個媒介,它本身也是某種web3的信息,透露出創作者經濟在Web 3 時代會有一種怎樣的變化的信號。
所以今天請劉果老師來,對於他們正在做的幾個項目,重點包括matters.news,travelogger,The SPACE,背後的設計理念,和我們社區有一個分享。
--Matters.news
主持人
當然首先就是matters.news。因為我現在在運營社區的官方賬號,所以有一些切身的體會,首頁由算法把讀者捐贈量化成數據排序,由社區來共同策展。這會不會讓捐贈活躍的讀者佔據過大的一個話語權?
劉果
對,我覺得也是。很多人費解為什麼要用區塊鏈來做這件事情,包括現在其實也是。我們看到的機遇是,一定可以做一種新的內容或者信息分發的模式。在信息分發的層面,去中心化了之後,個體和社群能夠控制信息的方式就變得不同了,一定是種新的分發的形式,它會更好。在哪個維度變得更好其實是未知的。
另外一個維度是新的商業模式也是有可能的。因為一旦有區塊鏈,我們就能夠定義一種新的ownership 的形態,所以一直都是圍繞這兩個方面,有點像一個很大型的實驗。因為我們並不知道終點是什麼,只是知道這兩個方向都是有一些突破口,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值得嘗試的地方。所以大概是從18 年到現在不斷地進行這樣的嘗試。 Travelogger和The SPACE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關係。當然這兩個項目的實驗性就更強。所以也是從這個當中總結出一些經驗,每一步都是通過依據之前的經驗在想下一步應該怎麼推進是比較好的。
回到首頁的問題,背後比較大的一個思路,如何避免流量經濟,少部分內容汲取大多數流量,其實和這個問題類似,商業模式是創作者拿到錢的模式還是依賴流量。流量經濟一定是應用或者平台要去刺激用戶的流量,這個是繞不開的,流量是完全跟它的商業模式是強綁定的。所以我們在想的一個方式就是我們能不能減少對流量經濟的依賴,因為不可能完全根除掉。因為流量經濟現在佔了創作者收成的80% 以上,這個比例實在是太高了,不可能繞開。我們只能減少對他的依賴。創作者收入可以分成直接和間接兩種,所有的廣告都是間接收入,我們為了降低這部分廣告間接收入的依賴,就增加直接收入。所以背後的idea最簡單的其實就是捐贈,不管是單次的還是重複的。所以我們就直接讓用戶去對文章進行捐贈,並且讓捐贈的數據成為主頁排序。主要機制就有點像微博的熱搜榜,但是此時不是大家搜索,而是哪篇文章獲得的捐贈更多。活躍的用戶就會被更容易發現。此時的活躍指的是捐贈的活躍程度,現金流的活躍程度。我覺得這個事情似乎無法避免,因為只要把權力交給一個群體,一定是這個群體當中少部分人,要么是他的創作大家非常活躍,要么是它社交非常活躍,能夠吸領大家的錢,它能夠排到上面去。最後我們發現,如果我們把權力交給交給社群之後,一定會出現這樣的金字塔結構,並且它還會有馬太效應。我們的想法並不是直接去牽制這一部分頂端優勢的出現,因為它是一個自然的結果,也是每個社群的特質,而是倒過來去想,怎麼能夠讓不同的社群能夠更快地建立。比如一個社群頂端優勢固化了之後,被排擠走的用戶有沒有辦法很快地成立自己的社群?我們現在大概更多地是從這個方向在想這個。
yihan
我也蠻贊同。任何的社會體系下,總會有頂端優勢和馬太效應出現。比如一個國家,也會出現所謂的統治階級或者有產階級,你多大程度上可以讓這些有志向有能力的,但是目前還是無產階級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新的有產階級。可能這就決定了整個社會的活力。如果他一直是固化的,他可能就會死掉。他如果一直能有廣大的底層上來的渠道,可能整個社區的活力就可以維持下去。我好奇Matters怎麼才能讓新的好的創作者獲得成為下一個頂端的機會?
劉果
是的,我很同意這個看法。頂端永遠會存在,但是它都需要避免的是權力的板結。任何一個結構,你不管金字塔的程度有多強,層級關係有多強,一旦它固化了之後,其實生命就會失去,需要有不斷的流動、有競爭。所以我剛才提到的讓人們能夠更快地去建立新的社群、新的結構。
回到內容排序場景,如果我們把內容髮現強烈地和捐贈綁定在一起,它確實有一個好處,創作者的收益變得更多。我可以更多地從用戶直接獲得更多的錢,而不是通過流量獲得錢。假設此時一些創作者,他因為自己的social connection 比較好,他支持者比較多,他的影響力比較大,他每一篇文章都會獲得很高的捐贈,每一篇文章都會上榜。你把信賴交給了大眾,大眾自然會出現網絡效應。我們發現一些好的方式繞開這個機制,對它進行彌補。比如matters也做過一個叫“在場獎學金”的,是一個有很多很專業的評委去做的一個非虛構寫作的獎項。這相當於是繞開這整套機制去找專業的人來進行評委。這些人就不會再受到社交網絡當中你的影響,他可能就會看,考慮到創作者雖然是新人,但是你有潛力,有一些閃光點。 matters專門有一筆錢撥給這個獎學金去挖掘這樣的創作者,他們的作品再進入到matters當中。這樣可以讓他們早期有一個快速被發現,快速去曝光的渠道,讓更新換代更容易進行。
還有一些更偏向機制設計的地方,我們考慮過如何激勵人們去發現尚未被發現的作品。不管是以NFT的形式,還是fungible token 的形式,有的直接是分潤,但大概思路都是我先給捐贈,如果我是第一個捐贈的人,後面捐贈的人的錢會分一部分給我,如果一個賬號還沒有太多人關注,我現在支持了,後面這個人會給我分成。
但是它有一個前提條件是需要讚賞高度活躍,否則最後沒有太多潤可分了。而且對於創作者來說,他也覺得很奇怪,明明是讚賞給我的錢,為什麼又分給這個人,雖然這個人是我的伯樂,但是還是有一點奇怪的。我們目前沒有去實現,但是如果之後規模更大,更活躍,有可能會是一種有用的機制。
yihan
我再簡單追問一個問題,就是剛才講的專業評委,這個事情讓我想到了現在的藝術行業,畫廊有時候就有這種感覺,因為畫廊很多時候沒有走量,流量邏輯就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獲得少量有實力的買家對你的認可。而這個認可其實很多時候就來源於所謂的一些權威,比如美院的教授、一些著名的藝術的評論家,他們是不是認可一個新人,但這個模式會讓我覺得它也會出現問題,大家好像在去討好這些評論家的審美,而不是完全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創作。
劉果
對,我完全同意。因為這些評委如果他能夠持續做下去,並且做得好,影響力足夠大,他就會變成新的中心。所有的領域都會看到這樣的情況。所以我覺得更本質地解決這種權力集中的方式,還是要讓新的權力結構能夠更快速地湧現,最根源的去中心化的方式還是市場化。如果能夠找到一種方式,能讓不同的機構能夠去進行競爭,競爭他們的信用,如果你出現了權利板結,你一旦出現了固化,新的機構很容易把你替代掉。
回到matters的例子,在場獎學金其實是我們團隊主導的,專門去找專業的評委、專業的創作者來進行評選的一個獎。我們其實有更多更小的活動,高度分散化的。我們會有一些小規模的撥款給某一些策展人,你自己去決定,發起一個活動,這個活動有些是有獎徵文,你認為哪些文章寫得好,你給他們獎學金。我們快速的用少量的資金,把策展人或者評判者的角色給出去,讓他可以相互之間快速競爭。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防止板結的方法。
K
我感覺機制設計很大程度上需要有一個高流動性、有更多的用戶更多參與,才能把網絡效應給搭起來。想知道matters早期的增長是怎麼來的?
劉果
很大一部分就是創始團隊潔平老師他們很多年在媒體行業內工作,所以早期比如前500 個用戶或者前1000 個用戶,可以找到質量比較高的創作者進來,發一些比較有趣的內容。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中文社區缺這樣一個東西,在海外的時候,我感覺非常明顯,有一個巨大的市場空缺。這是從媒體市場的角度來說。另外一方面,全世界的社交平台有很多,不管是Facebook、Twitter,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平台是讓中文的人能夠匯聚在上面的,沒有任何一個平台讓兩岸三地的人都可以去用,而我們都相信同文同宗,只要是同一門語言,能夠相互交流,其實人們是可以在一起進行討論的。
前500 個人,前1000 個人,我覺得團隊的基因非常重要,或者影響力非常重要。但是到差不多2000,或者5000 個用戶之後,這些基本上就和團隊早期的就沒有太大關係了,後來出現的基本都是自然增長。我覺得自然增長基本上還是一個大勢,比如很明顯可以看到在大陸地區的用戶,每次出現比如大規模豆瓣被封或者微博被封,就會湧向matters。台灣的用戶也會有大量的進入matters,因為缺少一個中文世界都會用的協作平台。
我們不去推任何為了web3 native 用戶而去推的功能,基本上還是在考慮普通用戶,普通用戶就能用得上。這個是和大部分其他web3項目的一個區別。 web3 項目其他的這些創作者協議也好,很難獲客,包括像lens,你看它數據基本上都是刷出來的。
K
我有個跟進的問題,咱們談到了早期用戶的畫像,我觀察到matters目前的核心用戶群體還是比較偏人文,偏思考向的華文創作者為主。在web2.0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豆瓣,它的變現就是一個問題,你覺得在web3相似的用戶畫像,它的變現會有一些質的區別嗎?
劉果
我們也很想知道答案。我覺得會有一些質的區別,但是它的外部的限制因子差異不太大。首先,流量經濟一定還是很重要,比如豆瓣,它其實嘗試了好幾件事情,它嘗試打廣告,它嘗試通過豆瓣閱讀去賣書,最後發現其實都不是特別work,因為賣書也不是一個好的生意。豆瓣是一個流量高度分散的地方,雖然它豆瓣小組最後流量拉起來,但是也很快又因為政治原因被斃掉,所以如果不是因為中國特殊的環境,豆瓣在流量市場上有可能還可以活得不錯。
進入Web3之後,流量仍然是重要的一環,只是流量如何變現,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開始重新思考。我們能不能賣廣告位,不賣廣告。因為之前的廣告很像在封建時期,你的所有的數據都掌握在平台手裡,平台讓你看什麼就看什麼,它賣廣告的方式是直接通過賣流量。它要去抓用戶數據,才知道用戶注意力在哪兒。 Web3提供的機會是,我們可以不再去賣流量,而是去賣廣告位。 Web3 很大的程度上是把應用或者數據實體化了。比如在一個應用當中的某一個廣告位,可以是以NFT 的形式,有特殊的交易邏輯,流量交易會變得破壞力更小,因為它不再需要去監控你的每一個人。背後可以服務於一定的公共性,像哈伯格稅這樣的機制, NFT 不再被某一個實體所擁有,而是被整個社群所擁有的。它就是一種公共品。
它的盈利也許會比傳統的廣告位要差一點,但是它的破壞性就少了非常非常多了。所以流量是一方面,另外一個方面直接變現的這條路又會出好幾種可能性。一個是把捐贈的規模做大,另外一個更偏web 3 的形式,就是資產化,不同形態的資產化,社群成員資格的資產化,或者是一個應用當中權限的資產化。
社群當中的人會很願意做某些讓自己的資產升值的事情,他很願意很在意做一個集體,在意自己社群的品牌,在意自己是社群產出的內容。但是它也不容易直接把這種信用進行變現。但這會是Web3 最新的一條路。這個也是我們下一步想去加速對它探索。
主持人
為什麼沒有學mirror 把每篇文章可以做成NFT?
劉果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沒有用的。 Mint NFT本身很簡單,我們每篇文章都放在IPFS上,所以你把hash 複製下來mint 就可以了。其實可能就是多兩個點擊的問題。
我們沒有整合到產品裡,我們認為這不是一個大家都有的需求,因為對大部分人來說文章是一個flow,文章是一個流。創作者也是,不斷地產生文章不斷地變現,不是產生一篇文章被收藏起來。少數書可能會作為經典,但是這種書都是鳳毛麟角。對於99% 的創作者來說,這個可能不是實用的點。背後可能還有一個考量,這個是和mirror 最大的差異。 mirror 的形態每個創作者是高度原子化的,所以mirror 只能夠serve 頭部1% 的創作者。因為只有這樣的創作者,你才不需要一個社群,你自帶流量、自帶粉絲,剩下的99% 的人玩mirror是玩不起來的。我們當時討論最應該去服務的創作者是什麼樣的時候,我們其實覺得不應該是頭部的用戶,而應該是中部的這部分用戶。因為頭部的用戶已經有大量的工具可以去選擇了,中部的創作者並不是那些一個人能夠開一個專欄就會有很多人來訂閱的那類創作者。但是他們會需要相互交流之後也能夠產生價值,產生好的idea,需要有更好的架構,更好地讓這樣的人匯聚在一起,產生價值的方式。
yihan
matters 的審查是怎麼執行的,它帶不帶價值取向,比如不要洗稿,這也算是一個價值取向。但是在政治層面上可能就比較難達成。再去中心化,總不可能完全沒有任何審查。
劉果
什麼內容被選出來是相對比較容易去中心化的。比如通過捐贈這樣的機制,所以能夠不帶某種價值取向,或者價值取向就是全體用戶的價值取向。但是出現負面內容需要被隱藏起來。現在的機制是有11 個選出來的用戶,他們叫馬特,是建築師,組成類似於陪審團的製度。任何情況下,有用戶覺得什麼樣的文章是人身攻擊,或者是誹謗其他人,這11 個人會進行裁決,覺得這個內容是否是OK 的。這些裁決會類似於判例一樣,作為之後的一個例子,以後再有類似的行為或者文章發生,運營團隊就可以把它隱藏起來,把對應的賬號會給予相應的處罰。某種程度上是讓社區自己去定義社區規則。它仍然會是帶有社區的價值取向,但是它至少是可以自下而上湧現出來的。
yihan
目前這11 個人是怎麼被選出來。
劉果
我印象當中應該是我們團隊給出了一個候選的名單,比如根據最活躍用戶,或者是獲得讚賞堆中最多的用戶等等。這樣一些指標,有個比較長的名單,其他用戶會去投票。選出這11 個人。
yihan
他們有什麼激勵?如果他們忙,最近沒有在做他們該做的判決,這怎麼辦?
劉果
是的,目前是完全沒有獎勵的,所以確實是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是這段時間其實沒有太多訴狀出現。在出現訴狀那段時間的時候,恰好也是這11 個人比較活躍的時候。所以那個時候還有一些相對比較順利。但長遠來看,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也在想,有沒有什麼辦法讓這11 個人不是固定的,要么是隨機抽取,要么是隔一段時間是那些有餘力的人能夠去參與的,以及是否讓這樣機制有一定的激勵。但有獎勵也就意味著這個機製本身需要有營收,或者有一個有比較強營收的國庫,能夠一直去給這些參與者提供獎勵。
我們內部經常在討論這樣的公僕性質同時也是一種榮譽,是否應該給予獎勵,本身也是個很好的問題。但缺點是,如果不給獎勵,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承認這樣的公權力是給個人帶來好處的。這種好處和濫用公權的邊界就會變得非常的模糊。
--Travelogger
主持人
關於travelogger和logbook,我把logbook2.0裝載的內容基本看了一遍,很有趣。有幾個其實挺有意思的,包括2022 年的預言機,有人還預言說BTC 要漲到10 萬美刀,現在回頭去看,就好像從地裡挖出一個時間膠囊。
劉果
關於travelogger 和logbook,可能是實驗性最強的一個項目。這裡logbook 有點像接龍,它是個NFT,但這個NFT 你可以想像是個筆記本,它是個動態的NFT,又完全是在鏈上的。它就像一個筆記本一樣,可以打開第一頁,你就可以開始寫東西。寫完東西之後,如果你把它transfer 給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可以接在你後面寫第二頁。它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功能是,如果我覺得某一個logbook 我很喜歡,但它又不是我的,我不能在上面寫東西。我可以Fork 一個版本,就很像GitHub 當中,在Fork 的版本上面可以繼續寫。任何一個logbook如果獲得捐贈,這些錢是分給所有之前的創作者的。所以logbook作為一個容器,它是共同擁有的。所有權由所有的創作者去共同擁有的。這是它最根本的設想。
當時做這個項目的時候其實有一部分私心,這是我們第一個比較複雜的智能合約的項目,所以對團隊內部是有一點練兵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是想去探索如果給出了一個完整的鏈上創作的工具,有多大程度人們會因為工具本身來使用。因為我們一直很關注共創這個事情,如果能夠把人們的創作力匯集在一起,它產生內容會比較有趣。並且你可以把所有權定義為一個所有創作者共同用的所有權,就會有一種新的協作的形態會產生,我們想去實驗這件事情。
這背後最大的假設是,目前的web3 社群有多大程度會因為這樣的工具屬性來使用一個產品。其實這件事情很大程度是被證偽的。我們的結論是人們不太會因為純產品的工具屬性來使用它,更多的還是在社群和其他人找到連接。某種意義上,這個實驗的一個目的是證偽這樣的一個方向到底能走多遠,但是它背後的對共創的ownership 的這部分實驗確實還是蠻有趣的。
主持人
所以你並不認為這個項目成功了?
劉果
我覺得它還是走完它的使命。我們團隊內部的需求,對市場的探索,想知道它到底能走多遠,這部分是達到的,但是它確實沒有變成一個大範圍使用的這樣的一個範例,從這個角度它並不成功。但是實驗本身我們也是為了知道它能走多遠,我們也知道它不是我們在做的這件事情的重心。
主持人
對於logbook,所有者既可以捐贈給其他人,也可以賣給其他人,如果只是單純的售賣,共創的氛圍好像就有點削弱了。
劉果
是的,所以我們也沒有強調賣這件事情。我們最開始的設想是認為它是更像禮物,比如我寫了一個東西,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開頭,或者是一首詩,我會把它送給我覺得適合的朋友,它可以在下面接龍,這是我們覺得會是更自然的一個場景。只是過了段時間以後,它可能會積累出一些價值,有人會想要去買它。
主持人
你說它如果只是一個單純的工具,而不是作為一個社區共創,就不會有太大的前景。但朋友前後的贈與,本身不是就有一個共創的氛圍在嗎?
劉果
是。但它的一個很大的區別是,這種紐帶是比較弱的,因為這種關係沒有一個場景去延展。如果我們先去構造一個社群,在社群當中發生的關係有一個外部性的存在,這個關係是可以延展到其他的關係,並且其他社群當中其他人還可以作為旁觀者而存在。但是在logbook 上沒有外圍的這部分場景存在,只有一個logbook 當中你和前面人之間的交互。
所以這個紐帶其實是非常弱的,它也只能來源於現實生活或者其他地方。這個也是我覺得mirror 不太容易做得起來的原因,因為它就是一個強工具屬性的東西。如果不是在牛市,用它的人很難有繼續使用的動力。
K
設想一個可能比較惡性的場景,如果有一個用戶,他不想將他的利潤進行分潤,可以選擇不fork,而是把前者的內容複製粘貼到新的logbook嗎?
劉果
可以的。但是,作為一個NFT,它的變現方式還是收藏,誰會想要去買它,或者誰會想去fork 它。所以這裡其實存在一個天然的市場製衡。因為當人們要去買一個logbook 的時候,還是會考慮logbook 是否是抄襲的,或者我要去fork logbook 的時候,我還是會想要去fork 一個信息保留完整的。所以至少還有一點點的牽制。
在其他的場景下,牽制變得更少,比如流量經濟的情況下,內容農場大量地抄襲文章,或者現在有AI,你把文章抄起來之後改一改,其實非常容易,你就可以去賺取流量了,這個問題其實就會變得更難解決。 Matters在上面這層是中心化的,下面這層是去中心化。如果遇到抄襲或者是被懷疑洗稿的文章,管理員是直接可以把它斃掉的。但問題是它又上了IPFS和區塊鏈,如果它獲得捐贈的話,所以在鏈上它是完全動不了的,它永遠都會在。其他的支持matters這套協議的客戶端,像planet 或者RSS3,他們上面還是可以看到,但是在matters.news 上,前端可以把它屏蔽掉。就像一種折中方案,我們可以把它隱藏起來,但確實一旦上鍊了之後,因為數據沒有辦法篡改,你也沒有辦法去動到數據。
主持人
這個項目是徹底結束了嗎?還是以後會衍生出類似的?
劉果
因為logbook 是在Polygon 上, travelogger是在以太坊上,我們給它一一對應的映射關係, travelogger 這個NFT 會一直作為matters 的一個身份標識。這也是我們想實驗的一件事情。
我們把NFT 的一小部分擁有者作為特殊的人群,現在特殊性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一些內測功能,我們常常是先給travelogger 打開的。 ENS 最早期相關功能上線的時候也是這樣。 Travelogger這個NFT會內嵌到matters 的產品當中,作為測試者,或者空投早期測試的token 給這部分用戶。他們作為第一批的探索者,第一批願意去冒險的人,所以從這個角度,這個項目應該永遠不會停止。但對logbook本身的開發,目前沒有在進行了。
yihan
你講到web3 目前以工具性為主要設計目標的這樣的產品比較難以被接受,我好奇,工具理論上來說應該是提升某種生產效率才叫工具。但是比如mirror,它是個工具沒錯,但是它好像還降低了生產力。我們的結論是目前工具性的東西不太容易被接受,這個原因是不是因為目前web3 中的這些工具並沒有真的讓事情變得更容易。
劉果
是,而且我覺得讓事情變得更容易的工具,其實是好的,是該被人們接受的。比如WordPress 就是個很好的工具。 planet 也是很喜歡的產品,工具屬性就是很強。我剛才想說,並不是寬泛意義的工具性不會讓你們直接來使用,而是可能狹義地把內容放上鍊,以及在鏈上能夠進行確權這一類事情,如果它不是內嵌在一個場景當中,不是內嵌在一個社交網絡當中,而僅僅是這一小部分作為一個工具的存在,它很難直接被接受。因為這些工具沒有提升任何特定方面的生產力的。比如確權這件事情,它並沒有提升任何事情的效率。或者是在鏈上的分潤,它也並沒有提升它的生產效率,因為還沒有解決前面的潤從哪裡來的問題。
--The SPACE
主持人
很多社區小伙伴還不熟悉The SPACE這個項目,請介紹一下?
劉果
它的設想和reddit 的place 很像,就是一個1000 * 1000 的畫布,你一次可以修改畫布當中的一個像素,但是我們加進了一個twist,就是哈伯格稅的概念,因為每一個像素其實是一個NFT,所以其實這當中是有100 萬個NFT。你可以去購買每一個像素,你購買之後才能去改它的顏色。這裡的有趣的地方是在於這購買的概念,因為每個人都是在哈伯格稅的情況下交易的。哈伯格稅的邏輯是,我買了任何一個東西之後,我都需要給他定一個價格,下一個人可以只要支付這個價格,就可以從我這裡把東西買走。但是我的價格又不能定得太高,因為我的價格定了之後,我還需要支付和價格相對應的稅收。所以這裡就形成一個權衡,我需要把物品,不管是一個房子,還是一個像素,還是任何一個其他什麼東西,定到我覺得合理的一個價格。它合理就意味著別人如果出這個價,我願意把它賣掉,它合理也意味著我願意支付對它相對應的稅收。所以在SPACE這樣的一個交易的規則下,可以去交易每一個像素。
實驗的初衷是覺得哈伯格稅很有潛力,能夠作為廣告位的一種治理的方式,用市場來治理,因為這樣讓每個廣告位很快的可以達到一個市場的均衡態。因為剛才有提到,如果我們不直接賣流量,而是去賣廣告位,其實很難定價。因為賣多少流量多少錢,但買一個廣告位,怎麼去定價,這廣告位是長期就放在那,所以哈伯格稅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它讓任何廣告都處於連續拍賣當中。我們做The SPACE就想看真實性的用戶能否理解哈伯格稅的概念,我們嘗試把產品簡化到極致,它的稅收邏輯其實都包裝在產品當中,看人們會去如何去交易,如何去實現,如何在這當中去玩遊戲。在web3 當中很多人都討論過哈伯格稅,很多人認為非常有潛力, The SPACE 應該是第一個去大規模去實現這一套邏輯的項目。
主持人
The SPACE 還在matters lab還是已經獨立出來了?
劉果
獨立出來了,有一個SPACE DAO 在運營,基本不再是matters 的團隊在參與了。我們相當於把它的底子打好了,做完產品設計、protocol,我們也提供了liquidity pool,讓SPACE 有一些初始的價格,之後有一小部分token分配給matters lab 團隊作為早期的創建者,但是和社區的分發方式沒有太多區別,之後社區的貢獻者也會一樣的拿到類似的獎勵。剩下的運營和金庫分發,這些都是SPACE DAO去決定。
主持人
我玩了一下The SPACE,發現大家共創的力度比我想像中要更保守一點。如果拉動時間軸查看的話,整體的圖景很少被改動,一般都是小修小補,加個貓咪,加個氣球。我猜測是因為創造一個圖案,需要買很多個像素才行,涉及到成本。
劉果
是的,我覺得這裡其實是有個產品設計上的一個教訓。我覺得對於我們目前有的用戶數量來說, 1000 * 1000的畫幅太大了,這是個最核心的問題。對於reddit,它當時做的1000 * 1000的畫布,是因為它的用戶數量實在是太龐大了,它能夠把1000 * 1000的畫布玩起來,其實對於matters 來說,有可能100 * 100 的畫布是更合適的,因為這樣大家可以去反复地塗寫。
這個項目後來又復刻了很多版本,有很多團隊都想自己在團隊內部玩玩看,或者團建的時候想去玩。比如harmony 也fork了一個版本到harmony上面。這些團隊fork的時候都改了像素的畫布大小,比如100 * 100 或者200 * 200。其實有可能是個更明智的決定。
--未來設想
主持人
Matters lab接下來會有什麼新的項目的計劃嗎?現在方面透露的。
劉果
有一些大的方向。現有的網站我們會進行一個很大的改版,刪掉一些不太有用的功能,把剩下的功能整合度提高。更大一點的改動是社群化,因為我們現在整體像一個大的社群,就意味著它就會排擠和社群不相容的人。下一步的方向大致會讓人們創建自己的社群。具體的方案會是tokenize 社群,我可以通過創建token 的形式創建自己的社群。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架構上,讓不同的社群可以host 自己的server,相互之間連通。這會是下一步的一個更長期的目標。
主持人
整個matters就轉型到social 領域了。
劉果
對,但social 和內容的邊界是非常模糊的,因為我們的定義還是一個帶有強social 性質的內容創作平台。它的social 的目的還是為了產出好的內容,但是social 本身又是闡述好內容過程當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不管是它的分發、篩選還是對創作者的激勵, social 是必不可少的一環的。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希望social 能夠為好內容的浮現來服務的。
--閒聊
zik
Matters 團隊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是像一個創業團隊一樣去打造產品,還是像web3 的團隊一樣,認為是社區的一部分,是社區的起點。
劉果
這是個很深奧的問題。我覺得這兩者之間可能會是一個光譜,因為我覺得matters 更偏向於一個創業團隊。這個也是我覺得做產品需要的方式。因為做產品有很多時候需要的是兩種不一樣的視角,它有它的面子和里子,常常是非常割裂的。你表面上實現出來的結果,和它背後如何實現的,這兩者差異非常大。實現產品的人一定會去使用產品,但是使用產品的人常常是完全不需要care,也不應當去care 產品是如何實現的。所以那種能夠完全通過社區湧現出來的產品,它的一個前提,每一個使用者,它能夠去hack 這個產品,它也應當或者有動力知道產品內部是如何實現的。它一般都會局限在這技術社群當中的工具,比如Git 或者Linux 這樣的項目,我覺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個mass adoption 的產品,我的使用者不需要去care 你的產品內部是如何運作的。就像蘋果做的一樣,給你封裝好了。裡面的部分是只有工程師才會知道。這種情況下,需要一個很強內核的團隊才能把這件事情做好。從這個角度, matters 更像一個創業團隊。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我們想做的很多事情有帶有很強的社區屬性,比如社區規則如何制定,一個社區需要什麼樣的模塊,需要什麼樣的變現模式,它的都有很強的社區屬性,它的決策權都不在matters團隊,都在社區。我們的開發會議也是完全公開的,所有人都可以來參加。我們在一些大的改動之前,都會在社區討論,比如內容治理。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又把部分傳統屬於產品的決策交給了社區。此時matters 的團隊又確實變成了社區一個協調者。所以我覺得在光譜上可能兩邊都會佔一點,但是取決於什麼事情,比如像產品、 UI、技術,這些肯定是更像一個創業公司的。但在社區規則、社區運作、社區運營上,這些又是作為一個社群來運作的,此時的matters 團隊又僅僅是這個社群的起點了。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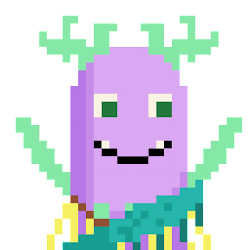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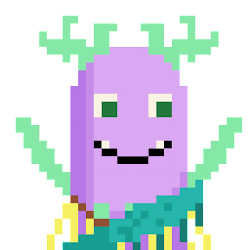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