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死亡」的北約如何在今天復活?
芬蘭於5月15日正式宣布將「歷史性」地申請加入北約,瑞典隨後也正式決定跟隨芬蘭向北約提出加入申請。瑞典執政黨社會民主黨同日晚宣布將同意加入北約。法新社稱,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產生的直接後果。對歐洲來說,北約究竟意味著什麼?
本文由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研究員Thomas Meaney發表於2022年5月5日,原名為「 How Putin's invasion returned Nato to the centre stage 」,由新不萊梅編譯。
北約回來了。
普京用入侵烏克蘭的方式單槍匹馬地拯救了北約,讓這個組織重回國際政治的中心。曾經自豪於中立的北歐國家現在正在加入;德國前所未有地增加了軍費,這意味著德國將為北約花更多錢;美國的戰略家們開始討論在太平洋國家裡發展北約夥伴;歐盟的官僚們則計劃著建立一個互聯網時代的新北約。就像川普時代人們學會了熱愛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一樣,自由主義者和疑北約論者都開始學著熱愛北約。冷戰時期的老警長重回戰場,而且人們驚訝地發現,在對抗俄羅斯的隊伍裡它幹得還不錯。

北約的回歸引發了人們關於其歷史的新一輪爭論,不同的利益相關方有著不同的故事可講。對俄羅斯來說,北約是一個意圖征服俄羅斯的邪惡計劃;對美國來說,北約一開始是保護西歐人不受自己和蘇聯傷害的一種方式,但在90年代,它成為民主、人權和資本的推手。對東歐國家來說,北約是阻擋俄羅斯的銅牆鐵壁;而對大部分西歐國家來說,北約是一個美國提供的廉價核保護傘,有了這個,他們就能把多的軍費都花到社會福利預算上去。而對世界的其他國家來說,北約曾是一個大西洋的防禦性軍事聯盟,但後來它變成了一個更全球化的進攻性軍事聯盟。
所有這些故事的共同特徵是,說故事的人都以為自己知道北約是什麼。但是北約的活動範圍已經不再「北方」,也不只在「大西洋」。它既不受「公約」的約束,而且也不太僅僅像是一個「組織」。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北約尚且需要開著巡迴大篷車向歐洲人解釋為什麼他們需要北約。現在北約早已贏得這場公關戰。從八十年代以來,對北約持懷疑態度的人越來越少。這個冷戰的產物在如今的西方政治軍事乃至經濟體系裡依然存在著,以至於它常常被人誤以為是歐洲秩序的自然產物。
實際情況卻是,儘管人們常常提到北約,但北約本身是什麼倒是沒人能講清楚。
軍事聯盟、制度安排與文化
字面意義上來說,北約是一個由三十個國家組成的致力於「自由秩序」的軍事聯盟。根據憲章第五條,北約各國在成員國受到攻擊時,將有條件地行使集體自衛權。 1949年誕生時,北約將自己視為二十世紀中期誕生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和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中的一員。它為自己維持了歐洲長達半個世紀的和平感到自豪。

儘管表面上北約的運作基於「共同同意原則」,但北約也沒有試圖掩飾美國的特殊主導地位。畢竟即使憲章也規定,當一個國家試圖退出北約時,它必須先向美國總統而非北約秘書長宣布其意圖。因此,從賬面上來講,北約每年的預算只有來自成員國捐款的25億歐元。但是美國的80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讓北約可以把預算都用來維持自身的官僚機構運作。
北約的總部位於布魯塞爾,但是它最重要的軍事指揮中心卻在美國弗吉尼亞。從1949年以來,每位北約總司令都是美國軍官。除了4000名文職人員以外,北約沒有其他工作人員。北約軍隊在任何時候都由成員國的軍隊組成,而美國軍隊出力最多。即使是北約參與的戰爭,從朝鮮到阿富汗,大部分也是由美國發起的。
北約最具威懾力的武器是它的核保護傘。從理論上來講,北約成員國中有三個核大國,英國、法國和美國。它們甚至在非洲部署了核武器,但這僅僅是儀式性的。如果俄羅斯真的向歐洲大陸發射核導彈,美國也將在北約採取行動之前作出反應。這是因為北約的程序十分繁瑣。
北約必須「一致同意」並向華盛頓索取核代碼後才能發射核武器。比利時、德國、意大利和荷蘭操作和維護自己的核武器,但是這些武器在沒有美國總統許可的情況下都無法使用。只有擁有自己核武器的法國和英國,才有能力在不諮詢白宮的情況下動用核武器。不談經濟,軍事上北約已經完成了第一任秘書長黑斯廷斯·伊斯梅為其設定的使命:「趕走俄國,拉攏美國,壓倒德國」。
也就是說,在實踐中北約更應該被視為一種政治安排。這種安排保證了美國在歐洲問題的決策中處於首要地位。儘管如此,北約也絕不僅僅是一個軍事聯盟,它還是一種文化。或者用北約第三任總司令阿爾弗雷德·格魯恩特的話來說,「北約是一種思維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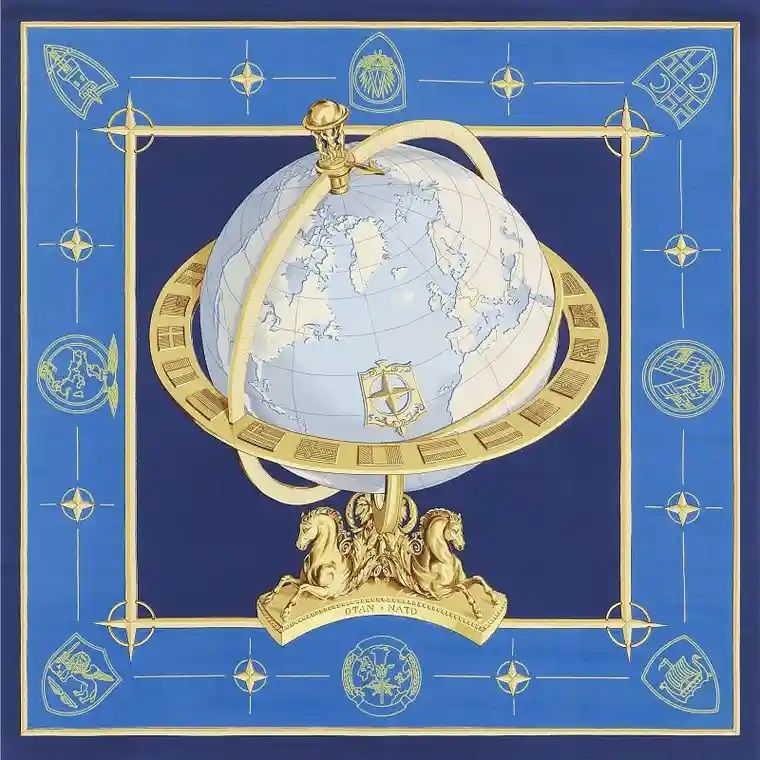
從為北約僱員子女開設的北約學校、教授北約軍事課程的北約國防學院、穿越德國的北約地下燃料管道、比利時的北約高爾夫俱樂部到展出了大量古希臘雕像的北約博物館;甚至北約助學金、北約講席、北約愛馬仕圍巾乃至北約歌曲、北約民謠和北約讚美詩,歐洲大陸到處都是北約的痕跡。
不斷敲響的喪鐘
自1949年誕生以來,北約的喪鐘已敲響多次。 1974年,北約成員國希臘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發生了激烈衝突;2011年北約干預利比亞以後,土耳其又和意大利支持的民兵以及法國支持的利比亞軍隊作戰。 2018年,土耳其在敘利亞圍攻美國和西歐的庫爾德盟友後,北歐的「團結」再度受到打擊,馬克龍更直指北約已經「腦死亡」。川普也不喜歡北約,儘管他任內美國在歐洲的支出和部隊人數都增加了,他卻對北約的目的和共同防衛條款嗤之以鼻。

實際上,從一開始,北約的前途就不被看好。二戰結束時,羅斯福預計美國和蘇聯軍隊在兩年之內就會離開歐洲。但西歐的政治家們卻更想由美國在他們重建經濟的時候提供安全保障。
這種保障有許多種實踐方法。美國戰略學家喬治·凱南提出了「啞鈴」方案,讓西歐和美國與加拿大各自擁有自己的防衛系統,在不大可能發生的蘇聯入侵時提供互相援助。著名的自由主義記者沃爾特·李普曼則認為,在一個核武器讓常規部隊不再重要的世界裡,美國在歐洲駐軍毫無意義。
但是對歐內斯特·貝文(譯註:時任英國外交大臣)和迪恩·艾奇遜(譯註:時任美國國務卿)這樣的反共主義者來說,剛剛戰勝納粹的紅軍不僅是歐洲大陸最強的力量,在西歐國內也極具人氣。所以,貝文主導成立了所謂的西方聯盟。
這個基於法國和英國簽訂的敦刻爾克條約組成的聯盟後來擴展到盧森堡、荷蘭和比利時。當該組織要求美國提供具有約束力的安全保證時,美國外交官搶占了主導權,並藉此發展出了北約。當時,北約的成員國祇有12個。關於是否將意大利等國納入北約成為了爭論焦點。凱南認為向南歐擴展成員國為無限擴張奠定了基礎,因此是對蘇聯的「微弱的挑釁」。
無論如何,從一開始北約就不受民眾的歡迎。杜魯門不能冒險在總統競選中向已經厭倦戰爭的美國人提及這個計劃。法國共產黨和法蘭西民族主義者聯合抗議法國於1949年加入北約。意大利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北約示威。而冰島戰後最大規模的示威也發生在它宣布自己將加入北約時。

二戰後的第一個十年對北約來說是動盪不安的。隨著歐洲經濟的全面復甦,美國的安全保障看起來更不值錢了,而杜魯門的朝鮮戰爭又讓美國看起來如此好戰。因此,西歐領導人制定了歐洲防務共同體計劃。只是英國將聯合部隊視為對其國家主權的威脅,而法國則更擔心德國的複興,這個計劃在各懷鬼胎的背景下胎死腹中。
當蘇伊士運河危機發生時,北約在想要堅守殖民地的成員國和爭取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者青睞的美國之間搖擺不定。一方面,北約加速了大英帝國的衰落,但同時北約也擔心英國的撤離會帶來中東的影響力真空,因此北約試圖成立中東條約組織來填補這一空缺,當然這種嘗試最後失敗了。
對美國來說,龐大的國防預算成了充分就業的工具,因此很快成了美國生活的一部分。二戰結束以後,美國仍然沉浸在這種永久的戰爭狀態之中。最鮮活的例子就是美國每一任總統都承諾從歐洲裁軍,但這些承諾永遠都無疾而終。而對西歐國家來說,因為北約而節省下來的經費,讓他們有機會建立一個福利國家來安撫越來越激進的勞工運動。一開始北約或許只是權宜之計,但很快它就變成了歐洲穩定的基石。
這種穩定從來沒有被打破過。
六十年代是北約的緊急時刻。戴高樂多年以來對北約一直興趣不佳。 1963年,他說,「北約是假的。由於北約,歐洲才被迫依賴著美國。」三年後,他宣布法國將從北約中撤出。當然,事實上法國仍然是北約成員,甚至繼續參加了北約的演習和技術共享。
戴高樂的決定部分源於他對法國大國地位的預設,但也出自於他始終將俄羅斯視為歐洲的一部分的夢想。對他來說,冷戰總有一天會結束,而北約則是美國蓄意阻止這一切發生以便維持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工具。儘管法國的宣稱帶來了大量北約的訃告,爭取獨立於美國的努力卻總是讓西歐國家更緊密地融入北約之中。 1955年,美國將西德拉入北約,蘇聯對此的回應是成立華沙條約組織。

在這些年裡,反對北約也是西歐左翼的重要目標。他們不僅將北約視為核戰爭的製度化形式,更重要的是,北約被視為美國和歐洲統治者的階級聯盟,被統治者用來剷除國內的反對派。事實可能不是如此,但也相距不遠。只要成員國是「反共」的,北約並不如它所宣稱的那樣關心成員國是不是真的民主。 1949年,薩拉查獨裁統治下的葡萄牙就加入了北約。 1967年,當法西斯的希臘軍隊推翻民選政府時,北歐成員國一度要求北約考慮按照憲章驅逐希臘。但這一建議從未被北約認真考慮過。
但北約真正的生存危機出現在1990年代。當北約的對手蘇聯解體時,即使北約官員也不清楚它的未來是什麼。除了幫助清理蘇聯的核武器外,如歐盟一樣的新組織提供了一個比美國相比更一致更自主的歐洲的未來。甚至蘇聯解體前,密特朗就在1989年提出了將美國排斥在外卻聯合了蘇聯的歐洲聯盟計劃。
1990年代的政治家和觀察家都認為,完成使命的北約將關門大吉。 1989年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對美國國務卿說,「讓我們解散北約和華約」。同年,捷克領導人哈維爾則告訴喬治·H·W·布什,他預計美國和蘇聯軍隊將很快離開中歐。隨著蘇聯解體和美國撤軍,歐洲人是時候將自己的安全重新掌握在自己手裡了。
甚至美國的戰略家也贊同這一看法。美國最重要的國際關係理論家之一的約翰·米爾斯海默在1990年的《大西洋月刊》上寫道,「蘇聯的威脅提供了將北約團結在一起的粘合劑。在這種進攻性的威脅消除後,美國很有可能放棄這塊大陸。」
北約的官僚在這一時期製造了大量的驚慌失措的立場文件,討論延長北約壽命的方法。然而,事實證明,北約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活躍。北約的領導者開始高喊,「北約必須走出去,否則就會倒閉。」短短幾年內,從一個防禦性的組織變成了肆無忌憚的軍事同盟,從一個地緣政治上保守的現狀維護者變成了東歐變革的推動者。
新時代的擴張
對喬治·H·W·布什政府來說,北約面臨的新挑戰並非是新生的俄羅斯,反而是一個統一的歐洲。洩露的1992年國家安全委員會備忘錄草案指出,「我們必須設法防止出現會使得北約僅包括歐洲的政治安排」。草案對北約的擴張持謹慎態度。但事實上,在戈爾巴喬夫的抗議下,統一的德國成為北約成員國。不久之後,北約開始訓練烏克蘭軍隊。當克林頓上台後,連這種謹慎的言辭也消失了,俄羅斯的勢力範圍變得越來越支離破碎。

某種意義上,克林頓本該成為解散北約的最佳人選,畢竟1992年他在競選中大肆宣傳縮減北約並用更新的聯合國軍來代替它的作用。的確,最初他也對北約東擴持懷疑態度。不過,最終於1999年,波蘭、匈牙利和捷克開始了加入北約的進程。
對克林頓來說,改變想法的理由並不復雜。東歐國家比他更渴望北約東擴,為此他們花了大量精力向美國施壓。波蘭領導人瓦文薩1993年說,加入北約「能讓俄羅斯軍隊感到不安,因此他們不會發動核戰爭」。除此之外,加入北約也是讓波蘭成為富裕西方國家的第一步。這種態度又使得克林頓不得不考慮到美國銹帶大量東歐移民的選票,對克林頓來說,這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最後一個原因則是90年代國際社會的變化。美國的權力在蘇聯垮台後如日中天,許多之前的北約批評者在冷戰後都轉而把它視為人道主義干預的唯一武器。 1995年,曾經為西班牙社會黨撰寫《拒絕北約的50個理由》的哈維爾·索拉納成為了北約的秘書長。而他此前甚至上過美國的黑名單。
1995年對波黑的轟炸以及1999年對科索沃的空襲不僅繞過了聯合國安理會,更證明了歐盟,特別是德國,沒有能力解決其周邊地區的安全危機,奠定了北約在冷戰後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同時,這更是一種武力展示,可以說這種武力展示比北約東擴本身對俄羅斯的震撼更大:空襲展示了現代戰爭對技術的依賴、不需要美軍地面部隊的軍事行動以及北約的干預措施帶來的與美國結盟的期待。最後一點在科索沃那裡尤為明顯,直到現在仍有許多科索沃人以克林頓和布什為他們的孩子命名。
克林頓對這種擴張的信心來自於他對資本與市場的信心。克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在1993年宣稱,「我們將重建北約,讓擴大的市場民主背後有著堅強集體安全支持」。這種情況下,北約開始扮演評級機構的角色。它的東擴讓東歐部分地區變成了外資投資的安全區。對美國人來說,這實在難以抗拒。因為這種把北約變成市場民主與地緣政治利益結合的混合物是美國人心目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完美結合。

到二十世紀末,只有一群熱心的遺老還在反對北約擴張。早前對北約擴張抱有懷疑態度的人,最終都成了北約擴張的信徒。喬·拜登就是典型的案例。同樣的,反對克林頓國內政策的共和黨們在這一問題上更勝克林頓一籌,甚至嫌克林頓的動作仍然太慢。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烏克蘭已經投入了北約的懷抱。它在1990年代成為了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第三大資金接受國。在俄羅斯入侵之前,它已收到超過30億美元。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烏克蘭面對俄羅斯的入侵仍能頑強抵抗,畢竟大部分的烏克蘭軍隊都由北約所訓練。
到喬治·W·布什上台的時候,北約仍然沐浴在巴爾幹戰爭帶來的榮光之中。 911之後,布什政府援引集體防衛條款,把全球反恐納入其戰略目標,並因此對俄羅斯和其他地區以反恐為名而進行的各種行徑視而不見。但比起克林頓,儘管他們都相信美國必然勝利,但布什顯然激進得多,他要擺脫北約的偽裝。
既然美國是北約唯一重要的力量,而人類已經進入單極的世界秩序,那麼來自布魯塞爾的附庸們還有什麼意義呢。因此,布什的伊拉克戰爭在法國和德國這些北約成員國的批評聲中開始了。顯然,布什認為這些國家的實際力量無關緊要。
在布什任內,你要么支持美國,要么反對美國。很明顯,東歐人都支持美國。因此,布什希望他們得到獎勵。在法國和德國的警告下,布什毫不理會俄羅斯關於承諾不讓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要求。隨著東歐與華盛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東歐的民族主義者們比起西歐國家吹噓的後民族主義顯然更適應美國式的民族主義,而美國則藉此把他們作為介入歐盟爭端的可靠盟友。
沒有別的選擇
今天,對美國的許多鷹派來說,如果北約要繼續存在,那麼俄羅斯就必須扮演一個北約門口的野蠻人角色。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個強大、自由、民主的俄羅斯將比一個專制、民族主義但軟弱的俄羅斯對美國在歐洲的霸權傷害更大。因此,美國不停地向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強調,不值得與一個不可救藥的國家重建關係。
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十分珍視他們擺脫俄羅斯得來的來之不易的主權。鑑於英國因接納俄羅斯寡頭而幾乎把倫敦變成倫敦格勒、德國消耗著俄羅斯的石油而法國又向來把俄羅斯視為潛在的戰略夥伴,在美國和歐盟的選邊站中,美國贏得毫無懸念。因此,美國在北約中最堅定的盟友是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
而更廣泛的歐洲卻並不這樣認為。人們一直期望歐洲遠離美國的保護,其中許多人至少在理論上歡迎一個更強大的歐洲的願景。 2018年,德國左翼政治家漢斯·馬格努斯·恩岑貝格把北約描述為一個成員國定期為美國的戰爭獻祭士兵的朝貢體系,他的法國同行雷吉斯·德布雷則呼應戴高樂的說法,稱「北約只不過是確認美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對西歐統治地位的一種安排」。川普的勝選讓默克爾呼籲,歐洲可能有一天必須照顧自己的安全。多年來,歐洲一直在談論「歐洲安全與防務」的新計劃,它建立在北約的基礎上,模糊不清卻又令人著迷。
但諷刺的是,歐洲防衛自主將有可能帶來別的麻煩。如果歐盟在如今的情況下變得更加軍事化,不難想像最後的結局只會是一支有能力的歐盟軍隊執行著複雜的遣返制度並迫使非洲和亞洲變成歐洲資源的來源與垃圾的去處。最後,「歐洲堡壘」將更穩定地變成仇外的新自由主義先鋒。
更重要的是,北約和現實一直破壞著這種願景。 2010年,荷蘭政府就因公眾拒絕北約對阿富汗的戰爭而垮台。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則直接打斷了這種走向自治的步伐。戰爭前所未有地展示出北約在歐洲大陸上根深蒂固的存在。德國外長已經斷言,「如果歐洲戰略自主的想法助長了一種幻想,即我們可以在沒有北約和沒有美國的情況下保證歐洲的安全、穩定和繁榮,那就太過荒唐。」
在未來的幾年裡,北約的力量將會增加。至於歐洲增加的防務開支,與華盛頓的防務開支相比仍然微不足道,這意味著從廣袤的薩赫勒地區到第聶伯河畔依然處在美國的看守下,可供迴旋的餘地將越來越小。
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在1978年寫道,「北約主義是一種包裹在空洞的意識形態中的病態,它只知道自己在反對什麼。」但當他寫下這句話時,廢除北約仍然不是一種陳詞濫調甚至惹人厭煩的主張。 1983年,北約在西德部署導彈的嘗試仍能喚起戰後德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北約的核武器仍然被視為一種危險的賭博。
但是,今天北約在利比亞和阿富汗的失敗且危險的戰爭得到的反對越來越少。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則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北約的聲譽,讓更多人不再懷疑北約對烏克蘭保衛其主權獨立的有效性。這帶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當北約對西方自由的限制和全世界人民的威脅打過它對兩者的保障時,它還是否能成為冷戰時它所扮演的「穩定器」的角色?
在這個從未如此需要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的時刻,俄羅斯的入侵似乎幫北約消滅了這種可能。北約再度回到舞台的中心,但它只能揮舞著舊日的旗幟,上面寫著「沒有別的選擇」。
(責任編輯:新不萊梅)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