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痛批張文宏,問題在哪裡?

對輿情稍有留意的人大概都注意到了,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在自己公眾號“饒議科學”上再三發文,連日來痛批傳染病專家張文宏,可謂火力全開。
他為什麼要罵張文宏?導火索是12月17日張文宏在2022年中美臨床微生物學與感染病學高端論壇上表態:“我們即將走出這次疫情已成定局,這個趨勢不會再逆轉。”
這番話可能讓普通人感到安心,但在饒毅看來,這是“不負責任的言論”,甚至“純係謠言”,因為“今天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斷定疫情走向,沒有一個人可以排除疫情永遠伴隨人類、一年三次、每次輕重沒有規律地搖擺”。
他奚落這是“科學不足,又不肯承認,而經常說錯話”,“個人的科學訓練和科學前沿敏感性不夠而不知道”。

兩天后,他更進一步將打擊面擴大到了張文宏的支持者們,影射、挖苦張文宏缺乏專業水準,所說的話只不過是為公眾提供了“一出幾年不衰的心理按摩活報劇”,而他的支持者“力圖將一位心理按摩者捧為神仙”,是“為造神而踐踏原則、犧牲科學的偽君子”。
饒毅這一輪的猛攻,讓許多人深感詫異乃至震驚,雖然學術觀點的分歧是常有的事,但為何出以這樣大字報風格的人身攻擊,實在讓人看不懂,以至於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不是“饒毅說得對嗎”,而是“饒毅為什麼要這麼做”,甚至是“饒毅怎麼變成這樣了?”
他為何如此反感張文宏? 張明揚認為,這本質上是派系爭鬥:“就科學談科學,就醫學談醫學,饒毅無疑是一名高水平,有預見性的科學家”,但他多次主張封控,“一直偽裝自己沒有既定立場,將自己的防控偏好'隱藏'在對'科學態度'的反复宣示中”,實際上是個“隱蔽的防疫愛好者”。
張文宏當然並不完美,並非批評不得,但有人發現,張文宏曾說了一些和主流專家“很不一致的觀點”,但饒毅的批評是有選擇性的,“很少去批評深受權力寵愛的學閥權力”。換言之,批評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有失公允,“張文宏的成績你也要看到啊,何況,你也罵罵別人呢?”
這是中國社會旁觀糾紛時常見的態度,尤其容易激發人們對弱者的同情——罵得太狠,“連我看不下去了”,言下之意,“雖然張文宏可能有毛病,但你罵的時候態度好一點啊!”
另一種頗具代表性的反應更為中立,強調的是公共討論中應遵守基本的規則,就像押沙龍所謙稱的那樣,“我判斷不出關於饒毅張文宏他們的是非對錯,只是單純不喜歡這樣的罵街而已”。
也就是說,科學家好歹是“有身份的人”,至少在觀點交流時應當紳士一點,饒毅看起來是“失態”了。更進一步說,不論觀點如何,都應對事不對人,不必上升到人身攻擊,對錯沒那麼重要,應當允許不同的觀點並存、交流,並尊重人們的自由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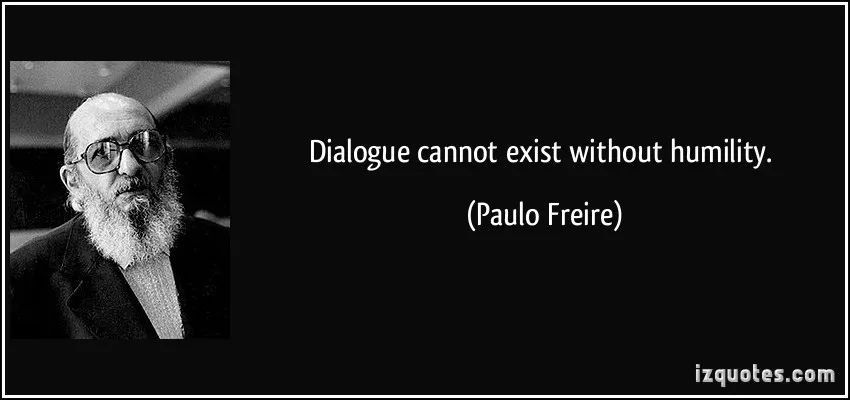
這些說法各有道理,但能說服饒毅及其支持者嗎?我想是不能的。
爭論中講規則的前提是“所有觀點都是平等的”,但對另一些人來說恰恰相反。林肯在面對南北戰爭的爭論時曾對人慨嘆:“你已經活了這麼久,難道還不知道,對於同一個問題,兩個人可以有完全不同但都正確的答案嗎?”他這話肯定讓許多人為之駭異,尤其我們中國人早就習慣了,每個問題都僅有唯一一個正確答案。
何況,就算政治、社會的問題有不同答案,但科學問題難道也這樣?既然真理是唯一的,那麼任何與之不一致的觀點,就只能是錯誤、低劣乃至邪惡了。
這樣一來,什麼禮貌、規則就統統不是問題了,“態度好一點”不過是和稀泥,畢竟,對待錯誤的異端有什麼好客氣的?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對秉持錯誤觀點的人心慈手軟,只能意味著自己信念不堅定,還有動搖。就像中世紀的信徒對魔鬼、女巫的憎惡,在他們看來這完全不過分,黑的就是黑的,不然還要承認“魔鬼也有優點”?
在這種情況下,對手的妥協退讓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再怎麼樣都是錯的。饒毅三年來不止一次批張文宏,但張文宏似乎從未回應過,有些人認為僅此就可見張文宏的態度更可取,然而在饒毅的支持者看來,這只不過是他啞口無言罷了,甚至更可惡——以退為進來博取不明真相的公眾同情。
事實上,不回應不過是“拒絕服從”的委婉表現,而在權威主義倫理學中,服從才是最大的善。只有一種行為能讓你的過錯得到寬恕,那就是真誠認罪,承認自己的錯誤,一如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弗洛姆在《為自己的人》中所說的:“即使一個人犯了罪,只要他接受懲罰並感到有罪,就會使他變善,因為這樣,他就是承認了權威的優越性。”
對這樣的心態,我再熟悉不過了,因為多年來,我在公共討論中被無數人罵過。雖然我基本從不回罵,有些人讚為“辯風真好”,但另一些人則嗤之以鼻,理由很簡單:你態度再好,也不能讓你錯誤的觀點變正確。最後的結果,是我在豆瓣上落下這樣的名聲:“維舟是好人,只是腦子不清楚。”
這就是關鍵所在:對這些自信找到了真理的人來說,寬容是不必要的,觀點的正確與否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那麼,哪種觀點才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呢?不好意思,恰好就是他本人所持有的那種。

這遠不只是饒毅的問題。龔鵬程在《近代思潮與人物》中指出,“把批判對象視為惡,以自己代表善與正義”,乃是“近代知識分子權威人格的根源”。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蔣介石1927年說過的一句名言:“我就是革命,誰反對我,誰就是反革命。”
社會學研究也證實,在1960年代的城市中學裡,“權威人格”是孩子們身上居支配地位的社會性格。對權威的順從,和對異己群體的攻擊,乃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因為他們不僅自信站在正確的一邊,往往還抱有一種糾正“錯誤”的強烈使命感,為此,任何激烈的手段都是允許的。
很多人都說,饒毅可是科學家啊,他自己不也一直強調要講科學?我的感覺是:饒毅對科學的理解是古典式的,那是一個聖殿,其中智者就像祭司,高踞在等級制的頂端,掌握著至高的權威,他說的話就是神諭。 19世紀的圣西門主義就是這樣,每個人都處於絕對完美的秩序之中,沒有給自由地犯錯留下任何餘地。根據這種特殊的理解,“科學”乃是少數知識精英壟斷的真理。
我不認識饒毅,但如果那些檄文確實是他本人寫的,那麼這就是文本所透露出的人格特質。當然,權威人格也不過是一種分類,我在意的也不是抨擊饒毅,而是試圖理解這種社會性格的普遍性,進而為當下的輿論提供一種解釋:為什麼饒毅們如此痛恨張文宏?又為何這麼激烈?
答案或許是:在饒毅們看來,張文宏是假權威,是偽神,竊取了他們所看護的真理聖杯,這是最不可容忍的。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饒毅一直盯著張文宏的“資格”不放,用他的話說,“絕大多數醫生不是科學家,這是常識”,言下之意,科學家才掌握終極真理,而他本人當然是——張文宏講的那些大白話,都是老百姓聽了高興的“心理按摩”,算什麼學術成就?
饒毅曾被廣泛視為具有理想主義的科學家,也因此,這次很多人驚訝他的表現,但對他來說,這恐怕並不矛盾。或許正是他在學術上的追求,使他更難容忍在他看來“不正確”的觀點,助長了他對權威的認同,而這也與國內長久以來“專家治國”的理念契合——任何領域都離不開權威,能一錘定音地給出唯一正確的答案,而在他看來,張文宏沒有這樣的資格。
因此,談什麼不同觀點、態度、規則,都無法從根本上駁倒他,那麼他這麼想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我想是,他對“科學”和“專業”的界定都太狹隘了。他可能太沉浸在自己所擅長的神經分子生物學領域,而用學術前沿、論文水平等科研標尺來衡量張文宏,就覺得他處處顯得“科學不足”,不過是個“網紅”罷了。很多人都不自覺地有這樣的問題,我一位朋友曾將廣受好評的散文家批得一無是處,我後來才意識到,她其實是用學術論文作為參照係來要求散文。
當張文宏判斷“走出疫情已成定局”時,指的其實是這一輪高峰過後,我們終於可以告別三年來的防疫局面,生活逐步回歸正常。這是公共衛生的視角,也是普通人能理解的話語。然而,饒毅說“沒有一個人可以排除疫情永遠伴隨人類、一年三次、每次輕重沒有規律地搖擺”時,所著眼的其實是病毒學的視角,渾然不顧張文宏再三說過“人類不可能消滅病毒”(那就意味著它隨時可能重新出現)。視角的差異,使得他恐怕曲解對方都不自知。
他以病毒為中心,但忘記了在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中,我們更要關心人的處境。在這裡,他所遵循的是19世紀末出現的細菌理論範式,認為健康狀況只是微生物層面的問題,然而,現在醫學(尤其是公共醫學)早已進入生物-心理-社會範式,需要全社會改變認知模式,協調各種資源,才能應對這一重大挑戰。
饒毅看不起張文宏的學術能力、專業水準,就分子生物學的科研成就來衡量,這應無疑義,但如果從全新的範式來看,那麼他所蔑視的“網紅”和“心理按摩者”張文宏,在改變社會認知等方面,不誇張地說居功至偉,比他本人起到的作用大多了。承認這一點沒什麼不好意思的。
如果說饒毅傲慢,那麼他就傲慢在這裡。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