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輝煌的美國汽車工業,為何一蹶不振?

作者|陶孟元
今年3月,新任美國總統拜登宣布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並將電動車等新製造業作為支持重點。拜登把這一計劃稱之為“二戰以來對美國就業的最大單筆投資”,期待它可以提振遭疫情重創的美國經濟。與此同時,拜登和哈里斯會見了美國的大型汽車製造商、汽配公司和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 Union,簡稱UAW)代表。勞資雙方的代表共同敦促拜登支持“全面”的電動車計劃,包括提供稅收優惠和購車補貼等。此舉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美國汽車工業在新一輪能源革命中拔得頭籌,我們不得而知。
然而,美國汽車工業早已不復當年勇,卻是不爭的事實。如雷貫耳的美國汽車資本三巨頭——通用汽車(GM)、福特和克萊斯勒,誕生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經過20世紀上半葉的發展,三巨頭在1962年達到巔峰:當時的通用汽車佔據了美國汽車市場一半的份額,三巨頭加起來更是達到了驚人的87%。但是,在之後的50年,三巨頭便由盛轉衰,其市場份額不斷下降。 2008年金融危機後,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更是靠奧巴馬政府的輸血才逃過破產的厄運。 2019年,通用汽車只佔據了美國國內市場份額的17%,三巨頭加起來也不過是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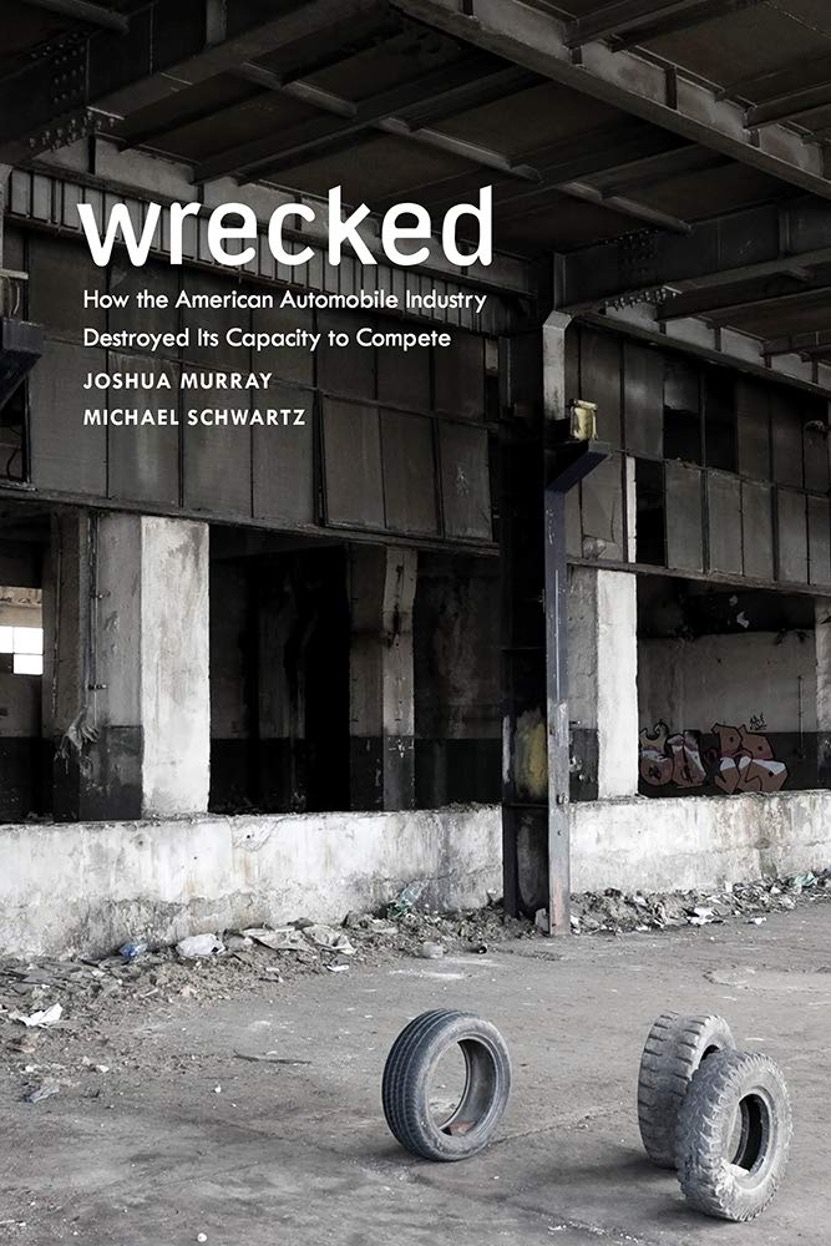
那麼,這50多年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能讓看起來這麼“結實”的三巨頭變成“弱雞”?如果說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的信貸收緊只是它們瀕臨垮塌的導火索,那真正的“炸藥包”又是什麼? 2019年,美國社會學家Joshua Murray和Michael Schwartz的著作《毀滅:美國汽車工業怎麼摧毀了自己的競爭力》(Wrecked: How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Destroyed its Capacity to Compete,以下簡稱《毀滅》)問世,為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
討論美國汽車工業成敗興衰的著作很多,尤其是在商業和經管領域。然而,《毀滅》不同意主流輿論常見的三種解釋,轉而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探討這段歷史。最終,兩位作者得出結論: “作死”美國汽車工業不是別人,正是三巨頭資本家自己。
對三種常見看法的反駁
作者首先回顧了以往三種針對美國汽車工業不斷衰頹,尤其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被日本車企赶超的解釋。
第一種理論是產品生命週期論。這種理論認為,每一個產業都有其生老病死的階段,這是由市場的力量塑造的生命週期。當產業的技術升級跟不上市場需求,生產難以擴張,資本就會主動減少人力支出、尋求廉價勞動力以節約成本,增強競爭力。表面上看,這個理論對美國汽車工業的衰落很有解釋力:最早的汽車產品問世後(初生期),在大蕭條時期技術得到長足進步(創新期),隨後是二戰後標準化生產的成熟以及美國汽車生產在國內外的擴張(成熟期)。最終,日產汽車利用廉價勞動力進軍美國市場,擊敗美國汽車工業(衰退期)。這是產業的命,我們得認命。
作者認為,這個理論不符合他們對各國汽車工業的觀察。第一,日本和歐洲的車企生產歷史比美國更長,但也不見它們像美國一樣或者更早步入衰頹的階段。而且,美國汽車產業是在全球擴張生產之後,才出現創新衰頹,而不是反過來。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於,日本汽車產業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它們的生產技術和流程創新,而不只是來自廉價勞動力。這一點其實也是絕大多數商業分析的共識。
那為什麼日本汽車企業有這麼強的創新能力呢?我們又看到了兩種常見的解釋:美日汽車工業不同的管理文化和工人文化。
持管理文化論者認為,日本車企的成功是因為日本傳統宗族、禪文化和日本傳統書畫藝術影響,因此日本汽車工業的管理層非常謙卑、非常重視細節,也非常願意承受創新帶來的風險。相反,美國汽車產業厭惡風險、管理文化非常傲慢、對細節不重視。所以日本/美國車企的創新/不創新是不可避免的,都是根植於其文化中的。然而,作者認為,汽車工業創新與否,是由生產系統的結構性決定的,管理文化只是對這些物質條件的一個回應。
而美日兩國車企的生產結構是由階級鬥爭、當時當地的事件和歷史路徑依賴決定的。日本車企創新的關鍵是靈活生產系統,這套系統其實是從美國二戰前類似的生產系統學來的。美國汽車產業用這套系統的時候,美國的分析師認為美國汽車工業很創新、很願意承擔風險。後來美國汽車工業棄用這套系統後,創新減少,各種“管理文化”論也來了。
除了管理文化論,工人文化論在主流輿論中也很有市場,尤其深得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歡心,是抹黑工人運動的常見話術。這種理論認為,美國汽車產業衰落,都是因為美國汽車產業以UAW為首的工會太強大了。工會通過和資方談判,使得工人工作只達到合同的最低標準,卻不斷要求更高的工資和福利,這些因素都阻礙了美國汽車工業創新。而且,因為這些又貪婪又懶惰的工人,所以美國車企在面對擁有更廉價勞動力的日本和歐洲車企時沒有競爭力,因此美國車企的市場份額從1960年代開始落於下風,最終奄奄一息。
作者也不同意這個說法:以1981年的通用汽車和馬自達美國工廠對比為例,通用汽車超過一半生產線在墨西哥等非工會廉價勞力地帶,時薪拿的是“高”工資的美國工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因此它的勞動力成本遠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高。而馬自達相比通用節約的生產成本,只有四分之一是來自更低勞動力時薪,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來自靈活生產:日企工人的勞動時間更少、零部件的成本更低、庫存更少、運輸費用也更低。因此,即使有了高昂的關稅,日本車企還是能以更低的價格賣出質量更好的汽車。

靈活生產系統:日本汽車工業打敗美國同行的關鍵
那麼,在兩位作者看來,是什麼造成了美日兩國車企競爭力的分野呢?答案是:不同的生產結構。美國汽車工業為了壓制勞工的力量,因此選擇了和日本汽車工業不同的生產結構,最終把自己活活作死。
兩位作者總結,日本車企(以及一些歐洲車企)採用了靈活生產系統。這種系統的特點是地理上的集中生產、機器靈活、長期單一供應商以及零庫存/及時交貨。這個系統能夠保證產品設計和生產的持續創新,實現生產和組裝的協作,以及增加工人的生產效率。美國車企則相反,它們採用了僵硬的大規模生產系統。這種系統的特點是地理上分散生產、零部件和機器都是固定的,以及大庫存,結果是阻礙創新,降低生產效率。
那麼,為什麼靈活生產系統會提高生產效率,促進創新呢?在進一步討論美日車企的選擇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靈活生產的四大要素及其意義:
- 零庫存/及時交貨(just-in-time delivery)。這是指上游和下游供應商同時開工,使得零部件可以在不需要庫存的條件下及時到位。如果整個鏈條順暢運行,車企就可以更低的成本及時試驗、調整和創新。
- 機器靈活(machine flexibility)。二戰後主流的量產方式,是一台固定作用的機器在一個環節固定待著,工人也是在工程師的安排下,在這個固定的生產流程中固定地各司其職。靈活生產系統則改裝或者代替原來的機器,使其可以在不同的作業步驟中靈活變換,車間工人也隨之靈活調整。這不僅可以改善零部件供給中的配合和調整,減少庫存,也可以增加產品的多樣性。
- 地理集中(geographic clustering)。零庫存決定了供應商和組裝廠在地理上的集中。這一集中以圈層分佈,核心層是最終的組裝廠,產出面向消費者的最終產品;中間層是一級供應商,主要生產組裝成車的零件;外層則是二級供應商,主要為一級供應商提供原材料和次級零件。由於成功的創新依賴長期、面對面的互動——包括管理層、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所以地理集中也為創新提供了便利。
- 長期單一供應商(long-term sole supplier relationships)。相對少而更集中的供應商,對於穩定品控和降低成本有利。這種關係也便於零部件創新和試錯。因此,地理距離近和互相信任在這一要素中繼續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這四個要素裡,工人的投入都是保證靈活生產順暢運行的決定性條件。因此,靈活生產系統賦予了工人較強的議價能力。一旦一兩個環節(尤其是重要環節)的工人停工,整個生產鏈條都會停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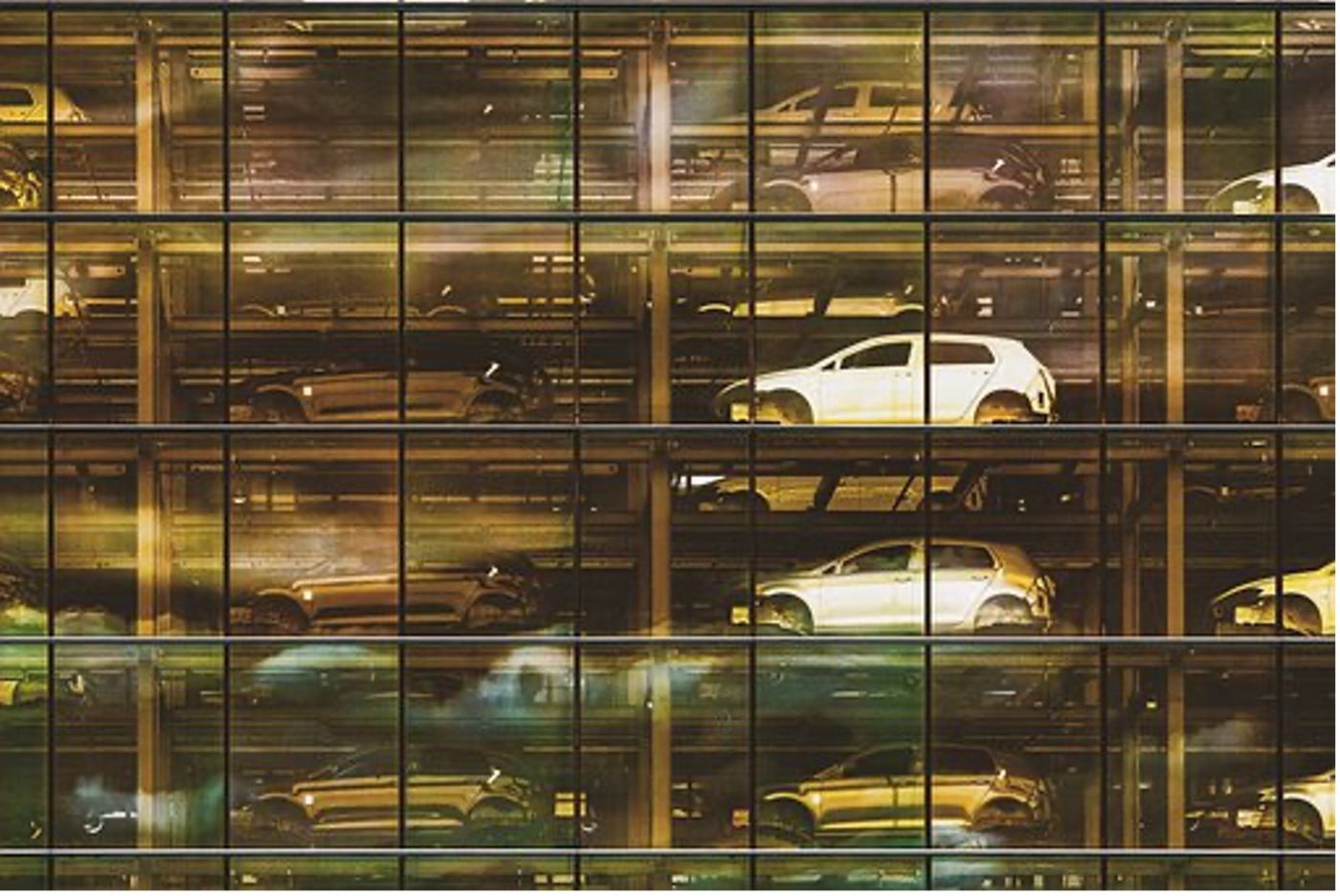
為什麼美國車企放棄靈活生產?
如果靈活生產有這麼明顯的優勢,為什麼美國車企後來會放棄呢?如果資本都憚於勞工的力量,那為什麼日本車企又願意向工人妥協呢?以及,既然後來美國車企都看到了日本車企因為採用了靈活生產而後來居上,為什麼它們還是沒有拾回這個自己原創的“殺手鐧”呢?為了回答這三個問題,作者認為,我們需要回到美日汽車工業的階級鬥爭去尋找答案。
事實上,泰羅制和靈活生產並非日本汽車工業的原創。恰恰相反,日本車企其實是從美國車企那兒學來的。一戰前,亨利·福特就採用了靈活生產系統,從而實現了持續的技術創新,降低了勞動力等生產成本。這種生產系統對工人的剝削很嚴重——不管是當時的美國還是後來的日本工人,都對勞動過程的去技能化和高強度非常不滿。
但靈活生產在地理上的集中和零庫存制度也增強了工人的議價能力。 1914年,福特工人罷工,導致福特公司癱瘓。因此,福特向工人妥協,用5美元日薪和提高的福利待遇來換取工人對惡劣勞動條件的容忍。這一做法後來也擴散到了通用汽車等行業巨頭,並演化成一種勞資之間的“社會契約”:工人接受因為技術革新帶來的失業、被迫無薪放假、降薪等後果,以換取技術革新後提升的物質激勵(如公司返聘之前因技術革新而下崗的工人,開的工資比之前更高)。當時美國汽車產業流行的口號是“同甘共苦”——雖然“同甘”時,資方拿“甘”的大頭;“共苦”時,工人吃“苦”的大頭。
到了大蕭條時期,美國經濟萬馬齊喑,車企也大規模裁員、降薪、“放假”。儘管如此,這時的勞資“契約”其實還沒破裂。 “契約”的真正破裂是在1936年:美國汽車三巨頭的利潤回到了大蕭條前的水平,但工人工資卻沒有回到相應水平。換言之,資本家忽悠了工人。因此,工人發起反抗——從數百名工人加入UAW,在廠區靜坐,逐漸演變為13.6萬名工人共同參與的弗林特大罷工。這是美國歷史上汽車工人第一次利用他們的議價能力成功實現的組織化鬥爭。四年後,美國汽車工人以組織程度高而聞名全國。
弗林特大罷工震驚了美國汽車三巨頭,它們也因此開始想辦法瓦解工人的力量。這個計劃被二戰延遲了。而且,儘管二戰期間,工會和羅斯福政府達成了“不罷工承諾”,但基層工人還是不斷發起零星的罷工,持續鬥爭。二戰後,汽車產業巨頭不願接受工會提出的加強版“社會契約”——這時的工會不只要求繼續增加工人的勞動所得,而且要求工人對生產流程的安排有一定話語權。因此,資本家希望降低工人的議價能力,增加他們發起集體行動的難度,從而“一勞永逸”。他們決定放棄靈活生產系統,轉而採用零散平行生產:分散生產,可以增加工人組織反抗的難度,減少像弗林特大罷工那樣的一廠起事、周邊數廠響應的可能性;平行生產,可以保證每個環節的生產都有替代方案,一廠停工無法“鎖喉”整個生產鏈條;大庫存,可以保證上游的停工不會馬上影響下游的生產。這個系統確實有效隔絕了罷工,但也隔絕了靈活和創新。最終,美國汽車三巨頭在日本汽車湧入美國市場後便完全敗下陣來,從此一蹶不振。即使眼看著日本汽車工業靠靈活生產發家,自己也無能為力,因為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僵硬和惰性已經積重難返。
那為什麼日本汽車工業沒有發生類似的情況呢?作者也是從日本汽車工業的階級鬥爭史中尋找答案。和20世紀初福特的罷工不同,最早採用靈活生產系統的豐田經歷過有組織、有力量的工會運動。這些工會主要由日本左翼力量組織,從1950年到1953年發動了數次大規模的豐田工人罷工。但是,1954年,親資方工會擊敗了左翼工會,從此開啟了日本汽車工業資方工會系統的歷史,也開啟了日本汽車資本和工人的“社會契約”——資本為工人提供高工資、終身僱傭和高福利。日本工人之所以會接受這個妥協,一方面確實是因為1954年的失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戰後日本工業的騰飛提供了物質基礎、日本工人長期忍受低工資和惡劣勞動狀況的歷史,加上資本對於工人未來的晉升和技能提升的承諾,日本工人也沒有經歷過像1936年美國資本家“背信棄義”的情況。所以,豐田工人接受了資本的妥協,資本也因此得以繼續採用靈活生產系統。作者認為,同樣內容的“社會契約”,如果發生在別的時間、別的地點,可能結果也不一樣。

思考和總結
《毀滅》運用唯物主義的觀點,通過紮實的歷史研究,以美國汽車工業為例,將資本和勞動這一個矛盾的兩面搞清楚,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闡述階級鬥爭,從而有力地回擊了主流輿論中對美國汽車工業衰落的錯誤解釋。筆者認為,這是值得我們所有輿論工作者學習的嚴謹態度和論述方法。
其次,《毀滅》從宏觀和微觀角度,為我們提供了思考工人運動的洞見。從宏觀來說,作者將美國和日本汽車產業在國內以及全球的擴張,還有美日汽車產業工人運動史一併考慮,動態地考慮工人運動在當時當地的得失。從微觀來說,作者在書中詳細回顧了美國勞工運動的不少細節,如由左翼政治力量主導的弗林特大罷工是如何組織、如何抗爭的,適合所有組織者一讀。礙於篇幅,這裡就不具體介紹了。
當然,《毀滅》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書中對美國汽車工業歷史上的勞資鬥爭複雜性闡述不夠。歷史上,UAW曾和資方達成協議,成為控制工人以及為美國民粹主義站台的工具。另外,工會領導層的保守性和基層工人鬥爭性之間的矛盾,美國工人運動和民主黨建制的矛盾,這些矛盾如何左右美國汽車工運的歷史,以及這些歷史對我們思考中國工人運動的意義在哪裡,都值得我們進一步去了解。筆者不才,只是拋磚引玉,還望各位方家指正。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