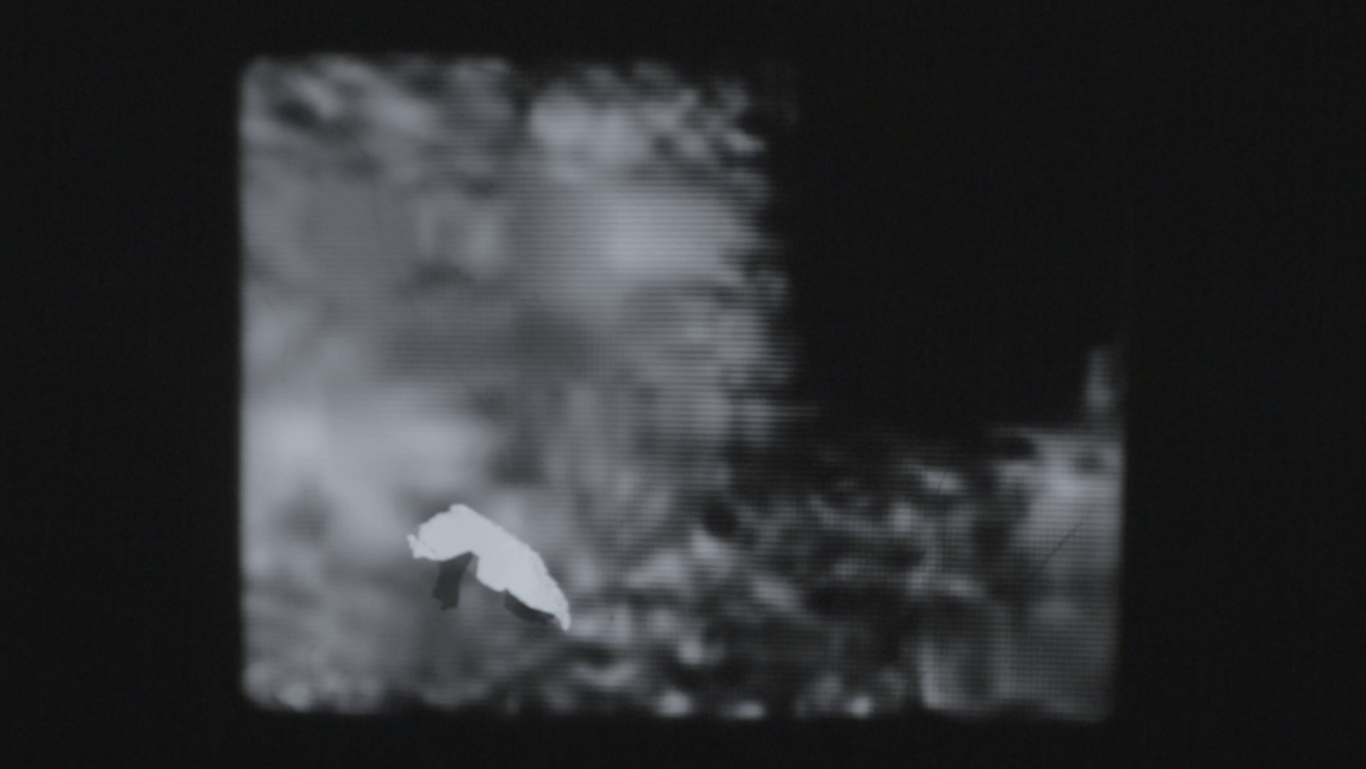總算學習恐懼
面對一張白紙,現在我倒出不知道該怎麼創作或回應。
說來諷刺,「創作」這件事很多年來我都以為是「我要做的」那回事。我或許太常把創作與工作連結在一起,也是在我為別人的創作打工後更留意,不同的人和技術為所謂作品和項目中的服務、勞動、消耗、付出。自己創作起來反而不大自然。英文也是直接的,這樣的活動都可以稱為「work」。 「職業藝術家「的稱謂及其工作方式讓我無法高攀,尤其當選擇走在不同社會縫隙之間、沒有選擇或沒能走入既有的系統或規則時,更要來回面對如何獲得收入的問題,也總要拷問自己究竟參與了什麼樣的社會?在迂迴和停滯中不斷回饋、審視,首尾觸碰後吞噬。我也還是憧憬著生產出革命的、反叛的、挑戰的、另類的、思考的作品留在人們的記憶裡——開篇就透露這樣的壯志多少讓此刻閱讀的人甚至我自己都懷疑我的創作的真誠或純粹,於是發現創作這個動作也只是常被掛在嘴上。勞動、創作、參與,這三者在我們的環境中可以如何並行?
又或許我總是在處理同樣一個問題:要如何找到讓自己自由的方式?這個問題天真了,但允許自己真正創作確為難事。總在潛水,遊走在各個空間之間。有本領穿梭在牆內外不同文化使用的社群媒體平台,卻安全地隱身在聊天框、奢望朋友圈中的讚,而暫未走入公共網路的廣場認識世界;或在網路那一頭雖知被平台掌控手中,也姑且放心Story只要在24h後消失便無事。沒有好好參與過一塊土地,沒能公開地在氣泡窗口裡留下文字。要嘛只剩整裝待發,渴望舞台上的短暫表演。在自我反思與自我禁言之間躊躇,太謹慎於不同網路世界、現實土地之間的不同規則而被這些縫隙間的道德感束縛。於是,在反覆點開、劃走、關閉matters的頁面的幾年間,不敢讀太多也沒法開始寫,以為真正抓住這個我所相信的、珍貴的地方還需要更多勇氣。或者經常把藉口留給我並不自信的中文表達,忘記了我一直相信的赤裸誠然是一種寶貴。遲來。但,今天我終於決定來重新學步,感受如何創作。與其說是終於來面對內心的羞愧,不如說是終於從躺著蜷縮的身體中爬起來。
21年初,我決定離開自15歲開始生活了11年的美國,決定面對、彌補我曾經以為錯過的關於中國的樣子。回國、回上海後的三年間,我或許是用了很多過於笨拙的方式理解周遭。以工作的名義走入了許多不同狀態中的、仍在溫水中度過每一天的人群和城鎮,以勞動(甚至用體力工作)來贖我參差視角的罪。那時候以為有本領流過需要掃場所碼的城市,拒絕戴看似無用的口罩,就是短暫地擁有自由。或許多年的錯位導致我本對周遭、鄰近的環境並不熟悉,也很難建立主動的關係。
懷抱著愧疚的同時只能以停滯的身體來回應。 22年的上海春天,我無法志願於我所居住的社區。即使對於天天相見的鄰居也只能在排隊做核酸時短暫點頭回應,最多去小區門口把整棟樓的物資帶回各家門前。我無法參與,也不願與社群連結。解封後是夏天到來之前的6月,我倒總想一個人往街上跑,走路或騎車。意識到,這是我在長大後第一次仔細看看這個城市的模樣,竟然是從每個街角的核酸亭開始的。每一次的進城就好像在多年後終於體會到了所謂電影的「虛擬」:3個月期間的朋友圈、視頻號中被不斷上傳、下載、反轉、上傳的低畫質圖片和視頻中出現過的街道、社區、大門,如今像電影片場一樣真實,卻比有限的影像多了更多圍欄,少了也曾聚集、拉扯過的高潮,聽不到了嘶聲裂肺的聲音。直到同年的冬天來臨前,第一次實在地跟所有人一起走在上海街上。如果這就是“連接”。終於,它總算將我因離開這片土地充斥著的多年的羞恥,成功地轉變為了實在的害怕和恐懼,反而有些滿足。這些恐懼總是在距離之外妄想來的,或只能努力透過感受別的地方的人的抗爭故事來體會我們體會不到的。這次不再只是躲在螢幕背後或迴避於平台之間,不過此處反觀的是當時無聲的走過、觀察,或是為了保護自身安危只敢把拍攝的手機藏在懷裡,以及批判那個並沒有吶喊、仍停滯的自己。
我當時這樣記錄了那個週末的兩天:「在十字路口或許力量最大的時刻是我們站在一起,在街對角面對面,哪怕只有幾秒鐘,最長的能有好幾分鐘。這個時刻是安靜的,我和右邊的朋友十指相扣,和左邊的朋友挽著胳膊,我們也互相望去以確定相互的溫度、心跳,安心。這樣的安靜在路口的上方似乎能凝結起強大的火團,對於好幾方之間來說是有威脅力的。雖然我們什麼都沒有做,只是看著,也被他們看著。或許也相互聽著。”
我曾經習慣的方法是使用攝影機的工作,是帶著距離的觀看、保留、聆聽、陪伴。當然,這一切發生在走過、掠奪、凝視、輕浮的看與聽之前,反思之後。我更願意相信,當我們手舉機器走近不同人的世界時,只有共同待上一段時間,這樣好像我們有在同一片時空中共同存在過,甚至記憶的記錄是讓我們將看和理解延續下去。一瞥有時候是我們能做的最多的參與,保留關懷。確實,我習慣在遊走之間停留、撿拾,得以分享、收穫交流。
而我們所獲得的流動的優勢與權力就好像我們所依賴的Virtual Private Network一樣,讓我以為我觀看了更多的人和世界。它是每日的基礎設施,讓我們得以同時生活在多重維度的網絡、文化、社會與地緣邊境之外,但也讓我們在靈活、舒適的錯覺中習慣了遮掩、潛伏、逃脫。這裡的「虛擬」是浪漫的,有時它是不可抗拒的性愛誘惑、皇帝的新衣,用看似牢固的兜底來支撐我們的僥倖。我借用這份虛擬來彌補心中對於離散的妄想,但我要如何理解每一次實實在在的發言或潛水、行動或停滯、參與或沉默?到底是為哪一塊土地?離得還遠嗎?既是幸運的,也是危險的。
It is the luck and the danger to free flow by either letting go or choosing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and act with responsibility; the luck and the danger to adopt method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without comprehensiveive underunder the lose of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without comprehensively underunder the lose of the lole of the loem and the loemr. the luck to know of the community codes and tactics of another without being able to apply to our physical communities here; the danger and the luck to cry for the greater pain afar while also shedding tears with loved ones here for the greater pain afar while also shedding tears with loved ones here; be private in order to be public; the luck and the danger of feeling both privileged and ashamed.
羞愧,這個感受是我在游泳和走動的生命經驗中殘留的最深的痕跡。這也是我這些年來一直想試圖表達的,卻又不知道怎麼說明白。也許只是自私地想讓自己感覺好受些。要主動流動,而非隱藏、躲避和僥倖。或許對於語言也是如此,在中、英文之間,而在這裡,也想感受更多簡體與繁體之間。然後,是共同存在的願望。
渴望向外拉、伸、抓、給……向前、向後、來回……我渴望在網路的連接與阻礙中終於向海底的光纖電纜吶喊。我也渴望真的做出參與、回應的活動,不再小心翼翼,而是以每一步的上傳、交換、揮手、握手、鼓掌……作為工作、作為行動。或許也不會止於表演的舞台,即使已經走在白盒子、黑盒子之外,但我今天也要真的走近每一個空間,既是私密也是公共的,讓每一次逗留、觀看、聆聽、陪伴的可能發生。在再次走出去之前。
先留在這裡。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