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秋水,一個失業部落客、喪逼青年
本文首發於「青年誌Youth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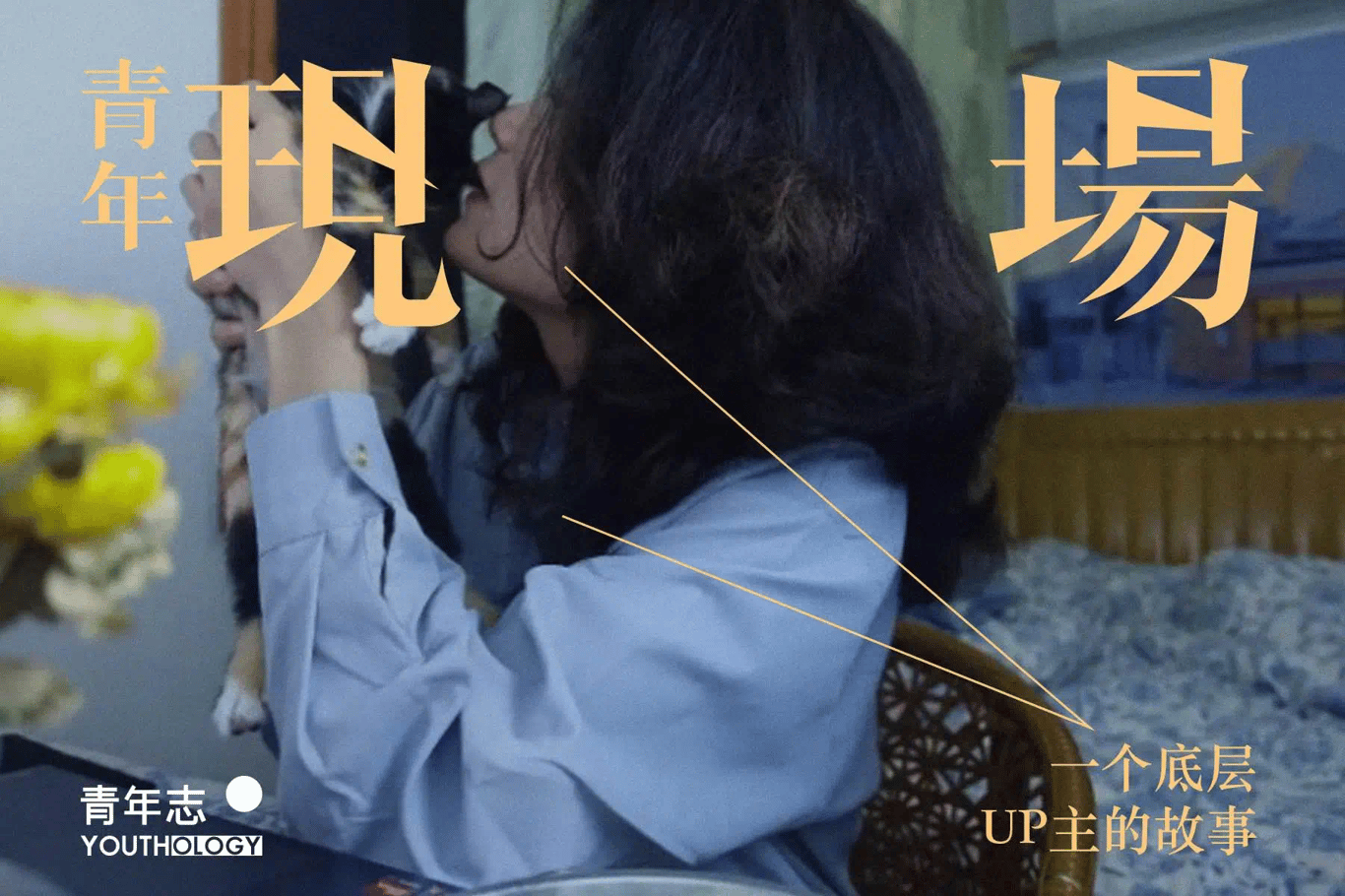
「你好哇,我是秋水」。
打開@崛起的歐巴桑的視頻,鏡頭裡她頂著一頭蓬鬆文藝捲髮,尷尬而迷人地傻笑著,說著一口藏不住湖南味道的普通話。
秋水是個普通的失業青年,在這個時代,不是那個相約在天門山自殺的青年,也不是一夜爆紅底層逆襲的青年。她夾在中間,是有點小運氣,但依然為生計發愁的芸芸眾生。
和其他部落客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秋水有些怯怯的、樂觀又頹廢,她不擁有網路部落客典型的自信健談、誇大高漲的情緒,她也不那麼耀眼。但她的怯是我熟悉的,她的自卑,她的嘴硬,她的不甘心,像極了那些在我走出縣城過程中,逐漸走散的朋友,那些初中畢業就去打工的同學,那些大專畢業就在城市漂泊的女孩。
她的故事沒有媒體需要的戲劇性,卻過於真實。打開她的視頻,她會對著你笑,間或流露出一種令人心疼的自嘲,當然也會有人說她矯情、文青、是個廢物。但我覺得她有著另一重的生命力,淡淡的。
她在無果的向上未來中,主動選擇了向下。
01
肄業大專生
失业人的日常住五百的隔断房喝两块钱一包的挂耳咖啡听资本主义爵士睡社会主义床远在故乡的外婆听了我的故事笑到模糊失業部落客、喪逼青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是秋水身上的標籤。
2021年底,她從《上班不過網咖上網》這段影片進入我的視線。影片裡,她穿著藍色外套,戴著耳機,記錄下上班瞌睡的摸魚日常——偶爾翻翻手機相冊,刷刷淘寶,扭頭看看老闆的動態,然後昏昏欲睡。
這是她第一首破百萬的視頻,觀看量遠遠超出了秋水的預期。她開玩笑式地說,或許是互聯網讓老闆看到了這條視頻,剛從失業五個月的魔咒中走出來,又在年底再次失業。

在此之前,她拍影片介紹在長沙租的500 塊錢的一間隔斷房,不到六平米的促狹空間,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書桌,廁所與床之間的距離不足一米,也放不下一個正常的衣櫃。由於沒有地方晾衣服,一個月滿後她速速搬去了另一間出租屋。
她曾在《住幾百的出租房,寫上百萬的項目》這則影片裡,和大家分享她編劇策劃的工作。
“我崩潰了”,她苦笑著。
正如影片標題所展現的激烈的反差感,她一邊談起工作是給房地產公司做上百萬的宣傳片策劃,一邊一張一張數著過年收到的紅鈔票,和微信、支付寶的餘額加起來,手頭上只剩下1480 塊。
“我想到的都是很悲傷的東西,我不知道怎麼去塑造幸福。”
她接著說:“但不工作就活不下去。”
在此之後,她開始拍攝失業青年的日常。 「開擺」「流浪」「土狗」「白嫖」「逃避」是她的影片裡最常出現的幾個詞彙。在鏡頭前,她自言自語、詼諧、自嘲,頹廢又孤獨,卻不失一點小小的浪漫。
《失業快樂》的影片裡,她用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的BGM 作為配樂,嬉皮笑臉地講述著自己被辭退的故事,同時欠著2000房租和電腦分期,工資才發了2600的悲慘故事,早已是一種渾然的發瘋狀。
愛她的人誇她文藝,厭她的人說她矯情。有人說她奇怪,但她說,「像我這樣的人,其實很多。」興許是這種喪氣的狀態照映了許多人的日常,流量開始眷顧她,非常短的時間裡,她的粉絲就快速破了六萬。
「有一部分人看我,可能是他們的狀態跟我很像,能夠在我這裡找到一種共鳴;還有一部分就是在窺探另外一種跟自己不一樣的生活。」秋水這樣理解她被關注的原因。
她曾在鏡頭前分享,自己曾因身為大專生感到自卑時,留言區的一則發言讓我聽了覺得很難過。 “你專科自卑,他二本自卑,我雙非自卑,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
“如果不上班的話就是躺著”,她這樣形容自己。失業,不自律,她一邊嘗試做著小自媒體賺微薄收入,一邊時不時去咖啡店兼職服務生覆蓋基本開銷。
開始失業時,她沒有在朋友圈透露出自己脫軌的狀態,甚至會刻意營造出自己正在上班的假象。但她現在覺得這種狀態也沒什麼不好,“因為你當韭菜,不如躺平呢”,她這樣安慰自己。

失業雖然會沒錢,但總還可以自由支配時間。身為自(失)由(業)撰稿人的我,對這樣的自我安慰如此熟悉。
在我和她聊天之前,她才發布了一則影片講述自己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 的工作,在家附近的一家店鋪做營運。但在坐班時,無論是碼字、拍攝、還是開一些無意義的會,她都覺得沒有意義,打趣道,“不過是一些即將被AI 取代的工作。”
即使她有一百種理由告訴自己需要這份工作,但一個理由就把這些理由都擊退了。雖然沒有錢買不到很多東西,但因為不合理的坐班和休假要求,她還是再次回歸「失業」。
“這都是我自己選擇的”,她說。
「大學畢業後,我意識到這是一個認命的過程。我徹底放棄了上班這件事情,我跟所有人都說我患上了不能上班的絕症。我把生活標準降到了最低,只要餓不死,就不去上班。餓不死太容易了,不是嗎?我想著人被逼到絕境的時候,一定會發奮圖強努力工作的吧,對不起這在我身上完全不起作用。」她在私人公眾號上悄悄寫下,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
曾有一個網友想用「無一技之長的底層人士」這個詞來罵她,說她這輩子只能是一個底層人,,無為成不了大事。 「你不努力,活該是個底層人」。秋水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是個底層UP 主這個身份,但「活該是底層人」這樣的敘事,讓她感覺自己有一股子氣提不上來。
「這本來就是一個失去聲音的群體,遇到不公平的事,吃了啞巴虧也是默默承受著,大部分底層人根本不知道要為自己的生活做主,他們也不知道有什麼樣的途徑,他們接觸的資源,接觸的東西太少了。別忘了,讓城市真正運轉起來的就是底層人。”
前陣子,聽到天門山年輕人相約自殺的新聞,她只能強迫自己麻木,因為那些人的環境,離她太近了。秋水身邊的親人、親戚、同學、朋友,幾乎都是中國農村工人、農子弟。
「他們都忙著怎麼生活,沒有時間上網。我還可以上網發聲,維持一種本該屬於自己的表達。但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這個選項。」因此當能夠有這個選項時,秋水把鏡頭對準了離她最近的人,做著關於底層的視頻,拍好友回農村自建房的婚禮,拍自己家經營的零售小賣部,拍失落的鄉村。
她不覺得住在不到6 平米,500 塊一個月的城市隔間是羞恥的,因為不會給當時仍是互聯網透明人的她帶來生活上實際的困擾,“雖然衣服經常晾不干,也會有臭味飄出來,但小時候我們還住過潮濕的水泥地下室改的房子,這個環境已經好很多了,沒有覺得特別困擾。”
一個月後,她從隔屋搬進了另一個出租房。

02
流動人口的女兒
以莫西子詩的詩句為標題的一期影片——《當風吹過這裡故鄉已很遙遠》,深深地打動了我。伴隨著周璇舊時代的婉轉歌聲,她用極其樸素的方式將鏡頭對準——湖南農村荒廢了很多年的「老家」。
低矮的鄉村土房已潮濕又爬滿青苔,牆面斑駁不堪,已倒塌的木頭床架歪七扭八。左邊淺藍色的布簾子半垂在空中,右邊打水的鐵桶倒了一半,上面是一排孤單的鐵絲衣架。熟悉的積灰塵、破敗的門窗,寫滿了主人過去的貧窮,今日的落寞。
她指著屋內的壓水井講起小時候奶奶在那裡幫她洗頭,指著紅色幾乎全褪去的碗櫥,那是她曾經洗碗的地方。幾大根木材粗魯地堆在屋內,屋外散落的紅土磚是已塌落的廚房。

拍完奶奶家,她在村裡轉了幾圈,沒有看到自己家房子的具體位置,最後她對著一塊空的泥土地和旁邊壘著的三堆紅磚指認為「以前的家」。
這段影片牽動了我內心深處非常隱密的角落,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條關於故鄉的視頻,更是一條關於那些留守農村成長的孩子的童年。
「他是打工太累了。而且他是死在了外面,就是在廣東還是在哪裡?嗯,就是太勞累了。」秋水這樣簡單地提起在外務工過勞死的父親,而後的故事我們所有人都能夠想像,媽媽迫不得已外出打工。最後哥哥、姊姊和她三兄妹被分散在不同的親戚家。
兩三年後,母親改嫁,接上了三兄妹一家五口人在不同的陌生小鎮之間流動生活,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也是我曾經的名字。我在一所東南沿海城鄉結合部的小學度過童年,班上四分之三是務工流動人員的子女。她們在早年會被有些歧視地稱為“外地人”,而我雖然戶籍在這裡,境遇卻與她們更相似。因為我們都知道什麼是暫住證、借讀費是多少。
這些朋友大多會在小學念完後,受制於戶籍制度,回老家念初中,也有一些會選擇在民辦學校讀初中。她們中的絕大多數會在九年制義務教育完成以後開始打工。由於輟學、黑社會、校園霸凌和師資不足,她們的工作提前開始並不是例外。
小學之後,我已經模糊地知道──人生不是公平的。我幸運地升學去了本地還可以的一所新初中,而後是重點中學,她們也慢慢消失在了我的人生視野裡。偶爾,我也想像她們回到老家度過的青春。
青春期的秋水像所有擰巴的少女,對繼父的角色有很多芥蒂與不理解,她不理解繼父為什麼不關心孩子,為什麼不努力讓家變好,要喝酒、打牌。國中時期,家裡開了手工的家具店,是在外打工的兩口子從廠裡學到了些小技術回小鎮開的。
生意做不下去也是因為繼父酒駕,送貨的時候出了車禍。他開著三輪車送貨,剛好在路上載了一個人,也是個醉鬼,碰上路坑坑洼窪,那人就摔了下來,斷了腿。一大筆的賠償金一下子讓艱難的家雪上加霜。
「主要也有生意賒賬,做家具貨幾百幾千地出去收不上來錢,不比小東西。」好說話的繼父在一杯酒下肚之後就不拒絕賒,最後資金循環不了,生意告吹。秋水一家又開始了租房流動的生活,頻繁地轉學。

「小時候媽媽對我說過最多的話是──沒錢。」秋水的媽媽去買的衛生棉就是網路上爆出來的那種「三無」散裝衛生棉。那時她意識到,她讀到國中畢業頂多就是走一個流程,「至少要拿個國中畢業證書才能進廠嘛」。她不知道人生還有什麼別的選擇。
「錢把什麼都限制了,吃也好、精神也好、物質也好,都限制了。」
秋水在生活中有一點社恐,但在網路上,她還是想要表達自己,想讓別人看見她。 「他們看到我是好是壞都沒關係,就是渴望被看到的一種狀態。」從小到大,秋水會想要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去引起父母的注意。但那時候,父母為了生計,根本顧不上她。一直到轉學和父親的過世,家裡依然貧窮,這些都將「退縮」染成了她生活的底色。
聊到這裡的時候,我想到如果我小學時沒有因為成績比較好,在校長的推薦下去唸一所還不錯的初中,我或許此刻也正在某個東南沿海的工廠流水線工作,或者從事某些服務業謀生。我不覺得我去唸了流動人口為主的民辦初中,在那樣的教育資源和校園氛圍下,能夠同樣發揮出自己的智力與才能,透過重重迷霧仍然進入重點中學。
進入重點中學之後我的人生像是兩篇小說的嫁接,我也隱去了自己那與城市中產階級小孩截然不同的童年。在生活無人注意的暗角裡,我仍然察覺到“匱乏”,察覺到差異,察覺到自己由於長期懷有某種墜落的隱憂而過分緊繃的神經。面對選擇時,我常常需要透過反覆確認,來克服不自信與退縮。
看完她的視頻,我在我的備忘錄裡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流動人口的女兒長大了,住在隔間房裡,她的人生和流量纏繞。 ”“工農子弟的孩子”、“盲流”還有“底層”,這些詞我都好久好久沒有聽到了。

03
縣城土狗
「他們的人生,是沒有人為他們規劃的人生,於是他們會重複上一代的人生。」國中念完就去打工,最多高中,打幾年工回來結婚生子,就是這樣。
秋水在講起身邊工農子弟們的人生想像時講到,「他們甚至想不到有『匱乏』這個詞。我以前也想不到人生究竟要有什麼意義,精神要得到什麼樣的滿足。所有的飢餓都只是一種對物質的渴望、想要很多很多的錢,而沒有辦法思考到自己想過什麼樣的生活,怎麼去接近。”
小縣城裡都是農村考上來的同學,和她的家庭狀態差不多。從前,在她的認知範圍裡,身邊就是世界。進入大城市以後,差距一下子就凸顯出來了,一種跌落式的、斷崖式的差距。
「當時在寢室,我迫切地想要和室友表達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會被笑話。」上高中的時候,她不覺得自己很醜,而到了大學的環境,她覺得自己很醜。秋水一度有著嚴重的外表焦慮,夾雜著莫名撲面而來的異樣感。
在龐大的訊息下,秋水感到自我變得微弱、瑟縮,自我否定成為了一種常態。她自嘲自己是個盲流,就是鄉下人盲目地走進大城市的那一個群體。
「我可能有一點小小的才華,但我不知道。當別人覺得我厲害時,我就會開始自我否定。如果很厲害的話,怎麼會過成現在這個狀態呢?」潛意識裡,秋水覺得自己是個廢物。
對大城市來說,似乎包容不下像秋水這樣成長的青年,擁有著並不完美、體面,甚至是有瑕疵的、缺陷的家庭。而對她身邊的同儕來說,她已經是正常且幸運的。孤兒、單親、父親年紀特別大的、不能承受勞動的、殘疾的,或多或少有些殘缺的普通人,在小鎮是非常普遍的。
只不過,從鎮上到了縣城,也還是一群窮人。

这个地方跟我是一样的就像我明明是一条土狗却传达出我在搞艺术,搞县城魔幻其实我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我土狗的本质不过我为啥要摆脱?秋水的姊姊國中畢業後就讀了衛校,最早出社會賺錢,給她墊付了一半的大專學費。比她大四歲的哥哥則給她買書,告訴她即便成績差也要堅持下去。秋水的哥哥成績不錯,家人給他考上本科的希望,最後也只是念了專科。
在那期談到大專生自卑的影片中,她提到每個班40 個人中,差不多只有一個人能上本科,整個年級可能都不到二十個人。教學資源、家庭期望以及生存狀態,都不是依靠努力就可以把學習「搞好」的。
「在外面的這幾年,我常常晚上醒來,望著周圍的黑暗,不知道身處何處。躺在那張床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好幾次醒來,我以為自己像小時候一樣躺在外婆的房間裡,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已經二十幾歲,躺在狹小逼仄的出租房裡,第二天還要上班。”
畢業後的幾年裡,她加起來總共上了兩年班,輾轉在中山、杭州、長沙等城市,薪資在4-5 千之間徘徊。現在她養了一隻小貓,在長沙租了1000 月租的一居室,沒有計劃結婚生育。
有別於傳統觀念,在網路的資訊大潮中,她意識到婚育對她來說,是沒有什麼利好的。在她的成長過程中,也沒有看過幸福美滿的婚姻。
她給回鄉結婚的發小拍婚禮視頻,透露著一種異樣,想祝福但惶恐。婚姻的決定倉促而草率,不是女孩真正想要的婚禮,秋水問出,“這是你想要的婚禮嗎?”
秋水對於自己人生的意義不能說沒有過期待。 「木村秋水」是她的微信名,讓人一時之間想到「農村拓哉」的五條人樂團成員仁科,忍俊不禁。我很驚訝在於她告訴我,「秋水」真的是她自己改後的本名。
高中時代,她看到馮唐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男主角叫“秋水”,一下子喜歡上了這個名字,覺得很好聽,希望身邊的人也叫自己秋水。很可惜是,只有一個朋友認真地這樣叫她。
「雖然有時候也會安慰自己,本名是奶奶取的,而且她去世地比較早,畢竟沒有什麼文化,就用著唄,但最後還是覺得太土了。」在結交新朋友時,秋水的真名容易被發現,讓她感到自卑,決意乾脆將它改掉。
這個名字是和過去自己的告別,拿到新身分證時,她確實有重獲新生的感覺,即便電話卡、銀行卡、學位證等全部證件的修改歷時了兩年。但改完這一切之後,她的人生並沒有發生任何顯著的改變,不過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生的延續。
「還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可能未來的生活除了年齡的變化之外,相差不大。」雖然在網路上是六萬粉絲的小博主,但她對於未來的預期,就是「為生活奔波,然後想辦法去搞一點錢。”

04
向下的選擇
基本上我是一个隐蔽青年如何你决定同我发展我们不会经常见面见面也只是带你流浪到海边然后我会告诉你一个重点重点就是我没有钱” ——mla 《社会主义青年》部落客生涯並不像大家預想中光彩。整整一年沒有漲粉的秋水,粉絲數長久地停在了6.6 萬,早早就遇到了普通人做影片的瓶頸。
最近的更新都明顯地透露出她的焦慮與迷惘。這當然與產業「二八定律」有關,絕大多數的資源與機會都聚焦到了頭部,同時經濟不景氣、自媒體也逢低潮期。但秋水也明確的知道,除了她個人能力的上限,她也錯過與放棄了一些東西。
「候翠翠就是抓住了B 站的推流,並且踩穩了,我還是太情緒化了。」秋水這樣告訴我。
“出於情緒”,為鐵鍊女事件發聲的視頻發出後,她不再收到推流。在為上海春天的事件發聲的影片被刪除後,她意識到自己應該是被平台拋棄了。無人指導、摸著石頭過河的她終究還是濕了鞋底。
這種不合時宜的「正直」也是她的選擇。四月份,她推掉了幾個廣告合作,一個是不寄送產品試用就讓她寫測評的圖文廣,另一個是女性私處護理的「智商稅」產品。雖然秋水的粉絲群很小,賺錢也不寒磣,但無論混到什麼地步,她都不願意恰這個爛錢。就像某些事件,她雖然聲音微弱,但要“沉默”,她於心不忍。
「搞錢很重要。搞錢排在第一位的時候,我特別想搞錢。但當面對搞錢要付出一些代價的時候,我想我還是接受我們普通的命運吧。」在聊天過程中,秋水屢屢談起做自媒體現在只剩搞錢了,她同時也非常清晰且悲觀地知道自己搞不了多少錢。
做自媒體一年,如果做得簡單一些,就像現在水水日常,也可以保持她的表達欲,但水視頻不會漲粉。而難度大一點對她來說又非常吃力,沒有人幫忙拍攝,也付不起拍攝成本,於是陷入糾結的兩難。
「有點理想又挺悲觀的,就是會非常容易打退堂鼓。」她的這一句自我概括,十分精準。

她很擰巴,另一些時刻,她覺得自己和身邊人雖然普通,但也不至於差到去做流水線的工作,還是可以做一些有創意的內容,但是時代似乎沒有給出平台和機會。 「我還是會有小小的不甘心,哪怕我的人生是那麼平凡,但這個平凡總該要泛起一點水花或者是漣漪吧。」
有時候,在音樂節或現場遇到她的朋友時,秋水會羨慕她們的童年與生長環境。她遐想,如果自己也擁有那樣的背景,是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不是一直都要處於跟自己自洽的狀態。
做自媒體,秋水收到最多的負面評價是覺得她太「向下」了,傳遞負能量,不好好生活。秋水認為這也是一個少數群體被排斥的狀態,自己沒有跟他們一樣,所以被排斥了。 “就像我們很多人都是一種思維,身邊即世界。這個人和我過得不一樣,她怎麼能不一樣呢?必須和我一樣。”
「當你們又在留言區裡說,秋水又在搞這些稀里糊塗、喪裡喪氣,是個廢物時,你們是對的。我只能說我搞藝術啊,要不然我怎麼安慰自己,我該怎麼在這個困乏的生活裡面找到一劑良藥呀,我只能說,這都是藝術。”
秋水非常喜歡電影《頑主》裡的一段話,張國立的女朋友讓他去找一份穿西裝打領帶的正經工作,他說:「我看似是在輕飄飄慢吞吞地下墜,可是你知道嗎?我的靈魂中有一種東西得到了昇華。”
而當我問到秋水,「向下」是經歷了這一切的自然狀態,還是如果有一個向上的選擇,你還是會抓住這個機會向上的?她告訴我,“我覺得是我的選擇。我的性格注定了我是一個永遠不會成功的人,儘早放棄的話也沒有什麼預期,有預期就會有失望。”
她覺得這樣沒有不好,她不想為自己向下的選擇做出解釋。
在最近的影片裡,秋水告訴觀眾她已經不像之前那麼悲觀了,準備找個班級。她煞有介事地說著:“雞蛋沒破的時候就是沒熟的雞蛋,當破了時,它就是藝術;出去拍照片,回家一看全糊了,模糊就是藝術,藝術就是模糊的。”
秋水會在貓貓拉稀埋不好粑粑,踩到家裡到處都是時,說那是粑粑藝術。
“這裡一點,那裡一點,都可以連成一條線。”

最後。
大專生是大學生嗎?我估計很多人根本答不出來。但這個群體同樣龐大。
社群媒體與城市交往塑造了一種人均中產階級的幻想,似乎只在一些狹隘的時刻,人們假裝「猛然」發現——猛然發現中職生的錄取率,猛然發現「努力就能成功」敘事的騙局,猛然發現那一切「體面」之外的東西。
菁英的孩子們用自己累積的文化資本置換著社群媒體的話語權,譜寫著「只要夠努力,就能獨立自信優雅」的女主人設,說著些與命運相關的雞湯。
但我的身分與經驗都不允許我對此不感到憤怒。社會看似給了每個人平等的機會,實際上並沒有給所有人把握機會的工具。
結尾,我也無意給看完這篇的人一個昇華。秋水是某種程度上比我更自洽的人,她喜歡看電影、喜歡詩歌,笑起來眼神很清澈。
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失業青年的故事,那每一個在我們視線範圍之內、或之外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千萬分之一。
找到我:
Ig:@kira_kilaaaa(生活偏多!)
Podcast: @氣泡Bubble(泛用型客戶端可以找到我)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