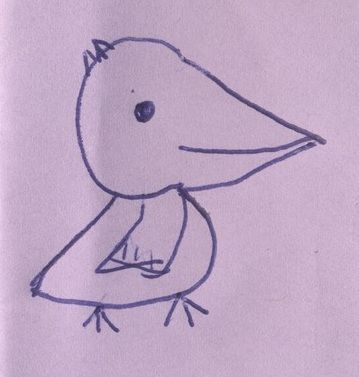
来自豆瓣的难民
災難性的懷念
2022 年 9 月左右,我們得到風聲,經過三年
封閉主義,中國開始允許外國人(例如我們美國人)
申請簽證進入該國。當時,我和易想
政府可以讓這個國家對外界關閉
天知道多久,所以我們抓住了機會之窗,
暫時半開,然後跳,跳,跳,通過
無數的官僚箍來確保簽證。
拿到簽證後,我們才真正開始擔心:中國還在
擁有最極端的零Covid政策:鎖定城市
數百萬——字面意思是沒有居民走出他或她的
公寓除了每天進行一次 PCR 測試——只有幾百
感染,並帶走所有感染者,無論是否有症狀,以
集中營。我不是誇張的:所謂的“Covid
隔離點”提供很少的醫療服務,通常是每個人一個廁所
一百名囚犯,24小時亮著燈,沒有任何可能
離開直到連續多次陰性測試。在受害者之後
被拖到這些營地,政府工作人員進入他們的家
到處噴灑消毒劑,經常毀壞書籍、家具和
家電。受害者的寵物經常餓死或在某些情況下
被那些“消毒器”幹掉了。
鑑於這種冷酷無情的政策,我們之前的主要恐懼
出發是我們會在旅行中感染 Covid 並被送到
夏令營,最終沒有機會見到我們的父母
煩惱。而他們的麻煩是:即使我們沒有被感染,所有
外國旅客必須被關在隔離“旅館”裡兩個人
在被釋放前幾週。此外,往返機票
中國過去每人花費約 1500 美元,現在接近
每人 8-1 萬美元。所以我們不得不充當我們自己的旅行社並設計
精心設計過日本和香港的路線,並找出許多
整個路線的疫苗接種和檢測要求。我的大部分
去年秋天的精力都花在了旅行的準備上,得到
文件,儲備維生素和飢荒食品,如堅果,併購買
降噪耳機,一切為最壞情況做準備
被送往集中營。
然而,事實證明,我們一直在擔心錯誤的事情。只是
當我們在 12 月中旬出發時,經歷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並且
坦率地說,對零 Covid 的抗議是可以理解的,可能還有一些
快速的社區傳播,意識到他們不能再堅持下去
以可承受的代價,政府突然改變了方向並決定
完全敞開,沒有任何準備。醫院
和藥房同時學會了完全開放的決定
和其他人一樣的時間。沒有儲備藥品或
在醫院為不可避免的激增做準備。政府有
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拒絕進口 Paxlovid,就像他們
之前拒絕批准任何國外的mRNA疫苗。連退燒藥
就像 Advil 的 Tylenol 開始用完一樣。確實有時人們可以
甚至在商店裡找不到溫度計!半官方的勸告是
“政府保護了你三年,現在你
當covid有時需要承擔起保護自己的責任
變得像流感一樣溫和!”。
我們在香港的幾天大部分時間都是進入香港前的最後一站
中國,被花時間匆忙拿脈搏血氧儀,更冷
家裡親戚的藥。
與此同時,不出所料,新冠病毒席捲了城市人口。
在大約三週內,2000 萬左右的人中有一半以上
在北京得到它,包括我們認識的幾乎每個人。醫院
變得淹沒了。火葬場外排起了長隊。
所以我們回到了一個我們正在準備的完全不同的世界。我
曾想,在最好的情況下,我會被我的
父母在他們的公寓裡,幫助他們囤積並試圖
說服我父親,他對“西方”(即現代而不是
草藥)一般來說,接種疫苗,因為我確信
稍後會出現放鬆和 Covid 浪潮,也許
2023 年春天。
相反,當我在的時候,我的父母都已經被感染了
香港。 (他們進行了抗原測試)。
荒謬的是,儘管 Covid 感染的傳播速度已經最快
在我們於 12 月 12 日進入中國時的世界上,如果不是永遠的話。
17 日,在我們在四天內獲得 *4* PCR 陰性結果後,
我們仍然需要隔離 8 天,而原來是兩週
之前,如果滿足某些條件,可以減少到五個。我
有脈搏血氧計和藥物,但無法將其寄回家
父母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我媽媽在兩天內就康復了,但我父親卻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他開始
兩天后發高燒,抱怨喉嚨痛
疼痛,所以他好幾天都很少吃東西,同時一直堅持說他有
沒有呼吸困難。但從他吃力而急促的呼吸中
電話,我開始擔心最壞的情況。仍然,沒有脈搏血氧儀我
無法確定。在我預定的“釋放”前兩天,媽媽
借了脈搏血氧儀,證實了我最擔心的事情。然後,與易
求助,我從朋友那裡借了一個氧氣濃縮器,這可能
在我獲釋前一天保住了他的性命。
當我結束五天的“縮短”隔離後回到家時,我去了
立即在附近的醫院附近轉轉,希望能找到一家不
完全不知所措,然後叫救護車把他送到
較小的當地醫院,唯一一家在入口處的場景是
還不如狂暴的諸神黃昏。
12月22日下午6點左右,我和爸爸一起坐救護車
去醫院。接下來的24小時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
我從未參加過戰鬥,但我想這一定是事實
喜歡眼睜睜地看著親近的人的生命在
在你的眼前。只有在我父親的情況下,而不是震驚
槍傷,他被水刑處死。
當我們第一次到達急診室時,爸爸沒有床。所以他被安放了
在移動擔架上,靜脈滴注和懸掛在移動支架上的氧氣。
雖吸氧,喉嚨劇烈疼痛,
呼吸衰竭,並且幾天來幾乎沒有食物或水,他
仍然奇蹟般地清醒,我想,很高興終於見到我
三年半之後。
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在擠滿了人的普通急診室裡有一張合適的病床
病人、護士和親屬,原來是一位老人
穿過房間。護士們對一個倒霉的親戚大聲命令
他們自己的車把他送到更大的醫院,因為他得了
心髒病發作,這裡的急診室無法處理,也沒有
救護車。親戚拼命玩手機,聲音夠大
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能聽到她談話的兩端
房間。麻煩的是,中間有一個巨大的生日狂歡
一場肆虐的 Covid 海嘯,以及整個家族、親戚和朋友,
男人、女人和青少年,都受到重創,因此無法
開車過來接族長。
當我向爸爸解釋荒謬的情況時,他的嘴角
在他的氧氣面罩下稍微向上轉身,最後一閃
咯咯地笑,來自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現在永遠沉浸在
我的記憶。
當一個半清醒的司機被找到來取心髒病時
受害者,他的床終於免費給我爸爸了,我已經把他推到
CT掃描取結果給醫生--chinese hospitals
經常把病人周圍的任何親戚都視為最低等的
勤務兵。 CT掃描證實了我最可怕的預感。爸爸的肺
早就被感染了。病毒攻擊和免疫防禦
他的大片肺部一起變成了死一般的白色。醫生在
職責,只有一個,非常坦率地告訴我
到那時只有奇蹟才能救他。
麻木地,我只要求她盡最大努力,如果無濟於事,因為
姑息治療,然後打電話給媽媽。這個消息對她打擊更大,
可能是因為她不太了解我父親的病情有多嚴重
惡化。
當她匆匆趕往醫院時,我們試圖再破解一個
開玩笑,甚至跟爸爸說話,都從絕望變成了絕望。他不是
不再抱怨喉嚨痛或口渴,只是喘氣
空氣。整個晚上他都在淺淺的噩夢中進進出出,
呼吸困難,通過積聚在他肺部的液體和
他喉嚨裡的痰,也許是為了理解他自己即將到來的厄運。
有時證明疼痛太大了,他試圖引起人們的注意
護士們,急診室那些粗魯的小暴君,去做點什麼,
任何事情,用他僅剩的最後一點搖晃他的床欄杆
力量。無濟於事。即使護士願意提供幫助,我
毫無疑問,沒有止痛藥可以防止窒息。
在疲憊和無助的打擊下,我和媽媽輪流對付他
床邊,不知道還能嘗試什麼。護士最終禁止我們
和他說話,或者給他喝水,因為他可能會窒息,所以媽媽
從家裡拿來香油和棉籤抹乾裂的嘴唇。我們
乞求草藥 IV 來減少痰,醫生曾經提到過
順便說一句,這件事給了他半神迷、絕望的希望。
媽媽被送去醫院的裂縫
黎明,最終沒有藥,爸爸也沒有希望。
他連接的機器不停地發出嗶嗶聲,警告他的
呼吸或心率或其他什麼都失敗了。痛苦和恐慌
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臉,即使他漂浮在意識中。我
想知道這一切什麼時候會結束,如果
結束應該早點到來。但那和其他一切一樣,是出於
我們的控制。
與此同時,整夜都有新病人乘坐救護車到達
汽車,尋求幫助並被拒之門外。絕望的親人受到威脅
打電話給當局。醫生讓他們隨心所欲,然後
緊張地請護士記下他們的車牌號。
終於,在第二天早上的中間,鬆了一口氣,來自
呼吸重症監護病房有人死亡,排空了一個
爸爸的珍貴床。又一個痛苦的懸念之後,等待一輛坦克
轉移時供他呼吸的氧氣,我們終於輪到了
他到幾乎死去的人的僻靜病房,在那裡,殘忍地,或
幸運的是,親戚被禁止。
在那裡,掛在呼吸機上,被大量鎮靜並處於不確定的狀態
不知不覺中,他從我們身邊悄悄溜走了。在隨後的
懸念在遠方的日子,只是偶爾更新一個醫療
有條不紊,醫生打來了幾個電話。媽媽和我
談到如何照顧爸爸,肯定大大減少了,在他得到
家,雖然內心深處知道他可能不會。
五天后,電話來了。醫院裝模作樣地問
我們進來並決定何時停止使他復活的嘗試,但是
勤務兵低聲說,他們打電話給我們時,他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
我們希望,不像我們在他身邊的那個晚上,沒有
在我們不在的日子裡受了太多苦難。但我們怎麼可能
知道?他一個人死了。
我們很快就知道醫院太平間那時已經
長期用完的不僅僅是冷藏空間,連裹屍袋都用完了,所以
我們必須盡快帶走我父親。但我們
然後被告知即使是最快的火葬場也需要幾天時間才能
取回屍體,所以,這意味著,我們最好開始四處打電話
馬上。只有在從太平間得到內幕消息之後
通過電話乞求火葬場,我有沒有人來接他
三天后,然後只為他被存放在那裡未知
數日之後,化為灰燼。我們得到的只是另一部電話
完成後打電話。
作為最後的侮辱,當我拿起爸爸的死亡證明時,有人告訴我
也就是說,如果死因是 Covid,則根據“規定”他的身體
不能留在醫院太平間,必須在兩分鐘內火化
小時!因此,當局將自己的無能作為武器來強制執行
我們默許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謊言,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他們能夠繼續下去
可以誇口說,與其他地方不同,在中國很少有人死於新冠病毒。
直到今天,我都無法擺脫所有的假設。如果我曾經是
更執著地試圖說服爸爸接種疫苗?像許多
在他這一代人和成長過程中,他對“西方”持懷疑態度
藥品。如果我不必在隔離區度過漫長的五天,會怎樣?
這樣我就可以在陰險的缺氧餓死之前把他送到醫院
他的器官?如果我更努力地尋找一家更好的醫院
會帶他去,也許是帶 ECMO 等生命維持設備的人?
但對於那些誇張的人來說,肯定應該有更多的假設
家長式政府,因為我的痛苦和損失幾乎沒有
獨特的?如果有更強有力的運動來接種疫苗會怎樣?
老年人,有更有效的疫苗嗎?畢竟很多地方都
但強迫幾乎沒有患重病風險的幼兒獲得
接種疫苗,作為上幼兒園和學校的條件。什麼
如果開幕式更加循序漸進、更有條理、更有準備,那麼,對於
至少,我可以有時間把我的血氧計寄給他們?如果什麼
高效的抗病毒藥物如 Paxlovid 已被廣泛使用,
我肯定會堅持讓他得到它?
我待在家裡的其餘時間都花在了忙碌的交易上
我父親去世後的後果。由於它的突然性,有
沒有意願。所以我們只能弄清楚陌生事物的來龍去脈
法律制度和官僚主義,以轉移父親的資產
給媽媽起名字。自始至終,媽媽雖然表面上都在深深地哀悼
強的。我不得不回到美國——她堅持我應該
不耽誤我的返程航班---許多法律步驟必須由
我們在一起,所以我很著急。
匆匆忙忙,我們幾乎沒有時間一起哀悼,如果有
確實是一個正確的方法。我為她即將到來的荒涼而戰栗,當我
和小伊一起回老家過年
她自己。我能想到的就是經常打電話。
易在南京的父母都被感染了,她的父親儘管
接種三聯疫苗(中國疫苗)受到嚴重傷害
到肺,很可能在早期呼吸衰竭,在恢復之前
有了易為他*在家裡*買的製氧機(醫院可以
絕對不提供任何東西。他們等了五個小時才拍了一張CT,然後
他們提供了五片藥片,是的,五片單片藥片,裡面含有寶貴的藥丸!)
幸運的是,就像我媽媽一樣,他們似乎正在恢復健康
力量和能力。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發布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