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明治,创办于2011年的Life Writing平台,以非虚构Storytelling形式激发创造力,并将生命故事运用于个体探寻、在地研究、出版策展、声音播客、儿童成长等领域。
在烏茲別克斯坦與流亡俄羅斯人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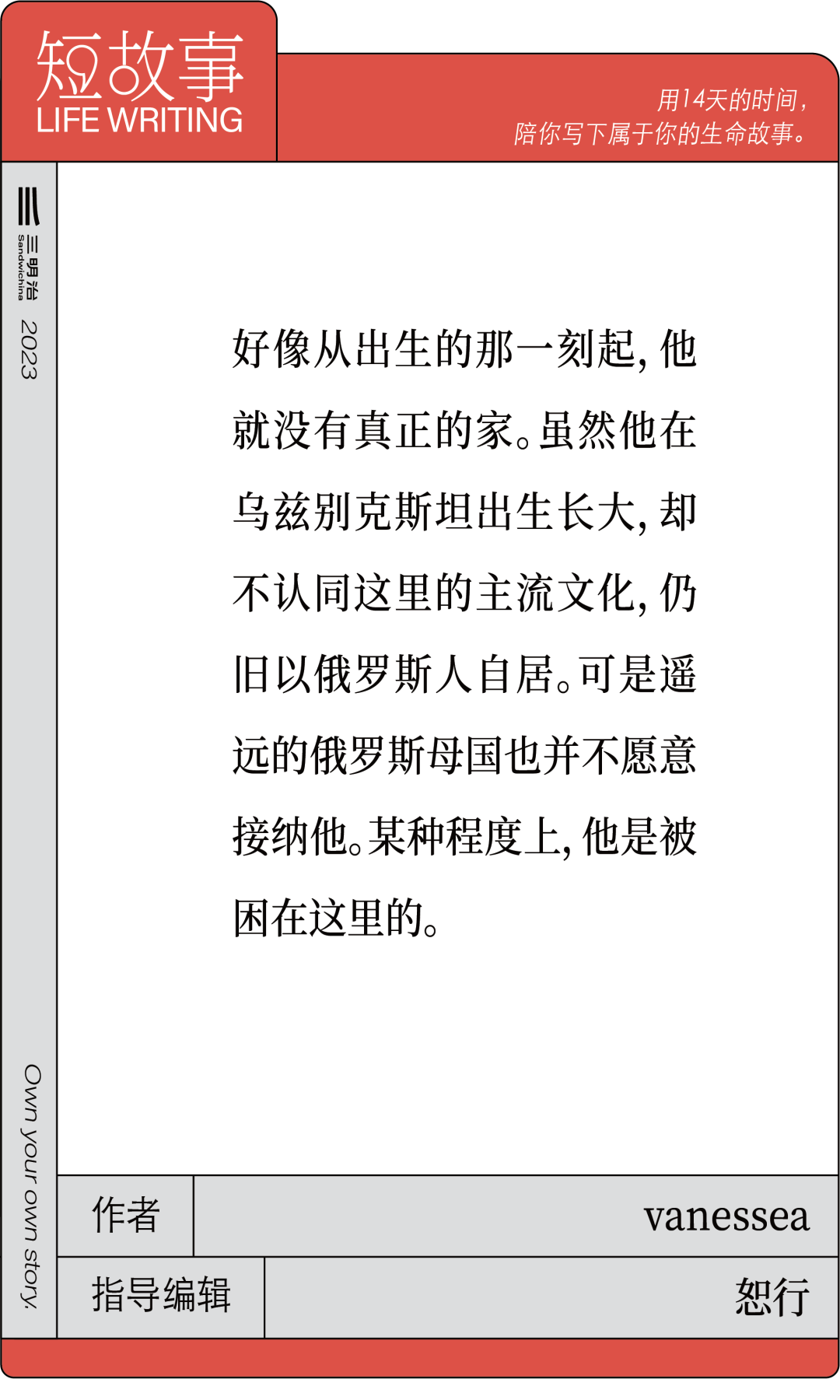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學院導師指導完成。短故事Life Writing學院邀請你來寫下屬於自己的個人故事。

走進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幹的青旅,我以為來到了俄羅斯。耳邊全是俄語,眼下也盡是俄羅斯人。
這間青旅剛開業一年,設施配置完備,除了客廳與廚房,還設有一間辦公室。公共空間裡的絕大部分被俄羅斯人佔領,更確切來講是俄羅斯男人。客廳的電視上播著介紹格魯吉亞的俄羅斯旅行節目,辦公室裡有人在用俄羅斯語開視頻會議,而打開廚房的冰箱,裡面堆滿了切到半截的紅腸,還有一鍋沒蓋蓋子的羅宋湯。
對於此番景像我不算毫無準備。預定網站上就有評論指出:“這家青旅整體很好,只是許多因為戰爭常住的人,不會講英語也不願意社交,影響氣氛。”很顯然,被指代的是俄羅斯人。他們來這裡是為了躲避兵役的。
俄羅斯男人從外表上來講絕對不是最有親和力的群體。他們大部分塊頭不小,留著鬍子,衣著算不上邋遢但也隨意得有些過分。他們趿著拖鞋在樓道裡穿梭,彷彿在宣示主場。我感受到作為闖入者的拘謹,但又夾雜著同情。青旅就算設施再完備也不是真正的家,六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裡,只有一張床的個人空間。如果不是沒有其他辦法,應該沒有人願意長期住下來。
我很快發現,這群男人並沒有看上去那般不可親近。那兩天我正好也有一些在線工作要完成,和他們共享著公共空間,很快就熟悉起來。其中和我最聊得來的是一個叫Artur的年輕人。
第一次見到Artur時,他坐在共享辦公室裡我旁邊的位置,敲著鍵盤。他穿了一件北歐花紋的毛衣,鬍子修理得很整齊,氣質要比其他人文靜些。
“你也是程序員嗎?”他瞥到我打開的編程頁面,伸過頭來問。
“也算是,”我回答,“我是做研究的,關於人工智能。”
Artur曾在網上自學過人工智能的內容。我們討論起基本的算法,他竟然對邏輯回歸、隨機森林和神經網絡這些概念都了然於心。不過那隻是為以後的機會做準備,現在還用不到。他目前是一名軟件開發工程師,為一家俄羅斯公司遠程工作。他的英語詞彙量不大,但是表達能力很強,能將有限的詞彙拼湊出準確的含義。
“你在這裡有多久了?”我問Artur。
“在塔什幹已經三個月了,之前還在阿拉木圖住了三個月。”他回答。
去年九月底,俄羅斯開始面向全民徵兵,Artur便立即申請護照準備離開。他在十月份成功去了哈薩克斯坦的城市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對俄羅斯公民有三個月的免簽,期限用完後他又來到了烏茲別克斯坦。
在如今的世界陣營劃分下,可供俄羅斯人選擇的目的地極其有限。他們被西方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排斥,戰爭打響後很難再獲取簽證。由於國內的教育與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絕大部分俄羅斯人從未出過國,也幾乎不會講英語,因此很難在一個過於遙遠的國度獨自生存下來。地處中亞的前蘇聯國家烏茲別克斯坦成了最優選項之一,地理距離近,生活成本低,民眾普遍會講俄語,而且對俄羅斯公民無限期免簽。
“像我這種情況被徵兵的風險最大。”Artur解釋他為何如此緊迫逃離。他離開兵營才不久,疫情之前的兩年都在特種軍部隊服義務兵役。因為有作戰經驗,他極其有可能成為這輪徵兵的入選者。可是在部隊的經歷讓他深知俄軍內部管理的混亂。他不願意殺戮,更不想白白送死。
“我知道他們有多蠢,許多做法簡直就是給敵人送子彈。”Artur說得有些激動。 “我努力生活了二十多年,並不是為了一個這樣的結局。”
今年初,Artur曾服役的連隊中了埋伏,死了五十多個人。他曾經的指揮官也在其中。
他沒有再往下說,換了個話題,邀請我和他的朋友們一起去吃晚餐。那是另外兩個俄羅斯人,年紀都比Artur稍大。兩人在俄羅斯國內時曾分別是電工和交易員,後來都通過Artur找到了IT相關的遠程崗位。他們和Artur在阿拉木圖的青旅相識,然後結伴來到塔什幹。
我們沿著塔什幹的主幹道往餐廳走。街上是清一色的烏茲別克產雪佛蘭轎車,排出的尾氣在空氣中徘徊,從四周將我們環繞。烏茲別克政府為了保護本國造車廠,通過加關稅的手段變相阻止外國汽車進口。
這並不是一座富有吸引力的城市,大部分建築都是上世紀60年代地震後由蘇聯重建的,沒有吸引人的伊斯蘭古蹟。來烏茲別克斯坦的遊客大多只是藉助塔什幹的機場進出,並不會久留。我也不例外,明天就要去古城撒馬爾罕。
我們走進一家餐廳,裝修是烏茲別克式的富麗堂皇,當地人很喜歡閃閃發光的東西。 Artur和朋友們經常來這裡,對菜品很熟悉。我在一眾烏茲別克特色中看到了俄羅斯紅湯,猜想是蘇聯時期傳過來的,指出來問他們味道如何。
“還不錯,但是和俄羅斯當地的完全不同。”其中一個朋友回答。
“你應該去俄羅斯嚐一嘗正宗的。”另一個朋友補充。
我點頭答應,又問他們是否想念俄羅斯的家,打算什麼時候回去。沒想到三人不約而同地否認。
“我現在是一個世界公民。”Artur鄭重地說。他的確想念在俄羅斯的親人,他的母親和姐姐還留在家鄉城市布魯賽克。但他很享受現在的生活,再也不想回到那座小城。
他打開手機地圖,將俄羅斯西北部放大,找到布魯賽克,指給我看:“我就是在這里長大的,這裡什麼都沒有,連條像樣的河流都沒有。”
刻板印像中的俄羅斯人愛喝白蘭地,可Artur卻對這家餐廳的草莓奶昔情有獨鍾。神奇的是,奶昔竟然也有酒精一般催吐心聲的效果。
Artur講起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那座閉塞的小城,上了一個不怎麼樣的大學,學了一個沒什麼用的專業,曾經打著雜工,對未來充滿迷茫。改變的開始在於疫情,他在家無聊便自學了編程。因為戰爭被迫離開俄羅斯後,他又找到瞭如今的遠程工作,從普通軟件工程師逐步做到小團隊的主管,工資翻了三倍。半年前,他絕對想像不到今天能在這裡,做著喜歡的工作,與世界各地的人交朋友。
“過去的這半年,真他麼是個奇蹟!”Artur感慨道,又吸了一口草莓奶昔。
那天晚上我們聊了許久,直到餐廳打烊來催我們離場。我們沿著同一條道路往回走。夜晚的塔什幹要比白天時漂亮,道路兩側亮起了彩色的燈光,而擁擠的車流已經散去。

從塔什幹到撒馬爾罕的列車是蘇聯時期的遺產。我買票晚了些,只剩下價格稍高的一等座。座位很寬敞,黑色的皮質座椅厚實柔軟,只是因歲月而敞開幾道裂痕。
我旁邊坐了一個金發女人,穿黑色高跟,塗淡紫色眼影。她把一盒烏茲別克糖果伸到我面前。 “你要不要嚐一個?”
我拿起一顆道謝,並順勢和她攀談起來。她也是俄羅斯人,來參加律師行業大會。往年俄羅斯的律師行業會一般在歐美旅遊城市舉辦,今年因為簽證限制,只得選址在塔什幹。會議剛結束,她要趁機到撒馬爾罕玩兩天。
我和她談起在塔什幹遇見的俄羅斯男人們。她並不避諱這個話題:“他們都是來逃兵役的吧?”
她的語氣有一絲疏離,好像這件事和她全無關係。她的一些律師朋友在徵兵之初也曾逃離俄羅斯,但最近回去了。俄羅斯政府近來重視起人才流失的問題,出台政策保護高端人才,確保他們不在徵兵範圍內。
“當然,這需要學歷達到一定標準。”她又補充。在塔什幹的青旅裡,似乎並沒有誰屬於這一範疇。
列車沿著絲綢之路的方向行進,兩側是棉花田。因為是春天,田裡還沒結出棉花,但枝葉豐茂。那天的陽光格外好,襯得萬物祥和又充滿生機,讓人覺得戰爭這個概念實在過於遙遠。

我向來喜歡到每座城市的露天集市拜訪。在撒馬爾罕,我選擇了比比哈努姆清真寺旁的大巴扎。路過一個賣香料的鋪子,戴圓頂帽子的大叔叫住我講起俄語。我猜出他在推銷自己的商品,但還是比劃著想弄明白具體內容。
“你需要幫助嗎?”一個清秀的年輕人從旁邊的鋪子走過來,“我可以幫你翻譯。”
他叫Roman,有精緻的五官和纖長的四肢,披一件繡東亞花紋的棒球外套。
不出所料,大叔在介紹自己的香料,紅色的可以煮湯,黃色的可以燉肉,全是當地天然原料,還可以免費送給我一小包試用......可我只是好奇閒逛,拿這些實在沒用,只好道謝離開。
“我是俄羅斯人,不要因此而討厭我。”這是離開香料鋪後,Roman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我當然知道,他剛剛幫我翻譯過俄語。不過單從外表看,Roman和塔什幹青旅裡的俄羅斯人風格差異巨大,而且講起英語來也沒有半點俄羅斯口音,反而像美劇裡走出來的人物。
我們走出巴扎,朝著雷吉斯坦廣場的方向去。我得知Roman剛剛21歲,是個“環球”旅行者,靠在線教英語謀生。說是環球,其實只能在俄羅斯護照允許的範圍內活動。過去的一年,他曾旅居白俄羅斯、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三天前剛落地烏茲別克斯坦。
他不是來躲避兵役的,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少了兩根手指,應該本來就不在徵兵範圍內,但他還是不願意留在俄羅斯。戰爭最開始的兩個月,他還沒有出國,與外部世界隔絕的孤立感令他窒息。國際品牌在俄羅斯的門店紛紛關張,一些在線平台也開始限制俄羅斯用戶,就連開戶地在俄羅斯的信用卡也全都被凍結。
“我現在用的是白俄羅斯的信用卡,我到那裡住了一個月才取得開戶資格。”Roman向我解釋。他還想在烏茲別克斯坦再辦一張卡,為此他也必須在這裡再住上一段時間。
然而他離開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是炮火。 Roman在聖彼得堡出生長大,但幾年前,因為克里米亞半島的旅遊業發展,他的父母投資了那裡的房地產,舉家搬到一所海邊的房子。克里米亞雖然被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承認是烏克蘭的領土,實際上卻被俄羅斯佔領。開戰以來,烏克蘭頻繁往半島上投射導彈,雖然突破不了俄羅斯的攔截系統,但還是會在半空中爆炸,發出震天的轟響。
我們終於走到了雷吉斯坦廣場,這裡曾是古代伊斯蘭文明的中心。廣場由三座經學院組成,建築表面以深藍和松石綠為主色調,以金色點綴其中,繪製烏茲別克特色的動植物圖騰。已經是傍晚,落日餘暉給本就恢弘的穹頂更添一分光彩。
才相處一會兒,我就感覺到Roman是個不太尋常的人。一方面是近乎浮誇的熱情,另一方面又是不諳世事的天真。他很容易對所見所聞大加讚歎,使用的形容詞在我看來總有些過頭。
我們來到烏魯伯格經學院門口,Roman對著高聳的宣禮塔讚歎。一個穿制服的警衛來到我們身邊,問我們願不願意登上塔頂。那裡一般不對公眾開放,但只要我們付10美元,他就可以破例帶我們上去。
“真的麼?這將是一次特別的體驗。“Roman興奮地看向我,以為我們是被選中的幸運兒。其實這不過是警衛賺外快的常規操作,大部分外國遊客都會被詢問。我早在旅行攻略裡讀過,但不想在此時戳破掃興。我們如Roman所願登了上去。
”我真的很開心認識你,雖然只是一個晚上,我覺得我們已經共同經歷了很多。“下回到地面後,Roman對我說。如果是其他剛認識的男生說這種話,我會提起戒備心,但對於Roman卻沒有。一方面,他一貫用詞誇張,而另一方面,我隱約感覺到他屬於性少數人群。
我的猜測很快被證實。我們在廣場前的台階上坐下,討論起當地的反同性戀法律。烏茲別克斯坦至今沿用蘇聯時期的法律,對同性交往處以上至三年的刑罰,而民間也有針對性少數人群的暴力事件發生。
”雖然如此,但我覺得沒什麼危險。“Roman的語氣輕快,“烏茲別克人長得矮,我一隻手就能把他們撂倒。“他應該是在開玩笑,但又好像帶有一絲認真。
這種特殊的幽默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消受的。許多時候,我實在慶幸烏茲別克人不怎麼聽得懂英語。這樣的感受在第二天達到了頂峰。
分別的時候,Roman約我第二天再去遊覽夏伊辛達陵墓群,可我已經與一個當地朋友約好,去探訪一座傳統村落。我向Roman表示他可以加入,他幾乎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我們三人雇了一個司機,往深山里開。村子的名字叫吉蘭,在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的邊界上,居民全是塔吉克族人。那裡的海拔很高,交通不方便,與外界幾乎隔絕,還保留著最傳統的房屋與生活方式。這是烏茲別克人都沒怎麼聽說過的地方,但我在一本書裡讀到,便一直想前去探訪。
盤旋的山路很不好走,但沿途的風景值得一路顛簸。到達一片開闊地帶,司機停車讓我們出去看。只見碧綠的山巒層疊,圍繞著中央的一潭湖水。湖水是綠松石的顏色,泛著淡淡的光,靜謐又深邃。
Roman向我展示他今天的服裝,一件繡紅色甲殼的綠毛衣:”這是自然的顏色,我特意為今天選的。”他跳到公路邊的台子上,讓我以景色為背景拍照,擺出一連串戲劇化的表情和動作,引得司機和朋友都有些不自在。朋友曾經在國外生活十幾年,是烏茲別克人中相當開放的,但還是難免對Roman的一些行為感到不適。
車又開了許久才到村子裡,司機預計車程兩個半小時,但最終用了四個小時還不止。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塵土的顏色,由泥漿和著草木砌成,只有門窗框刷成鮮亮的藍色。我們沿著貫通全村的泥土小路走,經過在路邊琢食的公雞,聽見牛圈里傳來的哞叫,也碰見騎驢的老人。驢子身上披的花布格外惹眼,藍色條紋,印大朵紅花。
村民沒怎麼見過外國人,對我們很好奇,但又大多害羞,就躲在窗戶後面看。父母帶著孩子,一家人一起觀望。 Roman發現時就笑著朝他們揮手,對方往往遲疑一下,也笑起來揮手回應。
路過一間種蘋果樹的院子,男主人邀請我們進屋喝茶。這是當地的傳統,對遠道而來的客人要盡最大努力招待,不管是否相識。這不是我們在這個村子裡第一次被邀請,但這家男主人的確是最熱情的,我們跟著他進了房子。
客廳的陳設很簡單,地上舖一張花地毯,中間擺一張炕桌。男主人和我們講話,他的妻子負責端茶。不只有茶,還有馕、乾果、蛋糕、烤包子和自家種的蘋果。正值封齋期間,主人和朋友在太陽落山前都不能進食,就只看著我和Roman吃。
他們三人在一起說俄羅斯語,不時會給我翻譯幾句,但大部分內容我還是聽不懂,只能觀察他們的表情。 Roman很有表達欲,同男主人熱情交談,面色愉悅,但突然就做出誇張的驚恐狀,雙手舉在胸前,把身子往後縮。後來朋友告訴我,那是因為主人邀請我們晚上留下來吃開齋飯,烤全羊,而Roman是素食主義者。朋友似乎對Roman如此反應頗有微詞。
男主人倒是沒表示出來不悅,繼續熱情招待,臨走的時候還給我們裝了滿滿一袋蘋果。 “願真主保佑你們。”他在道別的時候祝福我們。
Roman很想回應這份好意,決定以自己的方式也進行祝福。他曾和我說過在學習占星和魔法,已經取得二級巫師的資格。此時他決定給這家人以巫術的祝福,念著英文咒語,轉著圈子上下比劃。可以看出來朋友十分希望能阻止他,而我則慶幸咒語是英文的,這家人都聽不懂。
從村子回到撒馬爾罕的時候已經很晚了,但我還是和Roman一起去吃了晚飯。我第二天就要離開撒馬爾罕,繼續向西,Roman執意要為我送行。他特意找了一家能看到雷吉斯坦廣場夜景的餐廳。我們在炫麗燈光的映襯下吃一種叫manti的當地食物,造型類似粗獷版的小籠包。 Roman要了把牛肉餡替換成南瓜的素食版。
我問Roman今後的計劃是怎樣的。他說自己也打算去烏茲別克斯坦的另外幾座城市,等成功在銀行開戶以後再去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
“再然後呢?”我又問。我好奇他的“環球”旅行打算進行多久。
“再然後我還是希望能完成本科學位。”Roman的語氣竟然嚴肅起來,一改往常的跳脫。
四年以前,他曾在加拿大留學,念新聞與傳播專業,但大一還沒有念完就遭遇疫情,學業被迫中斷。他就是在那段時間開始做在線英語老師的,慢慢積累起了穩定的客戶群。他也逐漸想明白這個專業不適合自己,打算換個專業重新申請大學。可是等到疫情結束他重新申請,俄烏戰爭開始了。已經有一所法國大學和一所波蘭大學分別因為簽證限制拒絕他。
“我是肯定不會留在俄羅斯讀大學的,”Roman解釋,“以後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都不會承認俄羅斯的文憑。”
目前他又申請了一所奧地利的大學,還在等消息。 “學校在阿爾卑斯,抬頭就能望見雪山,你要來找我旅行啊。”他的語氣裡滿是希望。 “好啊。”我笑著回答。 Roman興奮起來,又開始計劃去巴黎找我的行程。
旅行中這樣的事經常發生,和另一位旅行者萍水相逢,共度幾天時光,熱切地約定再次見面,但實際上再也不會見面。我早已適應這樣的遊戲規則,只是偶爾反思自己的虛偽,可Roman似乎要認真得多。
分別後我還總是收到他的語音消息,多次重申我們的“友誼”,同當面交談時一樣,語速飛快,情感充沛。我的回复越來越簡短,他也就慢慢停了下來。後來他的instagram動態裡又出現了新的“朋友”。照片裡他的笑容很燦爛,可我卻感受到孤獨,掩藏在表面喧囂之下。過分熱情又誇張的言談是保護色,而一個又一個臨時“朋友”則是消解的方式。

我乘著擁擠又破舊的夜班火車來到希瓦,這次行程中最靠西的城市。希瓦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埋藏在卡拉庫姆沙漠裡,曾是九死一生之地,如今卻被開發成一處別緻的旅遊景點。這裡的古建築豐富而集中,可是由於位置實在偏遠,交通網絡又落後,大部分遊客並不會到訪。
即使如此,俄羅斯人的身影還是隨處可見。他們信奉東正教,此時正是複活節假期。對俄羅斯的普通遊客來講,因為簽證限制,烏茲別克斯坦也是熱門目的地。他們穿著從紀念品商店買來的傳統服飾,穿梭在古城的大街小巷。男人戴繡花的穆斯林圓頂帽,女人穿鮮豔的紮染真絲長袍。這些服飾穿戴到金發碧眼的俄羅斯人身上,竟然也不顯得太違和。
畢竟烏茲別克斯坦和俄羅斯的糾纏由來已久,早在沙皇時期就被俄羅斯人征服,後來又被納入蘇聯。希瓦古城也正是在蘇聯時期演變成如今的模樣。蘇聯政府秉著“個人服從集體”的原則,將內城的居民全部搬遷至城牆外,只留下經營民宿和商店的人家,打造出一個露天博物館。
在同一套行事邏輯下,大批俄羅斯人也在蘇聯時期被安排到烏茲別克斯坦落戶,發展當地農、工、文化等產業。這是聯邦內對人力資源進行整體分配的一種方式。蘇聯解體以後,其中的大部分回了俄羅斯,但也留下一批滯留者,大多聚居在塔什幹。我接下來要去見的就是其中一位。

在烏茲比克斯坦的行程已接近尾聲,我要回首都塔什幹再住一天,從那裡乘飛機離開。我在沙發客網站上聯繫了Yura。沙發客是一個在線平台,幫旅行者和願意免費提供住宿的當地人建立聯繫,相當於沒有金錢交換的airbnb。我不是那麼需要一個免費住處,只是被Yura簡介裡的攝影項目吸引,發送了借住請求。
Yura是俄羅斯人,但是在塔什幹出生長大,是一個膠片攝影師,正在進行一個關於世界各地旅行者的攝影項目。他接待來塔什幹的旅行者,為他們拍攝肖像,並讓每個人用母語寫下一封講述自己故事的信,希望最終集結成攝影集。從四年前開始,他已經招待了近百位旅行者,而這些旅行者也都在他的頁面上留下了好評。他很快通過了我的請求,並邀請我參與他的項目。
“沙發客的目不是免費住宿,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我希望你理解這一點。”他特地在信息裡向我強調。我表示同意。烏茲別克斯坦物價低廉,住一晚青旅只要十美元左右,我使用沙發客本來就是為了與當地人交流。不過後來我發現,這種交流並沒有我設想中的輕鬆。
我跟著谷歌地圖找到了Yura的住處。那是一片老式蘇聯街區,堆疊著一排又一排的灰褐色筒子樓。走進Yura住的那一棟,空氣裡瀰漫著陰冷的霉味,樓道裡的牆皮一塊塊開裂脫落,地面和台階都是裸露的水泥,沾染著不知多久沒被清理過的污漬。
來給我開門的是一個高大的男人,穿著一件鬆垮的白色背心和同樣不合身的牛仔褲,給人不修邊幅的感覺。兩撇復古的小鬍子,讓他看上去像是蘇聯老電影裡走出來的喜劇人物。公寓的陳設也同樣像是蘇聯電影裡的場景,不論家具還是擺件都像是從舊貨市場上淘來的蘇聯老物件,只有客廳牆上掛的民族花紋地毯透露出一點烏茲別克風情。
“我剛做好了早飯,等你一起吃。”Yura熱情地邀請我進門。因為面積限制,房間裡並沒有正式的餐桌。我們坐在陽台的折疊小桌上吃類似醬油的當地調料製作的炒麵,配上生的青蘿蔔片。 “我本來想加一點雞蛋,但是家裡正巧沒有了。”他有點抱歉地說。
陽台是封閉的,連著客廳,除了折疊小桌,還擺一台木質三腳架,上面固定著一台膠片攝像機。三腳架對面放了一把小凳子,大概是給被拍攝者坐的。一間簡陋的攝影工作室在此設立。
公寓只有一間臥室,我要住在客廳的沙發上。沙發也上了年頭,破舊的布面有幾處露了陷,能看見內裡的填充物。 Yura解釋,這是他的寵物狗Chandra的破壞成果。 Chandra是一條看不出品種的黑色小狗,很怕生人,在我進門的時候一直沖我叫。但Yura保證她很快就會對我親和起來,提議吃完早餐後一起去遛狗。
我們帶著Chandra來到小區的街心花園,遇見的其他遛狗人Yura都認識,總會打上兩句招呼。 “你有沒有發現遛狗的全是俄羅斯人?”Yura問我。他解釋說烏茲別克人因為宗教原因,不喜歡狗,認為他們是不潔的生物。雖然牽了繩子也帶了嘴套,但還是有人看見Chandra時會躲閃。 Yura於是一遍又一遍地用俄語重複:“我的狗是一條好狗,不傷人的。”
除此之外,Yura對烏茲別克人的一些其他做法也不甚認同。四月底塔什幹的太陽已經有一些狠毒,路邊卻沒有幾顆遮陰的大樹,只剩下許多光禿禿的樹幹。 Yura說烏茲別克人很喜歡砍樹,拿來賣錢,蘇聯時期種的樹後來都被新政府砍了。 “烏茲別克人沒有長遠發展的眼光。”
Yura還講到烏茲別克文化中對女性的禁錮。這裡的傳統房屋有點像四合院,圍著中間的小院子在四面搭建。所有窗戶都在朝向院子的一面。 “朝向街道是不能開窗子的,因為他們害怕家裡的女人被看見。”
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不同種族之間的融合。當地穆斯林女性是絕不會外嫁給俄羅斯人的,也只有極少數烏茲別克男人會娶俄羅斯女人。即使世代生活在此,俄羅斯人也不會學習烏茲別克語,生活圈子局限在俄羅斯人群體內部,並失去在政府等公共機構的工作機會。
”既然如此,你為什麼不回俄羅斯生活呢?“我問出來一個有點天真的問題。
Yura回答:”沒有那麼簡單。“他的家族在好幾代人之前就遷移到烏茲別克斯坦。他在這裡出生長大,只有烏茲別克國籍,去俄羅斯要申請簽證,而且條件苛刻。他二十出頭的時候曾嘗試到莫斯科打工。那是一段地獄一般的日子,每天要像奴隸一樣工作,但是工資很低,生活成本又高,他最終決定回到塔什幹。
好像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沒有真正的家。雖然他在烏茲別克斯坦出生長大,卻不認同這裡的主流文化,仍舊以俄羅斯人自居。可是遙遠的俄羅斯母國也並不願意接納他。某種程度上,他是被困在這裡的。
”那你的祖先是為什麼來烏茲別克斯坦的?“
”我只知道他們是在蘇聯時期過來的,具體為什麼我父母沒有告訴過我。“
看我有些驚訝,他又解釋:”我的父母從來不和我講這種事,他們只是盡力生活。“
遛完狗,Yura接到父親的電話,叫他過去一趟,說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不方便在電話上講。他決定帶上我同去,順路給我展示塔什幹的城市風貌。路過院子裡的一輛老爺車,他停下來指給我看。他說這輛車屬於他,但是今天不開,要乘公交。其實我很懷疑這輛看起來快要散架的汽車是否還能開動。
Yura父母的房子在另一區域的筒子樓裡,樓道的味道更刺鼻,房間的規格也更狹小。他的父親拄著拐杖來開門,我在廚房裡等待,聽他們在客廳裡爭執。十分鐘之後我們就離開了。
原來Yura的父親丟了價值相當於100美元的現金,認為是被Yura拿走的,於是叫他過來盤問。 100美元是個大數目,他的退休金每月也只有200多美元。 Yura解釋說他沒有拿過,估計是被患有阿爾滋海默症的母親放到了哪裡。父親不願意相信,兩人的爭執沒有結果。
Yura的父親一直看不上這個“不務正業”的攝影師兒子。母親對他要更加疼愛,但如今深受阿爾滋海默症的折磨。遛狗的時候Yura就已經接到母親的好幾個電話,每次都是哭訴弄丟了剛領的退休金。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耐心解釋,退休金不是弄丟了,只是還沒到該領的日子。
我有點想離開了。我雖然一直樂於體驗生活,可這樣的生活實在過於沉重,而Yura又多次強調“沙發客重在人與人的交流,不是一個免費的住所”,讓我不敢自行安排活動,只能繼續跟著Yura完成他的日常事務。他說有一個德國客人曾經生硬地甩開他,要去市中心觀光,回來以後就被他禮貌地請離了。
我能夠理解Yura,他被困在這座城市,困在這樣的生活裡,太需要一個出口了。和世界各地旅行者交流是他排解壓抑的方式。可是經過長途旅行的我此刻也非常疲憊,無力再進行他需要的交流。
讓我打定主意離開的是廚房裡的蟑螂。我原本只發現了一隻,叫Yura來確認。他不以為意地捏起來,扔到地上,隨意踩了幾腳,也不去處理屍骸。他說蟑螂不會傷人的,叫我不要怕。他曾經嘗試清理過,可是整棟樓都有問題,他也沒有辦法。後來,我發現灶台上的黑色污點全都是蟑螂的屍體,我原本以為只是油漬。
我找了一個藉口,告訴Yura我要提前離開,不在這裡過夜了,但還是對他的攝影項目感興趣,願意參與。他挽留了一會兒便也同意,開始給我展示他的攝影作品,
作品里人像是黑白的,用古老的膠片照相機拍攝。 Yura將衛生間用作暗室,沖洗膠片,再掃描到電腦裡保存。在我之前,他已經為81位旅行者拍攝了肖像。照片都未經過美化,將人物臉上的毛孔細紋,和眼底的期盼不安都悉數保留。我看得很入迷。
Yura展示照片的時候也會一併講述對每一位客人的回憶,像小孩子清點珍寶一樣認真。他特意在一個男人的照片上多停留了一會兒,那是他之前接待過的唯一一位中國人,是一位計劃橫跨亞歐大陸的騎行者。他接待過的大部分客人都是這樣的硬核沙發客。
終於到了拍攝時間。 Yura播放起搖滾樂,把天花板上的白熾燈關掉,打開牆上的紅色裝飾串燈。房間裡的氣氛馬上變了,陳舊的家具竟然有了前衛的風格,雜亂的擺設也變得鮮活而富有藝術氣息。 Yura的狀態也和白天截然不同,他哼著搖滾的調子準備膠片,佈置場景,調整相機,好像甩掉了日常生活的重壓。
Yura用的膠片照相機是機械的,曝光時間要一分鐘左右,並且需要手動輸送光源。他叫我眼睛看著鏡頭,雙手放在膝蓋上,不要動。他按下快門,隨後來到我這一側,環繞著我轉動光圈,好像在舉行一場神聖的儀式。我在炫目的燈光下努力睜開雙眼,余光瞥到Yura,他的眼裡也有一種類似於光的東西。
夜色已經很深了,我向Yura道謝離開,打算在機場附近找個酒店睡一晚。明天我將離開烏茲別克斯坦,去往下一個目的地。我隨時可以抽身離開,但更多的人沒有這樣的幸運。
我攔下一輛出租車,往機場的方向去。司機講起俄羅斯語,我還是聽不懂。可是那片我從未踏足的土地,已經不再顯得那麼陌生。人類命運之間的共性總是要比差異大。不管是作為一個輝煌時代的餘燼,還是大國博弈的犧牲品,總是個體命運在時代的角落裡被悄然改寫。
一排又一排的筒子樓很快就在夜色中消失。路上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除了汽車的遠光燈,照向幽暗無底的遠方。
*本故事來自三明治“ 短故事Life Writing學院”
閱讀更多作者作品






支持三明治,让更多个体表达与独立创作被看见。
發布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