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嗎?

8月24日,中國歷史研究院發表《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連日來在坊間激起巨大爭議。雖然也有像胡文輝的看法認為,從史學上來說,此文的觀點是立得住的,至少有其可取之處,但絕大多數人的反應,看來是把這看作一個最新的信號,用我一位朋友的話說,“懂了,看來'閉關鎖國'並不愚昧落後,明清時期早就開始'內循環'的艱難探索了!”
不止一個人來問我的看法,本來我不打算捲入這樣的論戰,何況這兩天也脫不開身,但看了太多人的爭論,忍不住也在這裡說幾句。
我發現,幾乎所有人的看法,都預設了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歷史和現實仍然是一個連續體。也就是說,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有何意義,仍然對當下產生著潛在的微妙影響。
正因此,當人們看到“閉關鎖國有利論”時,第一反應想到的不是歷史事實如何,而是這發出了一個什麼樣的信號。說實話,歷史上的閉關鎖國究竟是怎麼回事,作為一個學術議題恐怕沒多少人關心,這次之所以成為一個公共話題,完全是因為它隱含的現實意味。
“修明經略”的一篇文章在談及這次的事件時,其觀點就相當有代表性:
歷史研究總是為當代服務的,歷史結論往往是和當代的政治聯繫在一起,對過往事件的評價的變化其實反映了當下的趨勢,這是需要萬分注意的。
既然如此,那麼討論歷史問題,其實就是一個現實政治問題。進而言之,一個人的歷史觀,常常折射出他的現實政治觀點;也因此,中國人對歷史的興趣,其實往往出於對政治的興趣。至少在這裡,“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仍未過時。

人們如此敏感,並非只是捕風捉影。在過往的歷史上,對歷史的重新挖掘、詮釋,曾一再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往往合理化了當下的現實,以至於有人感嘆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適的原意是否如此,也有爭論,姑置不論)。
1979年,清史權威戴逸就曾寫過《閉關政策的歷史教訓》,胡文輝說此文“是批評'閉關鎖國'的當代史學先鋒,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顯然意在為'改革開放'製造輿論,在性質上是'影射史學'的延伸”。
中國股市1989年成立時,我記得當時報紙上也有考證文章,從馬克思的日記裡翻出革命導師也曾炒股,證明他至少並不反對股市。不管這樣的文章立論如何,但它出現的時間點、具有什麼意味,中國人通常只要鼻子聞一下就都懂了。
基辛格就曾感嘆,雖然新中國誓言要“與封建歷史決裂”,但卻無人質疑“距今久遠的歷史先例與中國當前的戰略需求是否相干”,似乎都覺得這是自然而然的事——由一個美國人發出這樣的感嘆確實也再恰當不過,畢竟這個國家歷史太淺短,以至於太多創新根本沒有先例可以援引。
當文明處仍處於傳統和現實的連續體之中時,不論古今中外,都會無師自通地通過對歷史的重新詮釋來開闢新的道路,也就是把“創新”說成是“復古”,以表示當下的做法既不新鮮,也是合理的。 《海洋與權力》一書中談到古希臘人的這種傾向:
雖然雅典有意識地選擇成為一個海權,發展一種獨特的文化身份,但這一進程是由既存的思想和範例決定的。在希臘世界裡,活躍的變化需要用過去的先例來加以確認,而這些先例往往是經過重新想像的,甚至根本就是虛構出來的。
這種做法,意味著“傳統”不僅仍然是相當有活力的,從而能不斷自我更新,而且也是為當下行為提供合理性的權威源泉。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人的這種自發傾向表明,雖然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就宣告與傳統決裂,但實際上社會心態仍未擺脫這種傳統與現實的連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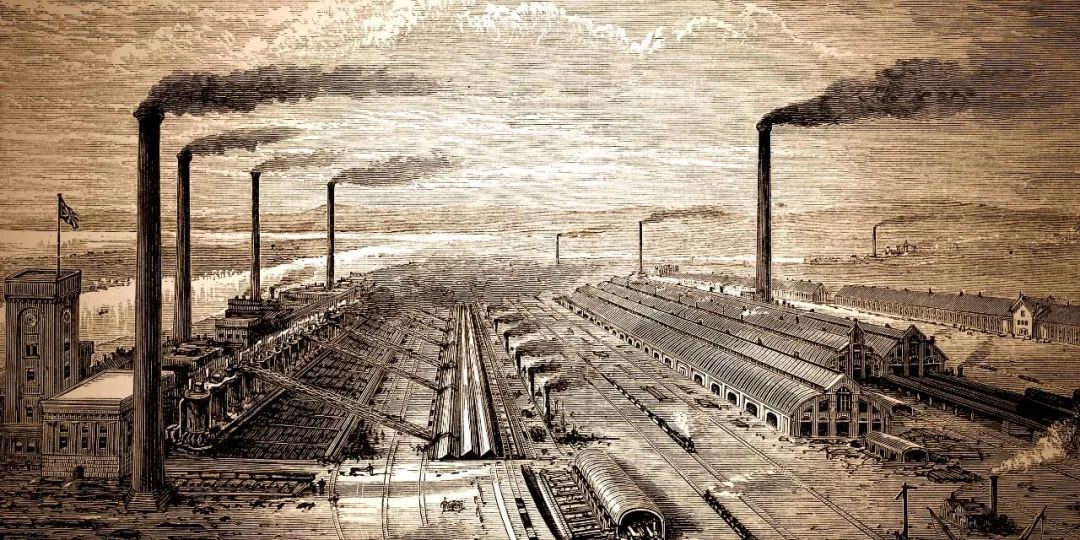
然而,基辛格的反應也表明,雖然中國人對此習以為常,但其實並不必然如此。很多現代製度創新是與傳統斷裂的結果,當然也無須藉傳統來為自己正名——對一個朝向未來的社會來說,“過去”也不再是權威的來源了,對一個現代人來說,就算過去的人是如此行事,那又怎樣?這就表明我也得如此行事嗎?
更重要的是,正如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洞察到的,新的話語其實在不斷地“循環穿梭”於自己的干預對象之中,不斷重新構建著那個客體,並使得對方也學會了用這樣的方式來思考。
如果說這聽起來很抽象,那這麼說吧:如果人人都意識到,對過去的重新詮釋其實不過是在為當下現實服務,那麼這種重新詮釋就難以成功。
試想一下,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之前,先撰寫了《孔子改制考》,試圖證明孔子其實就曾變革製度,以此表明自己的做法正是尊奉先聖所為。然而,不管他本人是否相信,大多數人卻都相信他根本只是“古為今用”而已,只不過讚許者推崇他變法的勇氣,而反對者覺得他曲解經文,簡直一派胡言,好像沒有哪個經學大師認真看待這本書在學術上的價值。
或許可以說,在經學衰落之後,史學部分起到了原本經學的作用。歷史學家朱維錚曾發現,中國學術史的規律之一是“學隨術變”,其意無非是說,當政治關切的重心變動時,治學方向也會隨之轉移,就像當初史學研究的“五朵金花”。然而問題在於,這麼做的結果,往往不僅是學術價值可疑,能起到多大作用恐怕也難說——因為人人都知道,根本上的動力不在於此,“對傳統的重新詮釋”已淪為“緣飾之說”。
因此,真正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歷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而是“打扮她幹嘛?”奧威爾曾有一句著名的斷言:“誰控製過去,誰就能控制將來。”但到了後現代社會,“控製過去”可能也已經沒那麼重要了,“控制將來”的道路一定要經過“控製過去”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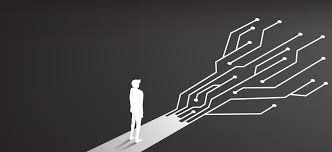
當一個社會真正實現現代化之後,雖然歷史和傳統仍是某些意義的來源,但邁向現代的斷裂越徹底,人們就越是無須從過往中尋求當下變動的合理性。
1889年法國大革命百年之際,圍繞著這一歷史事件的諸多問題,不同政治派別曾展開長期激烈的論辯,此時歷史仍是鮮活的、激發著新思潮;但到了1989年兩百週年之際,這個國慶節對法國人來說已經只是一個放氣球的歡樂假日了。歷史真正成了過往,而“過往如異國”,既陌生又與當下生活並無多少相干。
然而正因此,歷史也獲得了解放,它無須再承受重負,而真正成了可以進行客體化研究的對象——反正無論歷史學家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對人們來說也不過是知識分子無傷大雅的興趣罷了,就隨他們去吧。
多年前我就注意到,年輕一代對於許多歷史已經淡忘了,對他們來說那隻是模糊的一團,無論是什麼形狀,對自己的現實生活都沒多大影響,甚至無法理解你們為何如此認真看待這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我一時感嘆,這樣新的一代人是幸運的,他們無須承受沉重的歷史,或許也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些新的轉機——結果是你可以想見的,我在此後幾年內,都不時被一些人震驚之下嘲諷為“替無腦的小粉紅洗地”,並質問我,難道不知道“忘記歷史必將重蹈覆轍”嗎?
經歷了這些,我也能想見,當“歷史-現實連續體”尚未斷裂之際,像胡文輝這樣的討論,無論其本意如何,也可能被人看作是在為“閉關鎖國有利論”洗地。至於我本人,其實並不關心這個問題本身,因為在我看來,這實在沒多大意義——想想看,現在誰還認真看待“資本主義萌芽”這樣的問題?不論在當時如何轟動一時,事後來看,其本身在學術上就不是一個有價值的問題。
坦白說,在這樣的問題上浪費時間是不值得的,時過境遷之後,我們甚至會驚訝,為什麼有那麼多聰明的頭腦都花費那麼多時間為此爭論。當然,它畢竟也不是全然沒有意義——雖然圍繞這個問題本身的論述沒多少學術價值,但人們為什麼會這樣激辯,卻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人們身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發布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