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寂靜的春天

上海短暫的春天已經過去了,無聲無息。之前看過一篇科普,按氣候學上的界定,上海的春天年均只有37天,而從3月24日起,像絕大部分上海人一樣,我就再沒能邁出小區一步。
有一段時間,下樓做核酸是每天唯一被允許走出樓道放風的機會。看到春光明媚,孩子們說,他們想念往年去江濱騎車、踏青、野餐的日子,聽得我也一陣悵然,誰不想念呢?
此時,唯一能寬慰自己的想法是:沒了我們,大自然或許可以更好。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感覺小區裡今春連蝴蝶、蜻蜓和甲蟲都變多了,或許也因為少了汽車尾氣和喧鬧,樹木更是無人修剪,蓊蓊鬱鬱,讓人感覺除了人靜止之外,萬物都在生長。
和別處一樣,以往小區裡最常見的鳥種無非是上海的“四大金剛”(珠頸斑鳩、麻雀、白頭鵯、烏鶇),遠東山雀、絲光椋鳥、棕頭鴉雀之類也不時可見,但這兩個月居然還有兩次見到了白鷺和夜鷺,本來它們都出沒於後灘的水濱,現在大著膽子擴展了自己的領地。
這倒未必是它們察覺到了我們的沉寂。鳥類學家Steve Hitti曾說過:“如果人類消失了,地球上至少三分之一的鳥類根本不會注意到這件事。”對生態系統來說,我們極有可能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重要。
反過來,這些鳥兒對我們的生活卻可能很重要。一位朋友和我說,被封在小區裡的這段時光,她每天的高興事就是突破封鎖線去和鄰居家的鸚鵡對話。
我談不上對觀鳥有多大興趣,只不過從小在鄉下長大,很自然地就成為我鄉土情結的一部分。在這個小區裡住了整整20年,雖然一度還曾想做一份“1平方公里的生態”,記錄這裡的草木鳥獸,但總是顧不過來,直到現在無處可去,只能翻來覆去觀察這塊郵票大小的地方。

話是這麼說,我得承認,絕大多數時間即便身在樓下,我也還是在散步、閱讀、沉思,往往是孩子看到了我沒看到的東西。昨天老大興奮地告訴我,在香樟樹葉叢裡,發現一隻絲光椋鳥幼鳥,還不會飛,只會呆呆地蹲在樹枝上。早春時分,他還發現了一隻烏鶇的鳥巢,每天去看,直到幼鳥全部離巢。
住了這麼多年,小區裡有些角落我還是第一次去,因為平日里都是固定路線就出門去了,從不覺得那些角落有什麼值得探究的。也是這次才發現,每棟樓的通風口,常常都成為鳥巢,似乎絲光椋鳥尤其喜歡在那裡做窩。月初,在水池邊的假山旁,第一次見到了刺猬,那是一隻死掉的小刺猬,孩子有點難過,嘟囔:“它的爸爸媽媽應該也在附近吧?”
在這個寂靜的春天,很難不想起蕾切爾·卡森的名著——1962年,她出版了《寂靜的春天》,到現在剛好一甲子。她開篇就虛設了一個風景優美的小鎮,但不久,“一個奇怪的陰影遮蓋了這個地區,一切都開始變化”,“神秘莫測的疾病”籠罩著村鎮,人群中“出現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釋的死亡現象”,“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鳥鳴的音浪消失了,魚群在死去,果樹也因為得不到授粉而結不出果實,這“不是魔法,也不是敵人的活動使這個受損害的世界的生命無法復生,而是人們自己使自己受害”。

當下的處境當然有所不同,說來令人啼笑皆非,由於我們的愚行,可能倒也無意中做對了點什麼:一牆之隔的那個世界,看起來像是已經讓給動物們了。往日熙熙攘攘的地鐵人民廣場站外,很多野貓在曬太陽;空蕩蕩的馬路上,成群的野狗遊蕩;在新涇路上,居然還有孔雀在散步。
這兩個月來,這座城市在驟然沉寂下來之後,自然正在復蘇。當然,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受到強烈的人工干預,所謂“自然”大抵也是馴化的景觀,但即便如此,當這種馴化停止,一個“文化為野”(rebarbarization)的反向進程就開始了。
時不時地,看到有人分享這座城市靜止下來後的景象:滯留倉庫一個月的葡萄苗都爬藤了;外灘的石縫間長草了;環貿奢侈品店外的台階上長滿了各種植物;張江足球場的草更是瘋長。
儘管有植物達人指出,這些植物本身有些也不完全是野草,彷彿不能算是“自然”,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讓人看到了我們消失之後,這座城市會變成什麼樣,而平日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城市景象,其實都是無數人不斷加以維護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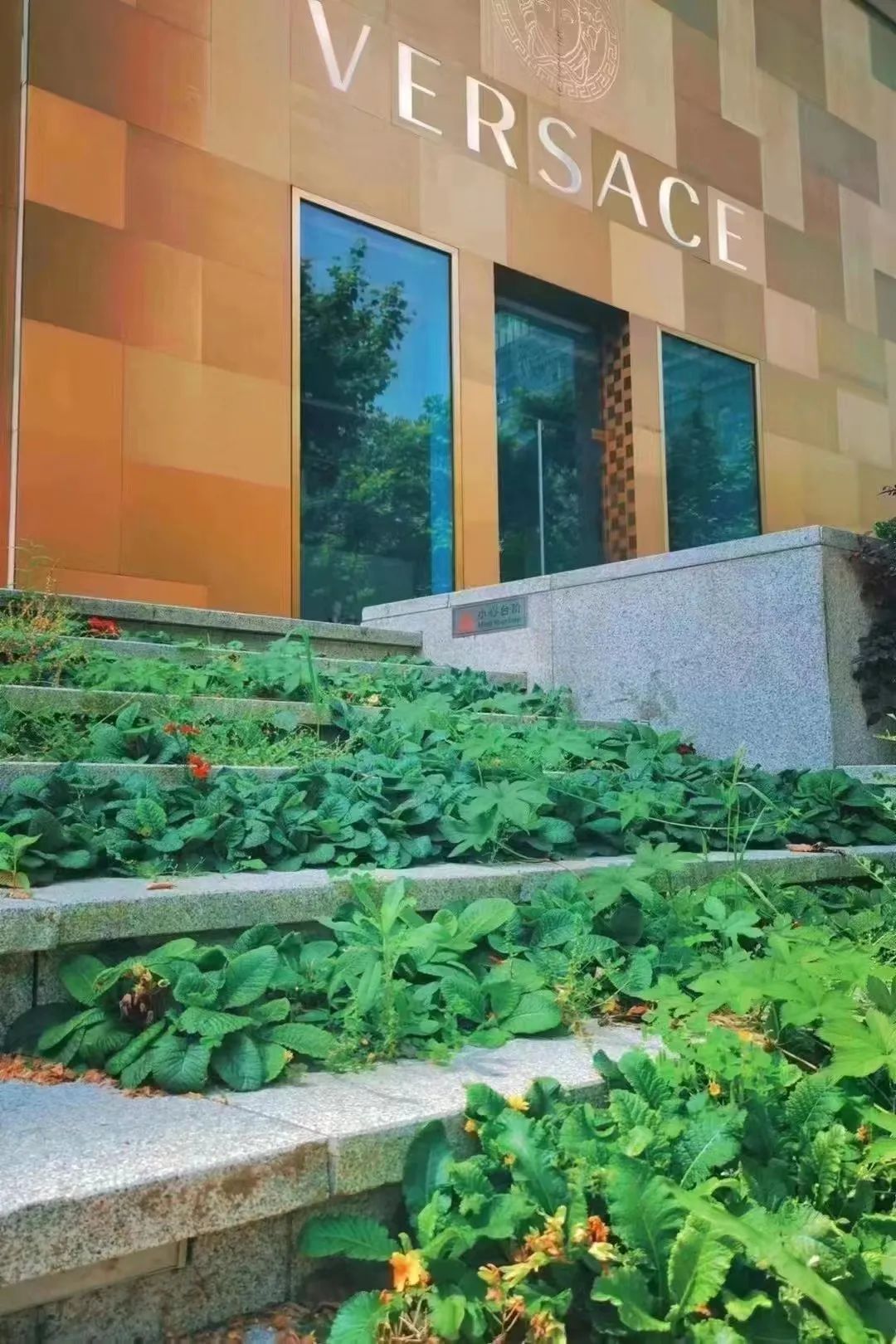
在網上,這有時激起了一種混雜著哀傷、感慨和戲謔的情緒,有一位移民多年的朋友頗感不解:“當時歐洲大封鎖的時候,到處讚美和傳誦生態的恢復。這反差太大了!”
當然,歐洲也不是一直如此。羅馬帝國衰亡後,繁盛一時的鬥獸場淪為廢墟,到1850年代,英國植物學家理查德·迪金寫了一部《羅馬鬥獸場植物誌》,列出這座廢墟上的420種野生植物,其中56種草類,41種豆科植物,有些在西歐甚至相當罕見,可能其種子最早是藏在野獸皮毛中遠道而來。不過15年後,意大利新政府將羅馬鬥獸場的管理權交給了專業考古學家,然後,幾乎每一株植物都被從牆壁上清除掉了。
冷戰結束後,英國皇家空軍格林漢姆基地不再作為核基地,大自然的反擊隨即開始,“蝙蝠棲息在導彈發射井內,黃條背蟾蜍躲在舊彈藥箱裡”。 1996年,勞拉·史賓妮在《新科學家》雜誌上撰文,假想了倫敦在被廢棄後,一點點恢復成從前那樣的一片沼澤。那隻需要大約250年。
作為一個建造在海濱濕地上的城市,上海如果有那一天,命運恐怕也差不多——按照倫敦的推算,兩個月相當於完成了進度條上最初的1/1500。看開了就覺得,那也沒什麼,畢竟歷史上遭到廢棄的古城不計其數,有多少都已鞠為茂草。從生態恢復的角度來說,也不算是壞事。
我們所珍視的文明,在時空的尺度上,可能也不過是一段有限的生命,只不過對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才會相信它是不死的永恆之城。這很可能是一種錯覺。
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人、所有城市,都“寄生”在地球表面,地球就是我們的宿主。病毒憑藉自己的生物本能,還知道殺死宿主的結果將是自己也無法存活,但人類在沒有了天敵之後,才剛剛開始學習進化的這一課。
《寂靜的春天》一書的扉頁題詞說,此書獻給人道主義哲學家艾伯特·施韋策,因為是他申明了“人類已經失去預見和自製能力,人類自身將摧毀地球並隨之而滅亡”之論。他當然是對的,但就像常有人說的,歷史的教訓是:人類從不吸取歷史教訓。這就看我們能不能在摧毀宿主之前,進化出新人類了。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發布評論…